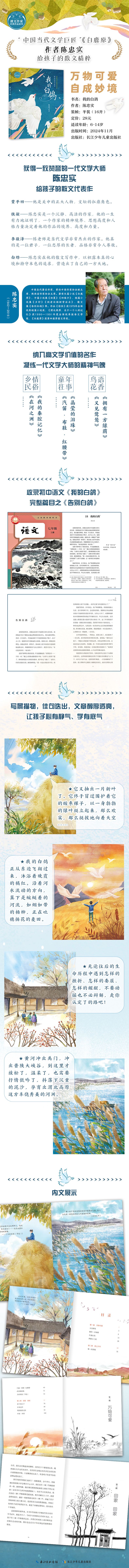出版社: 长江少儿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7.10
折扣购买: 课文作家经典作品系列·我的白鸽(七上)
ISBN: 9787572156878

陈忠实(1942—2016),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散文集《告别白鸽》等。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第一辑?万物可爱 又见鹭鸶 那是春天的一个惯常的傍晚,我沿着水边的沙滩漫不经意地散步。旱草和水草都已经蓬勃起来,河川里满眼都是盎然生机,野艾、苦蒿、薄荷和鱼腥草的气味混合着弥漫在空气里,风轻柔而又湿润。在桌椅间窝蜷了一天的四肢和绷紧的神经,渐渐舒展开来、松弛开来。 绕过一道河石垒堆的防洪坝,我突然瞅见了鹭鸶,两只,当下竟不敢再挪动一步,生怕冲撞了它、惊飞了它,便蹑手蹑脚悄悄默默在沙地上坐下来,压抑着冲到唇边的惊叹。哦,鹭鸶又飞回来了! 在顺流而下大约三十米外,河水从那儿朝南拐了个大弯儿,弯儿拐得不急不直随心所欲,便拐出一大片生动的绿洲,贴近水流的沙滩上水草尤其茂密。两只雪白的鹭鸶就在那个弯头上踯躅,在那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草中悠然漫步;曲线优美得无与伦比的脖颈迅捷地探入水中,倏忽又在草丛里仰起头来;两条峭拔的长腿淹没在水里,举趾移步优然雅然;一会儿此前彼后,此左彼右,一会儿又此后彼前,此右彼左;断定是一对儿没有雄尊雌卑或阴盛阳衰的纯粹感情维系的平等夫妻…… 于是,小河的这一方便呈现出别开生面、令人陶醉的风景,清澈透碧的河水哗哗吟唱着在河滩里蜿蜒,两个穿着艳丽的女子在对岸的水边倚石搓洗衣裳,三头紫红毛色的牛和一头乳毛嫩黄的牛犊在沙滩草地上吃草,三个放牛娃三对角坐在草地上玩扑克,蓝天上只有一缕游丝似的白云凝而不动,落日正渲染出即将告别时的热烈和辉煌……这些时常见惯的景致,全都因为一双鹭鸶的出现而生动起来。 不见鹭鸶,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小时候在河里耍水,在河边割草,鹭鸶就在头前或身后的浅水里,有时竟在草笼旁边停立;上学和下学涉过河水时,鹭鸶在头顶翩翩飞翔,我曾经妄想把一只鸽哨儿戴到它的尾毛上;大了时在稻田里插秧或是给稻畦里放水,鹭鸶又在稻田圪梁上悠然踱步,丝毫也不戒备我手中的铁锨……难得泯灭的永远鲜活的鹭鸶的倩影,现在就从心里扑飞出来,化成活泼的生灵在眼前的河湾里。 至今我也搞不清鹭鸶突然离去、突然绝迹的因由,鸟类神秘的生活习性和生存选择难以揣摩。岂止鹭鸶这样的小河流域鸟类中的贵族,乡民们视作报喜的喜鹊也绝迹了,张着大翅盘旋在村庄上空窥伺母鸡的恶老鹰彻底销声匿迹了,连丑陋不堪、猥琐笨拙的斑鸠也再不复现了,甚至连飞起来遮天蔽日的“丧婆儿”黑乌鸦都见不着一只,只有麻雀种族旺盛,村庄和田野处处都只能听到麻雀的叽叽喳喳。到底发生了什么灾变,使鸟类王国土崩瓦解、灭族灭种,留下一片大地静悄悄? 单说鹭鸶。许是水流逐年衰枯,稻田消失、绿地锐减,这鸟儿瞧不上越来越僵硬的小河川道了?许是乡民滥施化肥农药污染了流水,也污浊了空气,鹭鸶感到窒息而逃逸了?许是沿河两岸频频敲打的庆贺“指示”发表的锣鼓和震天撼地的炮铳,使这喜欢悠闲的贵族阶级心惊肉跳、恐惧不安,抑或是不屑于这一方地域上人类的愚蠢可笑,拂尾而去?许是那些隐蔽在树后的猎手暗施的冷枪,击中了鹭鸶夫妻双方中的雌的或雄的,剩下的一个鳏夫或寡妇悲怆遁逃? 又见鹭鸶!又见鹭鸶! 落日已尽,红霞隐退,暮霭渐合。两只鹭鸶悠然腾起,翩然扇动着洁白的翅膀逐渐升高,没有顺河而下,也没见逆流而上,偏是掠过小河朝北岸树木葱茏的村庄飞去了。我顿然悟觉,鹭鸶原是在村庄里的大树上筑巢育雏的。我的小学校所在的村庄面临河岸的一片白杨林子里,枝枝杈杈间竟有二十多个鹭鸶搭筑的窝巢,乡民们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引为荣耀,视为吉祥。一只刚刚生出羽毛的雏儿掉到地上,竟然惊动了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合议着推一位爬树利落的姑娘把它送回窝儿里。更不必担心伤害鹭鸶的事了,那是被视为作孽短寿的事。鹭鸶和人类同居一处无疑是一种天然和谐,是鸟类对人类善良天性的信赖和依傍。这两只鹭鸶飞到北岸的哪个村庄里去了呢?在谁家门前或屋后的树上筑巢育雏呢?谁家有幸得此吉兆,得此可贵的信赖情愫呢? 我便天天傍晚到河湾里来,等待鹭鸶。连续五六天,不见踪影,我才发现没有鹭鸶的小河黯然失色。我明白自己实际是在重演那个可笑的“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然而还是忍不住要来。鹭鸶的倩影太富于诱惑了。那姿容端的是一种仙骨神韵,一种优雅、一种大度、一种自然;起飞时悠然翩然,落水里也悠然翩然,看不出得意时的昂扬恣肆,也看不出失意下的气急败坏;即使在水里啄食小虫、小虾、青叶、草芽儿,也不似鸡们、鸭们、雀们饿不及待的贪馋和贪婪相。二三十年不见鹭鸶,早已不存再见的期冀和奢望,一见便不能抑制和罢休。我随之改变守候而为寻找,隔天沿着河流朝下,隔天又溯流而上,竟是一周的寻寻觅觅而终不得见。 我又决定改变寻找的时间,于是舍弃了一个美好的出活儿的早晨,在黎明的熹微中沿着河水朝上走。大约走出五华里路程,河川骤然开阔起来,河对岸有一大片齐肩高的芦苇,临着流水的芦苇幼林边,那两只鹭鸶正在悠然漫步,刚出山顶的霞光把白色的羽毛染成霓虹。 哦!鹭鸶还在这小河川道里。 哦!鹭鸶对人类的信赖毕竟是可以重新建立的。 我在一块河石上悄然坐下来,隔水眺望那一对圣物,心里便涌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来: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拥有一方绿荫 农历十月初一是家乡的鬼节,活着的人要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送钱,好让他们在冬季到来之前备置防寒的衣物。在这种事情上我一直是处于理智和情感的分离状态,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顺从了情感的驱使,便匆匆赶回乡下老家,去为我的那位终身都在为吃饭穿衣愁肠百结的父亲烧一扎纸钱,让他在冥冥之域不再饥寒交困。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瞅见我的家园。那株法桐撑开偌大的三角形树冠,昂昂扬扬侍立在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我的树——每一次回归家园第一眼瞅见这株法桐,我的心里就会涌出“我的树”的欣然浩叹。原因再简单不过,这株法桐是我栽的。父亲在世时喜欢栽树,我们家的房前屋后现在还蓬勃着他老先生栽植的树群,场塄上的那株白椿树已经有一搂粗了。然而,我每一次回乡看见自己栽下的树都要比看见父亲栽的树更亲切,说穿了不过是栽树的人对那株幼苗当初所寄托的希冀将实现。是的,当我看见自己掘坑栽下的那株不过指头粗细的幼苗终于雄壮起来,倚立在村巷里,在浩渺的天空撑起一片绿盖的时候,我的那种感觉颇近似阅读自己刚刚写完的一部小说。 十二年前的这个月,我调进陕西作协专业创作组。我那时的唯一感觉便是开始进入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专业创作对我来说它的实质性含义只有一点,所有时间可以由我自由支配,再不要听命于谁对我的指派了。压力也同时俱来,生活、学习、创作既然全由自己支配,那么再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也就没有任何托词可以替自己遮羞了。 我几乎同时决定回归老巢。回归我父亲、我爷爷、我老太爷一脉相承的家园。不是因为他们都死了需要由我来承继,纯粹是为了图得一个耳根清净的环境,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读书,思考一些不单是艺术也包括艺术的问题。我深知自己知识残缺不全,而生活演进的步伐又如此急骤,好多好多问题太需要沉心静气地想一想了。 住在乡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所有的骚扰和诱惑都自然排除。每每在清静到令人寂寞的时候我便走出大门,和村巷里随意相遇的任一个人拉拉闲话,哪怕逗小孩玩玩也觉得十分快活。夏天暴日当头时,走出门来就招架不住炎炎烈日的烤炙,暴晒后我的头顶和赤臂就生出一层红红的小米粒似的斑点,奇痒难支,医生说那叫日光性皮炎。我便畏惧已构成暴力的太阳,于是便想到应该有一方绿荫做庇护。出得大门,站在浓厚而清凉的树荫下和农人闲谝、抽烟,那真是太惬意了……想到栽两株树。 首先是树种的选择。我要栽两株法桐。几近四十年前我读初中,看过一场中国和法国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筝》,巴黎街道上那高大的街树令我记忆特深,我在家乡没有见过这种树。又过二十年我才知道这种树叫法桐,它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公路两边已经形成风景,家乡的一些农家屋院也栽植起来。 是我动手那部长篇小说写作那年的早春,我托村子里一个青年从庙会上买回两株法桐,一株一块钱。树买到了自然很遂心愿,只是遗憾着它太小太细了,仅仅食指那么粗。天哪!想要乘它的荫凉,想要拥有一方绿荫,得等多少年啊! 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挖了坑,给坑底垫下土肥,把它栽下了;栽下了它,也就把一种对绿荫的期盼坚定地埋下了。我拄着铁锨把儿抹着脸上的汗水,欣赏着只及我胸脯高的幼株,一缕忧虑产生了,猪可以拱断它,小孩随手可以掐折它,它太弱小了嘛!于是我扛着镢头上山坡,挖回一捆酸枣棵子,插在幼株周围,把它严严密密地保护起来。 令我失望的是,几乎所有树木的嫩叶都变成了绿叶,我的两株法桐依然叶苞不动。我拨开酸枣棵子在那树干上掐破表皮,发现已经是干死的褐色。我想把它拔起来扔掉,就在我拽住树干准备用力的一瞬,奇迹发生了,挨近地皮的地方露出来一点嫩黄的幼芽,我的心就由惊喜而微微颤抖了。 这是从法桐的根部冒出的新芽,证明树根还活着。树根活着就会发出新的幼芽,生命多么顽强又多么伟大啊!那是一个尚看不出叶形的粗壮的锥形幼芽,刚刚拱破地皮而崭露头角,嫩黄中有淡淡的嫩绿,估计也不止经受过一两回春天阳光的沐浴吧。我久久地蹲在那里而舍不得离开,庆祝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我把扒掉的酸枣棵子重新插好,这幼芽不仅经不起车碾马踏人踩猪拱,鸡爪子只要一下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刨断、把它摧毁。 我一日不下八次地看那幼芽。它蹿起来了。它由嫩黄变成嫩绿了。它终于伸出一片绿叶了。它又抽出一片新叶了。它终于冒过围护着它的酸枣棵子,以一身勃勃的绿叶挺立起来,那么欢实,那么挺拔地向着天空……唯其丝毫不敢松懈,每年春天挖一捆酸枣棵子加固防护的围障,它依然还弱小,依然经不起意外的或有意的伤害。 它长到我的胳膊粗的时候,我终于享受到它的绿荫了。那树荫投射到地面上,有筛子般大小,我站在我的树的阴凉下,接受它的庇护。它尚不雄壮的枝干和尚不宽厚的绿叶,毕竟具备遮挡烈日烈焰的能力,我想拥有一方绿荫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年底,我也终于完成了历时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工程,回城里去了。临走之前,我仍然给它的周围加固了一层酸枣棵子。 去年夏天我回去,发现那树干已经长到小碗那么粗了。不知哪家的孩子用小刀在树干上刻写下我的名字,刻刀的印迹已经愈合,颜色却是褐红色的,在树皮的灰白色中十分显朗。从去年到这次回归,我发现那树干急骤加粗,刻着我的名字的那俩字也在长大。树下已经有偌大一片绿荫了。 法桐已经成为一株真正的树挺立在那里,巨大的伞状树冠撑持在天空。父亲在世时给我说过,树冠在天空有多大,树根在地下就会伸延多远;树干有多粗,树的主根也就有多粗;树枝在空中往上往前伸长一尺一寸,树根在地下也就往下往周围延伸一尺一寸。我至今无法判断父亲这话有多少科学的可靠性,但确凿相信,这树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即使往坏处想到极点,譬如说突然被过往的汽车撞断了,或者被几十年不遇而在某一天却遇到了雷劈电击,这自然都无法预防,但这根是不会被撞毁劈断的。它会重新冒出新芽,它的生命还会重新开始。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将无怨无悔地再去挖酸枣棵子,重新开始对我的法桐新芽的围护。 我久久伫立在我的法桐树旁,欣赏着那已经变形却依然清晰可辨的我的名字,那刻下我名字的淘气鬼也该和这树一样长高长壮了吧?天空飘落着零星小雨,日头隐没了,虽然看不到树荫,却也毫无遗憾。到明年三伏那燥热难熬的时候,我就回家园,享受暴日烈焰下的我的那一方绿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