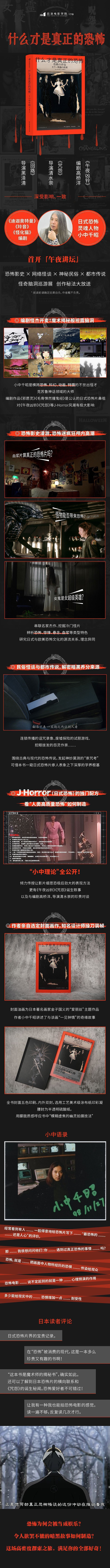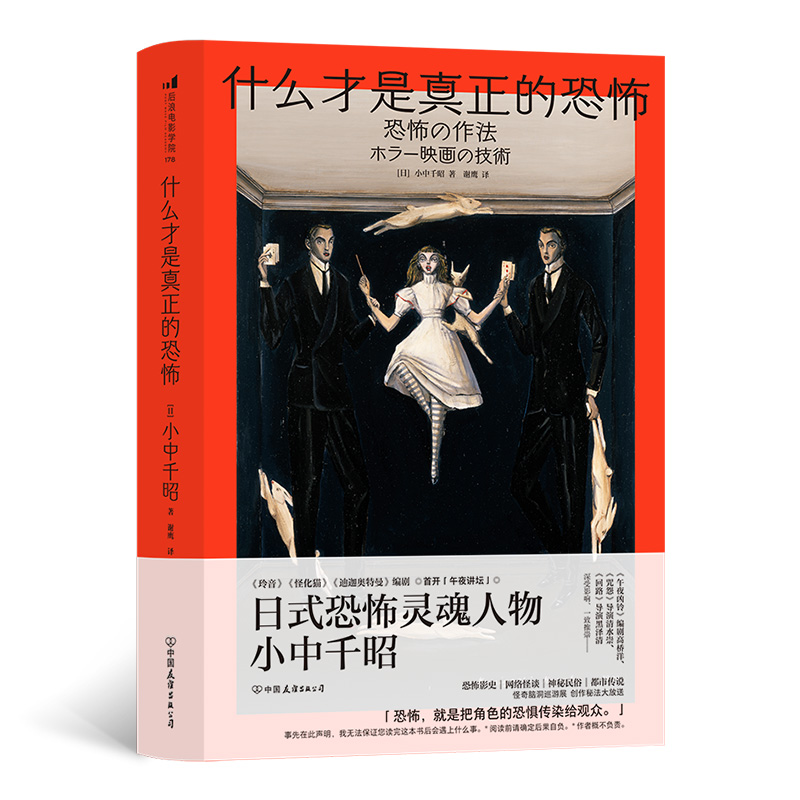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51.00
折扣购买: 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
ISBN: 9787505752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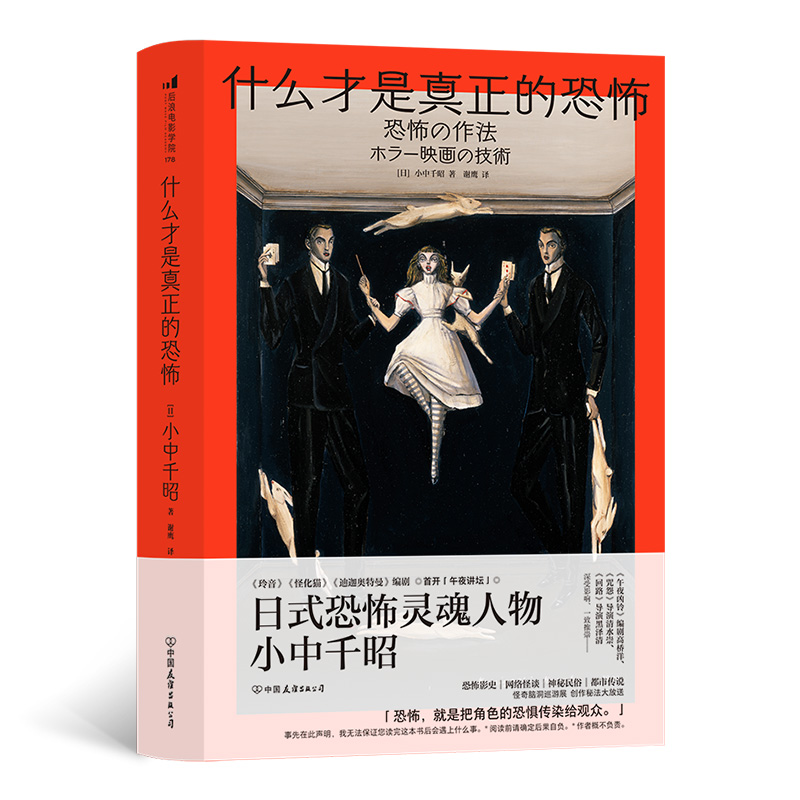
著者简介 小中千昭(Chiaki J. Konaka),196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编剧、作家。毕业于成城大学文艺学部,专业为电影符号学。毕业后曾从事影视导演工作,1988年在录像片《邪愿灵》中首次担任编剧。作为恐怖理论的代表人物,参与过多部恐怖类型的影视创作,引领了“日式恐怖”(J-Horror)风潮。主要编剧作品有《玲音》(日本文化厅媒体艺术节动画部门优秀奖),《迪迦奥特曼》《盖亚奥特曼》(TBS电视台),以及《怪~ayakashi~》《怪化猫》《数码宝贝3:驯兽师之王》(富士电视台)等。在部分作品中还担任过特效化装、音乐制作等工作,并在日本映画美学校担任剧本课讲师。 译者简介 谢鹰,自由译者,译著有《森林大帝》《火鸟》《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谷中复古相机店的日常之谜》《螺旋之底》等十余部。
第一章 《午夜凶铃》《咒怨》的恐怖 现代的原教旨主义恐怖 《午夜凶铃》的成功 1998年,电影《午夜凶铃》(Ring)上映。日本电影已经很久没出现过这样的热门作品了,影院甚至爆满到有人站着观影。我作为观众之一,当时也在影院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大银幕。观赏电影时,我深深为高桥洋先生优秀的剧本以及中田秀夫导演恰到好处的调度所折服,但渐渐地,在观看银幕上电影的同时,我也观察起了观众们的脑后和侧脸。 能让观众的反应如此鲜活的电影,其实并不多。 观众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换着姿势,腰部慢慢往前下滑,拼命让脑袋远离银幕。 我也曾深刻体验过这种姿势,这些经历成了我立志创作恐怖电影的契机。关于那部电影,我们之后再讲。 说到《午夜凶铃》,铃木光司先生的原作小说首先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小阵热潮,后来播出了电视电影,此次的电影算是第二次影视化。无疑,这一次的电影起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所以有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电影第一次知道《午夜凶铃》的。 然而,电影版《午夜凶铃》绝不是什么大制作。它的大热是依靠口碑的传播,即“电影真的很恐怖”,其效果甚至超过了宣传。 《午夜凶铃》的确是一部恐怖的电影。这固然得益于原作扎实简洁的结构所带来的恐怖加速感,但同样也得益于在谨遵原作大纲的基础上进行的高度优化删减的改编。 《午夜凶铃》的故事由两部分组成,前段的主题和都市传说有关,描写了原因不明的恐怖(诅咒)传播,后段则是逻辑解谜。 把长篇小说改编成两小时长度的电影时,通常会去枝剪叶,仅保留主轴部分。可要是这样处理恐怖电影,电影就会变成普通的解谜故事。推理作品这样做倒没问题,但对恐怖电影而言,逻辑解谜和情感宣泄扯不上关系。 高桥版剧本在处理原作的解谜要素时,将男主角(真田广之饰演)设定为有感应能力的超能力者,在剧中用画面直接呈现往事,在一口气解释清楚的同时(原作本身就涉及了“念写”的超能力现象,所以并不突兀),又在“诅咒录像”里加入了原作没有的恐怖画面,即一名被袋子罩住脸的男子正用手指着什么。 看到《午夜凶铃2》(1999)时,观众或多或少能明白一点该男子的身份,但至少在《午夜凶铃》中,他完全是个不明不白的离奇人物,也因此成了一种恐怖。 高桥洋与中田秀夫 共同造就了《午夜凶铃》的高桥洋先生与中田秀夫导演,此前曾携手推出过《女优灵》。这部低成本电影因为“真的很吓人”,早已在日本国内影迷间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女优灵》由中田秀夫导演拟定草案,再由高桥洋先生撰写原创剧本,放大了其中的恐怖成分。 高桥先生早在初稿打印出来时,就主动送给我看,当时的临时标题叫作《心灵》。一遍读毕,我预感到自己在原创录像带电影中所追求的东西,将逐渐在剧场电影的银幕上实现。 在成品里,中田秀夫导演那扎实的导演调度一点都不像新人,营造恐怖的关键点也一踩一个准,拍出了一部地道的恐怖电影。 不过就电影的完成度而言,可以说在剧本阶段就早已定型。随后,高桥与中田的组合又创作了《午夜凶铃2》这部脱离了原作的独立续集电影。 可以说它的剧情架构——“恐怖的信息由人传播开来”,是原作《午夜凶铃》中“诅咒录像”的精神延续。 在与高桥先生分开后,中田导演拍摄了《鬼水怪谈》(2002),还曾与我合作了电视作品《学校怪谈f》(1997)中的《灵异录像》一段。但正如他平日公开所言,他真正想拍的并非恐怖片,而是像我担任编剧的《玻璃之脑》(2000)那样的非恐怖类作品。 高桥先生同样也参与了一系列恐怖片的创作,如与鹤田法男导演合作的《午夜凶铃0》(2000),与堤幸彦导演合作的《新生厕所里的花子》(1998)等。他还凭借与盟友黑泽清导演合作的《蛇之道》(1998),与佐佐木浩久导演合作的《疯狂艳唇》(2000)、《外太空血块》(2001)等作品不断开拓新领域,更是以监修的身份参与了清水崇导演的录像带版《咒怨》(1999)。 《咒怨》的清水崇 清水崇导演的商业出道作,便是由我负责综合架构的电视作品《学校怪谈G》里的两部短篇。这部电视作品集结了黑泽清导演、高桥洋先生、动画创作者角铜博之先生等人,可以说,它展现了当年“恐怖片顶级新人”的风采。 我的目标正是要组成恐怖界的巨蟒剧团。 我计划通过中篇、短篇、掌篇(即超短篇)、短篇动画来组成作品,其中各式各样的恐怖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而且会采用电视播出的方式。电视播放的特点是,观众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观看,但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寸步不离,彻底沉浸在恐怖的世界里。 我想在其中插入一点实验性的短故事,于是问黑泽清导演有没有不错的年轻导演推荐,他便介绍了清水崇先生。清水先生是映画美学校的学生,黑泽清导演、高桥洋先生均在那里担任讲师。清水先生似乎算不上什么“优秀”学生,但据说他拍摄的实验录像带有一股“非同寻常的恐怖”,我在观看之后便邀请他加入了《学校怪谈G》的拍摄工作。 他在《学校怪谈G》中导演的两部掌篇《4444444444》和《角落》,在录像带版的《咒怨》里直接成为拼图一般的长篇元素。随着《女优灵》《午夜凶铃》的巨大成功,恐怖电影及录像带作品大量涌现。在此之前,恐怖片其实有点萎靡不振。 在这段恐怖片泛滥的时期,录像版的《咒怨》获得了“出类拔萃之恐怖”的评价。虽然出货量不大,但或许是在口碑的帮助下,“真的很吓人”的评价扩散开来。 对拥有短篇创作天赋的清水崇导演来说,《咒怨》可算他最信手拈来的形式。碎片化的恐怖片段逐渐联系了起来,最终隐隐浮现出主要的剧情轮廓。 据说高桥洋先生主要以监修的身份参与此次剧本(剧本由清水崇本人负责)。让擅长短篇的新人创作者拍摄长篇商业作品时,如果手法凡庸,电影就会沦为一部无聊的长片。但是他非常聪明地把《咒怨》拍成了短篇和掌篇相组合的作品。 录像带版《咒怨2》(2000)推出后,紧接着是电影版《咒怨》(2003)、电影版《咒怨2》(2003),甚至还有好莱坞出资的翻拍版电影《咒怨》,清水崇导演孜孜不倦地对咒怨世界进行着再生产。注意,“再生产”这个说法并不是什么贬义词。 黄金模式能为观众带去惊栗不已的恐怖。当创作者摸索出了这种模式时,便能以此为武器,不断创作出新的恐怖。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集中创作恐怖录像作品时,内心并未意识到制造恐怖的套路(routine)。 序章中我也写到过,当年自己经常和高桥先生讨论这些,但详细的内容让我们后面再提。清水崇先生作为比我和高桥先生晚一辈的创作者,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我们自己设定的严禁事项,不仅没有削弱恐怖效果,反而生产出了令观众忍不住与人分享的恐怖。 在电影版《咒怨2》中,清水崇先生的《咒怨》世界似乎开始脱离短篇风格。而好莱坞出资版的《咒怨》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恐怖呢? 为数不多的“恐怖”作品 前文写到过,随着《女优灵》《午夜凶铃》《咒怨》的成功,恐怖电影/录像带大批涌现。 然而,能称之为“真正恐怖”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这段时期,在我执笔的唯一一部恐怖作品《蛇女》(2000)里,我本想呈现出恐怖元素,但电影想要的效果却近似于古典怪谈。虽然怪谈风才是这部电影的包装策略所追求的风格。 当时有一个叫《难以置信的奇迹体验!》(富士台)的电视节目挖掘到了杉泽村事件等恐怖素材,令社会为之瞩目。 那段时间,出现了一堆顶着恐怖片的名义却一点都不恐怖的电影。 如果电影能利用别的元素来娱乐观众,倒还有可取之处,但最凄凉的还是想吓人却吓不到人的恐怖作品。 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很多导演、编剧本身并非爱好恐怖电影的观众。 然而,上述现象不止出现在日本电影界。 在日本,恐怖电影的制作数量会随着流行趋势起伏变化,可是在欧美却一直维持着稳定的产量。 不过,“真正恐怖的电影”实际上又有多少呢? 谈到最近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可能就是《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1999)了吧。 女巫电影的方法 在《女巫布莱尔》中,不仅录像摄影占据了大部分内容,而且比起在大影院里上映,它可能更适合半夜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盯着屏幕观看。 我的弟弟——电影导演小中和哉称,在影院里看这部电影感觉很恶心,并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一直晃个不停的画面。 让我们谈谈别的。在这部影片里别说女巫了,连惨不忍睹的尸体和杀人场面都没有一个,但却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关于这部电影为何恐怖,或许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纪录片风格所带来的真实感。 影片在日本上映时,两位导演都来日本举办了记者发布会。几乎所有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纪录片风格的虚构电影。 的确,纪录片风格的虚构故事(即伪纪录片)——这种形式依然有杀伤力。 之所以用“依然”二字,是因为我的处女作《邪愿灵》以及与和哉搭档的《脑内潜在麻药物质报告 无药物》(1991)也采用了伪纪录片的形式,我对这种技法的杀伤力了如指掌。在《女巫布莱尔》上映之时,高桥先生、黑泽清先生及众多熟人都指出了它与《邪愿灵》的相似性,令还没看过影片的我很是为难。可是这绝不代表只要用了这个技法,什么样的烂片都能恐怖起来。关于伪纪录片和《邪愿灵》,后面我会再详细论述,总之我想说明的是,《女巫布莱尔》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借助技法进行了极为有效的描写。 《女巫布莱尔》之所以吓人,是因为它不断向观众呈现出画面中的登场人物(影片里的纪录片拍摄者本身)所亲身体会到的(类似)恐怖。 血浆片算原教旨主义吗? 在超自然电影的热潮冷却、人们不再追求“恐怖的电影”之时,1978年却有一部小成本电影创下了火爆纪录,它便是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 《月光光心慌慌》是一部剧情简单的恐怖电影,里面减少了神秘(即超自然)元素,单纯讲述了荒唐的杀人狂接连行凶的故事,可是简单的情节却威力十足。影片的受众以青少年为主,他们对待这部影片的态度就像去游乐园的恐怖欢乐屋(鬼屋)玩闹一样。 和《驱魔人》相似,《月光光心慌慌》也引来了一堆效仿作,包括续集在内,它引发的效仿作可以说超出了超自然电影的范畴,诞生了砍杀片/杀人狂电影(slasher film)、血浆片(splatter film)等众多作品。 其特征表现为,杀人动机通常只在故事结尾提一下,片中呈现大量的杀人场景,并竭力将其刻画得真实、离奇又残忍。 通过特效化装,即利用合成橡胶制作仿真替身的这种特殊摄影技术在发展进步,该技术被人们竞相追逐。然而,《月光光心慌慌》里没有一处直接的血腥场景。不如说,卡朋特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相当正统。 尽管大家都知道《月光光心慌慌》中的象征性杀戮者the Shape[后来更多地被称为亡灵/恶魔人(Boogeyman),不过演职员表里是这样写的]是一个名叫迈克尔·迈尔斯(Michael Myers)的心理变态,可他全程戴着面具,从未露出过真实容貌,不管受多重的伤都能重新站起来继续杀人,他的这种“超级英雄”属性正是本片的革新发明。 令我好奇的是,作为该片效仿作的众多血浆片,它们在目的上为何会与《月光光心慌慌》出现本质差异呢?核心影迷层中也出现了血浆片的狂热爱好者,血浆片甚至被定论为一种类型延续至今。 可是,血浆片算“恐怖的电影”吗? 出场角色纷纷担忧下一个被杀的会不会是自己,这种紧张感成了此类作品中的主导情绪。但它终归是电影媒介里寻常可见的“惊慌”感,应该被称为“悬念”才对。 斯皮尔伯格曾经展示过惊吓效果的威力,这已成为血浆片的基础配置。可总的来说,血浆片中的惊吓全然没有考虑过观众的反应时差等,大多都沦为单靠巨大的响声来吓唬人,然而它仍旧具备杀伤力。 观众坐在影院的座位上时,是希望被恐怖电影给吓到。但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同时也带有一种反抗心理,认为“就凭这点恐怖可别想吓倒我”。 惊吓段落迎合的正是观众的这种心理信号。它是一种信息,告诉观众——“这是恐怖电影,你们可以尽情害怕”,也可以说是一种将观众的观影模式转向恐惧的装置。 而接收到信号的观众,会对剧中人的一举一动产生同化作用,当人物面临威胁时,观众将体会到悬念感。 很明显,正是在花钱买刺激的观众及电影创作者的共同作用下,恐怖电影才有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想经历的“恐惧”情感。然而,血浆片引发的情绪其实是悬念,而非恐惧。 尽管有必要深究二者之间的差异,但我们先来说说血浆片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吧。 前面说过血腥场面(gore scene)是血浆片的表现特征,那么观众对这些场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些东西令人不适,随之而来的感觉是厌恶,说到底还是和恐惧不同。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超乎恐惧的厌恶是人们绝不愿遇到的,因此二者在这方面还是存在着相似性的。 在电影的早期,特效化装因为操作简单(但有很大的创造空间)而兴起,后来又有了假肢、填充术等化学材料方面的进步,经过多年的研究累积,特效化装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花结果。在此前的电影中,绝不可能通过单个镜头来表现狼人变身的场景,但如今也不再是梦。于是有些电影人意识到:一旦能够逼真地表现出受伤及凶杀的场景,那么由此带来的不适感也将是以往的电影所无法制造的。 而独立电影、地下电影界还诞生了另一类不同于商业血浆片的电影,主要通过让观众产生不适感来深度挖掘人性。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橡皮头》(Eraserhead,1977)、弗兰克·亨南洛特(Frank Henenlotter)的《篮子里的恶魔》(Basket Case,1982)、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坏品味》(Bad Taste,1987)等电影都属于此类,另外还诞生了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这样的创作者,他让肉体的毁灭与变异深入人心。 在所有电影类型中,恐怖片是一种奇特的存在,怕者避之不及,爱者欲罢不能。而日本现代恐怖片则是“异色”中的“异色”,它利用人的心理、潜意识和幻想,激发出我们zui本能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式恐怖片(J-Horror)一跃成为现象级热潮,这样一股席卷全球的“暗黑力量”是怎样形成的?它吸收了哪些文化养分?风格化的表现方式背后有何奥妙?日式恐怖创作理论的领军人物小中千昭在本书中为你一一揭晓。 ◎ 编剧怪杰首开午夜讲坛,魔术揭秘般全盘托出玄妙心路 小中千昭是在恐怖、科幻、动画、特摄领域全面开花的不世出怪才,也是享誉全球的克苏鲁神话写手。处女作《邪愿灵》为日本恐怖片创立框架,而后编剧的《毛骨悚然撞鬼经》《学校怪谈》可谓日本流行恐怖剧集的典范;《迪迦奥特曼》《数码宝贝2》等都可见其克苏鲁私货,“不可名状的未知与恐怖”为剧作注入灵魂;集趣味大成的意识流实验动画《玲音》更凭其先锋诡异的情节成为一代赛博朋克神作,引发众多解析讨论。 ◎ 世界恐怖影史+超自然小说漫游,让恐怖迷疯狂颅内高潮 血浆片算真正的恐怖片吗?何物能唤起人类心底的恐惧?恐怖片的黑暗力量有何迷人之处?……串联名家杰作、挖掘冷门怪片,辨析恐怖、惊悚、悬念、血浆等类型特色作用于观众心理的区别,研究日式与欧美恐怖文化的源流关系、理念异同——这场高密度的原教旨主义探索之旅,勾魂摄魄、魅力无边。 ◎ 网络怪谈、神秘民俗、都市传说……解密暗黑养分来源 后果自负的连锁物语、废墟探险的试胆游戏、挖眼拔发的怨灵作祟、四谷怪谈的流传演绎……围绕古典与现代的恐怖传说,发起神妙莫测的“祟咒考”,试图解答:诅咒如何通过各类媒介传播?社会事件与虚构故事怎样交缠?人类为何会有恐惧的情绪?可借本书一窥日式恐怖片瘆人表象之下深厚的学养根基。 ◎ “小中理论”全公开,看“人类高质量恐怖”如何制造 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名编剧,从数十年实践中萃取出“小中理论”,引领了日式恐怖片风潮。恐怖讲究刻意安排、没有逻辑才恐怖、描写恐惧中的人方能制造恐怖……从内涵到技术,倾力传授让影片细思恐极后劲大的表现方法,更有《午夜凶铃》《咒怨》诞生轶事,以及与编剧高桥洋、导演清水崇的珍贵对谈。 ◎ 作者亲自挑选、阐释封面画作,知名设计师操刀整体装帧 封面油画为日本著名画家金子国义的“爱丽丝”主题作品,作者小中千昭讲述了与该画“命中注定”的奇缘故事。全书封面五色印刷、内外双封,选用色彩饱和度高的工艺美术级涂布纸印彩凝;腰封选用半透明硫酸纸,用朦胧质感呼应书中“模糊虚焦的幽灵拍摄技法”。圆脊精装、版式舒适,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