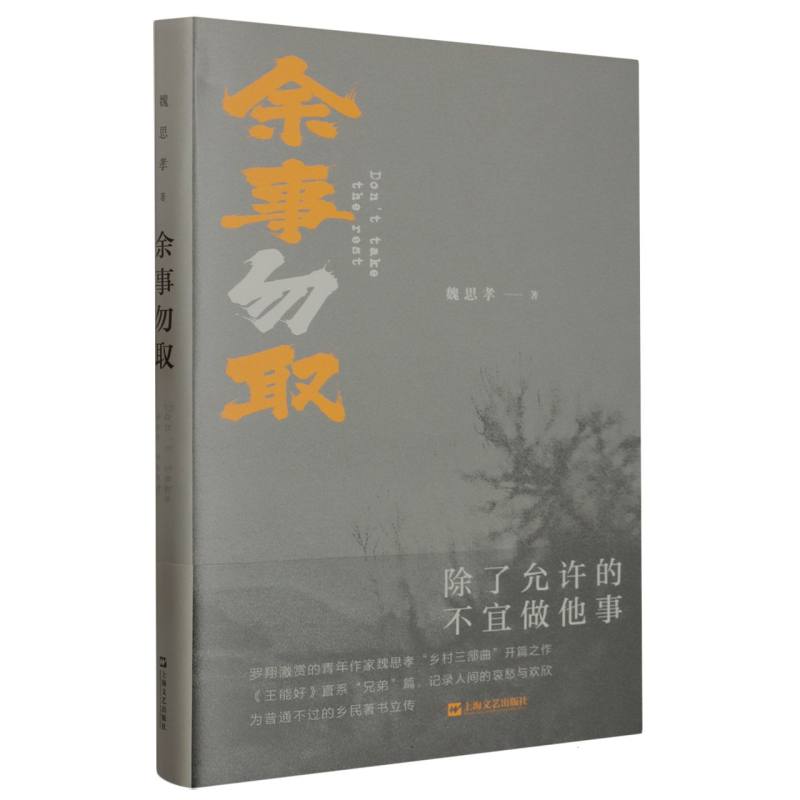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7.80
折扣购买: 余事勿取(精装版)
ISBN: 9787532187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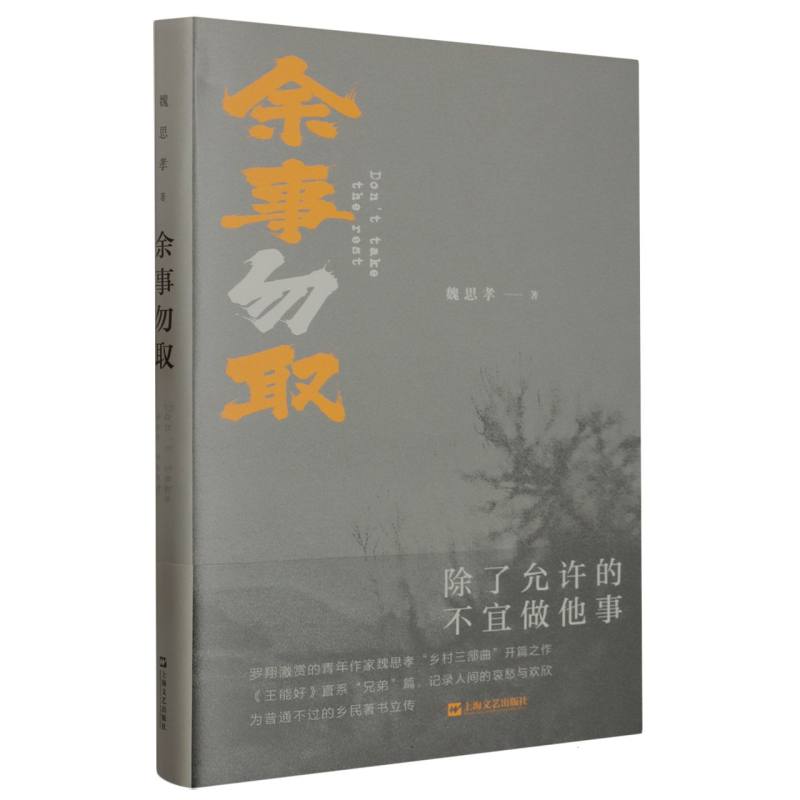
魏思孝,男,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现居临淄乡下,写小说,作品多表现底层青年的生活状态。著有《不明物》,短篇小说集《豁然头落》。
壹 楔子 2007年12月7日早晨,张店四宝山劳务市场路旁的小树林里,一名工人准备小解时,发现一男子全身赤裸着跪在一棵树旁。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裸身男子已死去。经过勘察,死者双手被自己的秋衣裤绑在一棵树上,全身跪伏。其衣裤散落在周边。尸体旁的一根木棍上面有血痕。民警在死者不远处的路边,发现了一辆摩托车。 贰 死讯 |公历| 公元2007年12月5日 星期三 |农历| 二零零七年 十月(大)廿六 |干支| 丁亥年 辛亥月 癸酉日 |生肖| 属猪 |24节气| 大雪(12月7日)冬至(12月22日) |宜| 祭祀 沐浴 成服 除服 结网 入殓 移柩 |忌| 结婚 开工 开业 安床 安葬 交易 开张 作灶 修坟 开市 嫁娶 出货财 在安乐街吉星旅馆的这两个月,侯军的生活十分规律。十点左右起床,简单洗漱后,在汽车站前面移动的摊位上买点吃的——煎饼果子、手抓饼、肉夹馍等,走进街口的新贵网吧。在等待电脑开机的过程中,侯军急忙吃着饭,开机后,他简单浏览了屏幕跳出来的新闻,然后戴上耳机听音乐,在QQ空间里写点人生感悟,有时长有时短,长不过几百字,短则几个字。他昨天写的是,人都喜欢成功的感觉。有人在下面回复了大拇指的表情。今天他写的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战争。这是他突然想到的一句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大概因为这两天的气温降得厉害,确实有种悲凉和孤独感。之前的日记,浏览次数最多的是10月7日,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你下一个幸福的开始。有十五个人浏览,三个人回复。“孤夜浪子”在下面回复,人生苦短,享受生活。“孤夜浪子”是王立昌,此时正躺在离新贵网吧三公里远的市第八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网吧人还不多,有几个通宵的在角落里埋头睡觉。睡眼惺忪的网管小郑端着一碗刚泡好的方便面,站在侯军的后面。小郑十九岁,在新贵网吧当了半年的网管。长期的作息不规律和缺乏户外活动,让小郑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已经是冬天了,他还穿着侯军第一次来网吧时见到的黑色卫衣。除了小郑的年龄,侯军还知道,他家是高青的,高中因为逃课玩网游被开除。来张店半年了,没别的技术,又吃不了苦,能熬夜又懂点电脑。当网管,小郑每天工资十五块,管吃住,每个月还给家里寄四百块钱。 小郑话多,爱指挥别人玩游戏。见侯军很快把自己玩死了,小郑在身后扼腕感慨。侯军已经意识到,游戏是逐渐让人失望的过程,这当然受技能的局限,他只是想获得一种参与感,就像在网吧里,大家玩得兴起不时破口大骂,安静地坐在一旁是不合时宜的。 小郑也问过侯军的情况。侯军对他说自己二十三岁,实际上他已经二十九了。小郑还想知道些什么,侯军知无不言,但多半都是他瞎编的。比如,小郑问侯军靠什么生活?侯军撩开上衣露出胸膛上一道六厘米左右的伤疤,轻描淡写地说,让人砍了一刀,赔了七万块钱。小郑问,怎么砍的?侯军说,和人打架。小郑又问,打架,为什么要赔你钱?侯军说,砍我的人家里有钱,他找另外的人顶罪,七万块钱是封口费。小郑说,这种好事,我怎么碰不到呢?侯军说,小命差点丢了。小郑对他另眼相看,改叫军哥。 实际上,胸口的伤疤是侯军那神志不清的母亲吕慧琴在2001年砍的。除了胸口,侯军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处伤疤,大多也是母亲留下的。胸口伤疤愈合后,吕慧琴在下一次的精神失常中,拿着菜刀去良乡物流园砍人,被一个江苏的货车司机拿扳手敲死了。司机觉得侯军这家人可怜,协议赔偿了五万块。其中的三万块侯军赔偿了被吕慧琴砍伤的四个路人,剩下的两万块,侯军和妹妹侯娟平分。侯军用六千块钱买了辆摩托车,剩下的到了年底也花完了。 小郑从侯军放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对他拙劣的游戏技术不时叹气。侯军退出游戏,说,别在我后面站着。小郑说,没事,你玩你的。侯军问,你有事吗?小郑笑起来,军哥,身上还有钱吗?侯军说,没有。小郑说,天冷了,想买件羽绒服,工资还没发。侯军说,我有件不穿的,送给你。小郑又说,也不只是羽绒服。这几天,小郑在网上认识个姑娘,昨天姑娘终于同意见面。他不仅要买羽绒服,还要请姑娘吃饭,如果顺利的话,开房的费用必不可少。本来小郑要向老板刘姐预支工资,但是昨天晚上三台机器的硬盘被人偷了。刘姐对小郑说,硬盘追不回来,损失要从他的工资里扣。三台机器的硬盘,少说也得两千块,小郑不吃不喝要干上四个月。 说了这些,侯军也没把钱借给小郑。一是,他和小郑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二是,侯军的身上只有一千多块。按照小郑说的,至少要借给他五百块。吃饭怎么着也得找个像样的馆子,少说也要一百块,住酒店的话,就算是标间一晚上也要一百多,说不定还要多住几晚。侯军说,火车站边上这么多餐馆,两个人二三十就吃得挺好,咱这条街上的小旅馆,一个床铺十块钱,单间的话也才三十。小郑觉得他的这份爱情不应该这么廉价去对待。安乐街上的这些旅馆,先不说环境太简陋,还都有色情服务。他想和姑娘住火车站对面的玫瑰大酒店,从网上查了下是三星级。侯军忍不住笑起来,还他妈的三星级。小郑没说话,转头走了。侯军把他叫了回来,你有钱。小郑说,我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吗?侯军看了下四周,没什么人,他问,网吧一天的营业额大概多少?小郑说,一百多台机子,一天平均下来不到一千五吧。侯军笑起来。小郑顿了会,跟着笑起来。 两个月以来,侯军按照一天两三部的速度,先是港片然后日韩和好莱坞,最后又是国产电影,不禁也把自己想象成了电影中的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行为举止。本来少言寡语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却又喜欢盯着别人的眼睛,等待着对方能有所表示。像刚才和小郑的交谈,是他难得去表达的时刻。这也是因为小郑是电影里微不足道的无脑小人物,只能被命运牵着鼻子走。侯军认为小郑也确实应该在生活中历经一番风雨,继续留在这个网吧,唯一的前途也只是腐烂而已。 充当导师的幻觉,让侯军的心情短暂地愉悦起来,当然还没有丧失理智到认为自己会是命运主宰的地步。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生活的旁观者,试着尽量去观察而不是冒失地去参与。这么多年,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同龄人陆续进入了娶妻生子的轨道中,只剩下他还在游荡。妹妹侯娟多次催促过他,但这并不是他想去做就能实现的,何况侯军压根也不想如此。别的不说,他对邓蓉还有着一丝的幻想。 侯军看了一段时间的历史纪录片,从“一战”到“二战”以及“冷战”,那些黑白的影像以及惨无人道的战争场面,不仅没有填补他空虚的内心,倒让他感悟到了人生在世的虚无感。从上周起,他开始看《法治进行时》《今日说法》等普法节目。真实的同时又不乏悬念,无论开始多么复杂、毫无头绪的案件,最终都被破获了。一个案件结束后,主持人和专家还坐着侃侃而谈,普及一下法律知识。侯军清楚地知道,他属于这些人口中需要震慑的潜在犯罪分子。从一期名叫“为情杀人”的节目里,他看到自己和邓蓉的影子,并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主持人略带威严的嗓音,娓娓道出他俩的故事。 2007年9月14日晚上,良乡张家村的村民侯军和两个同事从新村路的一家饭馆出来,骑着摩托车来到火车站。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许多纳凉的群众正伴着音乐跳舞,侯军一行三人蹲在路沿石上,加入到观看的队伍中。这是北方普通的夏季夜晚,天气预报说的雷阵雨迟迟未下,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水汽,让人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淄博火车站”五个红色的灯光字,像是悬挂在半空中。不时有旅客提着行李经过广场,其中体态妖娆的女性让侯军等人意识到了孤独和内心的渴望。与朝北的火车站相对的天乐园,是座六层楼高的娱乐场所,半年前刚进行了重新装修,楼面加装的LED显示屏正在播放韩国某女子团体的劲歌热舞。侯军一行人穿过马路,来到了天乐园的前面,仰着头看着歌舞表演。不时进出天乐园的汽车和走下来的高挑女郎,让这个夜晚更加躁热。天空下起的细雨,不但没有浇灭他们内心灼热的欲望,却预兆着这个夜晚应该会发生点什么。天乐园浮夸的外观以及所代表的不菲消费水平,轻松地和侯军们划清了界限。经过天乐园,往西走不到五十米,是一条两旁林立着旅馆和按摩店拥挤杂乱的巷子。这条丁字型的巷子,大家私底下称为安乐街。侯军他们慢悠悠地走在街上,打量着招揽顾客的小姐。昏暗灯光下的浓妆艳抹和夸张的衣着,让他们有些眼花缭乱。两个同事被热情的大妈一把拽进去,再也没出来。走到吉星旅馆,侯军看到坐在玻璃后面抽烟的邓蓉。邓蓉朝他招手。侯军走过去。邓蓉操着蹩脚的山西普通话说,大哥,进来避下雨吧。 邓蓉下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裙,上身是领口过大能看到白色胸衣的裹身短袖。她跷腿坐在凳子上,脚上趿拉着黑色的高跟拖鞋,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有些掉色了。行人少了,店门外堆放的杂物以及立着的“音像制品”“保健品”“十元住宿”等红色招牌,让街面显得没有那么空旷。眼前这一切,让军感到一丝的温暖。身后不知哪个房间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呻吟声。邓蓉说,这雨下得挺大。侯军点了下头。 如今回想起来,邓蓉娴熟的抽烟姿势,小腹鼓起的赘肉,浓重的粉底和夸张的假睫毛,让侯军想到了电影《出租车司机》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贫民区的站街女郎,放荡之中夹杂着对生活的无声反抗。邓蓉的不主动和无所谓的态度,激起了他的性欲。后来侯军和邓蓉并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问她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邓蓉把头放在侯军的胸前,我只是有点累了。她抚摸着侯军的疤痕,你这是怎么弄的?侯军说,我妈砍的。邓蓉说,你们男的没句实话。邓蓉错了,从认识的这一刻,侯军对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两个月后,邓蓉不辞而别。侯军扬言要杀了她,但还没有兑现。 遇到邓蓉之前,侯军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感情是空白的。2005年,二十七岁的侯军经人介绍,认识了饭馆服务员李莹。李莹接受了侯军阴郁沉默的性格,以及他破败的家庭——包括父母的双亡,以及房屋。而侯军毫无节制的花销和游手好闲的做派,在李莹看来,也属于可以改造的范畴。李莹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比如让侯军学厨师,在良乡物流园的边上也开个家常菜馆,收入稳定后再生几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考虑到侯家是外来户又人丁稀少,侯军想要多生几个开枝散叶,李莹也没什么意见。李莹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的性格和她看起来能生养的屁股,理所应当有个稳定幸福的家庭。但侯军并不想去追求稳定,提出分手也是他自省后的理性判断。他不想耽误李莹,更不想去学什么狗屁厨师。李莹说,你不想学,我可以去学,你安心当老板收钱就行了。侯军也不想去当什么狗屁老板。李莹问他,自己哪点做得不好?侯军只是觉得婚姻和家庭像是枷锁,会束缚住自己。这话在李莹看来,像是找借口。 一个多月的相处,李莹给侯军在集市上买过袜子和内裤;知道他喜欢吃苹果,也从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拿出钱买了一箱。晚上两个人在路上散步,李莹挽着侯军的手,说得最多的是她在饭馆偷听到的那些长途货车司机的对话。比如哪个人出了车祸,哪个车的油在外省又被偷了。侯军觉得这都没什么意思。有时,李莹也想听侯军说他在工厂里的一些事。侯军想了下说,没什么事。 李莹家是日照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在物流园上班,一眼就看穿了侯军,私底下让他离李莹远一点。当天晚上侯军把李莹喊出来,在小旅馆里把她睡了。趴在李莹的身上,侯军闻到了油烟味,性事草草收场。李莹穿上碎花的四角内裤,蹲在水泥地上哭了起来。侯军躺在床上抽着烟,哭泣声让他心烦意乱。李莹爬上床,依偎在侯军的怀中问他,是不是对自己不满意?侯军说,没有,还可以再来一次。第二次,李莹没有了第一次的拘谨,她大声喊叫了出来,情到浓处,她问侯军爱不爱自己?侯军躺在床上,看着李莹。李莹娇喘着说,我稀罕你。分手后,李莹辞掉工作回了日照,侯军再也没见过她。 在后来孤独和毫无舒适可言的两年中,侯军偶尔会想起李莹,却从不掺杂任何情欲的成分。和李莹朴素的外观相比,侯军天生白净柔弱的样子,让人产生一种怜悯感。李莹总是深情地看着他,忍不住地笑。侯军认为这是女人在恋爱中无脑的表现,也不失为讨好他的方式。过去了很久,侯军在心底很不情愿地承认,除了李莹,没有人在乎过他。也只有李莹试图去靠近侯军的内心,相信他有潜力去生活得更好,而不只是一个软弱无能、没心没肺的混子。 …… …… 交响乐与安魂曲(代后记) 项静 魏思孝以书写小镇焦虑青年而为人所知,在中短篇小说短暂的时空中,有时候分不清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的界限,他们在虚构与纪实的模糊地带并肩创造出一种奇特的冲击力,调笑又模拟着小人物无力掌控的庞大生活。《余事勿取》是带着这个文学世界的惯性开始的,但与之相比有一些改变,如果之前的故事是直线系的,这部作品则是团块状的,开篇即以低抑的视角和冷静的叙事声调,拉开了与那些故事的距离,这是这部结构规整的长篇小说铺叙成篇之必要工具。 《余事勿取》以“人物”为索引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侯军、邓蓉、李道广、王立昌等为主体的乡村或者小镇青年,他们活跃在乡域社会中,创造也沿袭着这个空间的生存法则,这一部分的情节是靠慢动作推进的,在三天的生活中完成了对青年群体的素描和彼此关系的钩沉,也完成了一次偶然性“谋杀”。第二部分看起来特别像辛留村的村庄志,清单式数字呈现,解说词一般的俯视,到最后在幕布上越来越清晰的是卫学金这个人物,是他的善良、隐忍、兴奋、发现、死亡的“英雄”史诗。第三部分写卫学金的儿子卫华邦,一个“八零后”的大学生,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对于父亲和乡村社会既游离又深度参与其中。恰如《余事勿取》的标题,小说弃绝其他集中于“生存”、以崭捷简单的风格透视和映照了新世纪初十年左右乡域社会的生活,融入了社会案件、乡村志、小镇青年的元素,撰写了一幅粗粝的乡域社会生存图。在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上,“齐鲁石化”进入村庄人们的日常视野,传统的标配产业砖瓦厂、淀粉厂破产,小镇青年们在各种行业间不停转换着“战场”,有的获利清盘,有的继续游荡,有的远走他乡,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没多少浪漫色彩,天然地带有一些暴力和沉沦的自然主义色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中间力量以自己的生命划出艰难的生存形状,情义与坚韧让他们承担着家庭与空间的责任,承受着上一代和子一代的压力,也感受到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精神压力。身体和尊严成为最早的牺牲品,即使身患重病,还没有逃脱偶然被杀的命运。作者魏思孝非常看重作品中的卫学金,在一定程度上置入了作者的个人情感(现实生活中父亲的去世和一个儿子对父亲一生的回望),从而把普通农民卫学金的一生叙述成英雄般的一生。平民的英雄无法与顶天立地、丰功伟业这种词汇和形象联系起来,但从生命的深度来讲,依然有其同构性。这个五十而逝的中年农民,在辛留村的背景之上完成了个人生活的“伟业”结婚生子,青年时代的高光时刻,他讲究义气满足于自己的所得,不忍心向破产的弟弟要工钱,在社会的浮沉中,个人生活也经历着大大小小的改变与升降。在生命的结尾,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就是逐渐被抛弃的过程,中间他曾想过跟紧这个时代,就像他最身强力壮的年龄是个骡夫一样,不远处车流不息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他的位置。”顿悟、兴奋、悲痛、无能为力,甚至那些深情的细节,一一建造着一个厚重、朴实、普通而有力的生命过程,有了这些因被凝视而具有质感的跌宕起伏,完成了渺小而英雄般的一生。 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不平和苦难,他们默默饮吞了宏大社会运动的一切,却没有找到自我释放的窗口和表达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卫学金是与辛留村最匹配的见证人和秘密守卫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人证。 小说中最年轻的卫华邦们是被保护的“温室里的一代”,他们不具备前两代人的野生和坚韧,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生活,遭遇爱情与消费主义的窘迫,提前看到了父一辈的辛苦恣睢、兄长一代的暴力与杀戮,父亲之死恰恰是他们的成年礼,温情与残酷联手为他们的人生盖上醒目的戳记。三代人的相遇是故事的收拢之处,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挽结处。相比来说,第一部分是紧张而跃动的,像悬疑电影的节奏;第二部分色彩浓重又压抑,局面却是开阔的,仿佛无处不在的长镜头;第三部分篇幅最短,情绪稀薄而伤感,是年轻一代的抽离与旁观,也是难以纾解和发泄的痛。《余事勿取》通过三个代际人物的描述,完成了新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命运的变奏曲,又以沉潜的情感赋予其间“英雄”们以安魂曲。 乡村社会已经很少进入当代文学写作的核心地带,它很难令人信服地产生具有吸附力和共鸣感的情感和处境,也无法即时提供未来的想象蓝图。但这个还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空间,是当代中国社会无言的见证者,居于其间的民众,依然是攀藤牵丝的“我们”,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复杂的心灵史和因凝视而产生的情感光晕,内在于真诚的书写者视野之内。如果一个空间不再产生精神的愉悦,我们会怀疑自己为何要重复走在恶之旅程中,如果这个空间充溢廉价的诗意和家园感,那也不过是蒙蔽者的视角。《余事勿取》不是孤立的作品,而是在这些背景之上的作品,它既是响彻村庄上空的交响曲,又是安魂曲,暴力和死亡让不同代际的人群在缓慢的生命推进中交混碰撞,也在彼此的映照中扩大了乡村社会的景深,《余事勿取》提供了掀起乡土写作厚重帷幕的一种方式,帷幕之后是什么,还需要更多的作品去擦亮和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