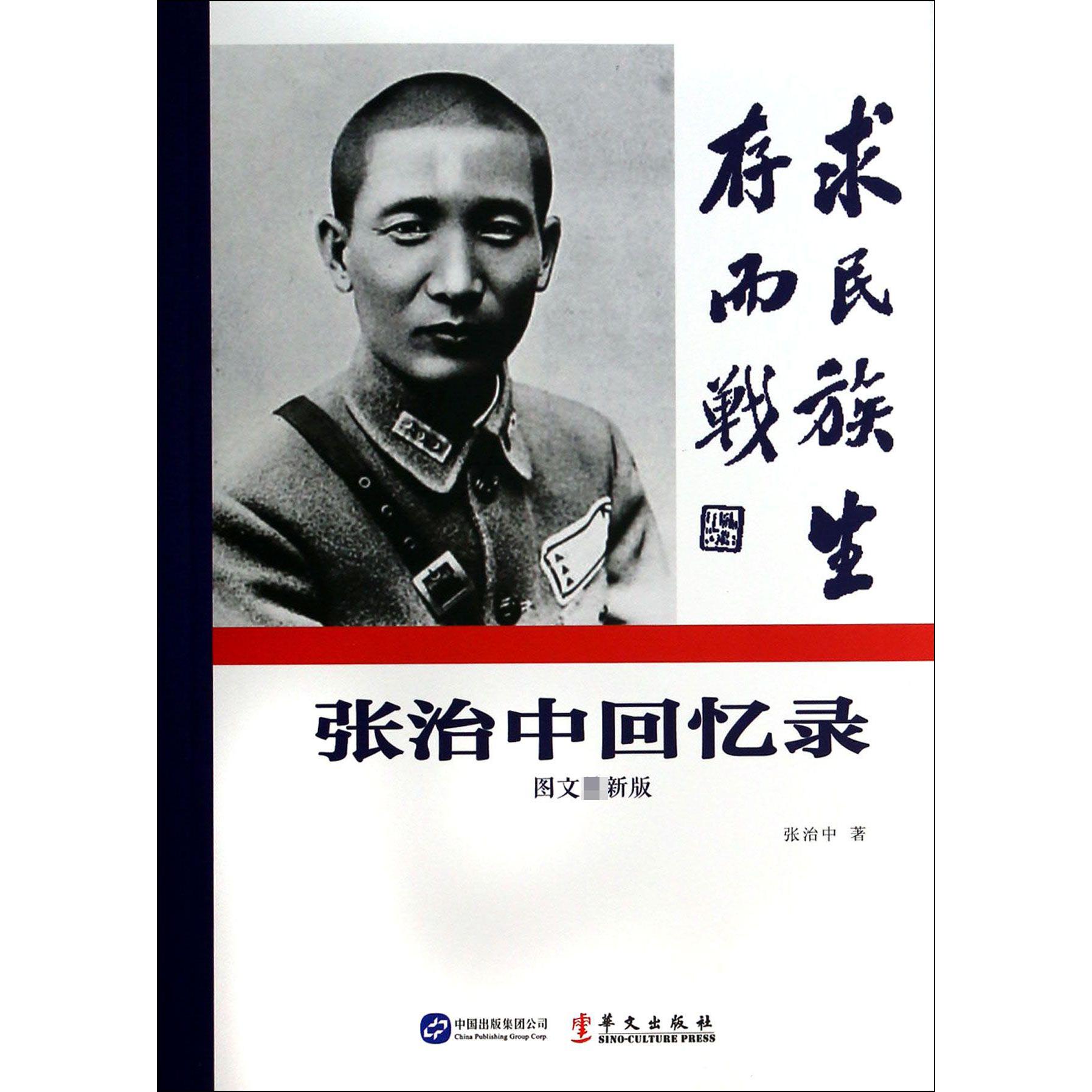
出版社: 华文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张治中回忆录
ISBN: 9787507541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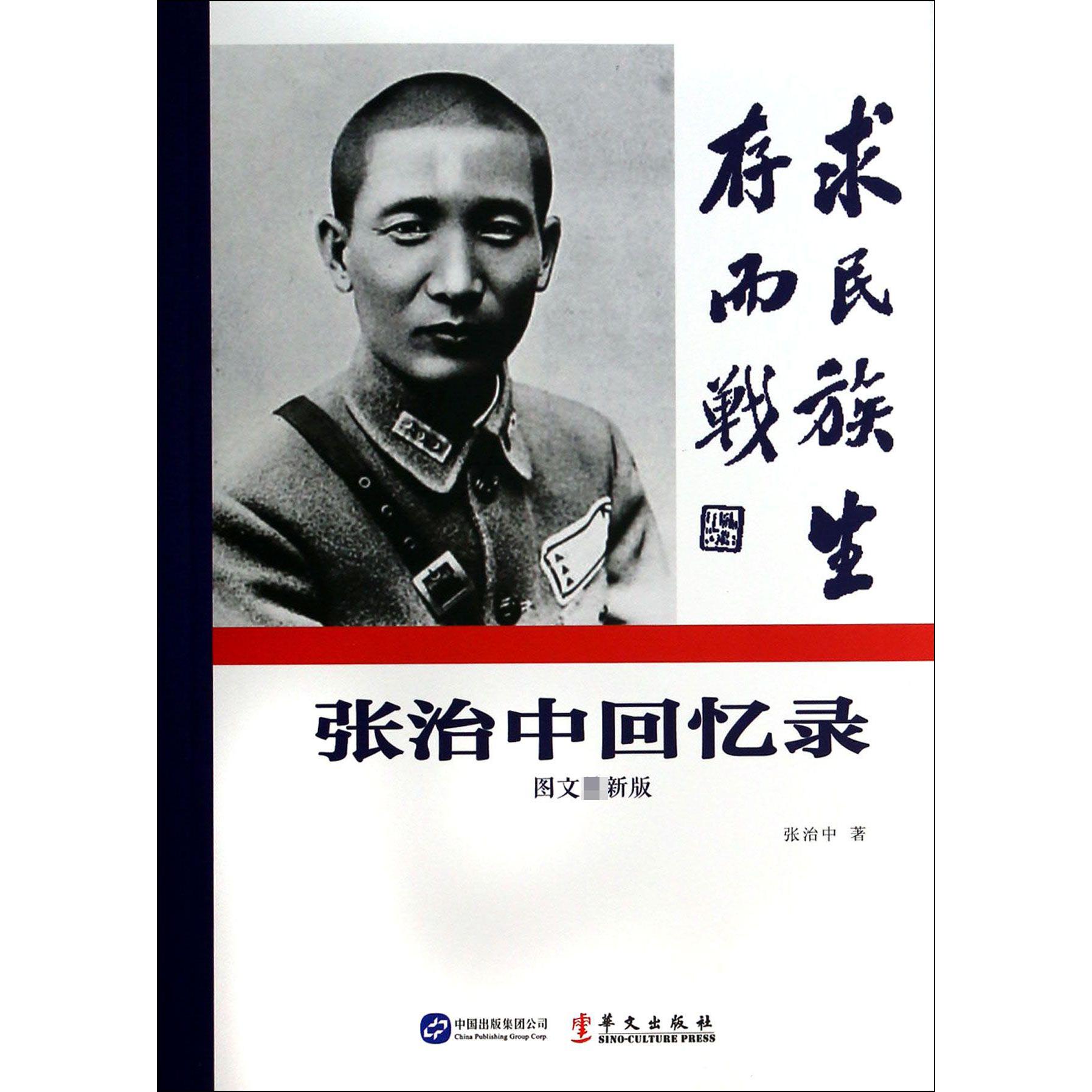
我们的村子是背山面湖的一幅画图。向东十五里 是炯炀河,向西十五里是长临河,向南二十里是忠庙 和四顶山。四顶山是一座名山,忠庙是一座名寺。四 顶山在离忠庙不过三里的湖边,山是四个顶,远望四 峰,对峙竞秀。 在黄山东麓有一个大庙,叫做指南庵。我记得, 在我幼年的时代,香火还是很盛的;光复那年,庙被 焚毁,一直没有修复。抗战前,我想把指南庵修复起 来,一方面保存古迹,一方面做研究佛学或研究其他 学术者的栖息之所。已经预备烧砖瓦了,因为抗战军 兴而停止。 这个寂寞古老的洪家疃村,在交通方面,淮南铁 路及合巢公路经过它东面十五里的炯炀河,东南与芜 湖、南京相衔接,朝发夕至。 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 ,男耕女织,各司所事。但是终岁辛勤,仅得温饱, 有的还得不到温饱。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一向是不发 达的。读书,被看做是特殊阶级的专业,过去科举时 代这里只有秀才,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风气太 闭塞了。我在一九二九年创办一所黄麓小学,后来扩 充为黄麓乡村师范。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 才开始领受现代教育的洗礼,读书的风气才渐渐展开 ,后来不仅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获得就学的 方便,皖北各县的来学者也日益增加,俨然成为这一 地区的文化中心。 我怀念我的故乡,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离我的 家,向北走不过百步,是我祖父母、父母、叔父的长 眠之所。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我们叫做坟 庄。我回乡时,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有一年在家中 过旧年元旦,大雪纷飞,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 庄的园里。雪越下越大,像百万玉龙盘舞。我孤清清 站在雪花中,俯看山麓的村庄,和平、幽静、纯洁, 一片粉装玉琢的乾坤。山泉淙淙,奏出天然的美妙的 乐曲。这时,我浑然忘了世界的尘秽,撇却了人生的 疾苦,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纯洁而光明。我 仿佛到了一个化境,一个超然出尘,遗世独立,飘飘 乎欲仙的化境。我相信,这种意境,是渊源于我对可 爱的黄山,可怀念的故乡,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 墓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 林泉的愿望。 我常常回到故乡去。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 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近民众的机会。其中最值得回忆 的一次是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四 十天。战前三十天的准备工作,从八月十二日到九月 二十三日整整四十天指挥作战的辛苦,使我的身体疲 惫不堪。九月二十五日从前方回到南京,虽已调任大 本营重要职务,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到了洪 家疃,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 。我一回到家乡,如释重负,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 我在休养期中,也和每次回乡一样,常向黄麓乡 师学生讲话,大多讲些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自己 亲自体验的现身说法讲出来,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 有恢弘的抱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应该关怀 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同时,我在他们面前,表 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我并不希望做大官,但愿有一 天回到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也许在教 育上的贡献,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我也常把孙总 理的遗训启示他们,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希望做 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 要他们为农村服务,埋头苦干。因为我们乡下总免不 了一种观念:做官是好的,做差事是好的。这成了一 种社会趋向,父母教儿子读书,乡党期望子弟上进, 全是为的做官。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 ,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使大家知道为 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中国人口百分之八 九十是农民,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能在乡村工作 ,不能为农民服务,而趋向政治活动,做官,干差事 ,把乡村风气弄坏,人才减少,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 ,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我分析这些道理,警 觉黄麓青年。 黄山虽好,可惜树木少。我提倡植树造林。有些 池塘没有鱼,我提倡养鱼。这时清水塘干了,是由于 塘身太浅,蓄水不多。我提倡挑塘,把塘掏深。我自 己带头下塘,领导大家踊跃挑塘。村里的人笑着说: “总司令①挑塘!总司令挑塘!”我觉得参加这样的 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 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 一个实验乡的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 炯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乡道,再在各村修村道 ;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 则办理。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想 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 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 尽有。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可惜我的理 想刚生了芽,尚在计划阶段,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 起来了。 这一次回乡小休,曾在四顶山小住十余天。四顶 山,像上面说过的,是巢湖湖边的一座名山,面着大 湖,松树成林。我在山的第二顶上盖了小房三间,终 日悠悠地在山上林间,踱来踱去,晒晒太阳,看看山 色湖光。忠庙、孤山、姥山尽入眼底,远望白石山和 巢湖南岸诸峰,参差如列玉屏。我常常一个人静悄悄 坐在山头,面对巢湖,天风浩荡,襟角飘开。每遇这 种境界,顿忘尘俗,栩栩欲仙,觉得心灵上受着莫大 的益处。 有一天,是我的生日,家里的孩子们,由长女素 我领着,从二十里外的家步行到四顶山来了。那是一 个清晨,我正坐在山头一块大石上观赏景色,忽然一 阵歌声从山下传来,渐近渐清,听出是我的孩子们的 歌唱。边走边唱,为他们的父亲庆寿,祝福。这一种 情景,大自然的殊恩与天伦间的至乐,交流合响而成 为人生的幸福的源泉,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回忆 。 我对于故乡的父老,从小就礼貌甚周。望见长辈 来了,远远打招呼,先喊他,所以父老很喜欢我。我 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他们对我也情意深厚。对每次 回乡,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们谈谈,问候他们,也请 他们喝喝酒,吃吃饭,有时也掷掷骰子。我掷骰子的 方式与众不同,我预备了许多铜板,每位各给一份, 只准押一注,输的归我贴,赢的带了走。我觉得这些 长辈们应该受我的尊敬。我每次回乡,有一定的程序 :进祠堂祭祖,上坟扫墓,分别恭请张、洪两姓长辈 公宴。敦约周围十多个村子的六十以上老人聚餐。抗 战胜利后,我也曾一度回乡,只是湖山依旧,长老凋 零,不禁感慨无已! 家世 在远远的年代,大概是明朝末季吧,从江西迁移 到安徽,落籍到巢县西乡的四大房姓张的,那便是我 的祖先。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我们是四大房中 的长房,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叫做“ 靠山张”。我家这一支以后又移到洪家疃,相距也不 过一里。这四大房就叫做“四房张”。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是没有做官的 ,连念书的人也很少(进学、中举,根本没听见,仅 有几名童生,都没有得过“功名”),大都以务农为 本业,有少数做手工的,经商的也少,一族人安分守 己地度生活。 我的祖父名邦栋,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者,性情 刚正,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 开洪家疃。只有在他的儿、媳——我的父母——居住 丰乐河的期间,偶然去过冬,可以说,他毕生没有出 过远门。祖母是洪家的女儿,早去世,我没有见过。 我的父亲名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 粗通文理。他是一个篾工,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 制农具店,即篾器店,当然是非常辛苦的。父亲为人 老实忠厚,是一个柔和的人,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 样。我的叔父名桂荣,也是篾工,也在丰乐河镇上开 了一间篾器店。 我的母亲,娘家姓洪,从小操作辛苦,得了气喘 病,终于因此而早死。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中间还 有一个妹妹,早天),带着病照理家务。这是一个贫 寒家的家务,她要自己烧菜,煮饭,洗衣,还要督促 篾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她是一位慈爱、和平、 厚重的伟大的母性。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 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