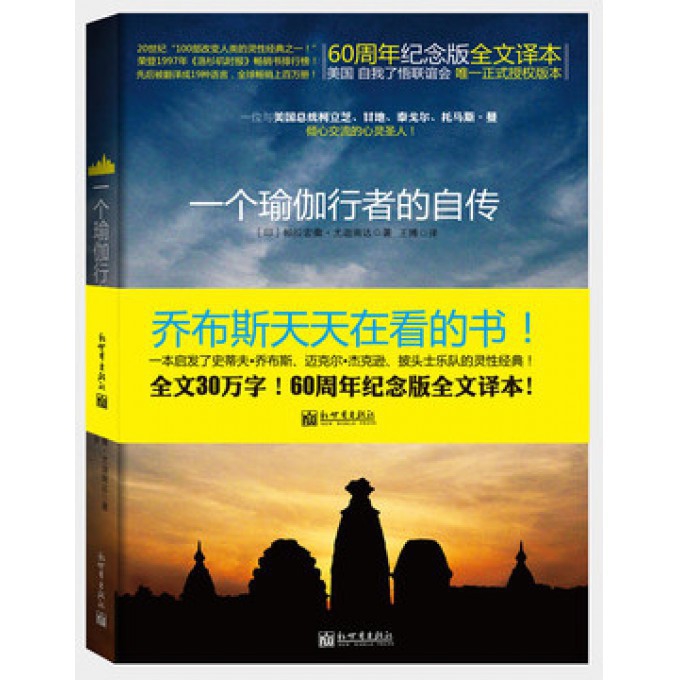
出版社: 新世界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
ISBN: 9787510424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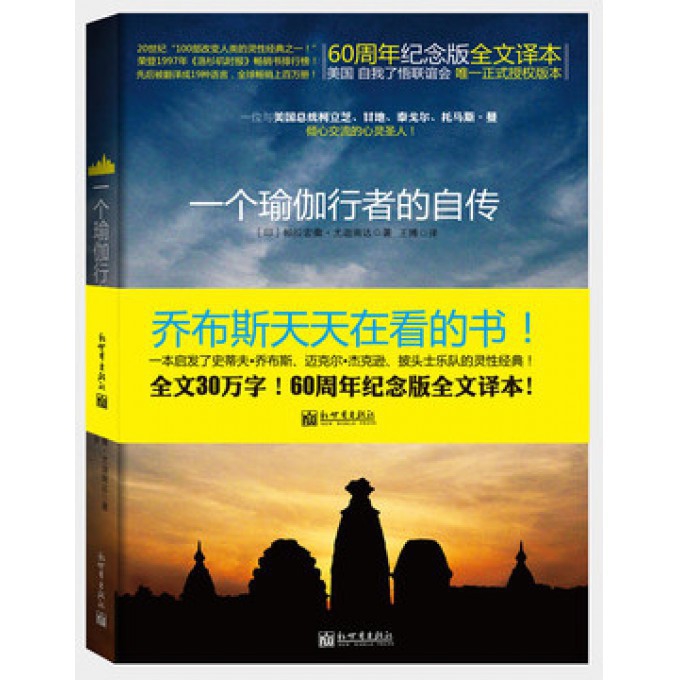
帕拉宏撒·尤迦南达,1893年1月5日出生于印度戈勒克浦尔,1915年取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正式加入僧团。1920年起旅居美国,展开为期约三十年的西方弘法生涯。1952年3月7日,在加州洛杉矶毕尔特摩尔(Biltmore)饭店欢迎印度大使毕内·山(H.E. Binay R. Sen)的宴会致词完毕后,进入最终涅盘。
19世纪末,我出生于印度东北部联合省的戈勒克浦尔(Gorakhpur),并 在那里度过8年的童年岁月。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八个,四男四女。我当时名 叫穆昆达·拉尔·高绪(Mukunda Lal Ghosh),排行老四,是家中的次子。 我的父母亲是孟加拉人,属于刹帝利(Kshatriyas)阶级。两人都具有圣 人般的品质。他们互敬互爱,内心平静,举止庄重,从不会有任何轻浮的举 止。他们之间完美和谐,是八个闹哄哄的小孩寻求安宁庇护的中心。 父亲名叫巴格拔第·夏蓝·高绪(Bhagabati Charan Ghosh),他仁慈、 勇敢,有时又很严格。我们都很爱他,但他让人敬畏,我们始终跟他保持距 离。他是个杰出的数学和逻辑学家,为人非常理性。母亲则总是充满爱,她 是我们的精神女王,凡事都以爱来教导我们。自母亲死后,父亲就经常显示 出他内在温柔的一面。他的眼神也经常转换为母亲般的眼神。 母亲在世时,我们就开始了苦乐参半的圣典学习生活。一旦需要强调纪 律,母亲就会用《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或《罗摩衍那》(Ramayana) 的故事来教导我们,有时也会进行惩戒。 父亲当时在一家名叫“孟加拉·那格浦尔(Bengal·Nagpur)铁路局”的 大公司做副总裁。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敬,每天下午,母亲都会精心地将我 们穿戴整齐,迎接他的归来。父亲的工作地点经常变换,小时候,我们曾先 后住过几个不同的城市。 母亲对贫苦的人慷慨好施,虽然父亲也同情穷人,但他比较理性。有一 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母亲将父亲一个多月的薪水都用来接济穷人。 “我只是希望,你在帮助别人时,能尽量合理。”父亲轻声责备道。但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觉得难以忍受。她不动声色地雇了一辆出租马车。 “再见!我要回娘家去了。” 我们惊慌失措!幸好舅舅及时出现,他在父亲耳旁私语了一些忠告,父 亲立刻说了一些安抚的话。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马车打发了,结束了我生平唯 一注意到的一次父母之间的纷争。我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他们之间的对 话通常如下: “请给我10个卢布,我要给一位无助的妇人。”母亲微笑着说,她的笑 容有着巨大的说服力。 “为什么要10个卢布?1个就够了。”父亲说道,“当我的父亲和祖父 母突然去世时,我第一次尝到贫穷的滋味,那时我早餐只有1根香蕉,之后 还要步行几英里去上学。后来读大学时,我曾向一位法官求助,求他每个月 施舍我1个卢布。他拒绝了,还说:‘1个卢布也很重要。”’ “被拒绝的那个卢布带给你的回忆是多么痛苦啊!”母亲反驳道,“你 难道希望这位妇人以后也像你一样苦涩地记着被拒绝的10个卢布吗?” “你赢了!”自古以来,丈夫总是说不过妻子。父亲打开钱包,“这是 一张10卢布的纸钞,请给她,并送上我的祝福。” 对于任何新的提议,父亲通常总是先说“不”。刚才的故事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不立即接受,这是典型的法国式心态。但我发觉父亲总是理性而 公正。一旦我提出任何请求,只要能列出一两项正当的理由,父亲总会让我 梦想成真一不论是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还是一次假期旅游。 父亲对我们很严格,但他自己的生活更加斯巴达式。比方说他从不看戏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修行及阅读《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他从不曾 拥有任何奢侈品,鞋子总是穿到不能再穿时才扔掉。当儿子们开着早已普及 的汽车时,他还是每日乘坐电车上班,而且心满意足i他从不会为了权势而 积聚钱财,这与他的本性不符。有一次,在组建了加尔各答市银行后,他拒 绝领取该银行的股权来为自己谋利——他只希望能在空闲时尽一个公民的责 任。 父亲退休几年之后,从英国来了一位会计师审查孟加拉·那格浦尔铁路 公司的账,后者惊讶地发现,父亲从未申请额外的津贴。 “他一个人做了三个人的工作!”这位会计师说,“公司应该补偿他 125000卢布(约41250美金)。”出纳开了一张支票给父亲。父亲觉得这是一 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没有向家人提及。很久以后,弟弟毕修(Bishnu)在银 行往来明细表上注意到这笔数额庞大的存款,才问起他来。 “为什么要为物质上的利益高兴呢?”父亲回答道:“一个追求心灵平 静的人,向来不会为得到什么而开心,也不会为失去什么而忧虑。他知道, 世间万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父母亲结婚之后不久,就成为贝拿勒斯(Benares)伟大上师拿希里·玛 哈赛(I,ahiri Mahasaya)的徒弟。这让父亲变得更加苦行。有一次,母亲告 诉大姐:“你父亲和我一年只有一次夫妻生活,而且还只是为了生儿育女。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