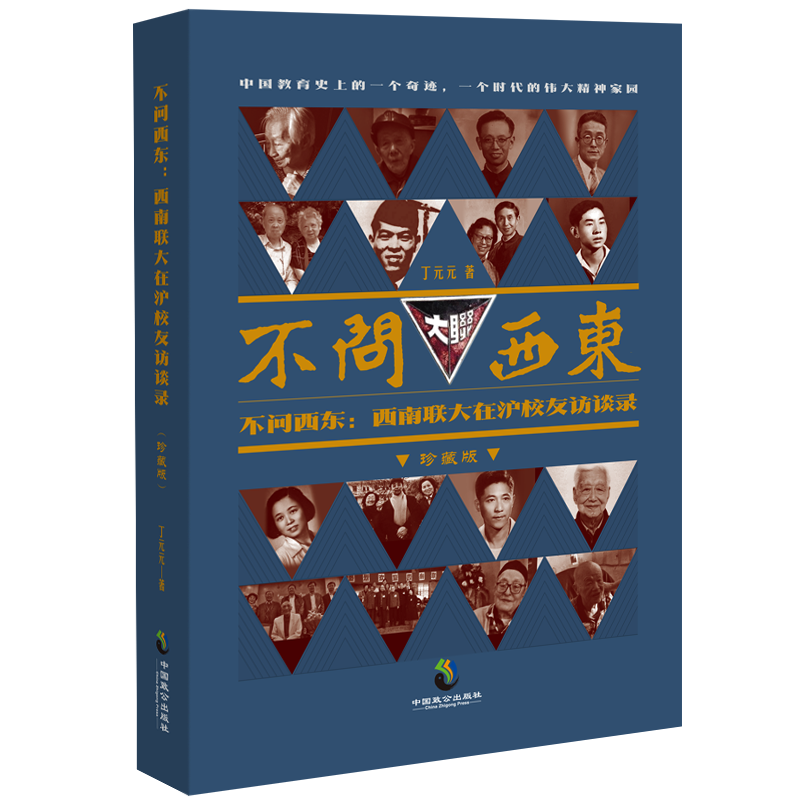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致公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6.10
折扣购买: 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珍藏版)
ISBN: 9787514514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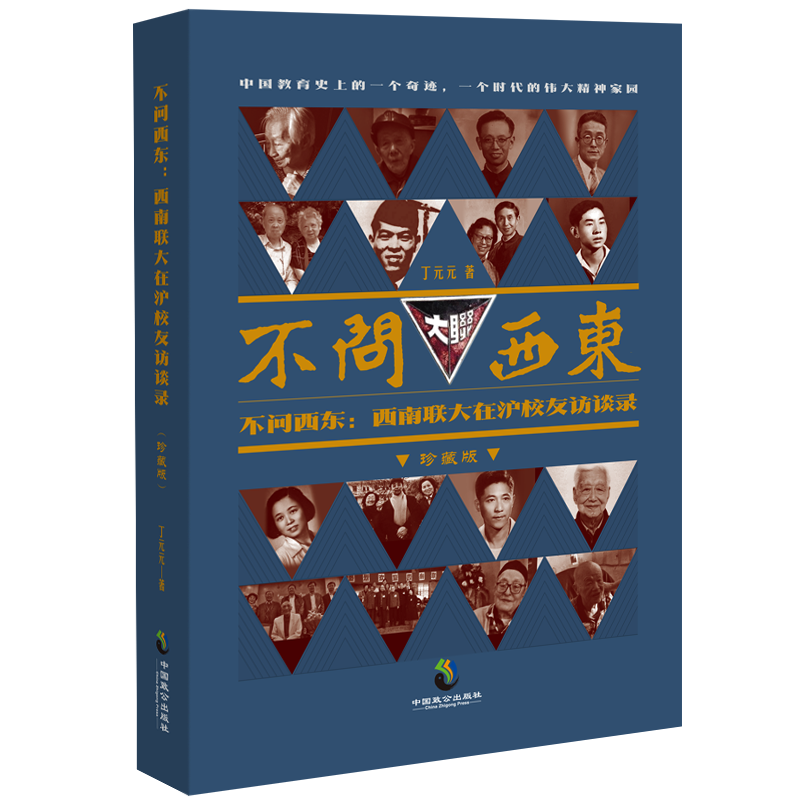
丁元元,男,生于1984,大学毕业后从事了10年媒体工作,做过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从2014年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老校友,听他们讲述往事,并且将之记录下来,希望给世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
隐姓埋名于 404 …………(节选) 就在我拜访赵仲兴之前不到一个月的 1 月 9 日,2015 年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也是他一生仅有的两次公开露面之一,之前一次是 1999 年出席国家“两弹一星元勋”授奖。 我说看到报道里说,于敏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搞氢弹。赵仲兴说:“确实是隐姓埋名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弹, 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厂的代号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厂里也没有电话,家里人只知道,要联系我就写信到兰州的一个信箱,信会转到我手里。” 那时候,赵仲兴告别家人,去了戈壁滩中的核工业 404 厂,在其中的第一分厂担任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这里面我们有个弱点,最初都是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设的,后来就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了,于是征调我们这些人去接上他们的工作。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对于我们一些核设施的内部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好在我们早期的一些设施已经放弃了,又在四川等地建了新的基地,这样他们就算想攻击,也构不成什么实际威胁了。” 为了保密,赵仲兴所在的 404 厂当初对外叫“西北矿山机械厂”。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他至今不会详细地向别人讲起,笼统的说法就是提供核燃料—从铀的开采就开始介入,一直到生产出合格的核反应物质。甚至对于 404 厂的厂址,他在写文章时也只是说“大西北”。 赵仲兴甚至以为该厂的情况至今丝毫没有解密,直到我告诉他,网上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核工业 404 厂”的资料了,甚至还有一篇专门写 404 厂的文章曾经广为流传。 据资料记载: 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核工业 404 联合企业(原名 800 联合企业),是我国核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难得的后处理基地。 404 厂在 1957 年确定厂址。1958 年 9 月、10 月间建设队伍就开进了戈壁滩。厂址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棵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二三十里地以外是茫茫戈壁, 荒无人烟,所以也没有征地移民问题。以后工作人员曾因工地孩子没见过树,便将他们用大轿车拉到玉门镇去看树。孩子们见到大树就高兴地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听我读完这段话,赵仲兴说:“对,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 我问:“核研究主要是物理方面的研究吗?”赵老表示并不尽然:“从铀的开采、提炼开始,再逐步氧化为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等,都是化学过程。虽然原子弹里的铀是单体,但要通过不断氧化提高纯度。核反应的过程是物理的,但反应后的放射性物质经过离心分离之后,如何净化处理,又是化学领域的。” “因为我家在上海,所以在交出合格的产品(核燃料)之后,我就申请调回上海,还是在二机部的系统内。1965 年 3 月,我调到了上海原子能核研究所,1975 年完成了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放射性气体的净化处理,为此被授予‘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 看(听)着《中华之核》,他很是专注。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1967 年 6 月 17日上午 8 时 20 分,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试爆…… 虽然片子拍得“点到为止”,至多只是呈现了一些过去未必看得到的镜头, 对核试验等的详细过程“解密”十分有限,但他还是高兴地说:“片子很好,大家看了就对整个过程有了了解。” 我说,他看这些东西一定比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一定会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他说是的,看着片子会勾起很多很多的回忆,虽然这些回忆也许永远无法和其他人分享。 我对赵仲兴说:“您也是‘两弹元勋’吗?”他解释说自己不是:“‘元勋’授予的都是‘搞弹’的人,都是做物理研究的,那个是原子弹、氢弹里面最难的。”但是,不可否认,那些为“元勋”们准备核燃料、清理核废料的科学家,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从联大到黄埔 …………(节选) 2014 年 9 月 11 日,我拜访了第一位西南联大校友,也是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夏世铎。 他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附近的一个小区内。老伴去世后,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住在这套宽敞的房屋内。两个房间的交汇处有一张办公桌,两面都是书橱,书桌边堆放着许多资料。 夏世铎家的客厅里挂着一些自己满意的书法作品,装裱在镜框里,电视柜上摆了不少奖章、奖状,最特别的是钢琴上的一张印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历的奖状,那一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作为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的第三任会长,他也许是联大学生中的一个异类——在这所名校学习了不到一年,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便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战之路,后来又成为黄埔第十七期的毕业生。 夏世铎有着令人惊叹的人生经历,他读过中国一文一武最有名的学府,几次差点死于非命,几次想上前线而不成,几次与留美擦肩而过……而当这样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坐在你面前时,只有聆听他醇厚的北方口音的讲述,才能开启那样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夏世铎可能是联大校友中晚年较多受到媒体等方面关注的一位。 他做过普陀区政协委员,至今担任着多项社会工作。显然他受访的经验很丰富,加之记忆力也很好,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条理非常清晰,也能恰到好处地讲出记录者所需要的案例、故事。 夏世铎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保留着文人的底色,却没有知识分子自负、散漫的特质。投笔从戎的经历,在他的身上显著地留下了一个军人严谨、“以服从为天职”的烙印。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注重纪律和秩序的“工作者”。 作为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他说自己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9 月底刚去夏威夷参加了黄埔军校校友纪念活动。“只要我还有这样的价值,社会还需要我去工作,我就应该去做。”夏世铎目前担任着上海联大校友会会长、上海黄埔同学会理事等五个社会职务,他多次和我说:“联大、黄埔同学会都是党的统战工作。为党工作,不但要把交到你手上的工作做好,还要自己去动脑筋,有创造性地去做一些事情。” “我现在还联系台湾国民党的五个上将、十几个中将、几十个少将。其中,经常联系的国民党老将军,就有四个上将、八个中将、三十一个少将。每年从 11 月开始,我就要陆续写贺年卡,因为给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很早就要开始构思。” 他给我拿来了两张贺卡,一张是原台湾“政战官”许历农上将寄来的贺年卡;另一张是原“陆军总司令”陈廷宠上将的贺年卡,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手书文字。 “陈廷宠有一个外甥和我都是普陀区的政协委员。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然后聊起来才发现,陈廷宠做营长的时候,他的军长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一直称我为‘世公’。” 他还说,自己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也觉得有顾虑,没想到自己的学生还有其他同期的学生都来看他,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将官,还站成一排要请他训话。 “有人对我说,你可惜了,如果当初来了台湾,也许现在的地位会很高。我说我不会去台湾,国民党腐败,对人民不负责,所以失败就失败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很多学生也同意我的说法,直到后来有人出来打圆场说:‘今天不谈政治。’” ………… 夏世铎 1920 年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在陈独秀执掌的安徽高等学堂读过书,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期在军政府当秘书,再后来在北京观象台做职员, 也在无锡做过税务局长。 他的母亲是原常州商会会长的女儿,也是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维乔的干女儿。所以母亲很早就到了上海,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 蒋维乔去 工作时,又把她带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后来做了小学教师。 因为母亲在北京的市立三十八小学任教,于是少年的夏世铎也就在这所学校里念书。 “我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又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中间(老三),所以最不受宠。但我很有志气,觉得要靠自己努力,将来要出人头地,所以功课不错,在班级里也比较活跃。” 之后母亲调到市立三十一小学,夏世铎也就跟着转学到了三十一小学。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夏世铎正在读高小一年级,“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有爱国思想,于是串联同学,奔走相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沈阳。”那时候他家邻居有几个日本小朋友,原来夏世铎和他们关系不错,由此也对昔日的小伙伴非常仇恨,从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 “我参加了北京大中小学生的大游行,还在街头演讲,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我们还到了张学良的官邸去请愿,要求张学良接见,要求他出兵。当张学良官邸门口的机枪架起来之后,我们小学生只能先撤退了,大中学生还在继续请愿。” “另外我还参加了宣传抗日的工作,为难民募捐。”夏世铎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冤狱》,无辜的穷人因为没有钱请律师辩护只能坐冤狱,当时就有了将来做‘公益律师’的想法,帮助穷人打官司, 所以后来报考了联大法律系。” 之后,随着抗战的形势加剧,北平也受到了威胁,夏世铎的父亲转赴无锡当税务局局长,全家也搬到了无锡。他进入当地的辅仁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集资创办的中学,在当地可算是名校。 “因为里面的校长、教师都是圣约翰毕业的,所以他的英文名叫 St.John's Middl。北大校长许智宏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但他要比我晚许多年。”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夏世铎在读高中二年级。因为举家逃难, 他第一次回了老家—安徽巢县(巢湖),也在那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巢县有两个宣传抗战的组织,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后援会’, 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家里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人都有。我参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因为家里有四个表哥都是共产党员。我有一个表哥叫陈其五(原名叫刘毓珩,陈是母姓,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家兄弟四个,老大刘毓璜也是共产党员,老三叫刘毓璠,在左权县(当时叫辽县)做过县委书记,日军在太行山扫荡的时候,打到这个县,他就带领机关人员一起参加战斗,在那里牺牲了。老四刘毓琳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所以他们都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讲述一群普通而不平凡的西南联大学生的故事! ★通过独特的视角、珍贵的史料以及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展现不同时代的历史变迁,让读者了解历史,感悟历史。 ★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