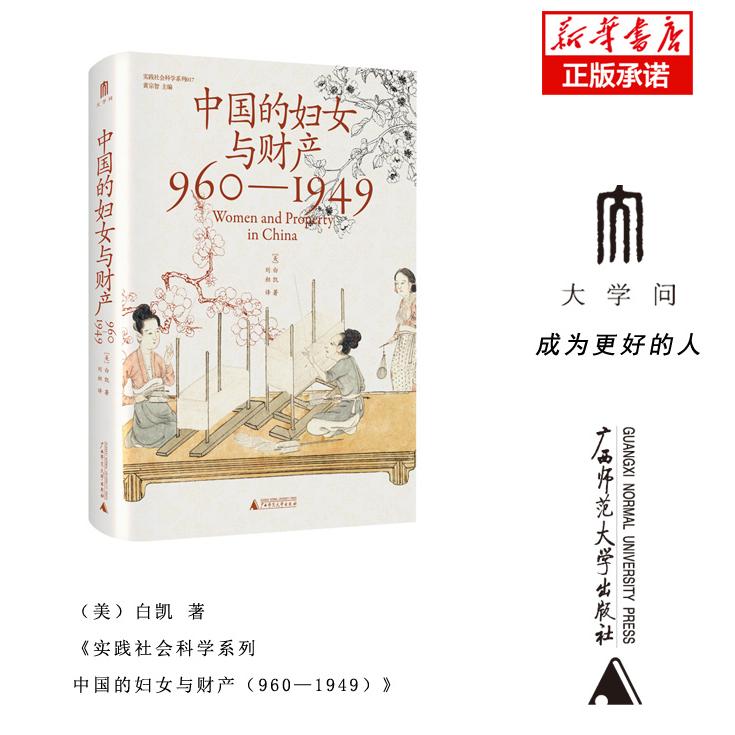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20
折扣购买: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ISBN: 9787559870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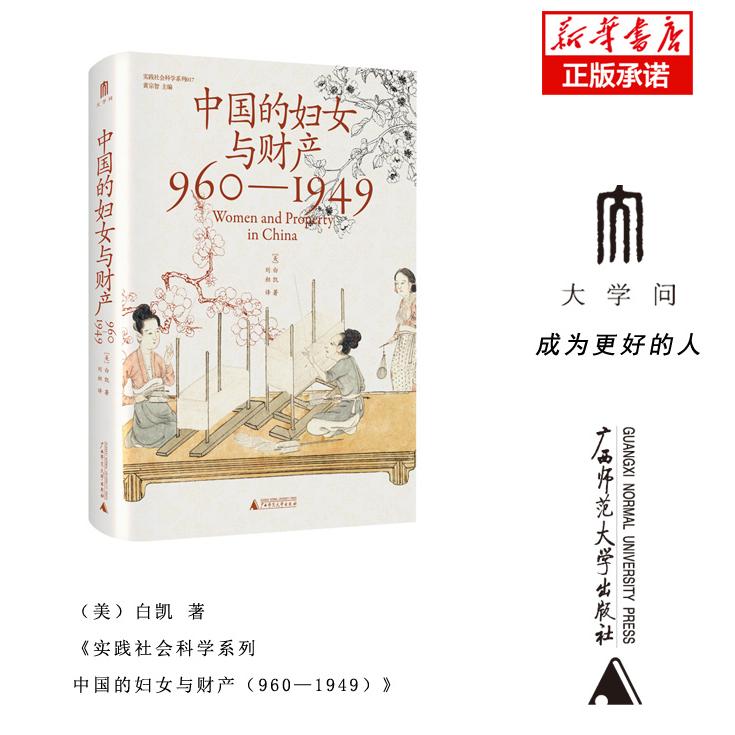
白凯,1952年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荣休)。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法律史及妇女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等。 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民国民法的实施使女儿获得了与儿子平等的继承权,这对城市中的有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富绅名流家庭中的财产官司随之兴起。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死亡时间对官司的判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说明传统法律与民国民法迥然相异。 ——编者按 女儿和法庭 女儿继承权的实施对都市地区的有产阶级产生了最大的冲击。确实,上海《申报》上登载的财产纠纷案读起来就像中华民国的名人录。涉入财产纠纷案的有晚清著名实业家、银行家盛宣怀(1916年有近1300万两银财产),李鸿章之子李经方(1934年有800万元财产),无锡丝绸商孙询刍(1930年有50万元财产),上海印染业巨擘薛宝润(1931年有财产300万元),英美烟公司买办蔡福林,华成烟公司创办人戴耕莘,垄断着租界粪便收集的“粪大王”马福祺(1935年有财产400万元)。 这些富绅名流的家庭官司自然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但从报章和法庭案件中我们看到,城市里中产家庭的女儿们也利用法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1930年,上海的三个未婚女儿状告她们的兄弟和两个入赘的姐夫,要求各得三幢房子和3.4亩地家产的六分之一。(《申报》,1930.6.15)北平的一位已婚妇女上告其娘家,要求得到其父亲财产(包括六间、四间的住宅各一幢,一家有十数辆黄包车的公司,十来头猪,衣物和家具,共值20 000元)的五分之一。(北京地方法院:1942-2510,1942-5705) 可以想象,除了这些大都市,新法律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在报章上或法庭记录中看到小城镇或乡村的女儿们为财产继承打官司。总的来说,在所有各方面,民国民法和其所奉行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乡村,人们对新法律的认知有限,而新法庭又常常路途颇远,交通不便,且乡村妇女更受蒙蔽,对变化的反应更为迟钝。所有这些,加上财产诉讼是民国时期最昂贵的诉讼,使得继承问题成为大多数小城镇和乡村妇女经验之外的事物。 新法律在1928年因为上海两个未婚姐妹提出诉讼而受到最早的检验。这个案件受到全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是这类案件的第一个,而且因为两姐妹是盛宣怀的女儿。(该案后来被编成一出戏剧,名为《小姐争产》,在上海上演。《申报》,1929.1.7)盛宣怀死于1916年,留下价值12 956 000两白银的家产,这在当时相当于1000万美元(许涤新、吴承明编,1990:851)。他的妻子庄氏死于1927年,留下60万至300万元(具体数字有争议)。在1930年初,盛庄遗产成为不少于七次法律诉讼的目标。所有的诉讼都是因女性继承权的法律变化而引起的。其中两件是关于未婚女儿的,一件是关于已婚女儿的,另外两件是关于已婚孙女的,剩下两件是关于外孙儿女的。盛家无休无止的官司为他们在上海的《申报》上赢得了“全沪健讼之魁”的“雅号”(《申报》,1933.5.28)。 在未婚女儿的官司中,财产标的是1927年解体后的愚斋义庄的资本。盛宣怀在1916年去世前命令将他的财产在适当安排了他寡妻的扶养和他女儿的嫁妆后,分为两份,一份在其五个儿子间均分,另一份则用来建立愚斋义庄。他死后,其妻和子谨遵他的遗命,他给寡妻和女儿留下了价值135 000两银的财产,五个儿子共得5 803 000两,余下的5 803 000两建立了义庄。(《女子继承权详解》,无出版年代:57—61) 1927年,江苏国民革命政府在反土豪劣绅的运动中,命令盛家把义庄财产的40%充作军需。盛家兄弟照办了,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解散了义庄。1928年初,他们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允许,将60%的义庄资本,共3 500 000两银,收归己有,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申报》,1928.6.22,另见1929.8.29,1933.5.28) 该年夏,两个未婚女儿之一盛爱颐在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对她三个健在的兄弟和两个侄子,即两个已死兄弟的儿子提起诉讼,要求从收回的义庄财产中得到她的一份。《申报》称盛爱颐为一个热心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的积极信徒,同时也是宋氏姐妹的密友。她在诉状中争论说她的兄弟、侄子违背了国民党1926年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和新近最高法院关于妇女财产继承权的解释。根据现行法律,她和她的未婚妹妹——盛方颐,有权各得到一份与五个兄弟、侄子一样多的财产。(《申报》,1928.8.29,1928.9.6) 案情的发展牵扯出了义庄财产法律所有权的问题。盛家兄弟和侄子声称这是他们的共同财产。作为盛宣怀的法定继承人,他们在1916年盛死时,不仅继承了他的另一半遗产,也共同继承了义庄。因此在1928年初,当他们分配义庄剩下的60%财产时,他们只是在分配早就属于他们的财产。因为在1916年未婚女儿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所以盛爱颐对义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正像她对父亲的其他遗产没有权利一样。(《申报》,1928.9.6) 临时法院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法庭认为盛氏兄弟不是义庄的共同所有者。盛宣怀临死前给家里的口头遗命明确指示将他财产的一半划出,不在继承之列,用以建立义庄。义庄自从建立,就成为一个财团法人,义庄财产归这个财团法人所有,而非被告所有。后来只是因为特别的行政决定允许解散义庄,被告才可能对义庄财产提出要求。但是这个行政决定只说将义庄财产归还盛家,而没有说这财产如何分割。这将由法庭根据现行法律来决定。根据现行法律,盛爱颐同她的兄弟和侄子拥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临时法院在1928年9月下旬判决盛爱颐应得义庄财产的七分之一,计500 000两银。(《女子继承权详解》,无出版年代:57—61;《申报》,1928.9.21) 在此判决后的几周内,盛方颐效仿其姐姐,也在临时法院对其兄弟、侄子提出了诉讼。她也打赢了她的官司,得到义庄财产的七分之一。(《申报》,1928.10.18,1928.11.9)1928年12月的上诉法院和1929年12月南京的最高法院维持了临时法院的原判(《申报》,1928.12.9,1929.12.18;《女子继承权详解》,无出版年代:57—61;China Law Review,4.5[1930]:176—180)。对这两个法院来说,和上海临时法院一样,盛家的诉讼是关于未婚女儿继承权的第一个案例。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盛家女儿诉讼的成功只是因为盛宣怀对他的财产做出了特别的安排。不然的话,她们对这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因为盛本人死于1916年,是在司法行政委员会做出女儿继承权的命令之前(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命令是逐步在国民党攻克的省份中实施的)。这一日期分界的结果是把一大批女儿放到旧的继承法律之下,我们将在下面对此做充分的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时效问题常常使女儿们在法庭上的斗争受挫。比如在山东的第一个这类诉讼中,济南的25岁未婚女子、国民党的积极分子钱瑞智,在同其哥哥的诉讼中失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死于1926年春,是国民政府攻克山东(1928年5月)的前两年。1927年,钱瑞智中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业,进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学习。1928年,她随国民军北伐,任河北省党部训会主任。1933年,据报道,她仍对自己的诉讼失败十分沮丧,并因亲密男友的新近逝世非常悲伤,在烟台投海自尽。(《申报》,1929.9.21,1929.10.18;《时报》,1933.9.25)其他的女儿们也因这不幸的时间问题而输掉了官司(例见北京地方法院:65-5-1660-1668;《申报》,1929.12.20,1930.4.11)。 更为幸运的是富有的上海银行买办步吉臣的女儿。步死于1927年末,在江苏省归入国民党统治之后,他留下了价值10万元的财产和一妾四子,还有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宝玉、满玉和生玉(报章报道称之为“三玉”)。步吉臣死后不久,四兄弟分掉了家产。在1929年末1930年初(具体时间不确),步家“三玉”要求按照新颁的《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来重分家产。1930年6月,她们在法公堂的一个判决中击败了她们的兄弟,每人将得到她们应得之份额,即家产的七分之一。(《申报》,1930.3.30,1930.7.18)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个成功的案例。上海的郁蒋氏在1929年末经法庭判决击败了她的兄弟,赢得她母亲(死于当年9月)财产的一半(价值17 600元)。(《申报》,1929.11.2)北平的李王友莲在1940年经法庭判决击败她的兄弟,赢得她父亲财产的四分之一,她父亲的财产共计有五爿商店、七处房产、105亩土地、价值21 500元的股票、88 000元现金及珠宝古董。(北京地方法院:1947-227)高梁毓秀于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在两个不同的诉讼案中击败她的后母和四个同父异母兄弟,得到她死去父亲(死于1937年)在北平的财产(十处共152间半房产)的六分之一,和在他老家通县的财产(一幢11间房的房子、一爿商店和47亩地)的六分之一。(北京地方法院,65-5-763-768,1942-3279) 另外一些例子不是通过法庭判决,而是通过调解来结束争执的,它们或是通过法官在法庭上调解,或是在庭外通过律师或亲友调停。虽然在民事诉讼中,调解的愿望总是存在的,但在财产案件中调解的动机特别强烈,因为这类案件的诉讼费用实在很高。通过调解,争执双方不仅可以避免日益高涨的律师费,也可以避开成为败诉者而承担所有诉讼费用的风险。 因此,1932年上海的方徐梅英通过庭外和解,从她的哥哥那里得到她死去父亲的约10 000 000元财产中的520 000元。(《申报》,1931.12.16,1932.5.1,1932.5.13)同是在上海,1930年代中茶商朱葆元的三个女儿,每人从她们的两个兄弟那里得到80 000元她们父亲的财产。(《申报》,1936.3.26)1942年,北平的已婚妇女赵陈淑珍对她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的诉讼通过法庭调解,使她得到她父亲财产的六分之一。(北京地方法院:1942-3271,1942-3747)在另一个发生在北平的法庭调解案中,已 编辑推荐1 以往研究对中国家庭中的财产权利多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女性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中国家庭的财产通常由男性子嗣继承;二是由此出发,以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历代财产继承权并无变化。白凯老师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从女性视角切入,通过研究大量案例,说明女儿的财产权利体现为继承权,而妻子或妾的权利体现为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宗祧继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围绕这一论题,书中做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如宋代女儿的财产继承权源自国家财政对绝户财产的需要、贞节崇拜对明清强制侄子继嗣法律的冲击、民国时期对妾这一身份的否定导致该群体的分流,等等。该书虽然篇幅简短,但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作者用语之简洁明快,逻辑之清晰流畅,学术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书中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作者将案件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使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情形跃然纸上。许多案件经历了多次上诉,特别是在法律变革时期,各级司法机构甚至有可能给出截然相反的判决。作者对其一一解读,展示了看似简单的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司法活动中产生的判例又受到何种社会观念的影响,如何对既定的法律条文形成修订或补充。清末至民国时期,法律观念与社会惯行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发源于西方的财产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现实不相匹配,有的群体从中获益,有的群体则显得无所适从。本书长时段的考察,使我们直观地看到传统法律与近代法律巨大的逻辑差异,从而得以体会新旧交替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 编辑推荐2 说到财产继承,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然而,在数千年历史中,男性与女性在财产继承中一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谈到古代社会,恐怕有许多人会认为那时的女性与财产继承无关。其实,女性的财产权利走到今天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经历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所需的远不只是法律的改变。而近千年来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过程,在白凯老师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民国时期是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在法律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强烈的新旧对比。许多女性因为新民法获得了属于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利,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城市中急剧增加的财产诉讼。例如,晚清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遗产便带来了旷日持久的争执,盛家人前前后后打了至少七场官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两个未婚女儿盛爱颐、盛方颐相继提起的诉讼,这在当时广受关注,后来甚至被编成了一出名为《小姐争产》的戏剧。在本书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儿对家产提出的诉讼,只要符合新民法的时限要求,基本都能胜诉。 但法律的转型还隐藏着更深的冲突:同居共财的社会与财产归个人所有的法律观念简直可说毫不相容,民国女性在财产继承中的劣势基本由此而来。由于财产属于个人,寡妻在与子女分别继承财产后,不再有权置喙属于子女的财产,而从前她们对家庭中的所有财产都拥有监护权;寡媳也不能在分家时获得财产,因为她的丈夫死时尚未得到任何财产,而她也不是自己公公的法定继承人。法律逻辑的转变让来自传统社会的妇女群体显得无所适从,这便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在此之后,社会中的妇女群体被重塑,守贞寡妇、妾等群体逐渐消失,现实与法律适配,男女的财产权利方才达致真正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