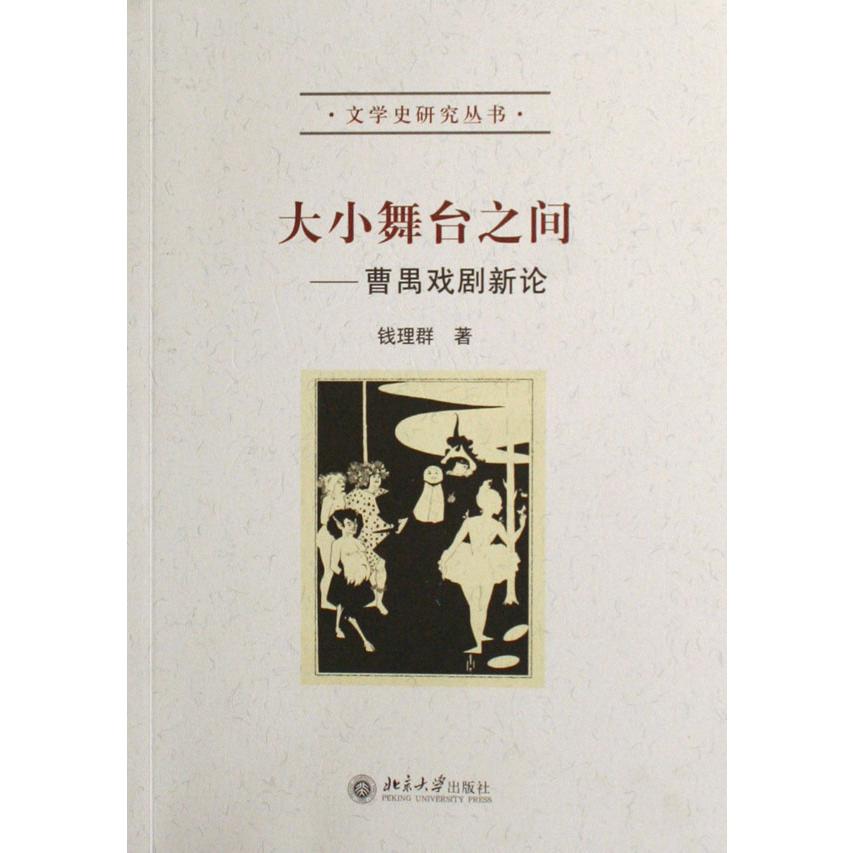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8.00
折扣购买: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14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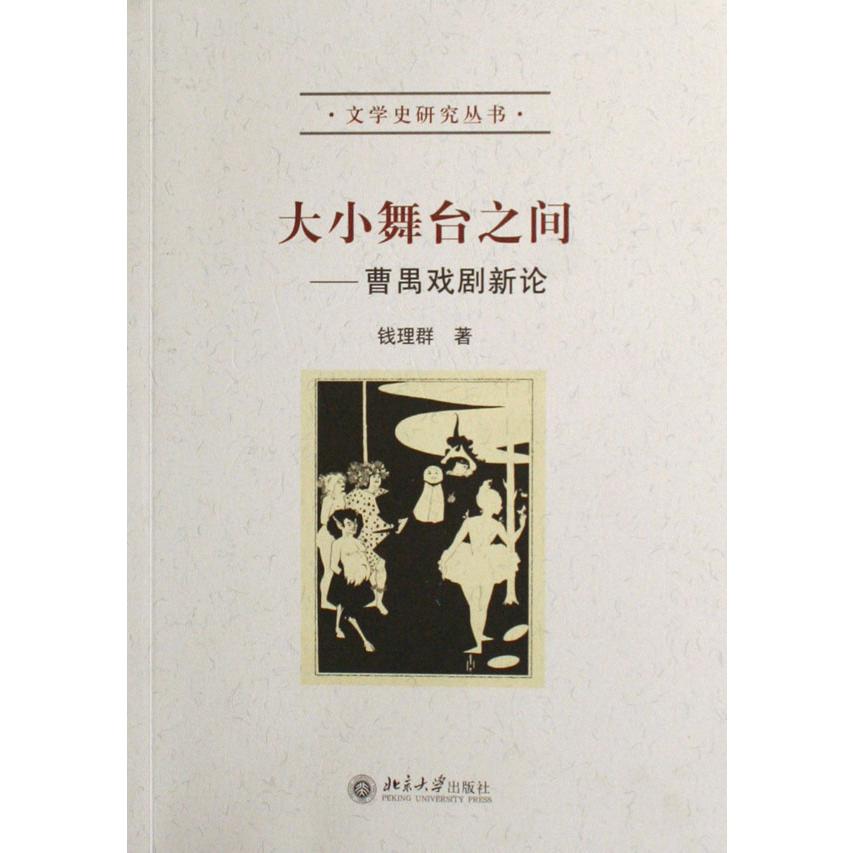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传承五四真精神,本着“接着鲁迅往下讲”的觉识,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致青年朋友》、《活着的理由》等等。主编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1933年的酷暑.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三年级学 生曹禺,坐在校图书馆杂志室一个固定位置上,沉浸在《雷雨》的 生命创造里,竟觉不出夏风的吹拂,窗外蝉声的聒噪…… 这时的曹禺,还没有涉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长 河——他毋宁说是一个站在岸边跃跃欲试的选手;他根本不知 道戏剧界圈内的消息,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正在发生 什么,更没有想到,那一切,会和他自己发生怎样复杂而微妙的 关系…… 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切都成为历史以后,人们才注意到 的事实—— 1927年11月,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化” 的剧团》的文章,作者是焦菊隐。文章一开头即高瞻远瞩地提 出了要“重新创造”“能适合现代化的人们的要求”的新的戏剧的 战略目标,宣布“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在创成新的戏剧的职业,以 替代旧剧的职业,使观众阶级把原始的美的观念从旧的移到新 的戏剧上来”。在焦菊隐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先要渐渐地培 养观众的嗜好,就需要不时地拿极精采的戏剧演给他们看”,这 里的关键是实现戏剧的职业化。焦菊隐回顾了中国现代话剧 (即所谓新剧)发展的历史: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从业余转向 职业化的第一个尝试,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过 历史的贡献,却因为本身的弊病而逐渐走向反面,成为“戏剧创 造运动一个大的阻碍”;于是有了五四时期民众戏剧社关于“爱 美的戏剧”即业余演出的提倡,对纠正文明戏过分商业化的倾 向、提高现代话剧艺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但其纯爱美的倾向, 终于流为大弊,导致话剧运动的无形消散;在此以后出现的人艺 戏剧专门学校(其前身即为与民众戏剧社齐名的中华戏剧协社) 和艺专戏剧系,即已认识到“毕竟戏剧界的主力军还是要职业的 而不是爱美的”,他们的演出,“已经富有职业化的色彩”。焦菊隐 呼吁,要将建立职业化的剧团的努力更加自觉化——这将是中国 话剧运动第二次由业余向职业化的历史转折。文章结尾,焦菊隐 谈到了曾经议论过的建立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以为“仿佛有些 痴人说梦”…… 两年以后,即1929年11月,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欧阳 予倩在《戏剧》杂志上发表了《戏剧运动之今后》一文,再一次 明确提出了“爱美剧团往往不能持久”,戏剧发展必须走职业化 的道路。欧阳予倩并且规划了实现职业化的具体蓝图,强调必 须抓好鼓励创作,促进戏剧文学的发展;训练舞台艺术家,培养 自由的职业的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建设专业的剧场;发 展健全的剧评等基本环节。欧阳予倩在文章结尾,满怀信心地 指出,微风起于青蓣之末,戏剧职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最近的 将来,就可以证明大家的努力绝对不是空虚的”。 欧阳予倩当然不知道,就在他作出这样的预言的时候,当时 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十九岁的曹禺正在开始酝酿创造《雷 雨》;而正是《雷雨》成为四年后终于出现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 团的起家戏,从而真正奠定了中国话剧职业化,使话剧从广场艺 术成为剧场艺术的基础。 前述焦菊隐的文章发表二十五年后,被焦菊隐视为“痴人说 梦”的计划竟然变为现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而担任 正、副院长的恰是曹禺与焦菊隐,他们的合作,创造了中国话剧 剧场艺术的典范…… 这一切,都是当事人所未曾料及,既偶然,又非偶然。 1930年,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另一位重要组织者、五四时期 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的田汉,在《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上 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的长文,宣布:“要建设新的艺术,还非 得经过一次无情的‘扫除作用’不可”,“我们在扫除虚伪的反动 的艺术以前,先得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来,……在批判别种 人、别种艺术运动以前,先可能的严肃的做‘自己批评’。”——这 就是在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田汉及其南国社的革 命性转变。据田汉在“自我批判”中所说,南国时期他“对于社会 运动与艺术运动持两元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 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 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情调,“表示(着)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 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和这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底 渐趋明确的反抗”。南国社的具有特殊的风格的演出,自然在观 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以陶醉的要求来接近我们的戏剧 以外”,也有尖锐的批评与拒绝。而后者尤其引起田汉和他的同 人们的震惊与反省。田汉在文章中引述的如下来自普通观众的 批评,确实很有意思。一位署名“一小兵”的南京观众这样写道: 最后的《苏州夜话》,剧情是诅咒战争与贫穷。这种乞 怜声气,你们或许以为可以讨得那班吸血鬼似的军阀们的 同情罢。他们会要发慈悲心,放松那抽紧的索子罢。先生! 伟大的先生!你的作品是多么背着时代的要求啊。……我 所倾慕的先生,莫要自命清高,温柔,优美,我们被饥寒所迫 的大众等着你们更粗野更壮烈的艺术!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