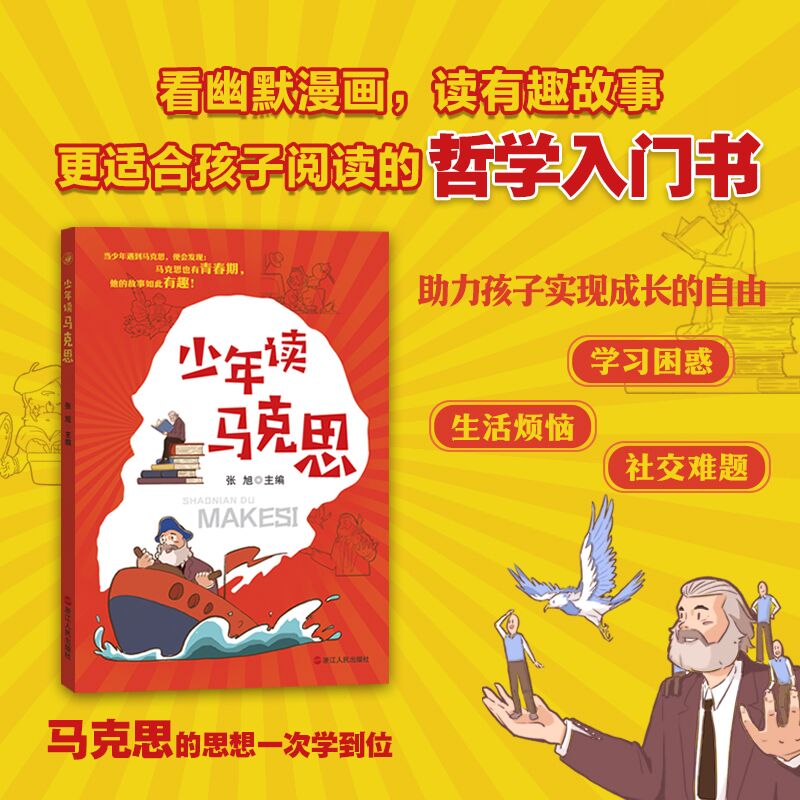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18.70
折扣购买: 少年读马克思
ISBN: 9787213114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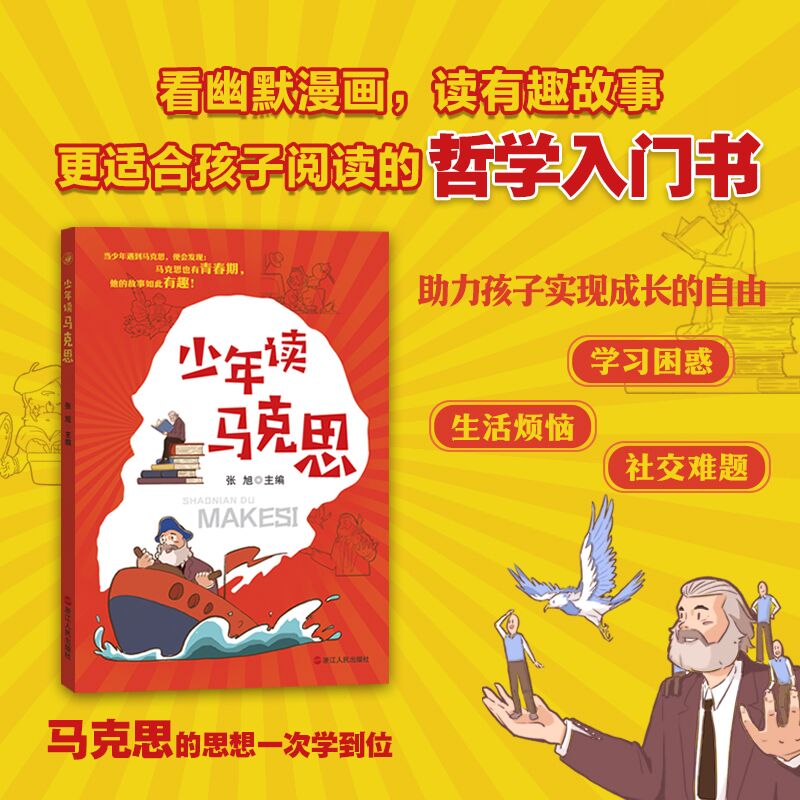
张旭,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等。
马克思喜欢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阅读他们的作品,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艺术享受,还看到了这些诗人的共同之处:对生活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息,即对“真正人类本质的理想生活”的不断探索。 他们的作品揭示和反映了所谓“合理关系”的本质,帮助马克思认识到人类苦难的存在:人类是会思考的,而会思考的人类正在受着压迫。 一身浪漫主义气质的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艺术之路,因为他认识到“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日渐成熟的马克思对“纯粹的艺术形式”兴致索然,他所理解的幸福生活是无法依靠艺术去实现的。他在17岁时写下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清晰地阐述过自己的幸福观: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的幸福就是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而斗争。 “诗人马克思被思想家马克思制服了”,苏联学者瓦·奇金这样概括马克思的转变。马克思把幸福观和斗争这个概念结合了起来,这是马克思的自然天赋,他就像革命斗争领域的莎士比亚。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到波恩大学读书,后转入柏林大学。由于当时柏林大学的学术氛围保守,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并且马上就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以后,马克思原本打算到波恩大学当教授,但因为他追求学术自由的倾向而未能如愿。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声名在外。在等待他前往波恩大学任教时,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莫泽斯·赫斯这样向朋友们介绍马克思:“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最终,马克思去了科伦,成为《莱茵报》的灵魂人物。由于他的渊博、深刻和雄辩,他的对手把他称为“凶恶的刀笔奇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领略到这位刀笔奇才的“凶恶”。 新检查令要求人们在探讨真理时必须严肃和谦逊。马克思批驳说,所谓严肃就是不允许人们用自己的风格去写作,但“风格如其人”;所谓谦逊就是不许人们探讨、发现和阐明真理,因为“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 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人民大众 青年马克思无疑是雄辩滔滔的,但迫于普鲁士政权的压力,他最终离开了《莱茵报》,离开了普鲁士,去了巴黎。 在《莱茵报》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后,他就已经感觉到深深的困惑。穷人连捡拾枯枝生火取暖都会被判入狱,虽然学者们从法律和哲学上就能把这样的暴政批驳得体无完肤,但什么也改变不了。青年黑格尔派甚至连谩骂都用尽了,但也无济于事,最终只能各自散去,做会计的做会计,当律师的当律师。 马克思并没有消沉,他知道自己需要新的认识论,也就是新的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向。 马克思很快就把握住了他所期待的新的认识论方向,在巴黎再次建立起新的阵地。 1842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目睹了资本主义大生产高度发展的状况和后果后,认识到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仅靠抽象理论和人道主义批判远远不够,必须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入手,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动规律。 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在文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恶化,这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 作为该刊物主编之一的马克思盛赞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他认识到,只有用政治经济学这把“手术刀”,才能“剖腹”取出资本这个“难产儿”。 思想上的战斗还在继续,许多重要的原理正从这些战斗中不断产生。1844年,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通过对主观意志至上的思辨哲学的批判,他们证明社会生活和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剖析,他们提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他们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一些曾经的进步理论家对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抱有深深的蔑视,比如布鲁诺·鲍威尔就非常鄙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贱民”,永远也干不出什么名堂。而马克思与苦难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始终未变,哪怕他们实际上表现出严重的愚昧,马克思也会将其过去与未来放到更宏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去考虑。 犹太人逃出埃及时,一部分人在途中畏惧艰难和饥饿,便怀念起做奴隶的日子来,因为至少那时可以吃饱肚子。现实中,被解放的法国农奴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反对他的解放者,马克思尖锐地警醒人们,不要迷恋“埃及的肉锅”。 《德法年鉴》的另一位主编阿尔诺德·卢格在创刊号上的一篇通讯中写道:“德国是由一些卑鄙顺从的庸众组成的,他们以绵羊般的克制忍受着暴政,因此,不应该幻想着德国会发生革命。”而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 即将来临的革命。” 能够从同一个事实出发得出截然相反而又正确的结论,这就是认识论的力量。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他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马克思不认同那些躲在书斋里凭空思想的学者。他在有关黑格尔的讽刺短诗中写道:“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 马克思对轻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的学者也总是毫不留情地批判和讽刺。比如在给次女劳拉的信中,他讲了一个“哲学家渡河”的故事。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 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思想武器 1849年,马克思流亡英国。1850年,他拿到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 伦敦成为他的最后栖宿地,他将在这里发明一种威力巨大的理论武器。这种武器将掌握群众,并将其转化为摧毁私有制的物质力量。 因为这一理论武器的发明,马克思成为一位真正的“千年思想家”,此后一直被奉为“天才”。但通俗尊称的背后,是他对社会的深刻领悟,而深刻的领悟则源于他超凡的努力。 后世一直流传着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地板上踏出脚印的故事,虽然是民间演绎,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治学的勤奋。 马克思的房间里杂乱堆放着各种图书资料,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整齐对他而言是一种混乱。他可以在无序中指挥着一大堆书籍一起工作:它们是我的奴隶,应当服从我的意志,供我使用。 白天在博物馆看书,夜里则在家动笔写作,马克思经常累得头昏目眩、胸部发闷,有时觉得实在难受,不得不合上有趣的书,走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思想家的严谨让人惊叹,即便为了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会专门去一趟大英博物馆。据恩格斯回忆,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时,仅仅为了弄清俄国的统计学知识,他查阅的书籍就足有两立方米多。 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者都涉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证了许多名气不大的作家的观点,他们也借此为后世所知。 从古希腊神话和抒情诗到农艺学和数学公式,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无不引起他的寻根问底。在晚年,为了深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完成《资本论》后几卷的撰写,马克思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科学技术和数学上。 真正能让马克思无比愉快的事情是收到恩格斯的来信。这位为了共同的事业能在经济上得以维持而不得不去从事最讨厌的企业管理工作的战友,总能给他提供实践领域的感性材料,帮助他思考。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回忆说:“有时摩尔(马克思在家里的外号)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流出眼泪来。” 马克思嗜烟,在他写作的时候,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名普鲁士警探在一份1850年的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马克思的家: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腾腾的烟雾刺得你双眼泪水直流,以至使你一时感到仿佛在洞穴中摸索徘徊。但到了晚年,为了健康考虑,马克思又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吸烟的习惯。 《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他才有时间给朋友们回信,他在给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回信中说,“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 与这样的刻苦相伴的是清贫到衣食无着的生活。马克思40岁生日来临之前的寒冬,冰冷的屋子里没有煤块取暖,餐桌上空无一物,妻子仅有的一条披肩被送进了当铺。因为房东的催租和各种店铺里的赊欠,他们一家人还常常被赶出门去。 “我扛了半个世纪的长活,结果还是一个穷光蛋。”1858年,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定稿之时,马克思通知恩格斯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费和保险金”。这一次又是恩格斯帮了忙,手稿不久后就寄到了柏林,并在那里出版。 这份“倒霉的手稿”告诉世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越临近《资本论》诞生的时刻,马克思就越清楚,他将把拥有强大威力的武器交给无产阶级。“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1867年4月的一个早晨,马克思上了一艘小客轮,离开伦敦港,为的是把这个武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送到欧洲大陆去。 《资本论》第一版,勉强才印了1000册,“甚至将不够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钱”。尽管马克思偶尔会发出这样令人凄然的感叹,但这个怀疑和否定一切的思想者从未怀疑过自己工作的意义。 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工作中安详地离世,“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里,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倾力打造,内容专业权威; 幽默插画,有趣故事,精巧32开本,让孩子爱不释手; 马克思的思想一次学到位,奠定孩子成长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