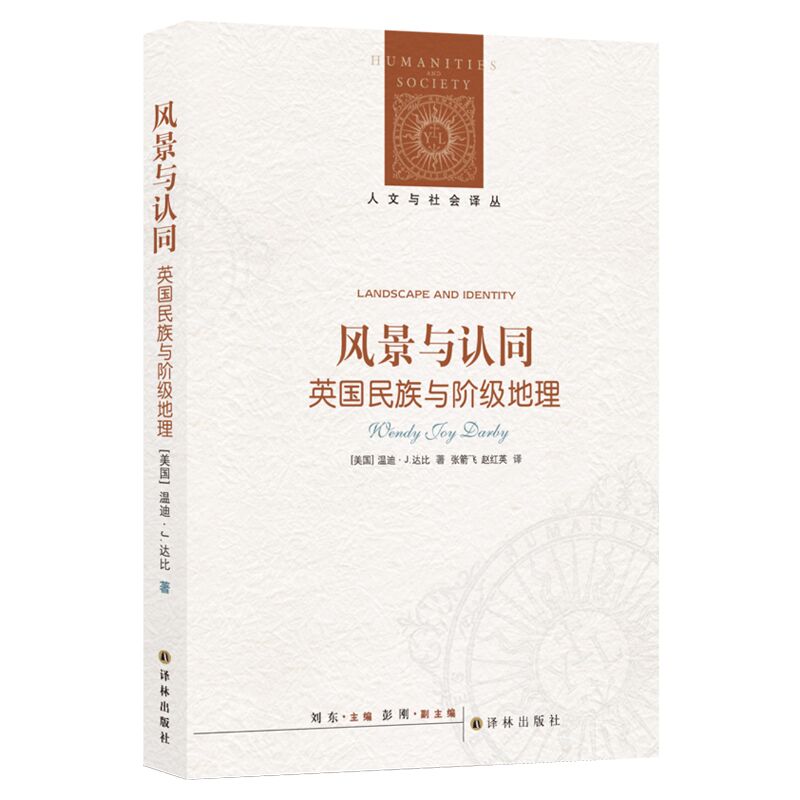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70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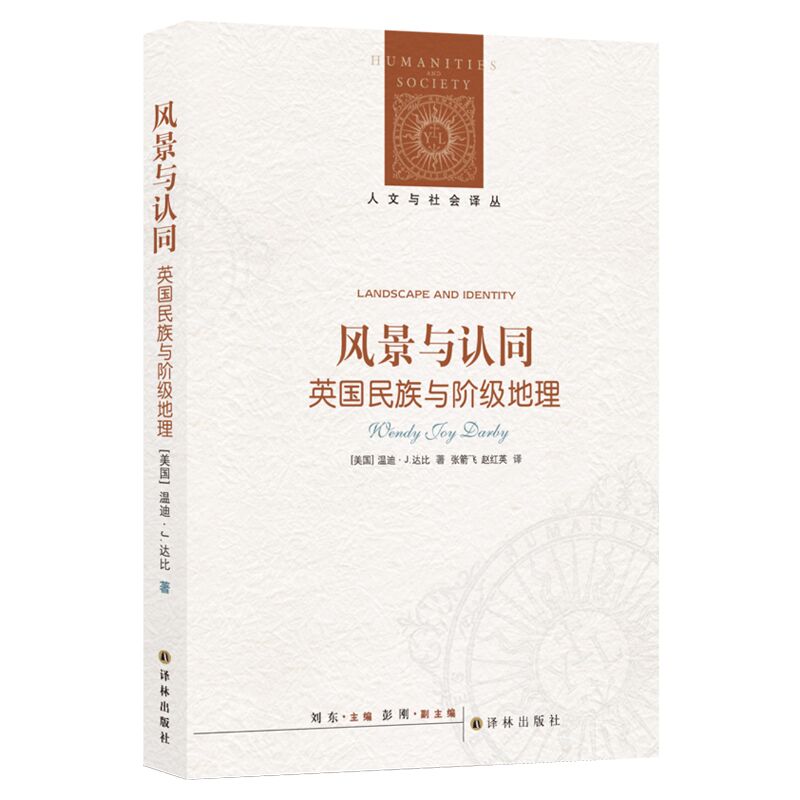
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博士,耶鲁大学土地研究项目博士后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的历史遗产保护硕士。达比获得过富布赖特基金、欧洲研究委员会、温纳一格伦基金会、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等的资助,出版过论述美国风景的著作,近期作品还论述了风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集体记忆。
导 论 展望/ 再想象风景 当教育科目日益增加,给已经负重的学生再增设一门新学科乍看上去似乎太强人所难。然而,你会发现人类学的真正作用是减轻而非加重学习压力。在山区,我们看见负重者欣然地多扛着一个载物架,因为架子可以收纳负载,平衡负重,便于搬运。两者相权,载物架的重量就不算什么了。“人类与文明”的科学也是如此,该学科把普通教育中那些松散的科目整合为一个易于掌握的体系。(泰勒 1891:V) 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这是人类学中很少涉猎的话题,即使这类活动在西欧、亚洲和美国等富裕国家许多个人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风景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赫斯科 1995)。 本章将要探讨的话题有:休闲与排斥如何相互关联,构成以阶级、年龄、性别或种族为基础的社会与地理的现实?英格兰的国家公园代表的是五十年的排斥还是包容?大风景区正在保存谁的观念,又为谁而保存?自由漫游运动(freedom-to-roam )再次兴起,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和历史学方面,面对它们,我需要采取跨学科的方式来探索历史上的阶级关系,追踪作为文化产物的阶级与民族身份透过风景及其进入权发挥作用的种种步骤。以英格兰西北部高地的湖区(Lake District)与峰区(Peak District)的风景为例,我分析了进入风景区问题的政治性。我把相当广阔的历史演进和地区特性结合起来 研究问题,这一工作对于正在庄严进行中的恢复人类学与历史的学科邦交是一种促进(科恩[1980,1981] 1987;贾哈 1987,米切尔 1997),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角,研究风景跳出了地理学和图像学的范畴(格林 1995)。 尾注作为附文贯穿全书。我认为尾注具有支撑全文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神圣见于细节,见于脚注”(查德威克 1997:16)。一个已经被人视为自然而然的、有必要在此点明的细节(从尾注中也能发现)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风景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派的资助人或是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是拥有土地并管理国家的男人的附属物一样。 安妮?华莱士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徒步游览风景在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位。然而,她的观察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性别区分的特征: 徒步者置身于农夫放弃的思维空间,以此达到维吉尔式的田园诗境界。这一结果,我称之为“逍遥游”(peripatetic)。所谓逍遥游,就是漫无目的的云游,是一种陶冶心志的劳作,能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改造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华莱士 1993:8,11) 本研究越过博雅之士的文学体系,从更单纯的行走视角展现华莱士所说的19导 论 展望/ 再想象风景 当教育科目日益增加,给已经负重的学生再增设一门新学科乍看上去似乎太强人所难。然而,你会发现人类学的真正作用是减轻而非加重学习压力。在山区,我们看见负重者欣然地多扛着一个载物架,因为架子可以收纳负载,平衡负重,便于搬运。两者相权,载物架的重量就不算什么了。“人类与文明”的科学也是如此,该学科把普通教育中那些松散的科目整合为一个易于掌握的体系。(泰勒 1891:V) 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这是人类学中很少涉猎的话题,即使这类活动在西欧、亚洲和美国等富裕国家许多个人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风景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赫斯科 1995)。 本章将要探讨的话题有:休闲与排斥如何相互关联,构成以阶级、年龄、性别或种族为基础的社会与地理的现实?英格兰的国家公园代表的是五十年的排斥还是包容?大风景区正在保存谁的观念,又为谁而保存?自由漫游运动(freedom-to-roam )再次兴起,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和历史学方面,面对它们,我需要采取跨学科的方式来探索历史上的阶级关系,追踪作为文化产物的阶级与民族身份透过风景及其进入权发挥作用的种种步骤。以英格兰西北部高地的湖区(Lake District)与峰区(Peak District)的风景为例,我分析了进入风景区问题的政治性。我把相当广阔的历史演进和地区特性结合起来 研究问题,这一工作对于正在庄严进行中的恢复人类学与历史的学科邦交是一种促进(科恩[1980,1981] 1987;贾哈 1987,米切尔 1997),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角,研究风景跳出了地理学和图像学的范畴(格林 1995)。 尾注作为附文贯穿全书。我认为尾注具有支撑全文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神圣见于细节,见于脚注”(查德威克 1997:16)。一个已经被人视为自然而然的、有必要在此点明的细节(从尾注中也能发现)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风景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派的资助人或是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是拥有土地并管理国家的男人的附属物一样。 安妮?华莱士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徒步游览风景在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位。然而,她的观察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性别区分的特征: 徒步者置身于农夫放弃的思维空间,以此达到维吉尔式的田园诗境界。这一结果,我称之为“逍遥游”(peripatetic)。所谓逍遥游,就是漫无目的的云游,是一种陶冶心志的劳作,能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改造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华莱士 1993:8,11) 本研究越过博雅之士的文学体系,从更单纯的行走视角展现华莱士所说的19世纪的逍遥游,并引入性别问题加以讨论。它描述了早期的文化精英如何利用描述性文本和圈地来占有风景,以及那些曾经被赶出风景区外的人如何通过自由漫游运动来收复失去的风景。 本研究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3章)通过追溯风景(作为将文化物质化的一个用语)的文学和艺术的根源,来探析关于民族的美学意义话语。研究集中在18世纪英国文化精英以图绘的、印刷的和实际的无人风景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将这一现象置于英国民族主义的表述与实践、如画风景盛行的语境下来考量。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基点,我把研究推向一系列“文雅社会”内的紧张关系,以及文雅社会与圈地运动的受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部分的重中之重放在湖区的文化赋值(cultural valorization)上,也即湖区从空旷之地变为文化恒产的过程。我探讨神话记忆如何替代了真实的记忆,并指出神话的创造者都是外来者。早在湖区成为人们的神往之地之前,那里不过是那些生于斯死于斯的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的“地方”。从巨石与石头点缀其间的山谷被清理成整洁的农田、石头围砌的地界等景象,可以推断他们如何向土地讨生活并与土地休戚与共。这一点,从当地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依山而筑、纵横交错的石墙亦能看出。 与这些实物地方标记呼应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命名。远在19世纪测量局成立之前,各处的峭壁、岩石、峡谷、通道、小径、小溪、瀑布、小湖、沼泽、碎石坡路、山脊和山腰已有名称。当地人的劳作形塑了空间外观,并且加以命名,是双重地赋予它们意义,两者合力早在这一带成为“湖区”之前确定了它作为一个地方而存在。 第二部分(4—6章)继续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为拓宽话题,我引入了峰区的案例,因为在峰区,进入风景牵涉到的阶级问题更要尖锐。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这是一个反讽性的转变。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于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 进入峰区风景区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偷猎行为,而湖区则以美学为重点,其差异的关键在于植被。峰区沼泽地的石南(Callunusvulgaris)是红松鸡(Lagopus lagopus scotius)最喜欢的栖息之地及主要食物来源。为了在狩猎季有松鸡可猎,文化精英们就想保护松鸡在高沼地的休养生息。这样做直接挑战了两类人,一类是想保持原有的穿越高沼地权利的当地人,一类是来自周边工业城市,希望在开阔的沼地自由漫游的徒步者。狩猎者视徒步者为完全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干扰了鸟巢里栖息的鸟,因为他们就是偷猎者。 由于石南并非湖区的主要植被,那里也就没有松鸡休养生息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美学方面的。自18世纪以来就具有文学和视觉意义的湖区风景,到了19世纪则面临着来自铁路和采矿业的持久危害。由于文化精英发起了反入侵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这些特别的风景区的保护问题,而且也触及到所有风景区的保护问题,特别是那些逃过议会批准的圈地劫夺的公用地。 从19世世纪的逍遥游,并引入性别问题加以讨论。它描述了早期的文化精英如何利用描述性文本和圈地来占有风景,以及那些曾经被赶出风景区外的人如何通过自由漫游运动来收复失去的风景。 本研究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3章)通过追溯风景(作为将文化物质化的一个用语)的文学和艺术的根源,来探析关于民族的美学意义话语。研究集中在18世纪英国文化精英以图绘的、印刷的和实际的无人风景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将这一现象置于英国民族主义的表述与实践、如画风景盛行的语境下来考量。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基点,我把研究推向一系列“文雅社会”内的紧张关系,以及文雅社会与圈地运动的受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部分的重中之重放在湖区的文化赋值(cultural valorization)上,也即湖区从空旷之地变为文化恒产的过程。我探讨神话记忆如何替代了真实的记忆,并指出神话的创造者都是外来者。早在湖区成为人们的神往之地之前,那里不过是那些生于斯死于斯的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的“地方”。从巨石与石头点缀其间的山谷被清理成整洁的农田、石头围砌的地界等景象,可以推断他们如何向土地讨生活并与土地休戚与共。这一点,从当地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依山而筑、纵横交错的石墙亦能看出。 与这些实物地方标记呼应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命名。远在19世纪测量局成立之前,各处的峭壁、岩石、峡谷、通道、小径、小溪、瀑布、小湖、沼泽、碎石坡路、山脊和山腰已有名称。当地人的劳作形塑了空间外观,并且加以命名,是双重地赋予它们意义,两者合力早在这一带成为“湖区”之前确定了它作为一个地方而存在。 第二部分(4—6章)继续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为拓宽话题,我引入了峰区的案例,因为在峰区,进入风景牵涉到的阶级问题更要尖锐。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这是一个反讽性的转变。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于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 进入峰区风景区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偷猎行为,而湖区则以美学为重点,其差异的关键在于植被。峰区沼泽地的石南(Callunusvulgaris)是红松鸡(Lagopus lagopus scotius)最喜欢的栖息之地及主要食物来源。为了在狩猎季有松鸡可猎,文化精英们就想保护松鸡在高沼地的休养生息。这样做直接挑战了两类人,一类是想保持原有的穿越高沼地权利的当地人,一类是来自周边工业城市,希望在开阔的沼地自由漫游的徒步者。狩猎者视徒步者为完全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干扰了鸟巢里栖息的鸟,因为他们就是偷猎者。 由于石南并非湖区的主要植被,那里也就没有松鸡休养生息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美学方面的。自18世纪以来就具有文学和视觉意义的湖区风景,到了19世纪则面临着来自铁路和采矿业的持久危害。由于文化精英发起了反入侵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这些特别的风景区的保护问题,而且也触及到所有风景区的保护问题,特别是那些逃过议会批准的圈地劫夺的公用地。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进入风景区方面合法的、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受到了立法的、法律的、超越法律的挑战。所有的斗争主要围绕峰区和湖区展开,并最终促成了1945年后的相关立法。据此,从1951年到195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地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这些公园有:湖区,峰区,达特穆尔,斯诺登尼亚(它们都在1951年列入规划);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1952);埃克斯穆尔,约克郡山谷(1954);诺桑伯兰(1956)及布雷肯山(Brecon Beacons,1957)。这10个公园占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9% 的面积。这一部分还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兴起的要求进入国家公园内和公园外地区的运动,以及环保术语如何用于空间争夺的行为。 第三部分(7—8章)话题转向人类学的层面,研究的依据来自对各类代表(如全国性徒步组织的代表)的访谈,以及与湖区、峰区和当地徒步俱乐部成员一起徒步的参与式观察。从“行走”人类学角度考证社会关系如何空间化及空间关系如何社会化的问题,深入探讨在社会分裂、全球经济重构和欧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力量,形塑着个人身份与共同体意识。 当探讨徒步者在一个高度层次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处都有阶级区分的标记,密集程度不逊于华兹华斯诗中烂漫山间的水仙)的文化性时,显而易见,主要问题在于徒步群体是否在建构新的感受空间时跨越了阶级差别。徒步所涉及到的性别意识也将纳入讨论。讨论兼及少数族裔的风景感知—他们是把英国风景当作非认同的风景来感知的。通过生活在该风景区的三位女性的观点,我深入分析了她们对于地方,特别是湖区的依恋。这三人的生活深受风景的影响。每个人的观点分别概括了本书的一个研究主题。 结论部分讨论了湖区的北部山地风景是否仍是关于英国的另一诠释或想象。位于英国东南部,以伦敦为中心的家乡郡,被英国文学塑造成精华地带,是“皇冠心脏”和“英国的腹地”,此说显然是误用转喻的例子,它以“南方”代表整个国家或地区(科斯格罗夫,罗斯科和尼克罗福特 1996;弗南德兹 1988;威内尔 1981;莱特 1985)。结论部分还剖析了在社会分裂及经济重建的影响之下,英国的某些地区更“英国”这种观念是否通过徒步活动得以实现的问题。 【译后记】 译后记 2004年,我和北大钱理群先生有过一次电话长谈。钱先生兴致勃勃介绍了他“认识脚下的土地”的构想和一些研究细节,并希望我能发挥自己的外语所长,引介一些理论文献。为先生的热情所感染,我满口答应。不曾料到的是:这次谈话把我这个偏安文学批评一隅的文体研究者引至一个更大的学术领域,从相对自闭的新批评分析模型转向更为开放的文化研究解释框架。 此前,我已经收到他的赠书《贵州读本》,对于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有了一个比较入微的了解。何谓“阅读脚下的土地”,钱先生引而不论,却为我后来的理论跟进预留了空间。当时,全球化话语的涡流席卷中外学界至少有十年之久。阿帕杜莱就宣称全球化是所有学院人士的焦虑之源。期间,相关议题、不同取向的研究势头猛烈,催化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学术谱系,产生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进入风景区方面合法的、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受到了立法的、法律的、超越法律的挑战。所有的斗争主要围绕峰区和湖区展开,并最终促成了1945年后的相关立法。据此,从1951年到195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地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这些公园有:湖区,峰区,达特穆尔,斯诺登尼亚(它们都在1951年列入规划);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1952);埃克斯穆尔,约克郡山谷(1954);诺桑伯兰(1956)及布雷肯山(Brecon Beacons,1957)。这10个公园占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9% 的面积。这一部分还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兴起的要求进入国家公园内和公园外地区的运动,以及环保术语如何用于空间争夺的行为。 第三部分(7—8章)话题转向人类学的层面,研究的依据来自对各类代表(如全国性徒步组织的代表)的访谈,以及与湖区、峰区和当地徒步俱乐部成员一起徒步的参与式观察。从“行走”人类学角度考证社会关系如何空间化及空间关系如何社会化的问题,深入探讨在社会分裂、全球经济重构和欧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力量,形塑着个人身份与共同体意识。 当探讨徒步者在一个高度层次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处都有阶级区分的标记,密集程度不逊于华兹华斯诗中烂漫山间的水仙)的文化性时,显而易见,主要问题在于徒步群体是否在建构新的感受空间时跨越了阶级差别。徒步所涉及到的性别意识也将纳入讨论。讨论兼及少数族裔的风景感知—他们是把英国风景当作非认同的风景来感知的。通过生活在该风景区的三位女性的观点,我深入分析了她们对于地方,特别是湖区的依恋。这三人的生活深受风景的影响。每个人的观点分别概括了本书的一个研究主题。 结论部分讨论了湖区的北部山地风景是否仍是关于英国的另一诠释或想象。位于英国东南部,以伦敦为中心的家乡郡,被英国文学塑造成精华地带,是“皇冠心脏”和“英国的腹地”,此说显然是误用转喻的例子,它以“南方”代表整个国家或地区(科斯格罗夫,罗斯科和尼克罗福特 1996;弗南德兹 1988;威内尔 1981;莱特 1985)。结论部分还剖析了在社会分裂及经济重建的影响之下,英国的某些地区更“英国”这种观念是否通过徒步活动得以实现的问题。 【译后记】 译后记 2004年,我和北大钱理群先生有过一次电话长谈。钱先生兴致勃勃介绍了他“认识脚下的土地”的构想和一些研究细节,并希望我能发挥自己的外语所长,引介一些理论文献。为先生的热情所感染,我满口答应。不曾料到的是:这次谈话把我这个偏安文学批评一隅的文体研究者引至一个更大的学术领域,从相对自闭的新批评分析模型转向更为开放的文化研究解释框架。 此前,我已经收到他的赠书《贵州读本》,对于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有了一个比较入微的了解。何谓“阅读脚下的土地”,钱先生引而不论,却为我后来的理论跟进预留了空间。当时,全球化话语的涡流席卷中外学界至少有十年之久。阿帕杜莱就宣称全球化是所有学院人士的焦虑之源。期间,相关议题、不同取向的研究势头猛烈,催化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学术谱系,产生很少的共识,却制造出更多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对于“土地”以及与土地一词联结在一起的概念,诸如“本土”、“地域”、“地方”的思考,则成为一种对立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与全球化话语形成参照。 部分受爱德华?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untrapuntal reading)的启发,部分受侯世达(Douglas R. Hoftstadter)写作方式的影响—他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Godel, Escher, Bach)一书中,尝试了一种他称之为不同寻常的结构:“在对话和章节之间有一种对位”—研究生讨论课上,我会引导学生细读一部理论原文经典,同时配备一部与其形成对立批评的著作进行对读,以期产生“思想对话,观念碰撞,势均力敌”的复调叙述的效果。所以,2004年春季,在《西方正典》 (Western Canon)的讨论课上,我为哈罗德?布鲁姆这本书选定了《贵州读本》。仅从二书的题目就可以想见它们的对称、对比乃至对峙的关系—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普世性/地方性;精英/草根……也许,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书写性文本/具象性土地。随着对读的深入,我和学生一起发现了许多微妙之处,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一个教学计划:“表面上在谈论一个想法,实际上以稍稍隐蔽的方式在谈论另一个想法”(侯世达语),但并未抵达我的目标:将钱先生“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一学术意识发展成一种连贯性和解释性的体系。 其实,丰富的理论资源已经存在,只等我们适度地挪用,创造性地借用。这就是方兴未艾的风景学(landscape studies)、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个业已壮大、貌似独立的学科,其实与决定性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走向的人文地理学颇多交错叠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乃至研究方法都源自人文地理学,又融入派系纷繁的文化研究之中。简言之,它们具有一切新兴学科的跨越性和模糊性;换言之,它们的疆界随着新的关注、方法或问题的介入而在不断移动。在为“阅读脚下的土地”寻找理论性支撑或解释性描述的过程中,我逐渐将范围锁定在与人文地理学瓜葛甚深、近乎同构的风景学上,试图以此为基点展开纵深搜索。之所以如此锁定,是因为在把“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个比较感性的表达切换到理论层面时,我注意到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Peirce F. Lewis)在其《阅读风景的原则》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一文中,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所有的人类风景,不管如何平常的风景,都有着文化意涵,因此,沃茨(M. Thielgaard Watts)认为我们‘可以阅读风景,正如我们能够阅读书本’。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究其知识谱系,这一原则应该是人文地理学泰斗杰克逊(J. B. Jackson, 1909—1996)观点的翻新:“一本丰富而美丽的书总是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必须学会阅读它。很少的共识,却制造出更多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对于“土地”以及与土地一词联结在一起的概念,诸如“本土”、“地域”、“地方”的思考,则成为一种对立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与全球化话语形成参照。 部分受爱德华?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untrapuntal reading)的启发,部分受侯世达(Douglas R. Hoftstadter)写作方式的影响—他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Godel, Escher, Bach)一书中,尝试了一种他称之为不同寻常的结构:“在对话和章节之间有一种对位”—研究生讨论课上,我会引导学生细读一部理论原文经典,同时配备一部与其形成对立批评的著作进行对读,以期产生“思想对话,观念碰撞,势均力敌”的复调叙述的效果。所以,2004年春季,在《西方正典》 (Western Canon)的讨论课上,我为哈罗德?布鲁姆这本书选定了《贵州读本》。仅从二书的题目就可以想见它们的对称、对比乃至对峙的关系—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普世性/地方性;精英/草根……也许,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书写性文本/具象性土地。随着对读的深入,我和学生一起发现了许多微妙之处,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一个教学计划:“表面上在谈论一个想法,实际上以稍稍隐蔽的方式在谈论另一个想法”(侯世达语),但并未抵达我的目标:将钱先生“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一学术意识发展成一种连贯性和解释性的体系。 其实,丰富的理论资源已经存在,只等我们适度地挪用,创造性地借用。这就是方兴未艾的风景学(landscape studies)、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个业已壮大、貌似独立的学科,其实与决定性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走向的人文地理学颇多交错叠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乃至研究方法都源自人文地理学,又融入派系纷繁的文化研究之中。简言之,它们具有一切新兴学科的跨越性和模糊性;换言之,它们的疆界随着新的关注、方法或问题的介入而在不断移动。在为“阅读脚下的土地”寻找理论性支撑或解释性描述的过程中,我逐渐将范围锁定在与人文地理学瓜葛甚深、近乎同构的风景学上,试图以此为基点展开纵深搜索。之所以如此锁定,是因为在把“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个比较感性的表达切换到理论层面时,我注意到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Peirce F. Lewis)在其《阅读风景的原则》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一文中,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所有的人类风景,不管如何平常的风景,都有着文化意涵,因此,沃茨(M. Thielgaard Watts)认为我们‘可以阅读风景,正如我们能够阅读书本’。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究其知识谱系,这一原则应该是人文地理学泰斗杰克逊(J. B. Jackson, 1909—1996)观点的翻新:“一本丰富而美丽的书总是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必须学会阅读它。” 我的一个假设是:既然风景(landscape)一词汇聚和裂变出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土地、地方、区域、空间、记忆、权力、栖居、家园、身份、国族等已经成为当代各种社会理论的建构基础或参照框架,它也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理论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作为一个地方的贵州、作为风景的贵州、作为表述对象的贵州…… 基于这样的动机,我申请了美国费曼基金,在UIUC进修一年。期间,我系统地研读了大量风景研究专著,并精选了一套丛书。从下列书目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主旨:《 风景与认同》(Landscape and Identity)、《风景与记忆》 (Landscape and Memory)、《寻找如画的风景》(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风景与权力》 (Landscape and Power)、《风景人类学》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恋地情结》 (Topophilia)等等。其中,《风景与认同》、《寻找如画的风景》两书,我认为对于贵州具有特别的理论烛照和旅游规划指导的意义。《风景与认同》重点考察了英国湖区和峰区文化赋值、公众为进入两大风景区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徒步团体的身份建构……而《寻找如画的风景》主攻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互动关系,对于正在急于把自己建造成“公园大省”的贵州颇能提供一些发展思路和前车之鉴。两书都涉及到如画美学(the Picturesque)如何改变了人们的风景感知和审美趣味,如何使英国西北部—凯尔特边区戏剧性地成为英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游客趋之若鹜的绝美之境,浪漫主义的精神圣地。“画境游”(picturesque tour)得以流行,剧院、绘画、明信片、杂志、广告等媒介的作用居功至伟,它们熏陶了,或者说规训了游客的品味,引导他们拿眼前之景比照他们熟悉的17世纪荷兰和意大利风景画作品,从而抬升了峰区、湖区、苏格兰高地的文化价值。 考虑到这套丛书的实用价值,我觉得将它们放在贵州出版似乎更能彰显书地相得。多年前,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时,曾在几个假期,与当过知青、机智老练的大师姐在贵州山区徒步漫游。美好的80年代犹如褪色的黑白底片,时常在我的记忆里显影:两个女生,肩背帆布包,携带一架海鸥相机(克劳德镜的升级版?),日行山间公路,夜宿乡村旅店,饱览如画美景。一路上,我总是把黔东南黔西南奇崛的群山、奔涌的急流、荒凉的原野“误读”成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高地风景,把远处田坎里身着百褶裙的苗家农妇“误认”成腰系格子裙的苏格兰山民,不时招来满腹现代派理论的师姐的反讽,惹出她关于“抒情”、“移情”、“矫情”的高谈阔论。某次,我指着路旁70度坡地上稀疏瘦矮的玉米对她说:“这可不是麦格瑞戈族人的农田吗?” 曾躬耕于凉山阿坝的师姐狂笑:“玉米不是燕麦。”向来俏皮的师姐还顺便帮我复习了一遍约翰逊博士著名的定义:“燕麦是英格兰人用以喂马 而苏格兰人藉以糊口之物。”可惜当时我是余生太早,身处前互联网时代,无缘得知诸如《恋地情结》 (1974)、《发现日常风景》 (Di” 我的一个假设是:既然风景(landscape)一词汇聚和裂变出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土地、地方、区域、空间、记忆、权力、栖居、家园、身份、国族等已经成为当代各种社会理论的建构基础或参照框架,它也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理论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作为一个地方的贵州、作为风景的贵州、作为表述对象的贵州…… 基于这样的动机,我申请了美国费曼基金,在UIUC进修一年。期间,我系统地研读了大量风景研究专著,并精选了一套丛书。从下列书目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主旨:《 风景与认同》(Landscape and Identity)、《风景与记忆》 (Landscape and Memory)、《寻找如画的风景》(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风景与权力》 (Landscape and Power)、《风景人类学》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恋地情结》 (Topophilia)等等。其中,《风景与认同》、《寻找如画的风景》两书,我认为对于贵州具有特别的理论烛照和旅游规划指导的意义。《风景与认同》重点考察了英国湖区和峰区文化赋值、公众为进入两大风景区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徒步团体的身份建构……而《寻找如画的风景》主攻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互动关系,对于正在急于把自己建造成“公园大省”的贵州颇能提供一些发展思路和前车之鉴。两书都涉及到如画美学(the Picturesque)如何改变了人们的风景感知和审美趣味,如何使英国西北部—凯尔特边区戏剧性地成为英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游客趋之若鹜的绝美之境,浪漫主义的精神圣地。“画境游”(picturesque tour)得以流行,剧院、绘画、明信片、杂志、广告等媒介的作用居功至伟,它们熏陶了,或者说规训了游客的品味,引导他们拿眼前之景比照他们熟悉的17世纪荷兰和意大利风景画作品,从而抬升了峰区、湖区、苏格兰高地的文化价值。 考虑到这套丛书的实用价值,我觉得将它们放在贵州出版似乎更能彰显书地相得。多年前,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时,曾在几个假期,与当过知青、机智老练的大师姐在贵州山区徒步漫游。美好的80年代犹如褪色的黑白底片,时常在我的记忆里显影:两个女生,肩背帆布包,携带一架海鸥相机(克劳德镜的升级版?),日行山间公路,夜宿乡村旅店,饱览如画美景。一路上,我总是把黔东南黔西南奇崛的群山、奔涌的急流、荒凉的原野“误读”成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高地风景,把远处田坎里身着百褶裙的苗家农妇“误认”成腰系格子裙的苏格兰山民,不时招来满腹现代派理论的师姐的反讽,惹出她关于“抒情”、“移情”、“矫情”的高谈阔论。某次,我指着路旁70度坡地上稀疏瘦矮的玉米对她说:“这可不是麦格瑞戈族人的农田吗?” 曾躬耕于凉山阿坝的师姐狂笑:“玉米不是燕麦。”向来俏皮的师姐还顺便帮我复习了一遍约翰逊博士著名的定义:“燕麦是英格兰人用以喂马 而苏格兰人藉以糊口之物。”可惜当时我是余生太早,身处前互联网时代,无缘得知诸如《恋地情结》 (1974)、《发现日常风景》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1984)这些风景研究的奠基之作,不得预见将有一批包括《寻找如画的风景》 (1989)和《风景与认同》 (2000)在内的风景研究力作问世,更未想到二十年后自己会从英美文学专业转入风景研究领域—这个转向并非由于学术兴趣的突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导接。在阅读相关文献时,我感觉一些新锐的话语或观念,诸如“地方感”、“定位于风景的自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深植于风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风景殖民主义”……与其说是领我瞻望学术前沿,不如说是引我“后视”(rearmirror)自己的风景经验。尤其是阅读达比的《风景与认同》时,我感觉仿佛有一束强光照亮了幽封在过去之洞穴的记忆,青年时代的即兴之举:原来与师姐在贵州的徒步假期,我们所看所想,我们的争论……是可以得到风景理论的追认、解释乃至放大到意味深长的程度。如果真能穿越,我好想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夏风拂面的下午,回到贵州威宁洛泽河岸某处。我要援引达比的考证来为我的文化模仿辩护:“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包括法国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格兰与法国之间充满公开的敌意,这种敌对关系具有周期性发作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出国休闲旅游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可能性或可取性大打折扣。同样,国内的远距离旅行也颇为不易或多有限制。但是若有可能,他们会到英格兰群山起伏的北部乡村以及北威尔士旅行,这也是英国旅行者能感受到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frisson)的最近距离……”。甚至,我要追加一句煽情的话:“我正在感受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更甚至,我要对屡屡带我绕开收费关卡,翻墙或跨栏溜进景区的师姐说:“搁在19世纪的英国湖区,我们这种行为属于‘非法侵入’。”当然,我也要用达比的观察来分析自己的误读误认:“古典教育,犹如绘画知识一样,使得游客把风景与文学联想起来,将当地人变成了艺术装饰。”反思自己的观景行为是否也是一种伪精英的“凝视”:在我们这两个来自相对发达的内地的游客眼里,欠发达的贵州苗疆是否犹如18世纪相对落后的凯尔特边界,只是一个引发审美联想的对象,至于如画美景背后的贫穷与衰败则不在我们的关注之内?追问自己对于贵州的依恋是否属于达比田野调查的范围:以象征的方式归属一个非出生地的“地方”? 为这个念头所激动,我致电好友,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张晓松教授,向她介绍我的出版构想。万里光缆那一头的她很激动地说,这套丛书交给贵州人民出版社来做,是最佳配置。晓松素来作风雷厉,很快说服贵州人民出版社全盘接下这套非盈利学术著述。然而,版权谈判似乎是个复杂的技术活,超出了出版社的想象。虽经晓松鼎力推动一年有余,翻译授权仍无着落。此时我已回国,开设了一门新课《风景与文学》,为研究生导读《风景与权力》等原著,指导自己的学生撰写关乎风景的毕业论文。口译释读原文的时候,难免想起钱先生的嘱托,不免惭腆。一日忽发奇想,电话刘东先生,试探柳暗花明的机会。我刚报上几本书的标题,他就要我速将内容提要E-mail 给他。一天之内,刘东先生回话,将丛书悉数纳入他的“人文与社会”系列。我原以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1984)这些风景研究的奠基之作,不得预见将有一批包括《寻找如画的风景》 (1989)和《风景与认同》 (2000)在内的风景研究力作问世,更未想到二十年后自己会从英美文学专业转入风景研究领域—这个转向并非由于学术兴趣的突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导接。在阅读相关文献时,我感觉一些新锐的话语或观念,诸如“地方感”、“定位于风景的自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深植于风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风景殖民主义”……与其说是领我瞻望学术前沿,不如说是引我“后视”(rearmirror)自己的风景经验。尤其是阅读达比的《风景与认同》时,我感觉仿佛有一束强光照亮了幽封在过去之洞穴的记忆,青年时代的即兴之举:原来与师姐在贵州的徒步假期,我们所看所想,我们的争论……是可以得到风景理论的追认、解释乃至放大到意味深长的程度。如果真能穿越,我好想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夏风拂面的下午,回到贵州威宁洛泽河岸某处。我要援引达比的考证来为我的文化模仿辩护:“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包括法国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格兰与法国之间充满公开的敌意,这种敌对关系具有周期性发作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出国休闲旅游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可能性或可取性大打折扣。同样,国内的远距离旅行也颇为不易或多有限制。但是若有可能,他们会到英格兰群山起伏的北部乡村以及北威尔士旅行,这也是英国旅行者能感受到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frisson)的最近距离……”。甚至,我要追加一句煽情的话:“我正在感受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更甚至,我要对屡屡带我绕开收费关卡,翻墙或跨栏溜进景区的师姐说:“搁在19世纪的英国湖区,我们这种行为属于‘非法侵入’。”当然,我也要用达比的观察来分析自己的误读误认:“古典教育,犹如绘画知识一样,使得游客把风景与文学联想起来,将当地人变成了艺术装饰。”反思自己的观景行为是否也是一种伪精英的“凝视”:在我们这两个来自相对发达的内地的游客眼里,欠发达的贵州苗疆是否犹如18世纪相对落后的凯尔特边界,只是一个引发审美联想的对象,至于如画美景背后的贫穷与衰败则不在我们的关注之内?追问自己对于贵州的依恋是否属于达比田野调查的范围:以象征的方式归属一个非出生地的“地方”? 为这个念头所激动,我致电好友,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张晓松教授,向她介绍我的出版构想。万里光缆那一头的她很激动地说,这套丛书交给贵州人民出版社来做,是最佳配置。晓松素来作风雷厉,很快说服贵州人民出版社全盘接下这套非盈利学术著述。然而,版权谈判似乎是个复杂的技术活,超出了出版社的想象。虽经晓松鼎力推动一年有余,翻译授权仍无着落。此时我已回国,开设了一门新课《风景与文学》,为研究生导读《风景与权力》等原著,指导自己的学生撰写关乎风景的毕业论文。口译释读原文的时候,难免想起钱先生的嘱托,不免惭腆。一日忽发奇想,电话刘东先生,试探柳暗花明的机会。我刚报上几本书的标题,他就要我速将内容提要E-mail 给他。一天之内,刘东先生回话,将丛书悉数纳入他的“人文与社会”系列。我原以为这套丛书与他的一向关注不甚关联,不曾料到他的新关注已在这个方向久矣。在英美大学里的数次演讲中,他已论及风景研究的热点议题,从中国城市景观或风景的视角反思全球化的冲击和“黑暗一面”—而“dark side of landscape”( 风景的黑暗一面)既是巴雷尔(John Barrell)的重要发现,又是米切尔(W.J.T Mitchell)辩证地定位风景之本质的基础。看来,我挑选出来的这些“天书”早在他的视域之内,而且融进他的“观点”背景之中。 这套丛书移交给已与刘东先生精诚合作多年的译林出版社后,版权问题迎刃而解。如我所愿,最先谈下来的就是《风景与认同》。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再现性的、政治性的和民族志的,从三个角度合围一个学术任务,即以跨学科的方式“探索历史上的阶级关系,追踪作为文化产物的阶级与民族身份透过风景及其进入权发挥作用的种种步骤”。这一任务的设计缘起于作者的敏锐观察:“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堪称跨学科研究的范本;就内容而言,本书不负数位资深书评人的赞语。瑞典学者肯尼思?奥尔维格(Kenneth Olwig) 夸奖第一部分对近年的风景研究做了透彻而富有价值的回顾,特别欣赏第三部分,认为最富创新性和挑动性,甚至建议作者改换成“风景、徒步与认同”。对此,我亦有同感。第三部分是“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对于地方的体验,以及‘使地理经验得以形成、交流得以进行的那些共享的象征手段’”。这一部分充分展示了达比的研究风格—精确、细腻和敏锐。她特别引入了三位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非常清晰的女性徒步者的口述史,揭示她们徒步湖区的经验与其身份建构的关系。由此我想到:国内的徒步漫游已经形成规模,杂志或网络上常见驴友各种形式的日志或报告,但对于这一“在路上群体”的田野调查或民族志学的研究,似乎鲜见。显然,《风景与认同》一书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内学人,特别是关注地方、环境、旅游等议题的学人颇有启发作用。书中着力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风景区的立法史、进入风景与进入政治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各种利益集团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等等都是值得借鉴的研究课题。我尤其激赏作者对于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精辟的分析,认为有心的学者,是可以顺着这一路径思考国内景区的种种现象的。化用刘东先生的一句妙语,《风景与认同》论及的峰区或湖区的难题,其实也在困扰着当代中国。例如,19世纪初期,暴发的工业家在湖区建造的豪宅,“颜色俗气,位置扎眼,只是为了抢占风景,不像当地的古旧民居那样隐入风景,不露痕迹”。类似的现象正在中国一些景区不断涌现,只不过可能是,工业家的豪宅换成了星级旅游饭店,而许多世代隐入风景的民居要么被拆迁,要么被改造成权力部门钦定的风格……看来,风景的商品化过程先后在英国和中国进行,但结果似乎大相径庭。早在19世纪,湖区精英或湖区之友就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文化资本,通过一系列的议案限制进入或开发湖区,从而保护作为英国之象征的湖区生态和如画美,而我们的文化精英,即使有类似的提议,却无促使提议落实的权力。此为这套丛书与他的一向关注不甚关联,不曾料到他的新关注已在这个方向久矣。在英美大学里的数次演讲中,他已论及风景研究的热点议题,从中国城市景观或风景的视角反思全球化的冲击和“黑暗一面”—而“dark side of landscape”( 风景的黑暗一面)既是巴雷尔(John Barrell)的重要发现,又是米切尔(W.J.T Mitchell)辩证地定位风景之本质的基础。看来,我挑选出来的这些“天书”早在他的视域之内,而且融进他的“观点”背景之中。 这套丛书移交给已与刘东先生精诚合作多年的译林出版社后,版权问题迎刃而解。如我所愿,最先谈下来的就是《风景与认同》。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再现性的、政治性的和民族志的,从三个角度合围一个学术任务,即以跨学科的方式“探索历史上的阶级关系,追踪作为文化产物的阶级与民族身份透过风景及其进入权发挥作用的种种步骤”。这一任务的设计缘起于作者的敏锐观察:“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堪称跨学科研究的范本;就内容而言,本书不负数位资深书评人的赞语。瑞典学者肯尼思?奥尔维格(Kenneth Olwig) 夸奖第一部分对近年的风景研究做了透彻而富有价值的回顾,特别欣赏第三部分,认为最富创新性和挑动性,甚至建议作者改换成“风景、徒步与认同”。对此,我亦有同感。第三部分是“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对于地方的体验,以及‘使地理经验得以形成、交流得以进行的那些共享的象征手段’”。这一部分充分展示了达比的研究风格—精确、细腻和敏锐。她特别引入了三位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非常清晰的女性徒步者的口述史,揭示她们徒步湖区的经验与其身份建构的关系。由此我想到:国内的徒步漫游已经形成规模,杂志或网络上常见驴友各种形式的日志或报告,但对于这一“在路上群体”的田野调查或民族志学的研究,似乎鲜见。显然,《风景与认同》一书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内学人,特别是关注地方、环境、旅游等议题的学人颇有启发作用。书中着力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风景区的立法史、进入风景与进入政治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各种利益集团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等等都是值得借鉴的研究课题。我尤其激赏作者对于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精辟的分析,认为有心的学者,是可以顺着这一路径思考国内景区的种种现象的。化用刘东先生的一句妙语,《风景与认同》论及的峰区或湖区的难题,其实也在困扰着当代中国。例如,19世纪初期,暴发的工业家在湖区建造的豪宅,“颜色俗气,位置扎眼,只是为了抢占风景,不像当地的古旧民居那样隐入风景,不露痕迹”。类似的现象正在中国一些景区不断涌现,只不过可能是,工业家的豪宅换成了星级旅游饭店,而许多世代隐入风景的民居要么被拆迁,要么被改造成权力部门钦定的风格……看来,风景的商品化过程先后在英国和中国进行,但结果似乎大相径庭。早在19世纪,湖区精英或湖区之友就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文化资本,通过一系列的议案限制进入或开发湖区,从而保护作为英国之象征的湖区生态和如画美,而我们的文化精英,即使有类似的提议,却无促使提议落实的权力。此外,我认为第二部分也相当精彩。达比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风景进入权运动的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 她以翔实的资料勾勒出底层反抗急流的源头、流域与结果: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如何与工人阶级进入乡村运动结合在一起。工人阶级争得在父辈被迫离开的土地上自由漫步权的同时,也争得了选举权。耐人寻味的是:“非法入侵”风景区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 《风景与认同》走的是严谨缜密的写作路线,没有我所仰慕的以赛亚?伯林和哈罗德?布鲁姆的丰沛之美(beauty of exuberance),但有着我所钦佩的学术专著的品质:论之有据、言之有物、行之甚远—这也是我向一些博士候选人力荐此书的原因之一。 然而,它跨越人类学—历史—文学的视角和严谨不免拘谨、缜密几近深密的文体风格,却对译者构成一个极大的考验。为了论之有据,作者旁征博引—从堪与正文媲美的尾注和巨量的参考引文就可以看出:她的常识、学识和见识远远超过译者的传译能力。实际上,书中有很多概念或者术语需要向行家求助或求证。译者曾有幸与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同屋半年有余,耳濡目染,近朱则赤,漂学了一些田野志、口述史等皮毛,因此,翻译此书,译者温习了一些旧课,也补习了不少新知,虽然有校译《浪漫主义的根源》等书的经历,但仍不敢肯定本书“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刘东语)。实际上,恰好是以前校译的经历使得译者深信翻译不仅是“遗憾的艺术”,而且是如履薄冰的冒险。一个貌似常见的词语也许指向的是殊异的概念世界。在寻找词语意义的过程中,时有不知所云的疑惑、失其所踪的慌乱和无从定夺的窘迫。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和编辑的宽容:他们原谅译者数次拖延完稿日期;我要再次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代译者翻译了最需耐心的索引部分,统一了各类名称。此外,我要感谢刘碧原和张倩倩两位同学的救急义举—是她们将长达几十页的参考书目转换成 可编辑的文本。 张箭飞 2009年11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外,我认为第二部分也相当精彩。达比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风景进入权运动的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 她以翔实的资料勾勒出底层反抗急流的源头、流域与结果: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如何与工人阶级进入乡村运动结合在一起。工人阶级争得在父辈被迫离开的土地上自由漫步权的同时,也争得了选举权。耐人寻味的是:“非法入侵”风景区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 《风景与认同》走的是严谨缜密的写作路线,没有我所仰慕的以赛亚?伯林和哈罗德?布鲁姆的丰沛之美(beauty of exuberance),但有着我所钦佩的学术专著的品质:论之有据、言之有物、行之甚远—这也是我向一些博士候选人力荐此书的原因之一。 然而,它跨越人类学—历史—文学的视角和严谨不免拘谨、缜密几近深密的文体风格,却对译者构成一个极大的考验。为了论之有据,作者旁征博引—从堪与正文媲美的尾注和巨量的参考引文就可以看出:她的常识、学识和见识远远超过译者的传译能力。实际上,书中有很多概念或者术语需要向行家求助或求证。译者曾有幸与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同屋半年有余,耳濡目染,近朱则赤,漂学了一些田野志、口述史等皮毛,因此,翻译此书,译者温习了一些旧课,也补习了不少新知,虽然有校译《浪漫主义的根源》等书的经历,但仍不敢肯定本书“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刘东语)。实际上,恰好是以前校译的经历使得译者深信翻译不仅是“遗憾的艺术”,而且是如履薄冰的冒险。一个貌似常见的词语也许指向的是殊异的概念世界。在寻找词语意义的过程中,时有不知所云的疑惑、失其所踪的慌乱和无从定夺的窘迫。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和编辑的宽容:他们原谅译者数次拖延完稿日期;我要再次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代译者翻译了最需耐心的索引部分,统一了各类名称。此外,我要感谢刘碧原和张倩倩两位同学的救急义举—是她们将长达几十页的参考书目转换成 可编辑的文本。 张箭飞 2009年11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风景与认同》一书深入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内学者颇有启发作用,引用刘东老师的一句话,即《风景与认同》论及的峰区或湖区的难题,其实也在困扰着当代中国。书中着力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研究课题,作者对隐匿在风景中的权力关系的精辟分析,也对思考国内景区的种种现象很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