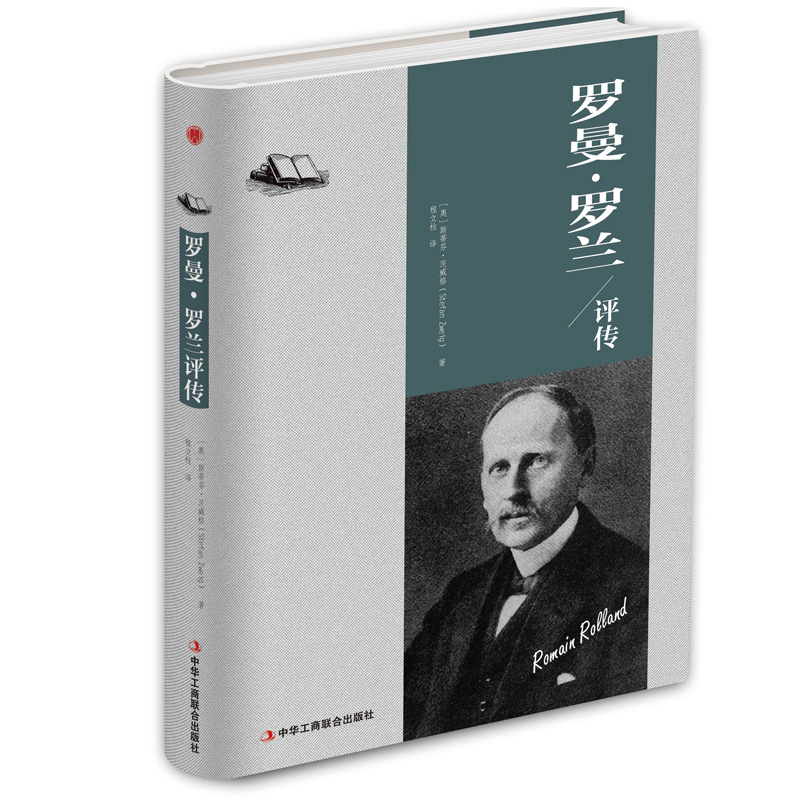
出版社: 工商联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罗曼·罗兰评传(精)
ISBN: 9787515823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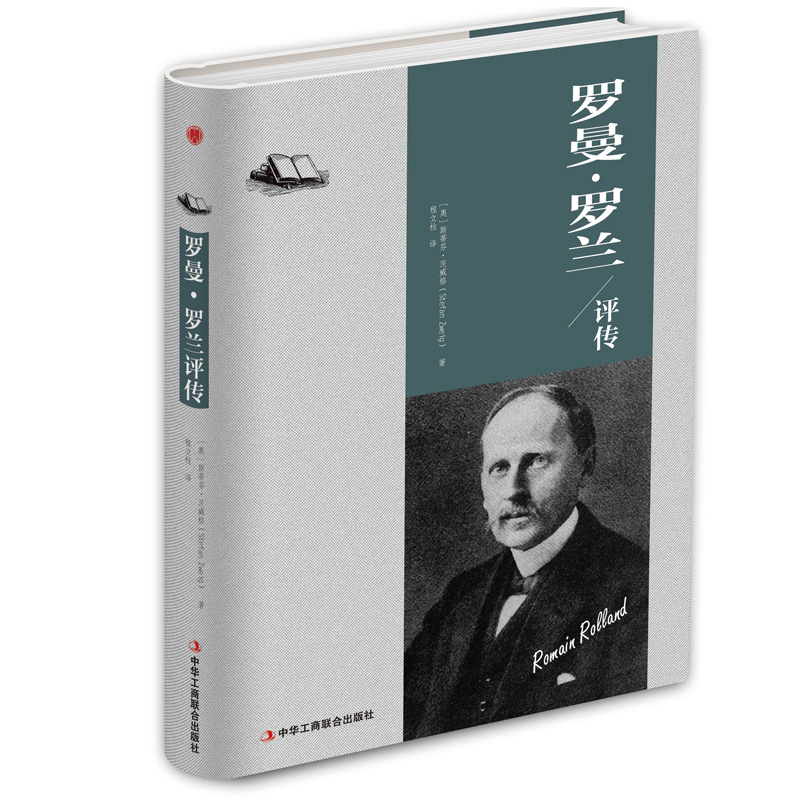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作家,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茨威格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以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心理刻画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不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的主要作品有《巴尔扎克》、《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昨日的世界》等。
来自深渊 在罗兰早期的作品中,他歌颂激情,认为那是个人的最高力量和每个民族创造的灵魂。他认为,只有燃烧着思想火焰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对于民族来说也一样,只有在强烈的信仰中团结起来的民族,才具有了灵魂。在青年时代,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个疲惫、萎靡、丧失意志的时代唤起这种信仰。后来,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理想主义者想要用激情来拯救世界。 无望的愿望,徒劳的行动。10年,15年,这些数字从嘴里说出来是多么容易,可心灵却要承受无边的痛苦,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火热的激情逐渐被失望吞没。“人民剧院”被迫关门了,剧本成了一堆废纸。 “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朋友们已各奔前程,他的同龄人都已成名成家,而罗兰还是一个刚刚上路的新手。可以说,他创作得越多,就越被人遗忘。他的理想没有一个得到实现。人们依旧波澜不惊地、昏昏沉沉地生活。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利益和钱财,而不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 他的内心生活也出现了危机,一度幸福的婚姻破裂了,这位30岁的艺术家的灵魂受到了最深的伤害。而对这几年的悲惨遭遇,罗兰绝口不提。一切的努力均告失败,于是他完全隐退到了孤独中。那间窄小的斗室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工作是他最大的安慰。然而虽然被世界抛弃,他依然没有忘记救助全人类的责任。 在那段孤苦的岁月里,罗兰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如果一个人在众人的喧闹声中总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他只会感到痛苦与孤独。 他详尽研究了艺术家们的生平,结果发现:“越是深入这些伟大者的内心,就越会更多地看到他们生活中的痛苦与不幸。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常见的考验与失望,这使得他们超越常人的敏感心灵备受打击。他们的天赋使其超越了同时代人20年、50年,甚至几百年,因此他们成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遭受着大众的冷遇,他们只能绝望地辛勤劳作。他们几乎无法维持自己日常的生活,更别提取得胜利了。” 可以说,这些受人仰视的强者,孤独人的永恒的安慰者,却也是“世界的胜利者和不幸的战败者”。一条无形的、痛苦的锁链,穿越数个世纪,将罗兰与他们的命运连成了一个悲剧性的统一体。托尔斯泰在给他的信中曾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是心满意足、饱食终日的享受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名拉撒路(一个满身生疮的乞丐,生前受尽苦难,死后进了天堂),忍受着无尽的苦难。因此,越是伟大的人,经历的痛苦就越多。反之,承受的痛苦越多,他就越伟大。” 罗兰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比他在作品中颂扬的那种行动的伟大更深沉的伟大,那就是痛苦的伟大。这时的罗兰,从这种最痛苦的认识中获得了新的信仰,绝望的情绪又一次得到了鼓舞。作为受难者,他向世界上所有的受难者致意。他想向所有的孤独者展示痛苦的伟大和意义,以让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同样在这里,在这个新的领域,他试图以伟大人物的事例来联合所有人。 “生活是艰辛的,对无法忍受平庸的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斗争。在多半情况下,这种斗争都是在孤独和沉默中进行的,无人注意的,毫无幸福的悲惨斗争。这些人生活困顿,为家事所累,所做的工作枯燥乏味,令人绝望,空耗着人的精力。生活对他们而言,毫无乐趣,毫无希望。孤独的生活甚至让他们无法去帮助其他不幸的兄弟们。” 于是,罗兰希望架起一座连接人与人,痛苦与痛苦之间的桥梁。以便让大众了解那些用自己的痛苦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人。正如卡莱尔所说:“在各个时代,那些将伟人与常人联系起来的神圣血统关系更加清晰可见。”千百万的孤独者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即使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信心,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苦难,向所有人证明了生命的意义。 他这样写道:“不幸者莫要怨天尤人,因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就在你们身边,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变得坚强。当我们感觉虚弱时,可以栖息在他们身旁。他们会抚慰我们。他们身上总是源源不断地涌出真诚的力量与强大的善意。我们甚至无须阅读他们的著作,无须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仅从他们的目光中和他们的存在中就能感受到。从来没有一种生活比痛苦中的生活更伟大,更丰富,更幸福。” 为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安慰仍处于痛苦中的弟兄们,罗兰写下了《名人传记》。 痛苦中的英雄们 同他创作革命剧时一样,这部新的戏剧集《名人传记》也以一篇宣言开始,呼唤人们去创造伟大。《贝多芬》中的序言如同催人前进的旗帜,他写道:“我们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古老的欧洲在沉闷、污浊的空气中呻吟。毫无伟大可言的物质主义压抑着人们的思想……世界在不择手段和斤斤计较的利己主义中奄奄一息,日渐衰竭。打开窗户吧,让自由新鲜的空气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们的伟大气息吧!” 那么,罗兰所说的英雄是怎样的人物呢?不是那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赢得革命与战争的人,也不是那些实干家和拥有毁灭性思想的人。他已认识到任何集体的活动都毫无意义,罗兰在自己的剧作中也已体现出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思想就像面包一样无法让人们共享,它往往会在人的大脑与血液中转化成与其对立的其他形式,这便是思想的悲剧。在他看来,真正的伟大是孤独,是个人同无形的阻力间的斗争。 “我所说的英雄,是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而不是靠自己的思想或权力取胜的人。有位伟人(托尔斯泰)说过:除了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代表卓越。如果没有伟大的行动,就没有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也没有伟大的行动者。有的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时代抛弃的大众顶礼膜拜的偶像……因此关键不在于显得伟大,而在于成为伟大。” 由此看来,英雄并不是为生活的某一个目标而战,为赢得某一项成就而战,而是为全人类、为生命本身而战。若谁因害怕孤独而逃避战争,那他就是战败者。若谁为了逃避痛苦,而巧妙地遮蔽整个世界的悲剧,那他就是谎言家。只有诚实的人才懂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他愤怒地喊道:“我憎恨懦弱的理想主义,它从不关心悲惨的生活和虚弱的灵魂。然而我们正需要大声地告诉人们,尤其是容易被花言巧语欺骗的人们:英雄主义的谎言是怯懦的表现。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并热爱生活。” 苦难是对伟人必要的考验,是对纯洁性的必要的过滤。用约翰内斯·埃克哈特的话来说,是“奔向完美境界的最快速的途径”。正如艺术是痛苦的试金石一样,只有在痛苦中才能获得对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认识,只有在痛苦中才能看到艺术在经历了数个世纪后变成比死神更强大的力量。 对伟人来说,切身的痛苦会变成对人生的感悟,而这种感悟又会变成强烈的情感力量。但是,伟大并非来源于痛苦本身,而是来源于对痛苦的克服。那些屈服于尘世压迫,或是逃避痛苦的人,必会成为失败者,这样一来,他那高雅的艺术品就会显示出由于挫败而留下的裂痕。而只有从苦难中奋起的人,才能将其思想带上精神的巅峰,只有经过炼狱才能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每个人独自寻找,但谁能在这条路上勇往直前,谁就是领袖,领导他人步入自己的世界。 “伟大的灵魂就像高耸的山峰。尽管饱受狂风暴雨的侵袭,云雾的遮蔽,但是只有在这里才能更尽情地呼吸。这里的空气清新,它能将污渍从胸中一洗而净。而当乌云散去,便能深情地俯视伟大的人类。” 罗兰希望用这种思想指引那些仍在黑暗中遭受痛苦的人们。他想让他们看到,在那巅峰之上,英雄们如何与异常剧烈的痛苦做斗争。颂歌在“振奋我们的心灵”的呼声中拉开序幕,又在对受苦的崇高形象的赞美声中拉下帷幕。 贝多芬 贝多芬是无形庙堂上的第一尊英雄雕像,是大师中的大师。早在童年时代,当亲爱的母亲教他用手指在琴键奇妙的森林里漫游时,贝多芬就成了罗曼·罗兰心目中的老师和劝慰者。虽然童年时代的爱好时有变动,但贝多芬始终陪伴在他左右:“少年时代的我一度陷于怀疑与消沉的情绪中,是一支贝多芬的旋律让我重新燃起了生命之火,时至今日它仍时时在我心中回响。”这个虔诚的学生逐渐萌生出一个愿望,去了解这位神明的尘世生活。 罗兰先去了维也纳,拜访了“黑色西班牙人小屋”(如今已拆除),就是在这里,在风雨大作的一天,那位天才的艺术家永远离开了人世。然后,他去了美因茨,在那里参加了贝多芬文艺节(1901),并去波恩参观了这位拯救了语言中的语言的大师的出生地,一间低矮的阁楼。所到之处,无不使他感到震惊,不朽的财富竟然产生于如此狭隘的生存空间。 从各种信件与文件中,罗兰看到了贝多芬悲惨的日常生活。为了避开这种生活,这位耳聋的音乐家让自己沉入无尽的音乐中。在惊愕当中,罗兰逐渐理解了生活在我们这个平淡、残酷、动荡的世界里的“悲哀的狄俄尼索斯”(指贝多芬)的伟大之处。 罗兰就波恩贝多芬文艺节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贝多芬》的文章,发表在《巴黎评论》上。但他感到仅凭评论性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向全人类介绍这位英雄人物,告诉人们,当痛苦达到极限时,这位伟人留给后人的却是第九交响曲那最崇高的人类颂歌。 罗兰饱含激情地在传记的开头写道:“别人对贝多芬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赞誉已经够多了。但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还是现代艺术的英雄人物,是一切正处于苦难中的和战斗着的人们最伟大的朋友。当我们为世间的痛苦伤心难过时,他来到我们身边,默默弹奏一曲如泣如诉的悲歌,以示安慰。当人们对与不良现象的徒劳斗争感到厌倦时,畅游在这意志与纯净的音乐海洋中,是多么幸福。 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奋发的感染力量,斗争的幸福感,以及感到上帝存在于自己内心的陶醉感。当这个不幸的、身无分文的、疾病缠身的、孤苦伶仃的、被剥夺了欢乐而成为痛苦的化身的人,自己创造了欢乐,并把这种欢乐赋予世界的时候,还有哪种胜利能与之相比呢?还有哪次波拿巴的战役、哪次奥斯特里茨的阳光能与这超人的努力所取得的荣耀相比。 他将自己的痛苦转化为欢乐,他曾骄傲地说:‘从痛苦中得到欢乐。’这句话是对他一生的写照,并成了所有英雄人物的座右铭。” 罗兰对自己所仰慕的人就是这种态度。接着罗兰告诉人们,当翻开这位艺术家的遗嘱时,他发现在这个遗嘱中,这位大师向后人坦诚了一件当时对同代人难以启齿的事,那就是他极度地痛苦。罗兰揭示了这位无信仰大师的信仰,那就是他的善良,虽然他曾竭力用假装的粗鲁加以掩饰。罗兰的这部传记使新的一代对贝多芬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亲切,这位孤独者的英雄主义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鼓舞了如此众多的人。 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苦难中的兄弟虽然遍布世界各地,但是他们都得到了这一消息。虽然这一传记没有取得文学上的成就,报刊对它保持沉默,学术界也对它熟视无睹,但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从中感到了幸福。他们争相传看,一种神秘的感激之情第一次将他们聚集在罗兰这个名字周围。苦难深重的人们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了真诚的安慰,深切的同情与善意。 《贝多芬传》面世后,罗兰虽然还没有获得任何的成功,但他已经得到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他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与追随者,他们密切关注着他的作品,并成了第一批陪伴约翰·克利斯朵夫迈向成功的人。这是他的第一个成就,同时也是《半月丛刊》的第一个成就。人们对这份不起眼的杂志的需求量突然增加,使之第一次不得不再版。夏尔·贝玑感慨地说,这份杂志是对伟大而无名的受难者贝尔·纳拉扎尔临终前最好的安慰,它的出版确实是“道德的启示”。 至此,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第一次对人们产生了影响。 在与孤独所做的斗争中,罗兰取得了初次的胜利。罗兰感觉到黑暗中有许多不见其身影的受难中的兄弟,正在等待自己开口说话。只有处于苦难中的人才能体味出痛苦的含义,这样的人真是不胜枚举。于是,罗兰想向他们介绍另一些伟大的人,他们忍受着另一种痛苦,并以另一种方式来克服这种痛苦。一些伟人满怀着力量与意志,他们从遥远的过去注视着他,他满怀对他们的敬仰,走近他们并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米开朗琪罗 在罗曼·罗兰的眼里,贝多芬是一位纯洁的、能够战胜痛苦的人。他似乎生来就负有向人们展示生活的美的使命。但是命运却毁掉了他宝贵的听力器官,将这位生性乐意与人交往的人抛入了无声的地狱。但是,虽然没有了听觉,他却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为他人创作欢乐的颂歌,这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不过,肉体的痛苦只是英雄主义的意志需要去克服的痛苦中的一种,“痛苦是无穷尽的,有时他来自天命的安排,如疾病、不幸和命运的不公;有时是出于人自身的原因,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天性,现实生活是不可能按要求与希望来安排的”。 这也是米开朗琪罗的悲剧所在。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不幸与痛苦便伴随其左右,像蛀虫一样一直啃食他的心灵达80年之久,直到他离开人世。忧郁是他全部情感的基调,他永远不会像贝多芬那样从内心深处发出清亮动听的声音。但他之所以伟大,便在于他将痛苦像十字架一样背负起来,像希绪弗斯一样永远推着石头,永不停歇。他已厌倦了生活,但在工作面前却永远不知疲倦。他将所有的痛苦情绪都敲进默默忍受的岩石,将它们变成了艺术品。 在罗兰眼中,米开朗琪罗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是一位基督徒、一位受难者。但他的痛苦中也有缺点,那就是软弱,但丁在《地狱篇》中诅咒过这种“听任自己肆意悲伤”的软弱。作为一个人,他是值得同情的,但却像是一个精神有缺陷的人在接受怜悯,因为这里产生了“英雄主义的天才与缺乏英雄主义的意志”之间的矛盾。 贝多芬是一位艺术家,但更是一位英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是一位艺术家,但是抛开他的艺术家身份,他却是一个失败者。他从不主动追求爱,因此也就得不到爱;因为从不要求快乐,所以也得不到快乐。他从不与自己的忧郁做斗争,反而任其发展,将它当作玩物,他享受着它,说:“忧郁是我的快乐,万千的快乐也抵不上一丝的痛苦。”他手握斧头,为阴暗的生命之路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这的确是他的伟大之所在,他引导着人们走向永恒。 罗兰也确实感受得到米开朗琪罗身上的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但深陷苦难中的人们却不能从中得到抚慰。因为这里还缺乏战胜痛苦的关键,那就是信仰。罗兰赞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和高尚的忧郁,但却带着暗暗的同情。而对贝多芬的颂扬,他却是满怀崇敬的激情。 贝多芬有着自由的思想,就宗教而言,他看到的是宗教积极的一面,如帮助人类、颂扬崇高等,所以他憎恨那些与人为敌、放弃生命的做法。而米开朗琪罗的例子只是说明,世俗的人究竟能忍受多大的痛苦。他的形象的确是伟大的,但是却是一种警示性的伟大。他虽然用自己的方式战胜了痛苦,虽然是获胜者,但是只能算半个胜利者。因为仅仅忍受生活的痛苦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生活,并热爱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托尔斯泰 在前两部传记中,罗兰热情地讴歌了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这是力量的颂歌,是英雄主义的召唤。而几年之后为托尔斯泰写的传记却语调低沉,像是一首安魂曲、一首哀歌、一曲死亡之歌。当时罗兰遭遇车祸,在死亡线上挣扎,身体尚未恢复便听到了自己敬爱的导师的死讯。在他看来,这一消息蕴含着伟大的意义与崇高的警示。 罗兰在书中将托尔斯泰描写成第三种英雄主义痛苦的典型。贝多芬正当盛年时失去听觉,米开朗琪罗的痛苦与生俱来,托尔斯泰则是凭自己自由自觉的意志安排了自己的命运。托尔斯泰健康、富有、独立、显贵,有自己的田庄和宅院,有妻子儿女,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生活的顺利与富足。 但是,这位本可以安享生活的人,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正当性。让他备感折磨的是他的良心,而他对真理狂热的追求成了附在他身上的魔鬼。平庸者追求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称不上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他坚决地放弃了这种生活。他像苦行僧一般将怀疑的尖刺扎进了自己的胸中,并在痛苦中赞美着它:“当对自己不满时,应该感激上帝。生命的最根本的标志,便是生活与它应当表现的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是一切善的前提条件。对一切感到满足,是绝对错误的。” 在罗兰看来,正是由于有这种冲突,才有了真正的托尔斯泰。因为在罗兰的眼中,只有战斗着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生机勃勃的人。米开朗琪罗认为神的生活高于尘世的生活,而托尔斯泰则认为真实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为了获得这种实际的生活,他毁掉了自己的安宁。 这位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就像骑士扔掉了自己的宝剑一样,独自走上忏悔之路。他还挣脱了家庭的锁链,日夜在偏执的怀疑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破坏着自己的宁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歇,以此来求得良心的安宁。他是一位为无形之物而战的战士,这些无形的存在,如幸福、欢乐和上帝的昭示,比语言有更丰富的表达能力。 他是一位为最后的真理而战的战士,而这一真理,他却无法同其他人分享。 这位英雄的斗争,同贝多芬与米开朗琪罗一样,也是在绝望的孤独与真空中进行的。他的妻子、儿女、朋友、敌人,没有一个人理解他,都将他当做异类,感觉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在与看不见的敌人斗争,其实他们不知道,那个敌人正是他自己。无人能安慰他,无人能帮助他,为了能独自死去,他不得不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逃离自己富裕的家,像乞丐那样死于路旁。在众人仰慕的最高境界的巅峰,永远都是刺骨的寒风,那便是孤独。那些为人民大众创作的人,自己却是孤独一生,他们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为自己的信仰与全人类受苦。 未完成的传记 早在第一本传记《贝多芬传》的封面上,罗兰就预告将有一系列的英雄传记问世。如伟大的革命者马志尼,多年来罗兰已经在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的帮助下收集了有关他的大量资料;另外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雄奥什将军,以及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等。 罗兰原计划要为更广泛的思想家立传,许多人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成形。罗兰还准备等自己更成熟一些时,能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歌德写一本传记,描绘他那平和宁静的内心世界。他感激莎士比亚给了他少年时代难忘的感受,感激鲜为人知的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给予了他巨大的友谊。 这些计划中的“名人传”最终都没有完成。虽然在随后的几年,他写了几本有关亨德尔和米勒等人的学术著作,以及一些有关胡歌·沃尔夫和柏辽兹的研究论文。但最终他的第三个作品集同样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的失败并非由于当初阻碍罗兰的那些因素(如他与时代的对立,或人们的漠然态度),而是由于对深层人性的道德认识。 罗兰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发现,真理——这个他认为最深厚的力量,无法同其创作激情相一致。而只有在贝多芬那里,才可以既持有真理,又给予人安慰,那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本身就能净化并提升人类的灵魂。在描写米开朗琪罗时,就有了些许压力,因为要将这位天生就忧郁的人写成一位胜利者,的确有一些难度。托尔斯泰则更多地在预言真正的生活,而很少提及丰富、热闹和有价值的生活。 当罗兰着手马志尼的传记时,他意识到,他在满怀热情地研究老一代人对这位已被遗忘的爱国者的痛恨。因此,他或者得背离真理,将这位狂热分子塑造成一个模范典型,或者描述事实而使大众失去对他英雄主义的信仰。他发现,为了对人类的爱,他不得不隐瞒一些事实。 因此,他也陷入了托尔斯泰曾面临的冲突中:“他对悲惨现实的深入了解与出于善良的本性而力图想掩盖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悲剧性的斗争。曾有多少次我们面临这种两难抉择,是否定事实的存在,还是直面它。当艺术家必须描述某一事实时,经常会遇到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对于同一个健康有力的真理,在有些人看来就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习惯了单纯的善良而变得衰弱不堪。怎么办呢?是绝口不提这致命的真理,还是不顾后果地将事实说出来?人们经常会面临这两难抉择:真相还是爱?” 这就是罗兰在创作中遇到的令人苦恼的发现:如果一个人既是尊重事实的历史学家,又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人类的朋友,那他是不可能完成伟大人物传记的。我们的历史展现的是否就是真理呢?历史通常不都是各个国家的传说与民族传统吗?每一个历史人物不都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与道德标准经过修改和美化的吗? “要描写一个人是多么困难啊。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想要了解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人,那是极不明智的。我们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亲人、每一个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人,实际上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他可能与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他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常常漫游在自己的幻影当中,但是判断与创造是必不可少的。” 罗兰面前障碍重重,既要公正地对待自己、公正地对待自己所尊敬的人,又要尊重真理、同情人类,这一切都阻碍着他前进的脚步。罗兰没有再继续“英雄传记”的写作,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只会粉饰现实而不敢否定它的“胆怯的理想主义”的牺牲品,所以他宁愿保持沉默。由于感到这条路不可行,因此他中途果断停下了脚步,但是他并未忘记自己的目标——“捍卫世间的伟大”。 人类要相信自己,就需要有崇高的形象与英雄的传说。但是历史只有通过对人物的美化才能提供给人以慰藉的形象。于是罗兰转而在一种新的、更崇高的真理中,即艺术中去寻找英雄。 现在,他以我们的时代为背景,创作出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他通过各种形式展现了我们这个世界日常的英雄主义,并通过一切的斗争,表现了那个信仰生命的伟大胜利者——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克拉姆西小城。童年时代,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这些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的滋养下成长起来。少年时代,其父为了使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迁居巴黎,并将之送进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一所古老而著名的学校——路易大帝中学。在这里,他为自己找到了第三位导师——斯宾诺莎。是这位大师解放了他的信仰,永远照耀着他的灵魂。后经过努力,他考取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高师学习的那段岁月,罗兰成了列夫·托尔斯泰狂热的追随者。托尔斯泰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勇于剖析自己、牺牲自己的精神赢得了他的尊重,而这位导师充满人性的行为和他热情的助人精神也深深震撼着这位年轻人。高师毕业后,罗兰幸运地被选去罗马继续深造,在那里他又结识了高贵的德国作家兼翻译家玛尔维达·封·梅森堡,这使他发现了生机盎然的德意志与许多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这期间,诗歌、音乐与科学这个三和弦,在不觉中与另一个三和弦——法兰西、德意志,还有意大利,融为一体,欧洲精神已然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年后,罗兰回到了祖国,先在高师任音乐史教师,而后,于1903年在索邦学院授课,期间,罗兰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些学术著作,并发表了一些有关现代音乐家评传类的文章。在初为人师的几年里,他的人生阅历大为增长。这位孤独者,开始同学术界以及上流社会打起交道来。他还不时去德国、瑞士、奥地利及他喜爱的意大利旅行,这便为他通过比较而获得新知识提供了好机会,并使其在自己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现代文化视野。 这位艺术家渴望有所作为,他对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但其内心世界却一直保持独立自由。他意志坚定,虽然总是竭力帮助他人实现愿望,但却并不听从别人的摆布。由于人性的弱点,他与别人的合作总是令他感到失望,人民剧院由于竞争而失败,他为人民大众创作的戏剧无果而终,他的婚姻也破裂了。但他从未失去对理性的坚持。在失望中,罗兰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系列伟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使他化悲痛为力量,从艺术中获得生活勇气。于是,他离开剧院,放弃教职,从这个世界隐退。在十年的孤独生活中,他创作出了一部从道德意义上讲比现实更真实的作品,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它将罗兰那一代人的信仰变成了行动。 这位在寂寞与孤独中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创作当中的艺术家年近50岁之际,赞扬之声突然如潮水般向他涌来。1912年,他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1914年,却已成为誉满世界的名人。在人们的惊呼声中,他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领袖。从1914年起,罗曼·罗兰就只为他的理想而存在和斗争。他不再是一位作家、诗人、艺术家和一个孤独的存在者,他是灾难深重的欧洲的声音。他是“欧洲的良心”。 如果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那么罗曼·罗兰就是这部史诗的缔造者。相信读者可以透过本书,去感受罗曼·罗兰这位大器晚成者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激情,感受其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