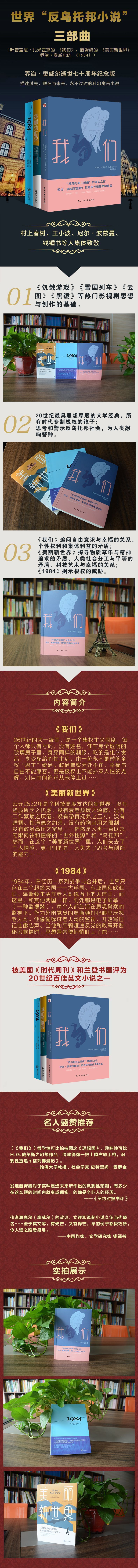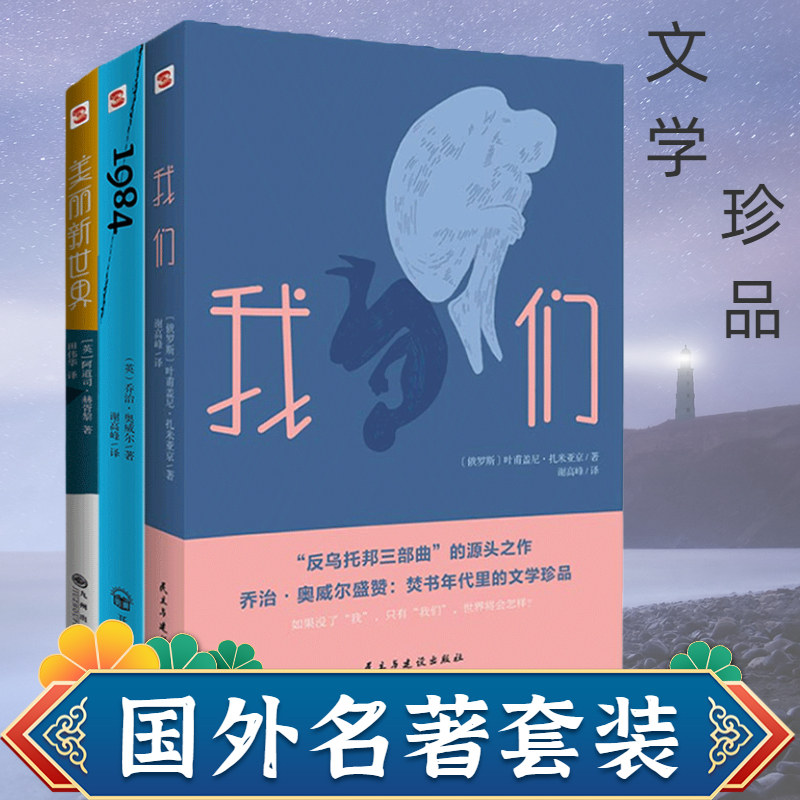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144.6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
ISBN: 9787510880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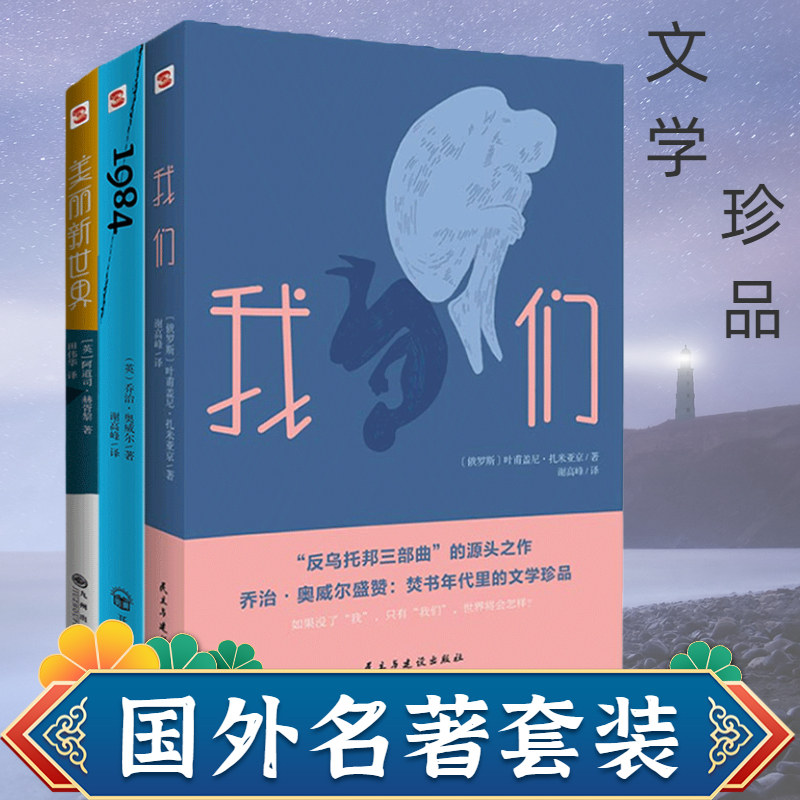
1、《我们》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以其风格独具的民间口语叙述文体和幽默讽刺的笔墨驰誉文坛.扎米亚京一生追求自由,这使得他不容于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苏维埃政权,被迫流亡法国,最后客死巴黎.主要作品有《我们》《一个外省传说》《岛民》《渔夫》《罗斯》等. 2、《198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原名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 奥威尔生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自幼同情悲惨的印度人民;少年时被派到缅甸做警察,又开始同情悲苦的苦役犯。20世纪30年代,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被划入左派,被迫流亡法国。“二战”期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因肺病去世。 在颠沛流离的47年中,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有《1984》和《动物庄园》。 3、《美丽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一生创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赫胥黎出生于大名鼎鼎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天演论》的作者,父亲是英国小说家,哥哥是著名动物学家,弟弟是诺贝尔奖得主。
1、《我们》 2、《1984》 四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寒冷,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躲避阴冷的风,紧缩着脖子,快步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尘土关在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一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的宣传画,在室内悬挂显得太大了。画上是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何况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迎接仇恨周而实行的节约运动中的一部分。温斯顿的住所在七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有一块因患静脉曲张而造成的溃疡,因此上楼梯时爬得很慢,中途还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宣传画凝视着。它是这种类型的画,无论你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神总是跟着你。“老大哥在看着你”,下面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圆润的声音正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长方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旋转了一个开关,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弱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能听得清。这个装置(叫作电子屏幕)可以放低声音,但没有办法彻底把声音关闭。他走到窗边。他的身体瘦小纤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的工作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皮肤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变得粗糙不堪。 外面,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看上去仍然显得很冷。下面的街道上,阵阵的小旋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闪耀,天空也蓝得刺眼,可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外,似乎一切都失去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能够看到街道的街角向下凝视。正对面的房子上就有一幅,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停地拍打着,把“英社”这个唯一的词汇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展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掠过,像只蓝色的瓶子一样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又划了道弧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倒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子屏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着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子屏幕能够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超过极低的私语,它都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他就既能被听到,也能被看到。当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你无法得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多长时间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进某条电线,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始终都在监视着每个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接上你的那条电线。你必须生活——真真正正地生活,从已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在一个设想之下,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会被听到,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是在黑暗中,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子屏幕。这样比较安全,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是背部,也可能会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这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一幢伫立在肮脏地带的白色的、巨大的建筑物。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里就是伦敦,一号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机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以便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破败的19世纪的房子,墙身用木头架子撑着,窗户上封着纸板,屋顶上盖着波形板,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被zha弹炸过的地方;还有那zha弹清理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肮脏的居民区,像鸡笼般的木板房。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缺少背景的、光亮的画面(其中的大部分不可理喻)以外,他童年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作“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有着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幢巨大的、由闪闪发光的水泥所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建筑,一层接着一层,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 …… 3、《美丽新世界》 第一章 一座灰楼,不高,就34层。门口有几个大字:中央伦敦培育所与条件设定中心,盾形纹章上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同一,稳定。 一楼有个大厅,是朝北的。窗户外头,整个夏天都是冷的,屋里却热得像赤道,一束刺目瘦弱的光从窗外射进来,贪婪地寻找着某个身披褶衣、平躺着的人形,某个一身鸡皮疙瘩、面色苍白的学者的轮廓,却没有如愿,找到的只有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镍和散发着惨白色的光的瓷器。与冰冷为伴的只有冰冷。工人们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手上戴着惨白色的手套,是死尸才会有的那种颜色。光冻住了,死了,成了鬼魂。只有在显微镜那发黄的镜头管下才能看到某种色彩浓艳的有生命力的物质,这种物质呈黄油状,看上去十分美味,躺在一长排一长排光亮的试管中,在工作台上朝远处延伸开去。 主任推开门,说,“这就是受精室。” 培育与条件设定中心的主任进屋的时候,300个孕育员正俯在仪器上,屋里一片寂静,几乎听不到呼吸的声音,有的在走思,有的在瞎嘟囔,有的在吹口哨,还有的在专心做事。有一群新来的学生,年纪都不大,一张张粉色的小脸,都很稚嫩,没什么经验,陪着十二分的小心,奴性十足地跟在主任屁股后头。每人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不管什么时候,伟大领袖说了什么话,都会像疯了一样赶紧记下来。这些话可都是伟大领袖亲口说的。这样的特权可不容易享受到。中央伦敦培育所与条件设定中心的主任总觉得必须亲自带着新学生们参观各个部门才行。 他向他们解释:“就是让你们有个大概的了解。”工作要想做得出色,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必须要对某些事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要想过得幸福,做社会良民,也要了解这些东西。因为谁都知道,美德和幸福源于细节,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精通是一种罪恶。哲学家不是社会的脊梁,锯木工和集邮者才是。 他用和蔼却又透着一点威胁的口气说道:“明天你们就正式上岗了。没时间了解大概的情况了。另外……” 另外,这是一种特权。把伟大领袖说的话记在本子上是一种特权。男孩子们疯狂地在本子上记着。 主任是个高个子,长得很瘦,身材却很挺拔,进了屋。他有一个长下巴,一口大龅牙,不说话的时候刚好能被他那红润饱满、曲线分明的嘴唇包着。老吗?年轻吗?30岁?50岁?55岁?说不好。今年是福特632年,社会安定,没人问这个,也没人想到问这个。 “我想从头说起,”中央伦敦培育所与条件设定中心的主任说话了,那群新来的学生又狂热了些,在本子上记着他的意思:从头说起。“这些,”他大手一挥,说道,“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隔离门,指着一排排编好号的试管向他们解释,“这是本周才到的卵子,必须保持在血液的温度,而非精子的温度,”这时,他打开另外一道门,说道,“必须保持在35度而不是37度。血液的温度会让它们丧失生育功能。”圈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种来的。 铅笔急匆匆地在纸上划着,字迹潦草,写了一页又一页,主任还在孵化器上靠着,简单地对他们说着现代受精过程,先说的当然是手术——“自愿做手术,不但有利于社会,更能让个人得到一笔相当于6个月薪水的奖金。”接着讲了保持剥离卵巢存活、活跃发展的技术,对最佳温度、最佳盐度及最佳黏度的考虑,提到了存放剥离成熟卵子的液体,又把学生们领到工作台那边,让他们看这种液体从试管中抽取的过程,怎样一滴滴地流到经过加温处理的显微镜的玻璃片上,怎样检查液体中卵子的异常情况,卵子怎样计数,怎样转入一种特定的有孔容器中,这个容器怎样浸入一种含有自由游动精子的热乎乎的肉汤中——他强调肉汤中的精子的密度至少为每立方厘米10万,浸泡10分钟后,怎样从液体中取出容器,再次检查里面的东西,如果发现有的卵子尚未受精,怎样再浸泡一次,如果有必要,就再泡一次,受精卵怎样流回到孵化器中,留下阿尔法们和贝塔们,直到最后入瓶,而伽马们、德尔塔们和伊普西龙们要等到36个小时以后才能再次被取出,进入“波卡诺夫斯基程序”。 主任重复道:“波卡诺夫斯基程序。”那些学生赶紧在小笔记本上这几个字的下面划了一道横线。 一个卵子,一个胚胎,一个成体,这是一种正常的生长状态。但一个波卡诺夫斯基化了的卵子能发芽,能增殖,能分裂。这样的一个卵子能长出8到96个不等的芽,每个芽都能长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胚胎,每个胚胎又能长成一个正常尺寸的成体。以前,一个卵子只能长成一个成体,现在却能长成96个。这就是波卡诺夫斯基程序。 中央伦敦培育所与条件设定中心的主任最后说道:“从本质上讲,波卡诺夫斯基程序由一系列对生物发展起抑制作用的因素组成。我们制止正常的生长状态,但有悖天理的是,卵子的反应竟是发芽。” 卵子的反应竟是发芽。铅笔们忙活开了。 他用手一指。一条缓慢移动的传动带上,满满一架子试管正在进入一个大的金属柜,另外一满架子试管正在露头。机器发出微弱的咕隆声。他告诉他们,这架试管通过金属柜要用8分钟。一个卵子能承受8分钟的X光的强力扫描。有几个死掉了,剩下的,最不敏感的那些会一分为二,大部分会长出4个芽,有些能长出8个,所有的卵子都会被送到孵化器中,芽会在那里生长,两天后,突然被冷冻,被冷冻,被制止。2个变4个,4个变8个,芽上轮流长芽,长芽后灌酒精,一直灌到快要死掉的程度,然后,芽的裂变继续进行,芽上长芽,芽上长芽,长个不停——以后给予致命性的制止——然后撒手不管了,让芽们踏踏实实地生长。此时,最初的那个卵子就能痛痛快快地长成8到96个不等的胚胎——这是自然界中一个神奇的进步,我想你们都会认同我这种说法。一卵双胞——却跟以前的那种胎生方式,双胞胎或者三胞胎,卵子偶然分裂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这个一次能分裂二三十个,八九十个。 主任重复道:“八九十个。”然后伸出两只胳膊,好像在分发奖金。 有个学生蠢透了,竟问这么干有什么好处。 主任猛地一个转身,看着那个学生说:“我的好孩子!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吗?”他抬起一只手,神情严肃地说,“波卡诺夫斯基程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批量生产符合标准的男男女女。一家小型工厂的全部工人仅由一个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化了的卵子就能搞定。 “96个一模一样的多生子操控96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那声音兴奋得都要发抖了。“你们能知道你们处在什么位置。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引用了世界国的格言:“社会,同一,稳定。”多棒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化,整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整个问题被标准化的伽马们、永不变化的德尔塔们和一模一样的伊普西龙们解决掉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终于适用于生物学了。 主任晃晃脑袋,说道:“可是,哎呀!我么并不能无穷无尽地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化。” 96个好像就已经是极限了,72个算是平均数,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配对时,尽可能多地生产出标准化的多生子——这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成绩,甚至连做到这一点都很困难。 “因为在自然界中,200个卵子的成熟期是30年。但我们目前要做的是稳定此刻的人口数量。花费多于1/4个世纪的时间零星生产几个多生子——这么做有什么用?” 显然毫无用处。但帕斯纳普技术大大加速了成熟的过程。他们有把握在两年内生产出至少250个成熟的卵子。受精,再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化——也就说,乘以72,就能得到差不多1.1万个兄弟姐妹,150批一卵多生子,年纪都一般大,都在两年内出生。 “特殊情况下,我们能让一个卵子为我们生产出超过1.5万个的成年人。” 这时候,有个留着金发、面色红润的小伙子刚好经过这里,主任冲着他打了个手势,喊了声:“福斯特先生。”那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过来了。“能跟我们说说一个卵子的生育记录吗?” 福斯特先生犹豫都没犹豫,张口就说:“1.6012万个,189批一卵多生子。不过,当然了,”他哇啦哇啦地接着说了下去,“有些赤道培育中心的成绩要好得多。新加坡的产量往往保持在1.05万个以上,蒙巴萨的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7万个的指标。但他们先天条件优厚,这么比未免有失公允。你们要是能够见识一下黑人卵子对脑垂体的反应就好啦!习惯了同欧洲卵子打交道,黑人卵子的反应肯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不过呢,”他补充道,“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还是想打败他们。我眼下正在培育一种叫做德尔塔加的卵子。只干了18个月,却早已培育出了1.27万个孩子,有的换了容器,有的还处于胚胎状态,势头很猛,打败他们不在话下。” 主任拍着福斯特先生的肩膀,大叫一声:“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劲头儿!跟我们来吧,给这些孩子传授传授你的专业知识。” 福斯特先生谦虚一笑:“乐意效劳。”一行人随即离开。 装瓶室里忙而不乱。大母猪的腹膜片正新鲜,即将被切割成合适的尺寸,正坐着小电梯从下层地下室的器官库里冲上来。先是嗖嗖直响,而后咔嗒一声!电梯门开了,装瓶室流水线上的工人只需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腹膜片,塞进瓶中,弄平整,这一系列的动作完成之后,一排排的瓶子才开始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传送带离开,嗖嗖,咔嗒!又一块腹膜片从下面蹿了上来,等着被塞进另外一只瓶子——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传送带上的下一只瓶子。 紧挨着流水线工人的是注册员。流水线继续前进,一个接一个的卵子从原来的试管中移入更大的容器中,腹膜内壁被熟练地切开,桑椹胚准确归位,注入碱盐溶液……此时,瓶子已经过去,下面就是标签员的事了。遗传状况、受精日期、波卡诺夫斯基组织身份——详细情况都从试管上转移到了瓶子上。这回就不是无名氏了,而是有了名字,有了身份。流水线慢悠悠地继续朝前移动,穿过墙壁上开的一个洞,缓慢进入社会身份预定室。 一行人进了屋,福斯特先生快活地说道:“索引卡片共计88立方米。” 主任补充道:“相关的信息都有了,并且每天早晨都会更新。” “并且每天下午都会整理。” “他们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仔细分析。” “个体多得很,还要分析这个性质,那个性质。” “按照这样那样的数量进行分配。” “随时保持最高的转瓶率。” “没有预料到的消耗会得到及时补充。” 福斯特先生重复道:“及时补充。你们要是知道上次日本大地震过后我加班加了多少时间就好啦!”他快活地大笑,随后又晃了晃脑袋。 “社会身份预定员把数据交给受精员。” “受精员交出前者索要的胚胎。” “瓶子送到这里商定社会身份预定的具体情况。” “之后送到胚胎库。” “我们现在就去那里。” 福斯特先生推开一道门,领着大家走下一组楼梯,进入地下室。 温度高得仍然像在赤道。他们朝下走,光线越来越暗。两道门,外加一个两道弯的通道,确保一丝一毫的阳光都不会透进地下室。 福斯特先生推开第二道门,幽默地说道:“胚胎就像电影胶片,只能承受红光的照射。” 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些学生此时正跟着他走进那个又潮又湿的地下室,里头黑灯瞎火的,但那种黑暗是可见的,并且真的是红色的,就像某个夏日的午后,闭上眼睛时,眼前的那种黑暗。一排又一排、一层又一层的瓶子鼓起的侧面,就像无数颗红宝石,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而在这数不尽的红宝石中移动着的,是长着紫色眼睛、带有一切狼疮症状的男男女女那暗红色的鬼魂。机器的嗡嗡声和咔嚓声微微搅动着空气。 主任懒得说话了,吩咐道:“福斯特先生,跟他们说几个数据。”福斯特先生巴不得要跟他们说几个数据呢。长220米,宽200米,高10米。他指指脑袋上头。那些学生就像喝水的小鸡崽儿那样抬头望着高处的天花板。 …… 1、《我们》 一个关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寓言故事 思考和警示反乌托邦社会,为人类敲响警钟 如果未来没有了“我”,只有“我们”,世界会变得怎样? 如果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没有幸福的自由.人们该怎么办? 如果反抗极权统治犹如飞蛾扑火,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 2、《1984》 ★20世纪杰出的社会寓言小说!“乔治·奥威尔风格”的代表作! ★被美国《时代周刊》和兰登书屋评为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之一。 ★名家全本翻译无删减,入选英、美、德、法等多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全球累积销量超过5000万册,拥有超过62种语言译本,风靡110个国家。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超越时代的可怕预言! 3、《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是20世纪的伟大经典之一,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著的《1984》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金所著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在世界影响深远。 ★永不过时的科幻寓言小说,充满社会性、警惕性和哲思,《云图》《黑镜》等热门影视剧思想与创作的基础。 ★一部饱受争议但畅销半个多世纪的经典之作,赫胥黎被指责为、\\\\\\\\\\\\\\\"色情文学作家,《美丽新世界》在一度被禁的时期,仍出版了近60个版本,销量近300万册。 ★20世纪英文小说评选中排名第五;英国《观察者》和BBC的阅读调查,《美丽新世界》居阅读排名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