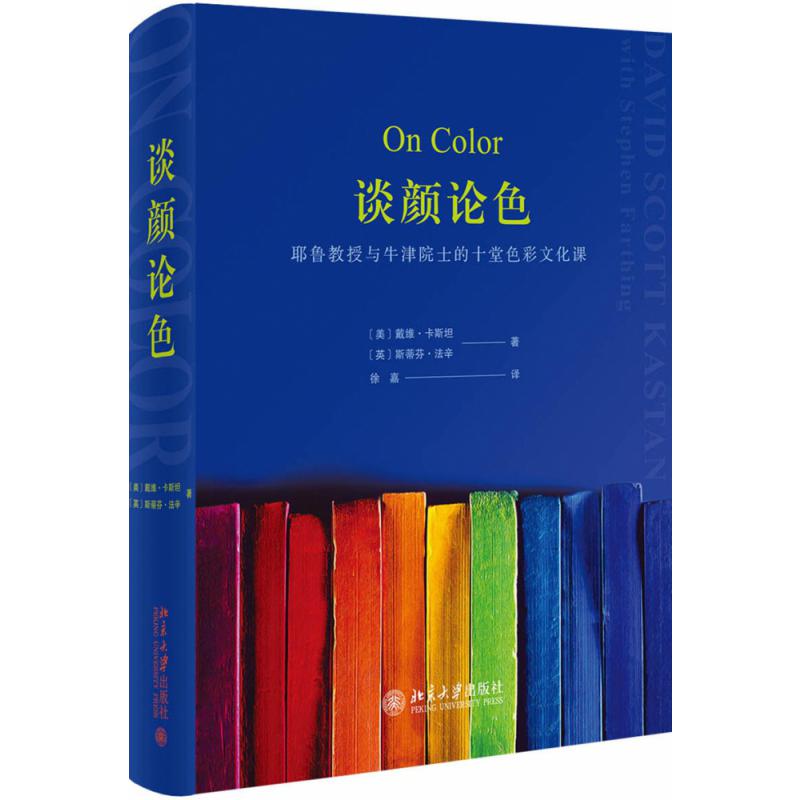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49.38
折扣购买: 谈颜论色:耶鲁教授与牛津院士的十堂色彩文化课
ISBN: 978730131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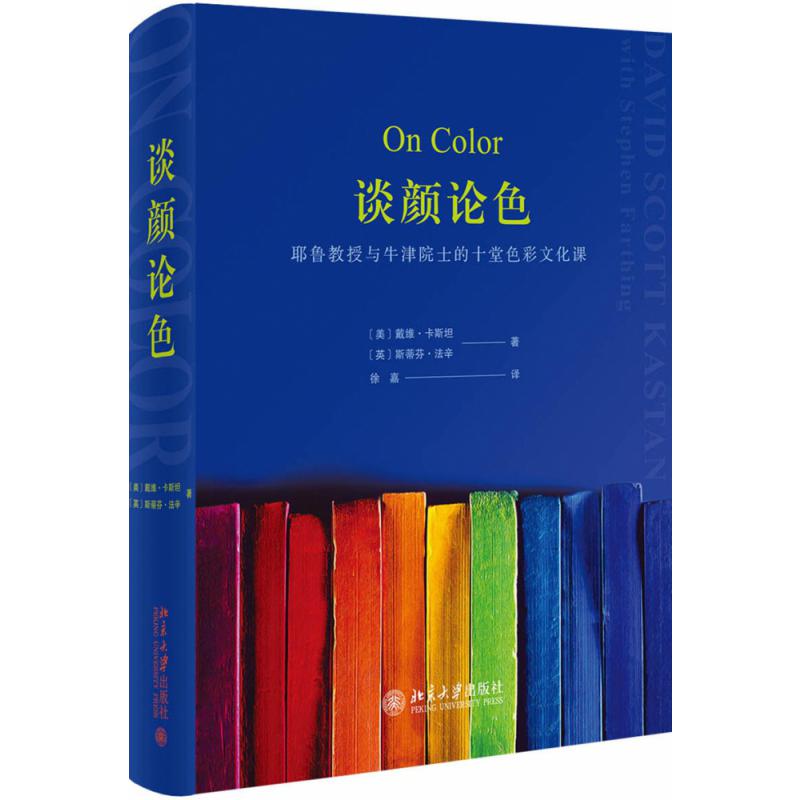
戴维·卡斯坦 | David Scott Kastan 当代莎士比亚专家,声誉卓著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者,耶鲁大学George M. Bodman英文讲席教授,《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主编,担任阿登版莎士比亚系列(Arden Shakespeare)联合主编的美国学者。 斯蒂芬·法辛 | Stephen Farthing 英国当代著名画家,皇家艺术院(RA)会员,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堂荣休院士,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罗斯金艺术学院(1990年至2000年)、伦敦艺术大学(2004年至2017年,执掌Rootstein Hopkins绘画研究讲席)。
解析“彩”虹 即便彩虹之“彩”也是如此。这道拱形可见光谱在空中从红到紫平滑渐变,完美地呈现出何谓色彩。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看到彩虹,写下了著名诗篇:“当天边彩虹映入眼帘,我心为之雀跃”(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这种欢喜,并非他一人独有。 对于约翰˙济慈而言,彩虹所触发的情感则更加强烈。“天上有一条可畏的彩虹,”他在诗歌《拉米亚》(Lamia,意为“糟糕”)中写道。Lamia并非我们现在使用的贬义,而取其原始含义,即“令人敬畏的”。济慈担心自然科学企图“解析彩虹”,会将彩虹简化为“常见事物的沉闷目录”中的一个条目。理解会祛除敬畏。1817年末,英国画家本杰明·海顿在他的伦敦工作室举办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晚宴,在晚宴中,济慈急匆匆地背书了友人查尔斯·兰姆的观点,认为艾萨克·牛顿“将彩虹缩小为棱柱色”,将彩虹的诗意毁灭殆尽(海顿新作《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群像里露出了牛顿的脸,因而引发了这则评论)。 对于牛顿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而言,牛顿的光学发现令人不忿,如诗人托马斯·坎贝尔所抱怨,它掀起了“魔幻的面纱”。但是,彩虹的璀璨色彩奇迹超越了科学阐释。另一位诗人詹姆斯·汤普森则对牛顿“永恒的大弓”一词相当沉迷。对汤普森而言,相比牛顿所解析的彩虹,牛顿本人才是“足可敬畏的”(取济慈Lamia的原意)。 学界逐渐意识到,用科学术语来阐释彩虹——由阳光反射和折射通过水滴产生、并从特定角度观察的视错觉——永远不会让彩虹丧失惊叹和欢愉(图3)。更有甚者,解释彩虹的科学之说自身也创生出了惊喜:没有两个人能看到完全相同的彩虹,即使两个人站在一起,即使他们看的是同一条彩虹,但每位观察者的一只眼睛所看到的彩虹和另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当光线照射到不同的水滴,彩虹就会不断变形。彩虹不是一个物体,它是一幅图景——一幅基于阳光、水、几何形状和复杂视觉系统所构建的图景。彩虹和颜色一样,即便加以解析,也仍不失为一个奇迹。 真正“令人敬畏的”、“曾经挂在天上的”彩虹,是大洪水之后上帝与人类盟约的象征。“我把虹放在云彩中,”作为立约的记号,保证再也不会“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创世纪》9:13)。彩虹的光谱是明亮颜色的完美组合,乃是天地和解的明确承诺。如今,看到彩虹,我们最有感受到的是快乐,而非敬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评论道:“我们飞快浮起微笑,迎接彩虹。”)对济慈而言,这道令人敬畏的和平的彩虹,虽然是一件颜色排列永远不变的礼物,但仍蔚为奇观。 虽然这么问可能有些忘恩负义,但是——这件礼物有多大呢?有多少种颜色?答案很明显:七种。众所周知,牛顿在彩虹无缝联结的连续体中看到了七种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广为人知的顺口溜Roy G. Biv(译者注:彩虹颜色顺序的七个英文单词首字母)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彩虹的顺序,在英国,这个顺序也被记作:“约克家族的理查白白地输了战争”。到了我们这个历史上无忧无虑的消费主义时代,这句话在英国已经变成了“约克的英国人(指的是英国的一家糖果厂,现在被雀巢公司收购了)实现了价值最大化”(译者注:这句话的七个英文单词首字母也是彩虹颜色顺序的七个英文单词首字母)。但无论我们如何记忆彩虹的颜色,几乎没有人(炼狱中的但丁显然是个例外)看到过七种颜色。牛顿起先也没看到七种颜色。 在1675年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的信件中,牛顿承认他的眼睛“不够犀利,分辨不清颜色。”他曾看出彩虹有11种颜色,常常又只看到五种颜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举目再看,数目又不相同。全音阶有七个音符。神创世界用了七天。彩虹是宇宙和谐的标志,所以它必定是七种颜色——牛顿因此在红色和黄色之间加上(看出?)了橙色,又在蓝色和紫色之间加上了靛蓝。虽然在《约翰王》里,莎士比亚说“给彩虹添上一道颜色”“实在是浪费而可笑的多事”(4.2.13-16),但对于牛顿来讲,有必要在他所看到的彩虹上再增加两个颜色。于是乎,我们的七色彩虹诞生了,与其说它出自科学,不如说它似乎更凭信仰。 亚里士多德和大多数古人只在彩虹中分辨出三种颜色。两千多年后,约翰˙弥尔顿看到的似乎也是如此。在《失乐园》中,弥尔顿用了“三色弓”一词,但必须承认,他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看到了四色彩虹。提香看到了六色(见提香画作《朱诺和阿古斯》)。很明显,史蒂夫˙乔布斯也看到了(看看苹果公司的苹果标志吧!)。 维吉尔显然更眼聪目明,他认出了“千种颜色”,而珀西˙贝丝˙雪莱则看到了“百万种颜色的弓”——但是,他过于浪漫主义了。无论如何,牛顿基于信仰而看出的七色彩虹沿用至今。如今,我们深信,彩虹是由“七种和谐的颜色”组成的,正如诗人罗伯特·布朗宁所写,他使用的分词“和谐的”(choreded)取自牛顿做的的音乐上的类比。事实上,无论彩虹是否有七种颜色,我们看到的都是七色彩虹。所见即所想。 《华尔街日报》“假日甄选礼品书”,耶鲁大学授权中文版! 颜值内涵兼具,一书领略耶鲁牛津两大名校的智识学养! 一流学者与一流画家的跨界合作,耶鲁教授与牛津院士双剑合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