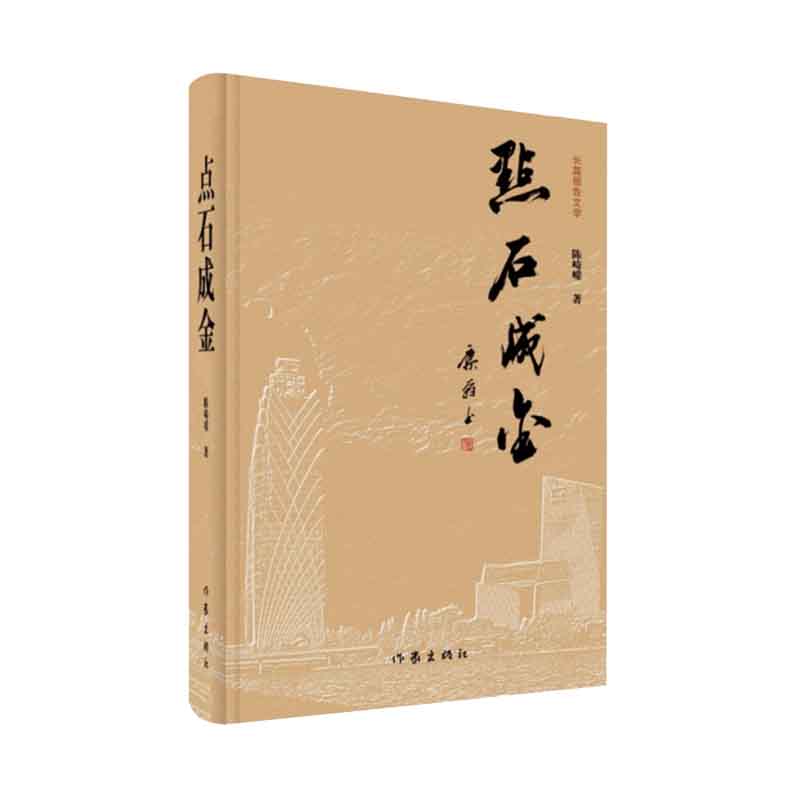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2.80
折扣购买: 点石成金
ISBN: 9787521219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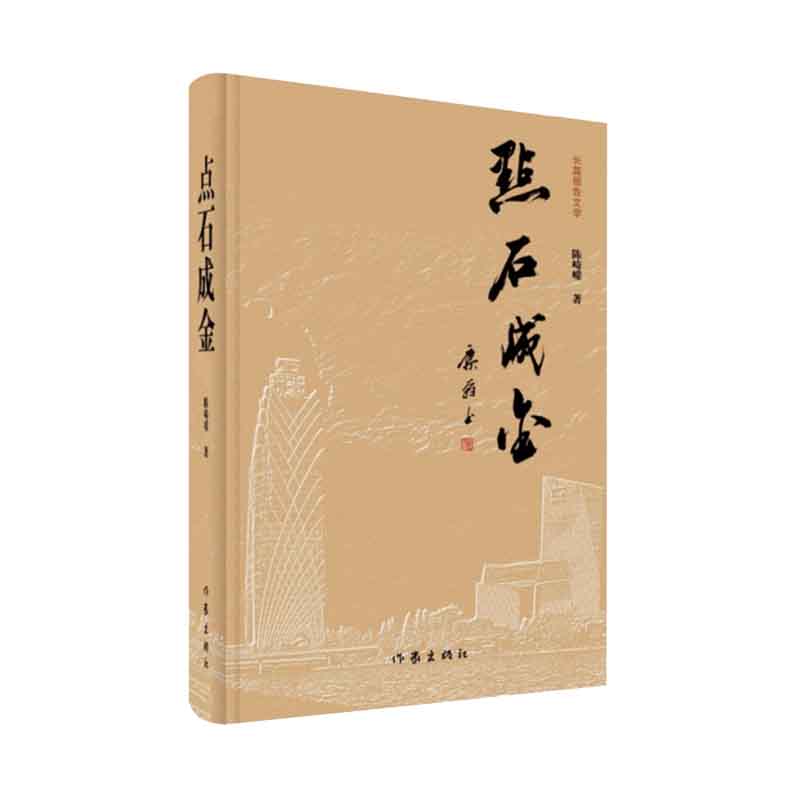
陈崎嵘,男,1955年9月出生,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浙江地方任职,2001年调任中国作协,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曾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诗文,主编或创作出版作品集有《中国小商品城纵横观》《中国历代人才诗选》《诗意的学习》《江南北国诗痕》等。
第一章 运河古镇孕育的初心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李白 定格:1972年12月30日的九江 张毓强怎么也不会想到,28年后,他创建的企业居然会收购眼前这个庞然大物——九江玻璃纤维厂。 那天,经过30多小时的长途颠簸,年仅17岁的懵懂少年张毓强终于走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坐落于九江市前进东路44号的九江玻璃纤维厂门口。 张毓强肩背着电动机和肥皂箱,顺便用棉衣袖口擦了一把自己额头上渗出的热汗,一边慢步走着,一边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九江玻璃纤维厂。 厂区正门朝北,大门用方钢焊接而成,显得分外坚固厚重。门两侧竖立着2根水刷石装饰的方柱,方柱两边是一道八字形围墙。围墙高约2米,其间隔着一根根造型水泥柱,形成波浪起伏之势。进得大门,一条20米宽的大道通向纵深。道路两旁,长着高大茂密的柏树,仿若站着两队威武雄壮的卫兵。他再往前走五六十米,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有个直径十来米的花坛。花坛正中,矗立着一尊伟人挥手的塑像。塑像用金黄色玻璃钢制作,在朝晖中熠熠生辉,给张毓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走在厂区马路上,映入张毓强眼帘的,是白茫茫的一片锯齿形厂房,拉丝车间、纺织车间、机修车间,一个连着一个。还有红砖砌就的办公楼、灰墙围挡的堆煤场、白灰涂抹的锅炉房和水塔,居然还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 后来,张毓强才知晓,九江玻纤厂是直属国家建材部的16家大中型国有玻纤企业之一,筹建于1958年。当时全厂约有3000名职工、78台坩埚,年产玻纤1000吨。生产区和职工生活区面积相加近500亩,约等于当时3个生产队耕地面积之和。 一个远在千里之外桐乡县石门镇东风布厂的挑水工兼采购员张毓强,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天哪!工厂原来可以这么大、这么办?他觉得自己的思维一时发生短路,根本来不及仔细观察,也没有心思欣赏。他只是惊讶地张开嘴巴,自言自语地絮叨着:大,大,实在是大!似乎除了一个“大”字,他竟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家企业,更无法确切表达此时此刻自己那种被震撼的心情。那时的张毓强,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小名“毛毛”,还没有掌握后来那么多词语,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话,或作报告。更不会想到,28年后,他居然成为这家企业的收购者、掌舵者。 那天是1972年12月30日清晨。对,是12月30日清晨。即使后来时间匆匆逝去,即使张毓强后来经手过无数个项目,但张毓强对这个日子记得死死的、牢牢的,仿若嵌入他的骨髓里,融化在他的血液中,根本不需刻意去记忆它。只要张毓强一想到九江玻纤厂,这个日期就会自动跳出来,闪烁在他的脑海屏幕上。 张毓强清晰记得3天前离开故乡石门轮船码头的情景。 冬季的日头早已偏西,并不强烈的夕光洒在古运河两岸低矮的水阁楼上,也洒在旧石板铺就的码头上。码头紧挨着大桥砣,一些无事可做的居民正倚着桥栏晒太阳。一大一小、凹凸斑驳的河埠头构成众人眼中的轮船码头,而那些长满了绿苔的石板台阶,说明着年代的 久远。 一艘“喜鹊班”客轮在人们的喧闹声中慢慢靠上码头。顿时,码头显得热闹起来。一拨人上岸,一拨人上船。个头不高、身材敦实的张毓强,跨过32级台阶的南高桥,随着拥挤的人群,好不容易踏进船舱。他肩膀上搭着一根绳索,绳索两端系着两件重物。悬挂在胸前的是一箱沉甸甸的肥皂,紧贴后背的是一台更加沉甸甸的3千瓦电动机。明眼人一看,这两件物品,少说也得毛重两百斤。因而,张毓强身上那件半新旧棉袄坎肩,被深深地勒出一道凹槽,绳索似乎嵌进了张毓强尚且稚嫩的肩膀。 “呜呜——”“喜鹊班”客轮在众人注目中缓缓驶离轮船码头,驶向附近的长安镇。石门镇不通铁路,自然没有火车。镇上有个传说,当年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时,非常看重石门镇风水,特意绕了一个大弯,从石门穿过,故而形成著名的古运河石门湾,为这一带百姓带来上千年的便利。谁知清末开建沪杭铁路时,石门人担心那个莽撞的铁家伙会冲坏石门镇风水,强烈要求铁路绕道。这一绕,就把石门镇甩出了铁路时代。 传说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也无法考证。但迫使张毓强那天用2小时15分钟时间,绕道长安镇火车站上车,却是铁打的事实。 没有人为张毓强送行。这趟差本来是王鑑初的。王鑑初是张毓强的领导,也是张毓强走上社会后的启蒙老师,厂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王。老王不是一般的人,上过朝鲜战场,做过一号首长的报务员,见多识广。有空时会跟张毓强讲那些他闻所未闻的事体,也教他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张毓强对老王有点小崇拜。王鑑初说他有事去不了,指名让张毓强去。既然是领导兼师父的意思,张毓强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他曾听老王说起过,厂里决定生产玻纤丝,需要几台拉丝机。跟不少企业联系过,各家都没有货。后来,终于打听到九江玻纤厂仓库里躺着几台备用的拉丝机,辗转找人,才与九江玻纤厂供应科长彭毓泉联系上。对方答应可以按原价调剂给石门东风布厂,但外加了一个调剂条件:要1台电动机和20条肥皂。彼时,全社会物资匮乏,几乎所有商品都供不应求。电动机是了不得的大设备,国家计划分配。肥皂也是紧俏商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能购买半块。对方要的电动机,显然是厂里公用,这肥皂或许是给厂里工人用的?东风布厂托人找桐乡县二轻局特批,才把一台3千瓦的电动机和20条肥皂搞到手。 这些事,张毓强没有经手,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老王不知是真有事,还是想考验考验他?张毓强也不清楚。当年他毕竟才17岁,心思还单纯得很。换成眼下的小青年,恐怕还在父母面前撒娇讨钱吧?不过,张毓强已跟着老王出过好多趟差,还见识过当时最牛的南京长江大桥。在厂里算得上半个采购员,在镇上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所以,厂领导很放心。 张毓强出差路线图是这样的:在长安镇,爬上那列喘着粗气的快车,沿着沪杭线、浙赣线抵达南昌站,再在南昌站中转换乘慢车,向着遥远的九江市行进。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又临近腊月,上下车旅客极多。但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彼时,铁路少,车次更少,真正的“一票难求”“一座难得”。 旅客上下车简直像一场战斗。有的旅客背着行李从车门下不来,就干脆把行李从车窗口丢到月台上,然后紧跟着人蹦到地上。也有上车旅客恳求已在列车上的旅客帮忙,将行李从车窗口接一下,然后自己艰难地从车窗爬进去。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笔者曾无数次经历过,想必张毓强经历得更多。 可以想见,背着那么笨重行李的张毓强,肯定比一般旅客上下车更艰难更吃力。好在彼时张毓强年轻,有的是力气。力气大可能是张毓强小时候吃“毛蛋”吃出来的。所谓“毛蛋”,就是孵化不出小鸡小鸭的死蛋,据说营养蛮丰富。同时,张毓强个子不高,且十分机灵。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三下五除二,总算把自己和两件笨重行李弄上了火车。 张毓强买的是站票。站票,就是允许你上火车,找个站的位置 而已。 车厢内照例到处是人和行李。不要说座位,行李架上、过道上,连两节车厢连接处,都站满了人、堆满了物。车内弥漫着汗酸气和大蒜味,充塞着南腔北调的嚷嚷声,还有小孩被挤哭被吓坏的叫喊声。 好不容易,张毓强找到了一个可以允许站立的空间,与其他旅客前胸贴后背,根本没有移动腾挪的空隙。他吃力地将行李卸下肩,稍稍移开双脚,伸出右手拼命拉住头顶上的行李架,左手抓住座椅靠背一角,使自己得以在晃荡的列车上站稳。然后,他把电动机置放于自己胯下,再将那箱肥皂压到电动机上面。他担心别的旅客不小心碰坏了它俩。眼下,这俩家伙可是全厂的宝贝疙瘩。没有它俩,就换不回拉丝机。没有拉丝机,石门东风布厂就生产不了玻璃纤维。 没有座位,没有食物,更没有极其需要的水。张毓强忍住饿、忍住渴,滴水未进、粒米未沾,整整十六个半钟头,站到了南昌;然后,又以同样方式,用六个半钟头站到了九江。在南昌站转车时,张毓强利用换车空隙时间,在车站自来水管边,将自己的肚子灌饱水。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着南昌、九江前行,偶尔拉开喉咙吼一声“呜——”!这趟火车算是快车,但彼时的“快车”,车速也就每小时60公里左右。车窗外的一切景物,似乎都成为一种延时摄影般的慢镜头。它根本不理解张毓强此刻焦急的心理,也丝毫不顾及张毓强因劳累饥饿而从帽檐边和面颊上冒出来的汗珠。 时间实在太漫长了,漫长得有点浪费、有点遥远、有点恍惚。 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张毓强有足够时间想想故乡石门,想想自己少儿时期。 张毓强的家和厂都在古运河边的石门镇上。 谁都知道京杭大运河是隋朝隋炀帝征用百万民工开挖的。这条运河当年耗尽了隋朝国库里的全部银两,因而加速了隋唐的朝代更迭。但后来的历史书写者,仍给这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工运河以应有的评价。 石门镇四面环水,形似小岛,张毓强形象地把它称作“湖心亭”,镇上住着5000来个居民。古运河从北方逶迤流来,在张毓强家边拐了个120度的弯,形成著名的石门湾,然后往东流向嘉兴。不,这样说或许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张毓强家选在石门湾磊石弄。 磊石弄南北向,只有两三米宽。人们开玩笑说,从这边楼上伸出手去,能握住对面楼上人的手。 相隔磊石弄10来米,平行着一条寺弄街,是老石门镇的主要街道,约七八米宽,两边开着一些店铺,煞是繁华闹猛。丰子恺先生曾称之为“石门湾的南京路”。 磊石弄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它出奇地狭窄和附近寺弄街的闹猛,而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传说吴越两国曾在此盟约,磊石筑墙划界:磊石西侧属于越国,东侧属于吴国。当然,吴越两国早已灰飞烟灭,走入历史,但磊石弄却传了下来,且成为张毓强和乡邻们的家。宅基在原属“越国”的地界上,家门朝东开。跨出家门,就踏入“吴国”地面。一家人就这样整天穿越于“吴国”“越国”之间。 张毓强出生于1955年9月18日。与《松花江上》歌中唱的“九 一八”是同一天,仿佛从娘肚子里就带来家国情怀。一家三代、6口人、3张床,挤住在一个25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父母亲给张毓强取了个小名“毛毛”,这小名饱含着亲昵和喜爱。出生在古运河边上,毛毛的第一声啼哭与古运河的水声交织在一起,毛毛的第一滴眼泪与古运河的水流汇合在一起,毛毛是名副其实的古运河的儿子。 按照当下年轻人的星座说,张毓强与笔者同年同月同星座,笔者比张毓强早出生12天,都属于处女座。百度上说,处女座的人有三大特征,一是追求完美,二是有很强的自制力,三是务实。同时,容易固执己见。不知张毓强是否认可这些,窃以为对于笔者而言,还真有点意思。 笔者老家还有一种说法,此年出生的人属羊,羊是吃青草的。但9月18日已属初秋,水草丰美的春夏季早已过去,此时的羊,一生下来就得为自己储存过冬的干草,所以比较勤劳和辛苦。 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似乎成为张毓强人生照片的底色,拂之不去、洗褪不变。犹如染布一样,一旦当白布浸染上蓝色后,再也无法去除,只有加深加浓。 毛毛出生时,正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高潮期。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似乎与城镇居民关系不太大,但敲锣打鼓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却与毛毛家发生了直接关联。毛毛奶奶解放前在石门湾边上开办的一家饭店被公私合营,改名为“合作饭店”。虽 然,奶奶仍是这家“合作饭店”的合作者和主管人,但经营收入却归了公家。 说起这位奶奶,张毓强的神情有点类似于著名作家莫言,对奶奶充满了敬仰之情。据说,毛毛的奶奶出身于富庶之家,个性蛮强,认得一些文字。后来不知怎么看上了从绍兴迁居而来的一位镶牙医生,自作主张,把自己嫁给了这位相貌堂堂、家徒四壁的牙医,为此她还与父母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她竟自立门户,在石门镇上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全家一日三餐无忧。 追根溯源,张毓强的血脉里似乎流淌着奶奶的倔强性格和经商 基因。 当然,对于毛毛而言,爸爸妈妈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大。 爸爸是个手工业者。桐乡历史上盛产烤红烟,爸爸的工作就是为镇上供销社刨制烟丝。刨制烟丝这活带点技术性,是有先见之明的奶奶让他学的,工作自由度大,有点像个体户。收入比供销社一般职工略高,每月三四十元薪酬,有时甚至会有五六十元。这在彼时已算“高薪阶层”。 爸爸平时不苟言笑,喜欢看书读报、临帖写字,常年订阅《解放日报》,还买些《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书刊回家,自己读完,也让毛毛姐弟几个看看。 毛毛幼小时,长得白白胖胖,爱端一把小竹椅,远远地坐着,看爸爸刨制烟丝。只见爸爸先将一张张干烟叶的茎脉抽出,涂抹上红油和香精,叠成一大摞,放进特制的刨凳里。然后,快速推动手中的刨刀。随着节奏感极强的“哧溜”“哧溜”声,细长条的烟丝被刨刀切割下来,均匀地掉落在黄纸上,四周弥漫开烟丝呛鼻子的香味。彼时,爸爸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偶尔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并用爱昵的眼神看一下毛毛。毛毛长大后曾看见过一张自己与爸爸合影的老照片。在那张老照片中,爸爸抱着出生百日的自己,眉开眼笑。从中不难感受到,爸爸其实还是蛮喜欢自己的。 当然,这样的场景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里,爸爸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 最爱护毛毛的,自然是妈妈。妈妈从小由其大伯带大,大伯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教给毛毛妈妈很多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怎么做人,怎么接待客人,怎么扫地擦桌子等。妈妈记住了,后来作为家庭传统教育,又把这些传授给毛毛。妈妈觉得那些话很简洁,但很管用。妈妈一生勤劳节俭,早年在镇里蔬菜厂上班,工作上是一把好手,每年都被厂里评为先进。在厂里,她腌制榨菜、酱瓜、萝卜等,从天亮忙到天黑,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每天一下班,她就急匆匆回家,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妈妈对3个儿女,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心血,她省吃俭用,把钱都用在三兄妹身上。平时,妈妈把家里角角落落打扫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张毓强始终认为,他是在母爱里成长起来的,他的品行、性格更多地得益于妈妈,也更像妈妈:外刚内柔,外冷内热。就是人们常形容的热水瓶性情。母亲生性热情好客,把亲戚或邻居上门当作喜事,张罗这张罗那的。譬如说,张毓强参加工作时,自然是想挣点钱,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谁知后来因为做供销员,有客户到厂里,公款不能请客吃饭。有点口吃的老厂长大手一挥,说道:张、张、张毓强,你、你把客人领回去,让你妈、妈妈炒、炒、炒几个菜。钱、钱、钱嘛,先……先记账啊!张毓强自然知道,这记下的账肯定没有归还之日。但他还是乐颠颠地把客人往家里带。爸爸偶尔免不了说上几句,埋怨儿子给家里添麻烦,每月20.5元工资还不够请客吃饭,是倒贴钱。但妈妈每次总是非常热情,准备好菜好酒招待客人。 张毓强爱整洁爱卫生的习惯和喜欢结交朋友的脾性,大概源自他母亲。他对家庭那份深深的情感,主要也缘于妈妈那份深沉的爱。 如果没有后来一场飞来横祸,毛毛的童年大抵也就如斯。 那是张毓强一辈子难以驱除的伤痛记忆。 那次刻骨铭心的伤害,是由与毛毛家为邻的一位女鞋匠造成的。女鞋匠来自西施故里诸暨,以做鞋谋生。诸暨人纳鞋底的方法与众不同,先用锥子刺穿鞋底,然后将绳线穿进锥子顶尖的针眼,再用手劲向一侧勒紧。那天,才4岁的毛毛不知怎么的,竟蹒跚到这位女鞋匠身边,用稚嫩的目光盯着女鞋匠穿针引线的动作。女鞋匠根本没有意识到身边有个小孩站着,自顾自穿刺、引线、拔针。“啊”的一声,毛毛的左眼被疾飞而来的尖锥刺中,顿时血流如注,视线一片迷糊,疼得在地上打滚。 赶紧送到杭州抢救的结果是,毛毛的左眼球保住了,但从此左眼视力严重下降。女鞋匠自然满怀愧疚,但毛毛妈妈并没有过多责怪那位邻居,只收下了对方支付的8元医疗费,此后再不提及。有人替毛毛抱不平,但善良的妈妈认为,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要再难为人家啦。 左眼创伤除直接影响毛毛视力外,还带来诸多隐形的伤害。有小朋友羞辱他,毛毛开始切身感受到不被尊重的痛楚,性格因而显得比较内向,自卑感拂之不去,好胜心逆向生长。大人们开始叫他“小鬼大王”。毛毛经常带着一帮小伙伴玩“夺军旗”的游戏,一次次与“敌人”作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赢得胜利为止。彼时,他未必会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好胜心,后来会转化为正向的强大的心理力量。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经济和社会逐渐恢复生机。毛毛在父母的关爱下渐渐长大。那年秋季,毛毛成了石门镇一家小学的学生,并正式启用大名张毓强。这家小学距离著名漫画家、缘缘堂主人丰子恺先生创办的小学不远。 头3年的学习生活极其顺利。张毓强凭着自己的智商、记忆力和领悟力,成绩在班级里遥遥领先。他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张毓强喜欢做的事比较特别。譬如说,养小鸡养小鸭,养大后,让它们生蛋,然后他拿到街上去卖,把卖蛋得来的钱补贴家用。他还擅长抲鱼捉虾,时常弄些鱼呀虾呀改善伙食。他在家中养鸡养鸭,弄得屋内乱七八糟,臭烘烘的,姐姐和小弟都不喜欢。姐弟俩不喜欢没有关系,母亲倒是非常喜欢,有时还在餐桌上表扬他懂事、能干、会炒菜。 照例说,处在那个年龄段的张毓强,其实还是个小孩。但他却显得早熟和懂事。奶奶和妈妈平时给姐弟们一些零用钱,张毓强却把这些零用钱积攒起来。家中急需用钱时,他会把自己积攒的零用钱拿出来。每年中秋节,亲戚或朋友家送来月饼,母亲会分给一家人吃。张毓强则把这些月饼存放起来,等大家吃完了,他再把这些月饼拿出来分享。 转眼到了小学四年级,全国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一片“破四旧、立四新”浪潮中,各级各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开始所谓的“停课闹革命”。学校废弃了全部课本,课堂改为学习背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到晚上,老师就带着学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走村串户,巡回到各生产队呼喊“革命口号”。有一次,老师居然带着张毓强全班同学,步行五六个钟头到嘉兴,进行“大串联”。那次“串联”给张毓强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用妈妈给的1.2元零用钱,给家人买回来几只嘉兴粽子。 在这种似学非学的环境里,张毓强熬到小学毕业。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点石成金》以浙江桐乡振石控股集团发展历程为主要题材,以张毓强先生为主角,生动描写其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呕心沥血的奋斗史、勇攀高峰的创新史、先行先试的改革史,艺术展示中国企业家的胸怀视野、精神品格和个性魅力,塑造跨国企业家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