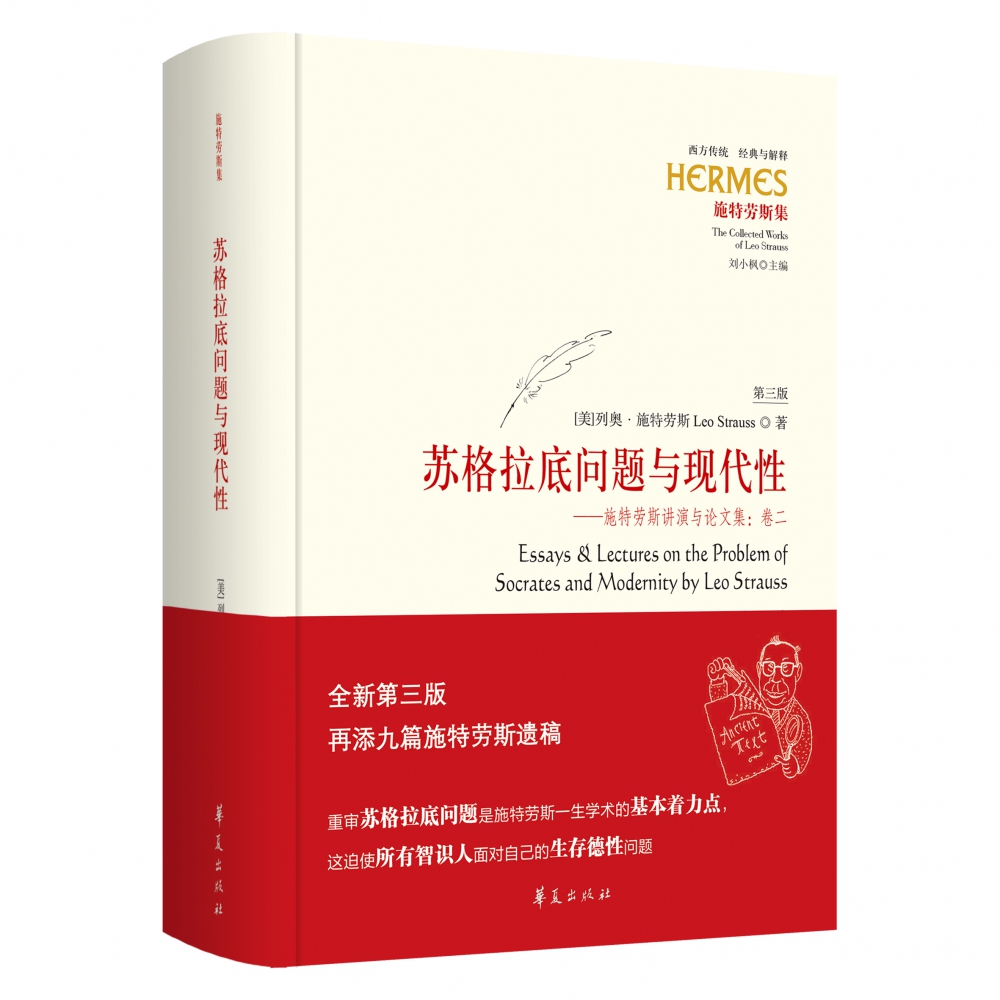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158.00
折扣价: 98.00
折扣购买: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三版)
ISBN: 9787522200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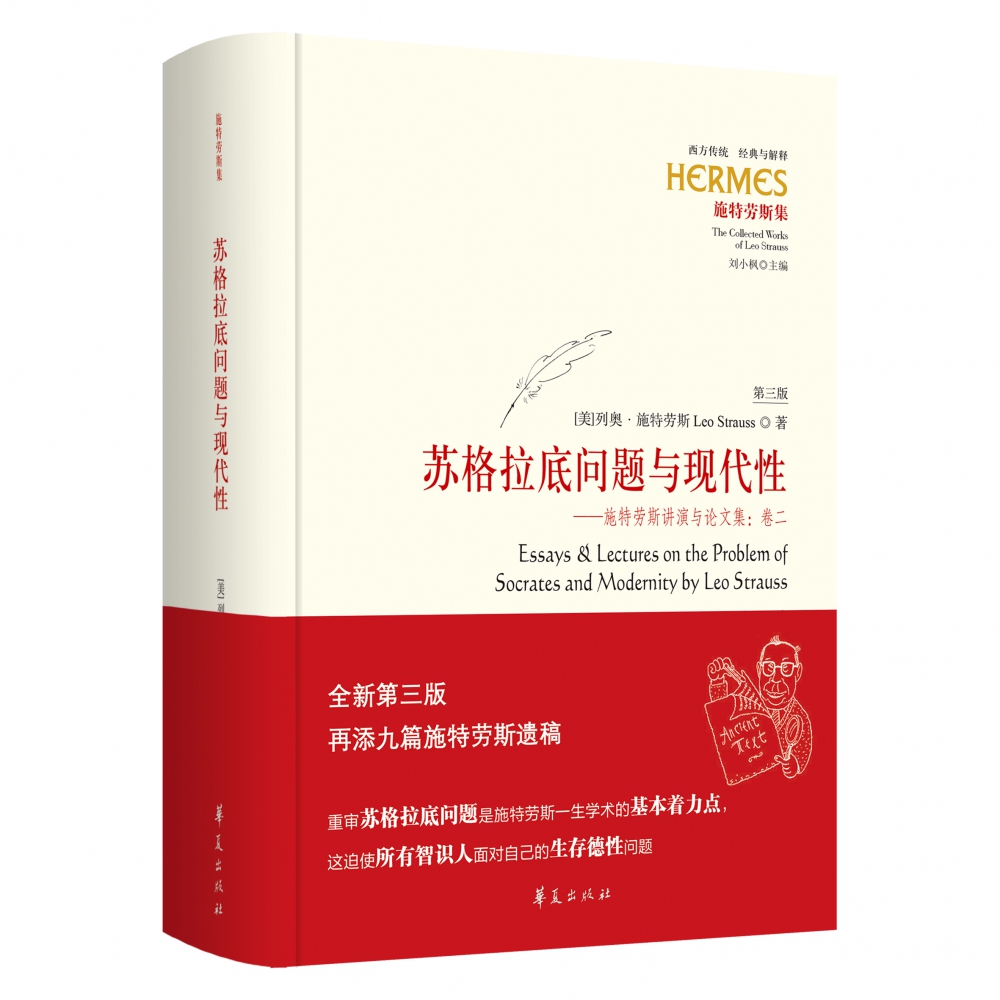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曾获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施特劳斯是由德至美的流亡哲人,在美国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死后却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的重要哲人。 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迫害与写作艺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哲学与律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等。
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 刘振译 我们正在寻找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件事情需要一些解释甚至澄清。我们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是为了达到对现代政治思想之本质的准确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要意图正是理解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我们必须自问,更容易也更充分的做法是不是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发达而成熟的形式,而非研究其萌芽形式。因为,一个事物的本质仅仅在其完成(perfect)状态中呈现自身。虽然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运用它却是有疑问的。因为,假设——比如说——当代思想在本质问题上比——比如说——17世纪的思想更发达,这或许是草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回到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首先不是为了比我们通过研究当代思想更好地理解那时的思想,而恰恰就是为了理解它。因为,在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否存在之前就问它是什么,这是徒劳的。或许可以被正确地称为现代政治思想的某个东西的存在,受到了质疑。 当然,我们所说的现代政治思想不仅指当代思想,也指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来四个世纪的思想。因为,我们通常将狭义上的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部分,正如我们也这样划分一般的历史:古代的、中古的(medieval)和现代的。这种做法表明,我们假设,姑且不论彼此之间的一切差异,所有现代政治学说都有某种共同点,这使我们可以将它们放到一起,将它们看作有别于中古和古代学说的一个整体。我认为,我们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已经在挑战这个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假设。卡莱尔(A. J. Carlyle)博士表达了如下意见: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至法国革命的理论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延续的,虽然形式有变化,内容有改变,但它的基本观念是不变的。 卡莱尔博士这个观点的题中之义是,17、18世纪政治思想与中古政治思想没有根本区别。可是,这就意味着,至今流行的认为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现代时期——正如一般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时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卡莱尔博士通过提出上述观点攻击老派意见,老派意见认为,在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古政治思想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决裂。这个意见的根据是对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事情的记忆。特地就眼下这个问题简要回忆一下这个现代进程最重要的诸多阶段,也许不无道理。生活在1500年的人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正在见证一场学术复兴,经过数个世纪的野蛮,经过数个世纪无用甚至危险的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古典古代或圣经古代或者这两者的伟大遗产正在重见天日。这些人不是仅相信发生了一场与中世纪(Middle Ages)的决裂——他们亲眼看到了那场决裂。但是,人们没有止步于与中世纪决裂:他们开始意识到,用古代的教诲取代中世纪的教诲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要他们至少还受到古代的观念——如果不是实际的古代——的吸引,他们就会通过寻找比古代希腊更古老的另一个古代,以取代对实际的、已知的古代的崇敬:格劳秀斯(Grotius)、斯卡林格(Joseph Scaliger)和斯蒂文(Stevin)这样的学者对世纪智慧(siècle sage)兴趣盎然,与世纪智慧相比,即使古代希腊也是一个野蛮时代。 这些人不仅试图与中古思想决裂,也试图与古典思想决裂。如此一来,他们就在创造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敢于依仗未来,敢于憧憬一种超越所有早先成就的进步。渴望进步就能实现进步。到17世纪中期,如下信念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已经取得了超越以往所有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依赖于人们已经建立了全新的基础这一事实。在随后的世纪里,这个信念日趋强大而稳固,并且在法国革命之前和法国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信念的鼎盛期,现代政治思想这一方与中古和古典政治思想这一方的根本区别被认为是极为清楚的。孔多塞(Condorcet)当然是法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对这个区别持有如下看法: 现代政治哲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不仅中世纪和人文主义者的政治哲学,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问题的科学,亦即经验科学,而不是一门立足于普遍原则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只有洛克(Locke)才发现了真正哲学的方法——对我们的观念和情感(ideas and sentiments)的准确分析;由于他们的错误方法,以往所有的思想者都未能达到关于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 的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包括阿尔图修斯(Althusius)、格劳秀斯和霍布斯(Hobbes);洛克和卢梭(Rousseau)是人权最重要的教师;他们最先从人的自然中推出了人的自然权利,并且认为政治社会唯一的目标就是保存那些权利;不同于以往所有政治思想,他们的政治科学的目的是在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平等而自由的人构成的社会。潘恩(Thomas Paine)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英国)革命虽然理解人权,但理解得不充分”。 他区分了新的政府体系与旧的政府体系——后者是“世界上存在至今的那种政府”的体系。 法国革命理论家们宣称,他们试图与整个传统决裂并且实现了这一决裂,作为对这场革命的反动而发展起来的历史运动的领导者不同意这一宣称。关于这一点,潘恩与柏克是完全一致的。潘恩说: 我们从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人事变动,或者说是地方局势的改变。它们当然像各种事物一样起起落落,就其存在或命运来说,它们的影响丝毫没有超出产生它们的地域。但是,通过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看到的是事物之自然秩序的一种更新,是一种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普遍的原则体系,它结合了道德幸福与政治幸福、国家繁荣。 柏克说: 在各国政府中曾经有过许多内部革命,既涉及人物也涉及形式,诸邻国几乎或完全不关心这些革命;[……],一场引发地方性不满或者地方性和解的革命没有超出它的领土。对我来说,当前这场革命似乎性质颇为不同,颇需另作描述;它与欧洲那些基于纯粹政治原则的革命绝少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它是一场学说和理论信条(theoretic dogma)的革命。 所以,柏克强调卢梭的学生们以一种新道德(“那种新发明的德性”)反对“旧道德”的事实, 就此而言柏克不亚于他的反对者们。因此,一种新道德,一种关于人、德性和国家的新观念,一种基本上不同于古典和中古观念的观念决定了法国革命的领导者,有识之士们在斗争尚在进行之时就不怀疑这一事实。但是,一旦这场斗争失去了原来的激烈性,斗争的目标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清晰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新道德的反对者自己深受那种道德的影响,他们的原则被它大大削弱,以至于他们不能充分清楚地理解这场斗争涉及的根本原则。与其说他们以旧道德反对那种道德,不如说他们用“历史(history)”反对它。尽管旧道德宣称自身立足于理性——就此而言它不亚于新道德,新道德最有影响的反对者却不诉诸理性(reason),甚至不诉诸立足于神圣启示的传统,而是诉诸纯粹的传统,诉诸演化(evolution)。 结果,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至少就比较保守的思想者而言,引导这种研究的是缓慢的、无意识的演化的观念;在寻找这种演化之时,历史学家们发现它几乎无处不在。当人们几乎完全遗忘了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政治观念与旧政治观念之间的原初斗争之时,从19世纪中期直到大战,人们甚至可能否认有过这样一场斗争;人们甚至可能认为并且宣称, 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至法国革命的理论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延续的,虽然形式有变化,内容有改变,但它的基本观念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现代进程的逻辑结果;但是,它的前提在于,人们已经遗忘了现代进程所有早先阶段体会到的经验,这是现代心灵只要必须与旧价值斗争就能体会到的经验。这个悠久的实际经验——补充说一句——极为清楚明白,它难道不是远比冷眼旁观的历史学家最博学的研究的结果更可信? 然而,历史证据总是具有很大分量。就历史证据而言,乍看之下,许多事实支持卡莱尔博士的观点。我不需要详述这些事实。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强调这一点就够了:通过收集这些事实,卡莱尔博士严重破坏了关于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古(或古典)政治思想之特有区别的流行看法。尽管如此,正如孔多塞所声称,本质的观点仍然成立:现代政治思想与早先政治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现代政治思想立足于人权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 可是,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切勿严格遵循孔多塞。因为,他的历史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导性的,这些论断在为卡莱尔博士铺路。孔多塞相信,现代政治哲学的创立者是洛克。众所周知,洛克极大受惠于明智的胡克(Hooker);至少就原则而言,胡克跟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教父们,后者所做的无非是一方面阐述《圣经》的观点,另一方面阐述希腊、罗马哲学以及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孔多塞这位如此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家的说法几乎自动导向卡莱尔博士这位如此保守的历史学家的判断,后者声称,从罗马法学家到法国革命理论家的基本政治观念是连续的。 可以表明,从西塞罗到孔多塞的这一进程没有看起来那么连续,就在胡克与洛克之间,这一连续性发生了一个明确的断裂。人们忽略了这个断裂,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一般而言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作品以及具体而言英格兰这一时期的作品制造的一个特定错误。 这个时期的思想已经是一种沿着古典甚至神学传统方向的反动,以反对激进得多的17世纪上半叶。我只需提到这个运动最原初的一些支持者的名字:莱布尼茨和斯威夫特(swift)。莱布尼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念重新引入笛卡尔和霍布斯建立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现代科学的框架。斯威夫特则是书籍之战的作者。 关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们——洛克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审慎的(moderate)思想家。至于谈不上审慎的卢梭,他在建立国家观念之时不是没有回顾斯巴达和共和制罗马,以反对17和18世纪特有的现代开明专制。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说,17时期较晚时期和18世纪的反动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现代特有的基本观念,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肯定是现代的,但是,这些思想家试图在现代基础上建立一个与传统理想尽最大可能相容的结构。结果,他们的工作容易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的思想与中世纪的思想仅有细微差异,同时,延续性没有发生任何断裂。经过必要限定,我们关于18世纪的说法也适用于19世纪:\[在此,我只能再次指出我关于历史研究在19世纪的重要性以及那种重要性之意义的重要性的表述。\]这些考虑引导我们得出结论,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则以及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仅仅在这一思想的最初时期,亦即始于马基雅维利终于霍布斯的时期,才表现出它的纯粹形式。我们之所以必须研究这个时期,不是为了比我们通过研究19世纪或20世纪思想所能做到的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思想,毋宁说,这就是为了理解现代政治思想。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时期的任何伟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博丹、阿尔图修斯、贝拉闵(Bellarmine)、苏亚雷斯(Suarez)、霍布斯。但是,为了不让复杂的人物和观点削弱我们对本质问题的理解,我建议我们今天唯独只研究上述思想家中最极端的人。那个思想家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具有特定特征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创立者。从这个角度看,显然没有任何神学思想家堪称极端。因为,即使那些像贝拉闵和苏亚雷斯一样不是完全延续中古传统而是拒绝这一传统的人——尤其是路德和加尔文——最终也将其政治教诲建立在启示的上帝意志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显然不是现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特征。 …… (继续阅读,请参考原书) 施特劳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他不仅对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前人的深刻解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即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避免成为“主义”的信徒。 本书包含施特劳斯就许多关键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文章为讲演性质,文字稍平易,适合入门施特劳斯思想。文章按时间编排,略可窥见作者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