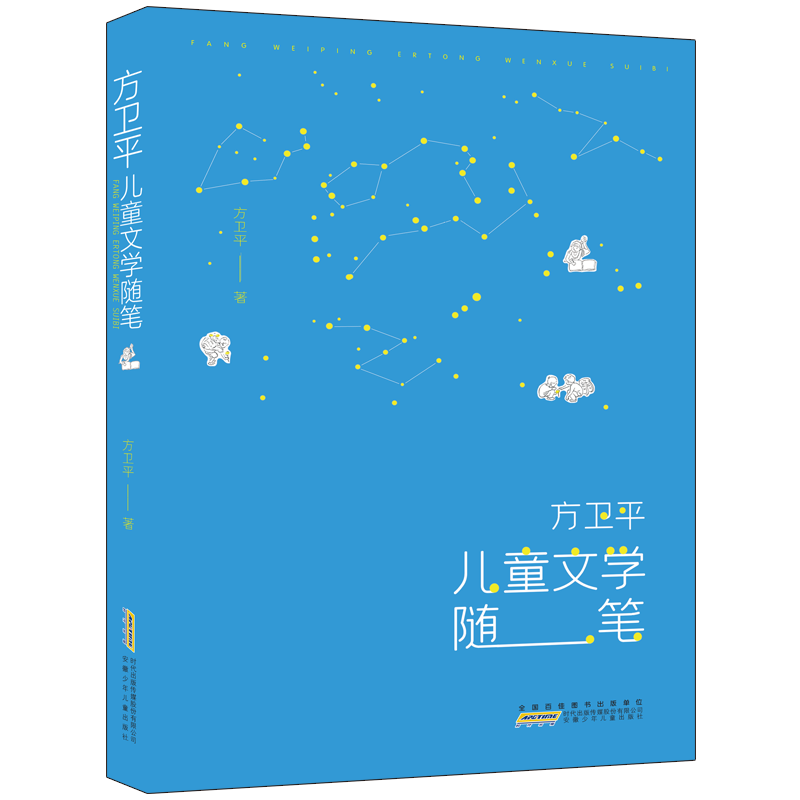
出版社: 安徽少儿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方卫平儿童文学随笔
ISBN: 9787539796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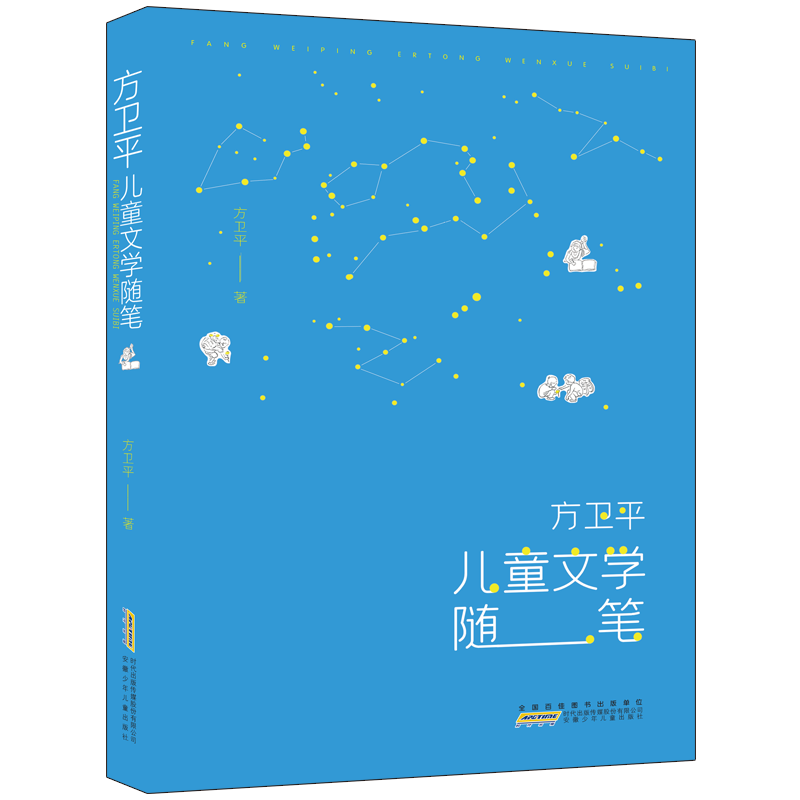
方卫平,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近年出版有《童年写作的重量》《儿童文学教程》《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中英双语版)、《方卫平学术文存》(共10卷)等。
“儿童节”提醒我们什么 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在各种围绕孩子展开的节庆和消费活动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儿童节首先是一个有政治含义的节日。就像每年岁末,在全球性的物质和精神消费的嘉年华里,人们也很容易忘记,圣诞节首先是一个宗教节日。 1925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国际儿童节”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其宗旨在于借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节庆日的确立,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儿童的普遍福利,关切全球儿童的生存权益。会议通过的《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与1924年发布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一起开启了20世纪全球儿童权益的保护和推进运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儿童问题是人的问题,认可、伸张儿童的权益,就是更好地认可、伸张人的权益。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支撑和引导下,20世纪中后期,全球性的儿童福利、权益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定为“儿童节”的6月1日,同样是一个充满政治含义的时间点。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以暴力毁灭了捷克的利迪策村,不但屠杀成人,更枪杀婴儿,囚禁儿童。最初为纪念这一悲剧事件而正式设立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只是为了纪念在这场灾难及所有战争中罹难的孩子,更是以此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保护儿童的生命和尊严,保障儿童的权益,都是人类文明不能忘记的一项基本伦理与职责。今天,技术和社会生活的革新正日益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对那些生存在战火、贫困等境况之中的孩子来说,身体和精神上的饥饿、贫穷、虐待甚至死亡,却从不曾远离他们。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事件中,他们的身影都太弱小了,太容易在权力的天秤上被视而不见。正因如此,设立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以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聚焦和宣告,向成人大声重申关注儿童,大声呼吁关心儿童,显得意义重大,同时也格外意味深长。 在一个经济开放、和平发展的时代,任何节庆大概都会不可避免地被附以经济的内容。自儿童节在世界各国设立以来,儿童节的政治含义渐渐被儿童节的经济内容所置换。或许,这种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从积极的方面看,围绕着儿童节和儿童群体发生的日益扩大的消费活动,首先是儿童的家庭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公众日益广泛的认可。实际上,对于迅速兴起壮大的当代儿童经济来说,儿童节只是数量众多的催化素之一,我们由此窥见的,是儿童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意愿在成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内得到认可。无论对成人还是对儿童,儿童节这个符号都提供了重视童年、满足孩子的一个理由、一次契机。无疑,这个姿态本身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儿童节经济,或者说,以儿童节经济为代表的儿童消费经济,以其特有的影响力推动着社会和成人了解和关注儿童的需求。现代消费经济的活动不仅在于满足既有的需求,更在于不断发现乃至创造新的需求,所以,当儿童消费经济的按钮被触动、打开,它必然会形成一种以儿童消费者群体为对象的日益精细的消费需求考虑。在儿童消费史上,这一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大众影响力和启蒙力,推动了有关童年需求的相关观念、知识的普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是18世纪的英国,作为约翰?洛克哲学及儿童教育思想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现代商业童书之父、英国书商约翰?纽伯瑞以他成功的商业童书营销事业,大大促进了“儿童在游戏的娱乐中学习”的观念在中下层民众意识里的普及。我们看,今天围绕着儿童消费者的形象组织起来的消费网络,对儿童生活各方面的考虑已经相当细密,对于儿童身体和精神的照料,也显出相当的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节经济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儿童节固有的政治诉求。 当然,在我看来,由于这种儿童节经济以营利为重要目的,它最终构成了对儿童和成人的一种消费压迫。这就是为什么起初为了响应积极的儿童游戏观念而兴起的儿童玩具业,后来会演变为开发过度的儿童玩具产业。凭借“儿童节式”的观念或情感勒索,消费经济将众多成人无可奈何地卷入无止境的儿童消费竞争中。在这个过程里,儿童节经济曾经内含的关切“儿童需要什么”的积极的政治诉求日益被关注“儿童想买什么”的消费诉求所取代和遮蔽。当“儿童节”仅仅成了一场消费追逐的热闹庆典,它的价值也在这样的追逐中日渐成为可疑的对象。 但我并不主张由今天的儿童节经济简单地回到一种关于儿童的政治吁请。我相信,这样的要求反而会剥夺这么多年这个节庆在广大儿童群体中培养起来的情感意义。我看重这个节日迄今为止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认为,对儿童节的反思应该带着这一重要而珍贵的情感联系,进一步寻求当代儿童生存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的实现。 今天,儿童节除了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福利,或许还应努力为这样一些关于童年的公共思考提供展示和探索的契机。 例如,在今天童年生活条件普遍比过去更为富足的时代,什么才是对童年的更高尊重?倾听孩子自己的意愿,努力满足他的愿望,其中当然包含了尊重这个孩子的良好愿望。但一味迎合孩子的欲望,一味纵容孩子的需求,恰恰可能是对童年的不够尊重和不负责任。在一个消费膨胀的年代,如何既赋予儿童充分的生活和文化的权益,又为儿童刚刚迈开的脚步把好分寸,守住门槛,恐怕是我们今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又如,在这个儿童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一个孩子?新世纪以来,媒介和技术的变革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变革带来的大量棘手和前所未有的童年问题也远超我们的预料和想象。许多既有的儿童保护伦理和规则难以及时应对新现实的冲击。自媒介泛滥导致的讯息的过度暴露,媒介启蒙滞后导致的文化上的“新文盲”现象,正在给当代儿童的生存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性影响。如何在今天做一个合格的儿童保护者,也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 再如,在儿童节的欢愉气氛中,如何不忘记它的背后当代童年的另一副面孔:饥饿、穷困、战乱、逃亡,以及其间发生的一切不应属于童年的悲剧?童年的这副面孔与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生活看似遥远,但实际上一直左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转。只要童年的这副面孔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便未真正完成。惟有不忘记它,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我以为,“儿童节”当然无法舍弃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属性与内容,但是归根结底,它提醒我们的应该是一种关乎童年的根本精神,一个我们社会、文化的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足以让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也足以让全世界忧伤。 童年的秘密从来不会停留在任何抽象的理论中,而永远是在孩子生动的日常生活里,在孩子蓬勃的生命状态中。 ——方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