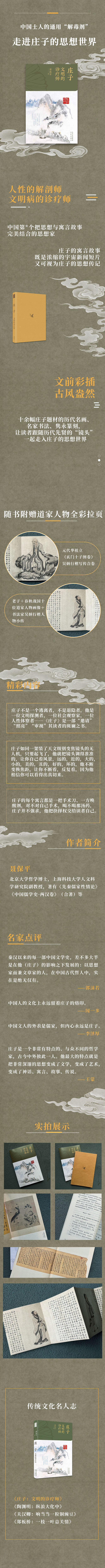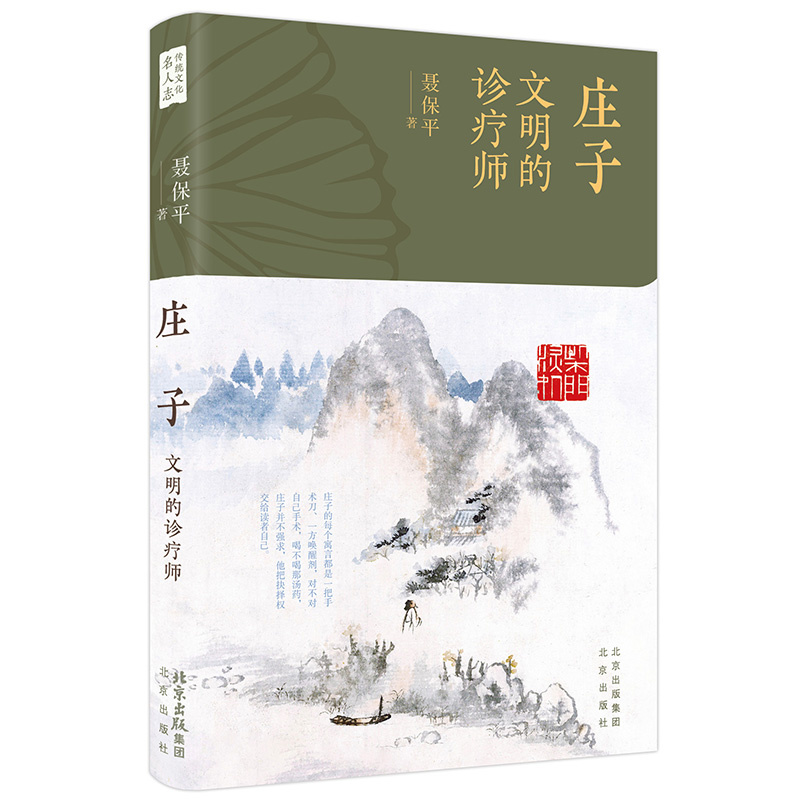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8.80
折扣购买: 传统文化名人志 庄子:文明的诊疗师
ISBN: 9787200188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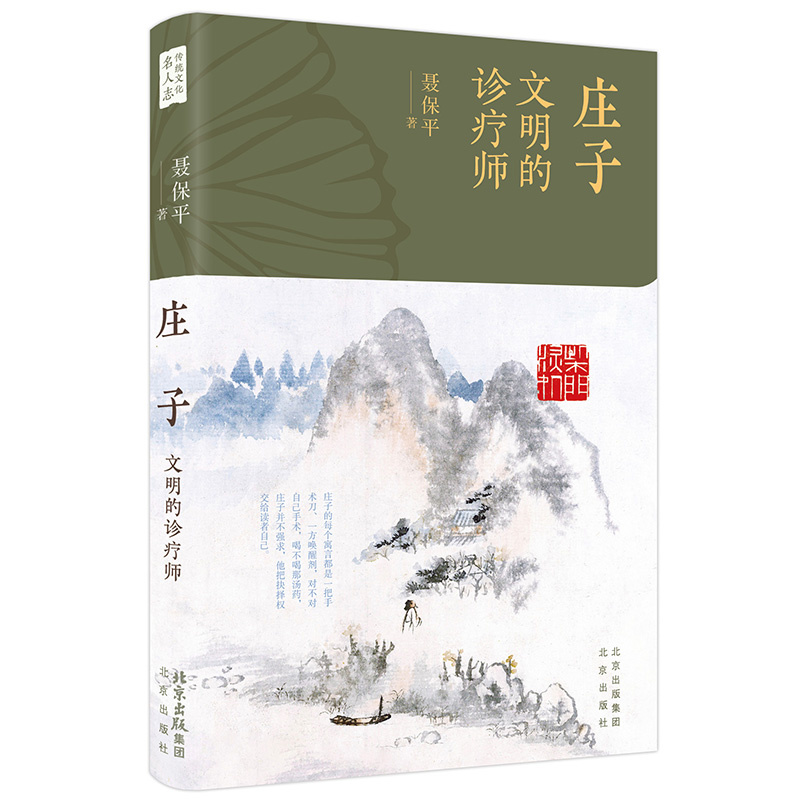
聂保平,安徽庐江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曾就职于无锡日报社、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著有《先秦儒家性情论》《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合著)等,现为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庄子的“反抗” 据实而言,《诗经·大雅》后半部分的许多篇章就已对文明本身有所反思,庄子不是上述文明悖论的发现者,却是对它进行最为深刻体察的省思者、反抗者、克服者。 庄子所居宋国,既是当时的商业强国,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由于地处中原要冲地带,宋国先是在春秋争霸中被多面捶打,而后在战国乱局中又被反复挤压。宋国的遭遇,像极了一个在文明竞争中既要自我保存还想出人头地的文明人的境遇。对庄子(约前369—前286)而言,存国八百多年、历三十四君的宋国(前11 世纪—前286),给予他“全景”地观照文明的足够素材。而且,在宋国,前有墨子、子思, 当世有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宋钘(约前370— 约前291)等人,他们都是“主流”。从《天下》中的评述看,庄子对他们可谓了如指掌。我以为,宋国的遭遇以及那些主流宋人,深深地“刺激”了敏感的庄子,以致他宁愿在文化、政治的边缘地带,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或许吧,庄子不愿像当时渐兴的“游售”之士那样,各国游历,以期得用,他有意地把自己“放逐”在边缘地带流浪,自甘边缘人、局外人,坚定地做一个反抗者。《庄子》开篇即讲“游”与“用”,应是他有意识地对彼时风气的“反抗”。但是,从《庄子》中诸多寓言之意看,庄子的反抗却又不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不是退化式的,也非发展式的,而是对前述单向文明化的反抗,他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之情”作为反抗的试验场,不断地呈现他那不可笼养的才性,“游”于万物,表达他的反抗之思。 他引入各种与文明对抗的原始意象(比如“天籁”“浑沌”“飞”“游”之类),作为自己思想的光束,期待人们沿着他的光束所至,看到些什么、清晰点什么。换言之,庄子是一个文明的批判性审视者,是反抗文明规制力量的探源者,他选择向原初之地出发,为自己,也为人类寻找克服文明悖论的光源。 时空、性命、是非,是人的根基,也是导致人彼此冲突的根源,庄子在《逍遥游》中对庸常的时空观进行了“爆破”;在《齐物论》中,他以超越庸常是非观的方式,对“是—非”本身进行了存在论意义的思考;在《人间世》中,他对“材—用”关系进行溯源;在《养生主》篇首和《天下》中,他留下了对文明无奈而对自己自信的“自白”痕迹;而在《德充符》《大宗师》中,对何以“相与”“相为”的根基作了非文明化的照亮;而后,在《应帝王》的末尾,以“浑沌”做隐喻,说明原初的整体性、根基性和自然性。庄子回到原初那里,掀开遮没它们的各种幌子,用思想与意象的双重光束,一点点、一层层地照着,告诉他的读者,那些都是什么,造成了什么,还会引发什么。 思想那不可遏制的光,意象那充满惊奇的启示,让庄周成为庄子,让《庄子》成为经典。庄子因此成为人性的解剖师、文明病的诊疗师,《庄子》又因此而成为诊治人类社会文明病的中式“宝典”之一。 “众人役役”的“弱丧” 看起来有序的文明社会,其中隐藏着无数的“断裂”和“破碎”,它们就像路上的玻璃碴和路边繁茂的荆棘丛,不经意地割得人伤痕累累。庄子行走在人间,对这些伤痛的敏感度远超常人。在《庄子》中,这种伤痛感几乎随处可见,“与物相刃相靡”(《齐物论》),是对这种感受的极致描述。但是,庄子并没有停止于对伤痛的描摹,那种极致的痛感,是促发他思考的核心力量。就如同人对世界的无能感,是促发艺术的内驱力那般。“弱丧而不知归”(《齐物论》)的说法,足以显示庄子对这种伤痛来由的深刻认知。“弱丧”之说,古注的理解基本一致,即“少小失离故土”。庄子对“众人役役”(《齐物论》)一直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无奈,他从“役役”中发现了众人悲哀的秘密——“弱丧”,人一旦深度参与社会进程,就会陷入“开端即丧失”的境地,而这是大多社会人不自觉的常态。 “弱丧而不知归”的人,其“不知归”并非不需归、不想归或不能归,而是因为他们处在那不断壮大的“役役”进程中,没有“参万岁”(《齐物论》)式的镜子,他们“归”的意识沉寂,而共处“役役”进程的他者,也一样在沉寂里。这样,“役役”情境中的人,只是“役役”的参与者和强化者,他们其实不具备自我觉醒或彼此唤醒的意识和能力。 “役役”的说法,暗示一种相互性——人与人之间、吾和我之间、役与役之间,都陷入了互役的状态。这种“役”的过程,是双向的,即役人者同时也被人所役。这个理解和表述,是庄子的理解和表述双重精微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庄子的“役役”与西式的“异化”有质地上的不同。役役是身心全失自主,异化是身心皆已质变。 庄子对社会人深陷的“役役”困境洞若观火,在“别样原理”和“纯素原则”的照明下(详见第七章),庄子洞悉了众人就像疲惫不堪的文明“移民”,他们从原初故园“移居”文明社会,无论文明有多么诱人、丰饶或舒适,人对原初的感受,对故园的记忆,一直蛰伏在心灵深处。而庄子要做的,就是以照亮的方式(“以明”)唤醒他们,让他们看见、听到、嗅到原初和故园。 庄子运用他的“别样原理”时,拒斥教化式的诱导,拒斥和风细雨式的劝说,他要爆破或撕裂,以不正常的物事、声音、意象去撞击人僵陈已久的心灵习惯。庄子做得很充分,他的故事、他的语气、他的刺激,都与众不同,以至于你不得不惊奇地问:真实是什么。这样的惊异一问或一瞥,成为“役役”旅行者心灵的新起点、新坐标。即便他会回望过往,他也会忍不住在新坐标上瞻望未来了。这,大概就是庄子“恣肆”地“编造”故事的隐秘原因。 人性的解剖师,文明病的诊疗师,中国第*个把思想与寓言故事完美结合的思想家。 庄子的寓言故事,既是浓缩的宇宙新闻短片,又可视为庄子的思想传记。 文前彩插,古风盎然,十余幅庄子题材的历代名画、名家书法、隽永篆刻,让读者跟随历代先贤的“镜头”一起走入庄子的思想世界。 随书附赠道家人物全彩拉页——元代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卷》吴炳行楷写传合卷 老子+春秋战国十位道家人物,尹喜、辛钘、庚桑楚、南荣趎、尹文、士成绮、崔瞿、柏矩、列子和庄子, 画像侧面为书法家吴炳以行楷书写的人物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