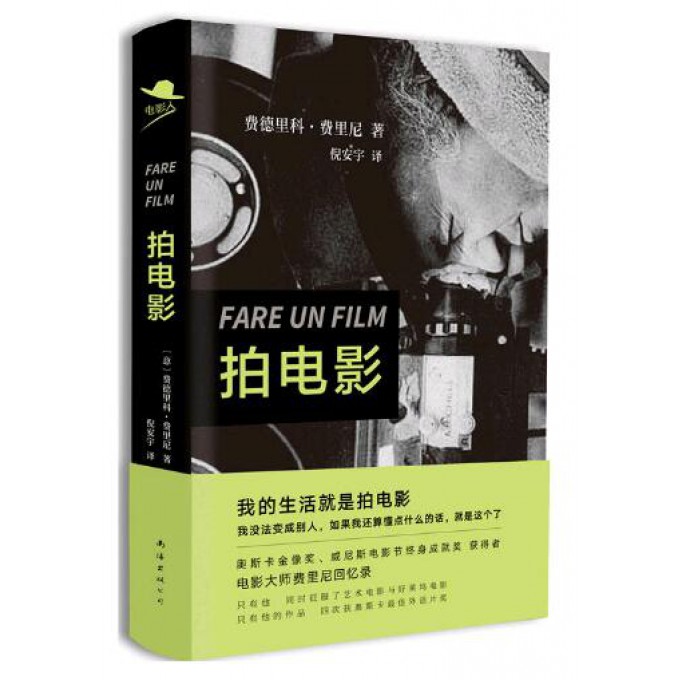
出版社: 南海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9.70
折扣购买: 拍电影(精)
ISBN: 9787544284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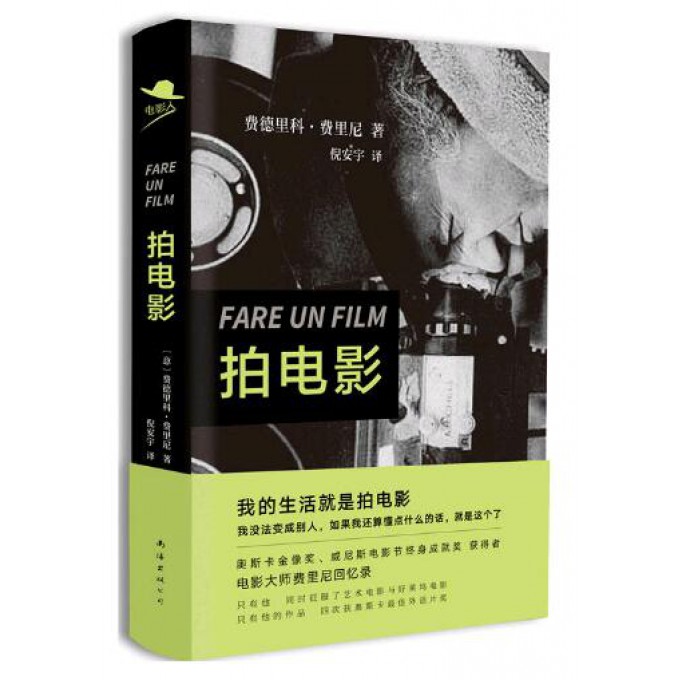
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 知名导演。生于意大利北部的里米尼小城。年轻时做过记者、编辑、电影编剧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担任导演工作,先后拍摄《大路》《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等二十余部影片。他执导的电影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本人也在1993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此外,他还获得过戛纳电影节四十周年奖、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等。 费里尼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扩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成为欧洲艺术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被誉为20世纪影响广泛的导演之一。
昨天晚上我梦见里米尼港湾,澎湃苍绿又骇人的大海,如大草原般滚动,海面上厚重的云块朝向陆地奔腾而去。 巨大的我从小小的、狭窄的港湾出发,想游到大海去。我告诉自己:“我如此巨大,但大海终究是大海,要是游不到呢?”然而我并未因此而苦恼,仍继续在小海湾中伸长了手臂划水。我不会溺毙,因为脚碰得到底。 这是一个膨胀的梦,或许是想让我重拾对大海的信心。一个自我保护的小小机制:诱惑人高估自己,或者低估那些可能会限制自己起跑的障碍。总之,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应该抛弃起步时的小港湾情结,还是应该高估自己。 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并不十分乐意回里米尼。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障碍。我的家人还住在那里,我母亲,我妹妹。我是惧怕某些感情吗?主要是我觉得,回到那里是一种对记忆欣然但自虐的反复咀嚼,这是一种戏剧和文学的动作。当然,它自有魅力。昏昏欲睡且混乱的魅力。其实是我没法把里米尼视为一个客体,不如说,也只能说,它是记忆的世界。的确,当我人在里米尼时,总是被已经存档、安抚过的记忆幽灵袭击。 如果我留下来,这些纯真的幽灵说不定会默默向我提出令人困窘的无声的问题,而我不能用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谎话来回答它。我必须从家乡找出缘由,不含任何欺骗。里米尼是什么?它是一个记忆的世界(虚构、掺假、被侵犯的记忆),而我利用它如此之久,以至于心里没有一丝尴尬。 但我不得不继续谈它,甚至有时自问:终有一天,当你遍体鳞伤、疲惫不堪、不再有竞争力,难道不想在这片港湾买一栋小房子吗?老城那一边的港湾,小时候,我在对岸看着它,看着船骨搭造起来。海湾靠这边的一半,让人联想到喧闹嘈杂的日子,与开奔驰轿车往海边去的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搭界。 其实,早期那里都是贫穷的德国人。突然间沙滩上随处可见斜躺的自行车和篮子,水中则满是小胖子与“大海象”(矮胖的大人)。我们小孩子戴着羊毛罩耳帽,由我父亲的伙计带到海边。那个时候,在老城那边的港湾,我只看到了枯枝,还听到一些声音。 前一阵子,通过朋友蒂达·本齐,我买了一栋房子,价格低廉。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固定点,或许可以回归纯朴生活。不过这不可能成真,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看过那房子一眼。其实,光想到一栋紧闭的房子,没有房客,在那儿空等,我就觉得不舒服。 当我决定卖掉房子时,蒂达跟我说:“那可是你的家乡!”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再一次背叛它。 在此之前,蒂达曾说服我在马雷奇亚买了一小块地。那地方看起来很适合谋杀 在乡下,从吉卜赛人那儿,我常常听到关于爱情 迷药和巫术的事。我想到一个女人,安吉莉娜,曾到 家里来做床垫(应该要有一整章献给这些行业:磨刀 工人和他的破车、全身墨黑的烟囱清扫工和最令佣人 害怕的人物)。安吉莉娜要在我奶奶家住三天,还包 吃。有一天,她正在把一个个棉花球缝进床垫里,我 瞥见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匣子:一个小玻璃盒,里面 装着一绺打了结的毛发。“那是什么?”我问她。“ 这些是我的头发,那些是我男朋友的胡子,是我趁他 晚上睡觉时剪下来的。这样,去特里艾斯特工作的他 就跟我紧紧绑在一起,不会分离。” 另外,马雷奇亚的小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可以使 鸡和羊生病或痊愈。 俱乐部附近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老婆会“恍惚出神 ”。她这样治病也能赚不少钱。有一天,我也排入要 去接受诊治的老先生和老太太的队伍中,最后我站到 一间小客厅的门口,房间里简直是家徒四壁。一张椅 子上,坐着一位脸上喷洒了水珠的老太太,弓着脊背 ,身体僵硬,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说:“克拉一多那 一累一特罗佩一特(那个女人比你强),你得让她去 。”说完话后,老太太哭了起来。后来走出一个惊慌 的大男人,他不愿被人看见。他站在阶梯上,头上戴 着帽子,不肯离开。或许他是想找到勇气,再回去寻 求不同的神谕。 大家也常谈到那些住着幽灵的鬼屋。“卡尔雷塔 ”是我朋友马里奥-蒙塔纳利的别墅。据说一百年前 ,别墅主人在灌醉表妹后把她掐死了。他们说,有些 夜晚,可以听到酒窖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大家认 为,那是被掐死的表妹戳破酒桶的橡皮盖往杀她的凶 手嘴里灌酒,好让他不得安宁,永远溺毙在酒里。 罗马涅——海上冒险和天主教教堂的混合体。这 儿有圣马力诺,一座阴郁而自命不凡的山丘。一种奇 怪的狂妄自大和渎神心理,掺杂着对上帝的迷信与挑 战。老百姓没有幽默感,也不设防,但是喜欢嘲弄和 自我吹嘘。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吃下八米长的香肠、 三只鸡和一根蜡烛——居然还有蜡烛,简直是马戏团 表演。然后,他真这样做了。一吃完,他们马上用摩 托车把他载走了。他脸色发紫,眼睛翻白,而大家面 对这种残忍和死亡的威胁却放声大笑。 有一个家伙叫“由山上升起”。是升——我也不 懂——而不是降:就仿佛一次假想的空中散步。还有 “哦不”,四海漂泊的水手,偶尔会寄一张明信片给 他在拉乌尔咖啡馆的朋友:“经过鹦鹉岛,想起你们 大家。” 这一带有一种口音,极为甜美,或许来自大海。 我记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夏日午后,在一条阴影层 层叠叠的小巷子里:“现在几点?”“应该恰好四点 ……”有人回答。而小女孩哼哼唧唧,好像是说一定 比这晚:“哼,才没有恰好……” 同时,女人有东方式的肉欲冲动和态度。早在我 站街女郎。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位尚未皈依的女管家,黑色 的头发和黑色的工作服,一张脸因为血脉偾张引起的 疖子而红扑扑的。很难说她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她 的女性特征像俗语所说的,一触即发。总之,这女人 搂着我,摩搓着我,身上散发出马铃薯皮、蛤蜊汤和 修女衬裙的味道。 我读的幼儿园是圣文森修道院建的,有大帽子修 女的那所。有一天,正在排队准备一场宗教仪式时, 她们让我负责握一支小蜡烛。一名戴眼镜的修女—— 很像电影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指着蜡烛,以不容 争辩的语气说:“不要让它熄灭,因为耶稣不喜欢。 ”那时刮着很大的风,幼小的我被那巨大的责任湮没 。有风,而蜡烛不能熄灭。否则耶稣会怎么处置我? 队伍开始行进,缓缓地,沉重地,随着手风琴的乐声 碎步移动。一段小快步,然后静止;又前进,再次静 止。领队在干什么?行进仪式中还得唱歌:“我们要 主,他是我们的父……”夹在一群长袍修士、神父、 修女之间,突然,一股绝对的忧郁、死亡和严肃的气 氛迎头罩下。就是这队人吓到我了。最后,我哭了起 来。 一二年级我念的是特阿提尼小学。我在班上都跟 那个一同在马雷奇亚看到有人上吊的卡森尼一起玩。 老师是个爱打学生的人,节庆的时候才变得特别友善 。家长们带来一包一包的礼物,堆叠在讲台上,像主 显节前夕那样。收完礼物后,在我们放假之前,他都 要我们唱:“青春啊青春,春天多美~~~丽。”他 非常重视那四个“~”。 之后几年,我被送去法诺,在一所慈爱的神父们 管理的寄宿学校读书,跟小金鲷的相遇就发生在那段 时期,一如我在《八部半》中的描述。中学位于马拉 特斯提安诺路,现在已改成市立图书馆和美术馆了。 当时,我觉得这所中学是一座高耸入天的大楼,上楼 和下楼都是一种探险。那些阶梯永无尽头。校长绰号 “宙斯”,标准的自大狂。他有硕大无比,跟600型 小汽车一样大的脚,用它残杀小孩。被他踢一脚能让 你的脊椎骨断裂。他总是先假装不动,然后出其不意 地用那只大脚把你像蟑螂一样踩得扃扁的。 中学那几年是属于荷马和“战斗”的时光。我们 在学校读《伊利亚特》,并得牢记在心,我们每个人 都以荷马书中的一个人物自居。我是尤利西斯,有点 孤僻,老是望着远方;当年已经微胖的蒂达是埃阿斯 ;马里奥·蒙塔纳利是埃涅阿斯;路易吉诺·道奇是 “驯马人赫克托尔”;斯塔克奇奥蒂是“飞毛腿阿喀 琉斯”——他每一年级都要重读三遍,所以是班上年 纪最大的。 下午时分,我们会找一个小广场重演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所谓“战斗 ”。我们带着用绳子绑好的书(那时大家习惯如此) ,然后挥舞着书互相攻击,展开一场书本和绳鞭的混 战。 P18-21 <p>★奥斯卡金像奖、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得主,电影大师费里尼人生自述</p><p>★只有费里尼,同时征服艺术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只有费里尼的作品,四次获奥斯卡*外语片奖</p><p>★讲述费里尼电影内外的写意人生,像《蛤蟆的油》一般趣味满溢,像《雕刻时光》一般执着动人</p><p>★费里尼的文笔让卡尔维诺赞誉有加,费里尼的电影让侯孝贤赞不绝口</p><p>★我的生活就是拍电影。那是我,那是我的生命——费里尼</p><p>★新经典电影人书系全新力作,精心设计,精装典藏,带你走近真正的电影大师</p><p> </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