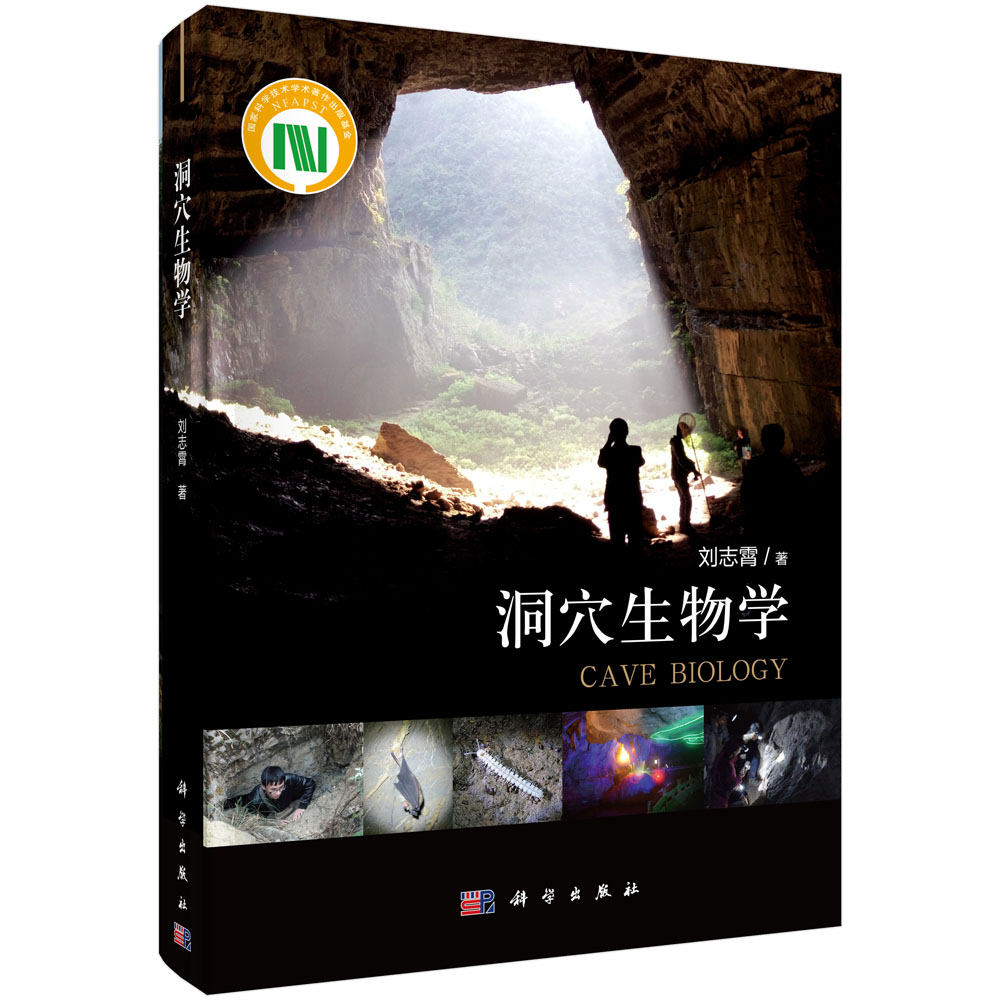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211.80
折扣购买: 洞穴生物学(精)
ISBN: 9787030677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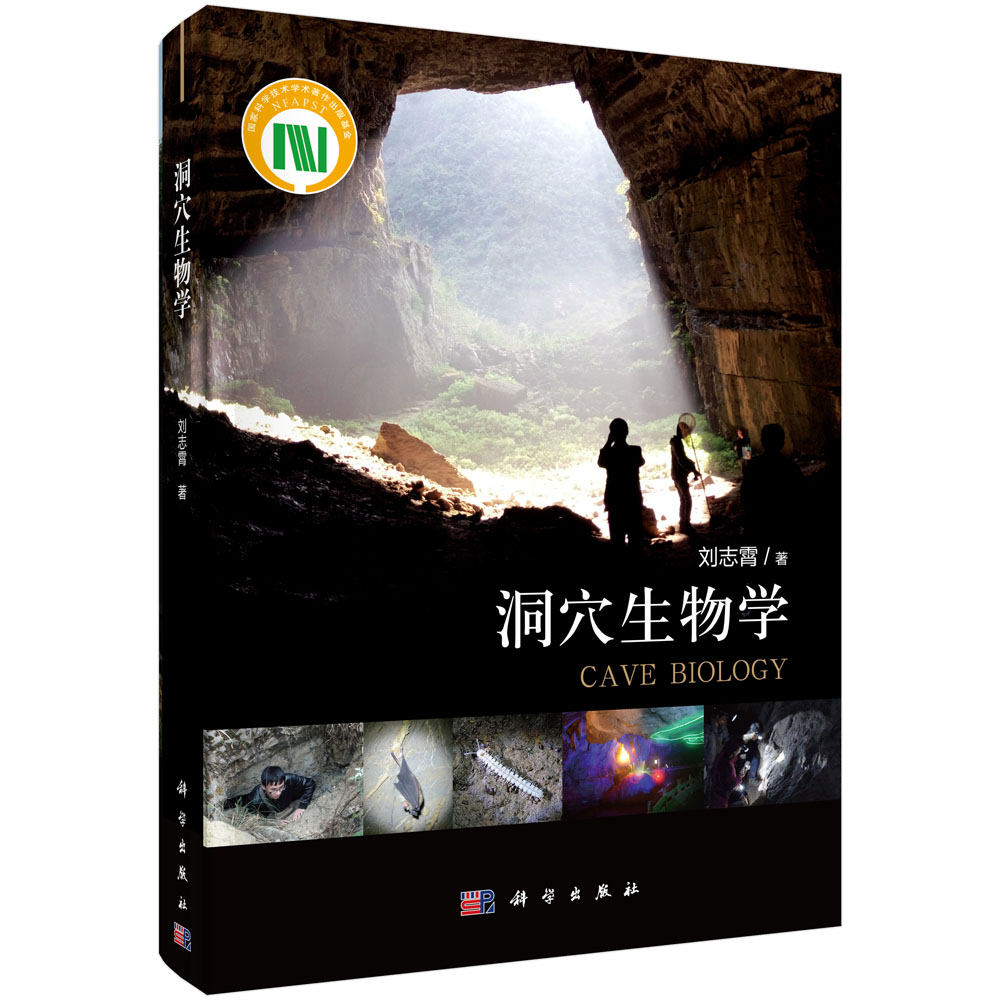
**篇学科范畴与洞穴学基础
洞穴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它以洞穴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多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其历史渊源久远,内涵丰富,在科学新世纪也焕发着勃勃生机。开展洞穴生物学研究,需要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洞穴学基础也必不可少。
第1章
绪 论
洞穴生物学(cave biology / speleobiology),是由生物学、生态学和洞穴学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与地面环境(surface environment)迥然不同的各种地下环境(underground environment)或地下空间(洞穴)的生态生物学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地下环境因子为生物的生存和演化提供特异的条件,使得适应于地下环境生活的生物体逐渐衍生出有别于地表生物的形态、生理、生态与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生活在地下环境中的生物对于地下环境的演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护地下(洞穴)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1.洞穴生物学的基本范畴
洞穴生物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在洞穴内部环境中生活的各生物类群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生理功能、行为生态、繁育遗传、适应进化,以及洞穴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利用等诸多方面。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基础洞穴生物学(fundamental cave biology)和应用洞穴生物学(applied cave biology),前者着重研究洞穴生态系统中各类生物的生态生物学特征及其发生发育规律,后者倾向于从旅游休闲、医疗保健、生物保护、文化演进等方面研究人类对洞穴生态环境、洞穴生物资源及洞穴文化的开发利用、多样性保护与区域文化承扬。
广义上,凡是在土层或岩层中自然形成、动物挖掘或人工开凿的地下环境或空间都可称之为洞穴(cave)。狐狸、兔、鼠、穿山甲、昆虫、蚯蚓等动物在土壤中挖掘的洞道虽然可能长而复杂,但人无法进入,不便于人类直接研究,通常不纳入洞穴生物学的研究界域;生活在土壤缝隙之间的生物,以及生活在地面湖泊、河流底层等昏暗及黑暗水体环境中的生物也不属于“洞穴生物”(cave creatures)。
洞穴生物学中通常所谓的洞穴是指人体能够直接进入或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开扩洞口或借助潜水设备等)能够进入的地下空间及与之连通的地下水体(地下水体实际上就是已被水占据的地下空间),主要包括陆地上的各种天然溶洞(karst cave)、火山岩浆喷发流动而形成的岩熔洞穴(lava tube)、海陆边际洞(anchialine cave)、海蚀洞(sea / marine cave)、海底洞穴(underwater cave),以及受外界环境因子影响较小、缺乏太阳光照、温度相对稳定、湿度较高的人工洞道(artificial tunnel),如具有一定规模及深度且黑暗潮湿的坑道、石窟、防空洞、矿井、矿洞、地下墓穴等,但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人体可以进入的各种形式的溶洞(参见第2章)。在我国很多地方,习惯上将溶洞称为“山洞”“岩洞”或“岩”,如狮子岩、甑皮岩、紫霞岩等。鉴于溶洞的自然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洞穴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溶洞生物学(karst-cave biology)。
在学科发展的早期普遍使用且现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学科名称是biospeleology,该词是由希腊词speos /spelaion(cave)衍生为-spel(e)o-,加前缀bio-和后缀-logy合成而来,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应译为“生物洞穴学”,主要归属于“洞穴学”范畴,但也有人将其译为“洞栖生物学”、“穴居生物学”或“洞穴生物学”等。可是,从学科渊源及实际内涵上讲,将其译为“洞穴动物生物学”可能更为确切,因为它主要是指关于穴居动物(cavernicolous animals)的生物学,即把洞穴当作动物体的栖息环境予以研究,着重探讨“真洞穴动物”(troglobites)的基本生物学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然而,为了不引起术语上更多的混乱并便于字面上的直接理解,本书统一将“biospeleology”一词译为“生物洞穴学”,意指在洞穴学基础上衍生的关于真洞穴动物特殊生物学现象及其机制的一门交叉学科。
而洞穴学(speleology)则是在洞穴探险(caving / potholing / spelunking)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早期主要涉及洞穴探索的一些知识与技能。随着学科的发展,洞穴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现代洞穴学(modern speleology)本身也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洞穴及与其关联的喀斯特景观特征,主要涉及喀斯特地貌及洞穴的组成、结构、性质、演化、生命形态及时空动态等方面,关乎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气候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制图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技术。
虽然早期的“生物洞穴学”(biospeleology)和现代的“洞穴生物学”(cave biology)的基本内涵很难区分,但可以认为,前者是在洞穴探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人员多为探洞爱好者、洞穴学工作者或带有非综合进化论思想的博物学者,有人将1832年施密特(Schmidt)首次科学描记洞穴盲甲虫(霍氏细颈虫Leptodirus hochenwartii)作为biospeleology的开端,而将1907年拉科维策(Racovitza)《生物洞穴学问题随笔》(L'Essai sur les problèmes biospéleogiques)著作的问世视为biospeleology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后者虽脱胎于前者,但继承了前者的现代科学内核,是现代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运用现代综合进化论等现代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洞穴等地下黑暗潮湿环境及黑暗水体中的生物学现象,揭示相关的生物学规律,为洞穴或地下环境中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对《洞穴生物学——黑暗环境中的生命》(Cave Biology: Life in Darkness)(Romero,2009)的学科内涵广泛而深入的理解,本书首次提出了内容广博的“洞穴生物学”的学科框架;强调洞穴生物多样性与洞外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系统性与统一性;重视洞穴生态环境因子、真洞穴动物类群、洞穴生态关系及生态过程的特殊性、一般性与代表性;注重洞穴的生态服务功能、民生作用、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意义及文化内涵;倡导洞穴资源保护利用和洞穴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创新。
总之,本书涉及洞穴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诸多方面,是在“洞穴生物学”(Romero,2009)的基础上新建立的学科体系(图1-1),因此也可将书名更改为《洞穴生态生物学》(Cave Ecobiology)(须知,生态学已独立成为与生物学并列的一级学科)。
显然,通过对洞穴生物学简史的梳理既可洞悉“洞穴生态生物学”渊源与现状,也可展望其广阔的研究前景。
1.2.国际洞穴生物学简史
毋庸置疑,科学史受到哲学、政治、宗教及其他人类活动形式多方面的影响,对洞穴有机体的研究观念及程式还必然受到有关地面有机体的主流生物学(mainstream organismal biology)概念及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洞穴特殊生态生物学现象及规律的认识也丰富了主流生物学体系的内容,因此洞穴生物学史是生物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洞穴生物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主流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在进化与生态学方面落后得更多,其主要原因是许多生物洞穴学家(biospeleologists)未能很好地理解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不加鉴别地接受与现代生物学思想相悖的概念、词汇或术语。因此,围绕生物洞穴学研究的主要方面,解析意识形态框架,批判性地检视生物洞穴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生物学思想完全融入生物洞穴学时滞性的理解,并有利于推进今后的工作。
较早关注洞穴生物学史的学者可能是法国动物学家阿尔贝 旺代尔(Albert Vandel,1894~1980年),他在1964年出版的《生物洞穴学:关于洞穴动物的生物学》(Biospéléologie: la Biologie des Animaux Cavernicoles)一书中概述了与生物洞穴学发展相关的一些历史事实。1966年,托马斯 巴尔(Thomas Barr)对自1822年以来美国的生物洞穴学及洞穴生物学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Bellés(1991)按年代顺序编列了生物洞穴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及轶事;Shaw(1992)在他关于洞穴学历史的论文中,也提供了少量有关生物洞穴学的历史信息,而Romero(2001)在其关于穴居性鱼类的研究论文中,主要涉及的是洞穴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史。直到2009年,Romero才在Cave Biology: Life in Darkness一书中,对洞穴生物学史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为了便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生物洞穴学与洞穴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同时对整个近代与现代生物学思想史的基本脉络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溯源细节上的把握,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参考其概要并予以重新整理、节删、补充和修改,而将洞穴生物学史大致划分为以下略有重叠的4个时期。
1.2.1.从史前雕刻画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话沿袭
史前时代,人类把洞穴当作庇护所,并在洞穴中进行艺术创作。现在已知最早的关于洞穴动物的图画发现于法国比利牛斯山(Pyrenees)中部的“三兄弟洞”,那是一幅大约于公元前2.2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刻在一块欧洲野牛(Bison bonasus)骨头上的关于一只无翅洞穴蟋蟀(Toglophilus sp.)的雕刻画。
创造文字之后,人类就开始用文字记事,很多叙事都带有神话或宗教色彩,通常还把黑暗的洞穴与阴间、地狱、死亡相联系。许多民族都有将死去的人埋葬在洞穴中的习俗。在希腊神话中,阴间或冥府就是“死人之王国”,人死后通过洞穴走向阴间。因此,不难理解,人类对于洞穴生物的观念自古以来就模糊不清,既有神话之形式也有现实之涵义;在印刷机发明之前,许多艺术创作描绘的是丑恶之人貌,或邪怪之兽像。
大约在2800年前,雕刻在青铜器上的一段文字较早地记述了岩溶现象,说的是亚述古国的国王撒缦以色(Shalmaneser)三世与一些学者探察底格里斯河河源处的洞穴和泉,并在洞壁上凿刻图案。地中海一带的岩溶现象也早就出现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诗人、哲学家的诗文中。荷马(约公元前9~前8世纪)的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到过海水和岩溶水之间的关系。古希腊集大成的博物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认为泉是由地下洞穴中的水汇集而形成的。
17世纪以前,人类对洞穴生物的认识仍然虚幻怪诞。1654年,Gaffarel发表了西方多数学者认为是最早的岩溶著作——《地下世界》(Le Monde Souterrain),这一关于洞穴的著作现今只剩下一些断简残篇保存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其中对洞穴的认识仍包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且记载了当时在地理、地质和矿业上的一些发现。保存较完好的早期岩溶著作是Valvasor于1689年发表的Die Ehre Des Herzogsthums Krain,该书记述了其家乡及邻近地区的洞穴、落水洞、泉等岩溶现象(涉及的空间范围较小),虽然也谈到了水在形成洞穴当中的作用,但仍受到神秘主义和民间传说的深刻影响。
1665年,博学多才的德国阿塔纳修斯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出版了可能是**本似乎专门论述“洞穴”的对开式两卷多达892页的巨著——《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1678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第二版中,增列了大量有关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所属岛屿上洞穴的记述。该新版更受欢迎,被当作那个年代标准的地质学课本。基歇尔并不拘于书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