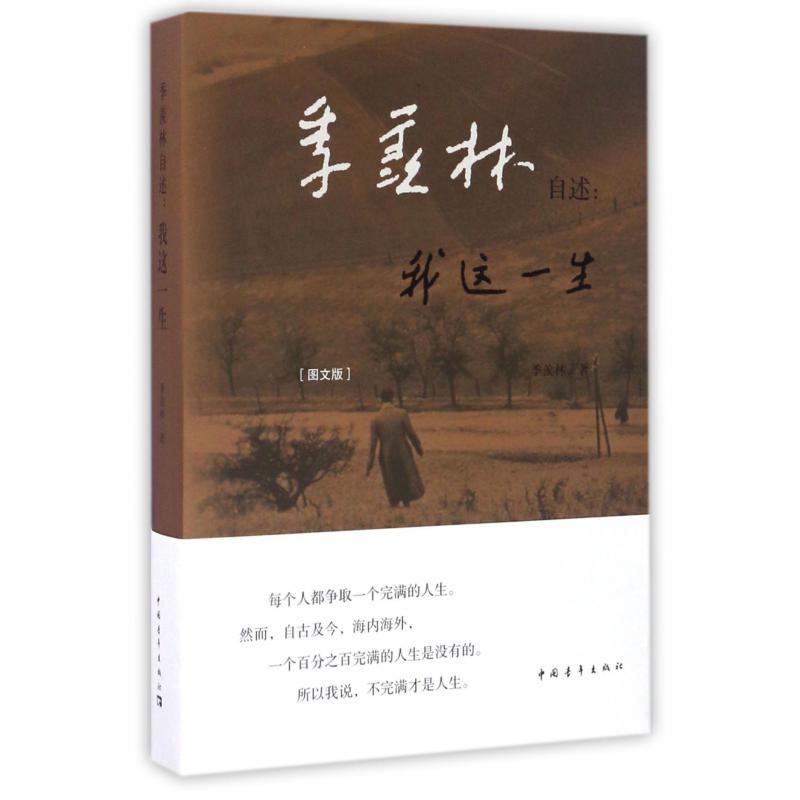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青年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8.40
折扣购买: 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
ISBN: 9787515322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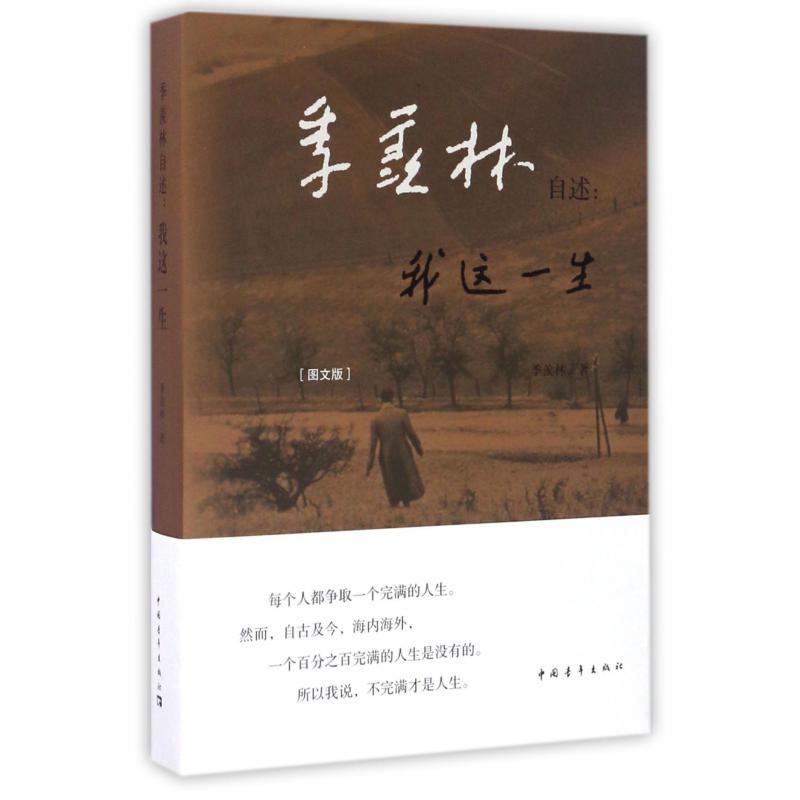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1 我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 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 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 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 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 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 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 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 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 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 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 。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 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 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 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3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 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 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 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 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 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 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 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 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 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 ”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 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 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 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 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 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 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 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 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 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 ,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 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 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 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 ,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 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 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 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 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 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 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 愉快。 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 每天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 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 ,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 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 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 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 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 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 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 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 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 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 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 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 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 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 总在4岁到6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 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 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 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 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 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 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 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 (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 名谁。我们3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 、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 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 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 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 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 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 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 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竞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 骄傲之意。 我在故乡只待了6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 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 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6岁那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 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 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 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 ,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 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 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 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 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 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 “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 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作没有 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 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 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 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 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 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 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 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人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 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 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 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 ,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 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 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 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 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竞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 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 真是变幻莫测啊!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