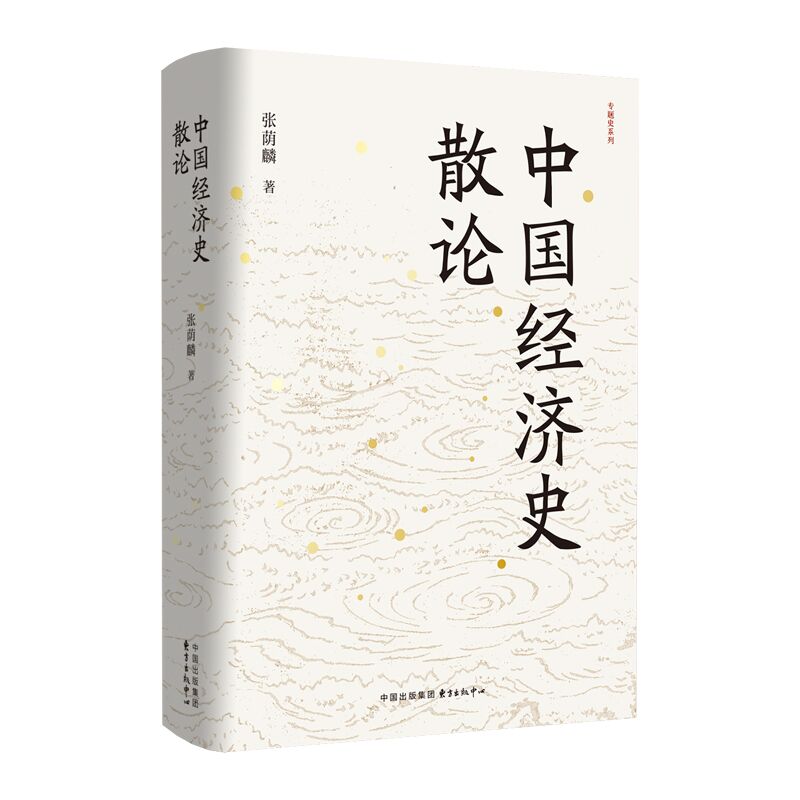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2.80
折扣购买: 中国经济史散论
ISBN: 978754732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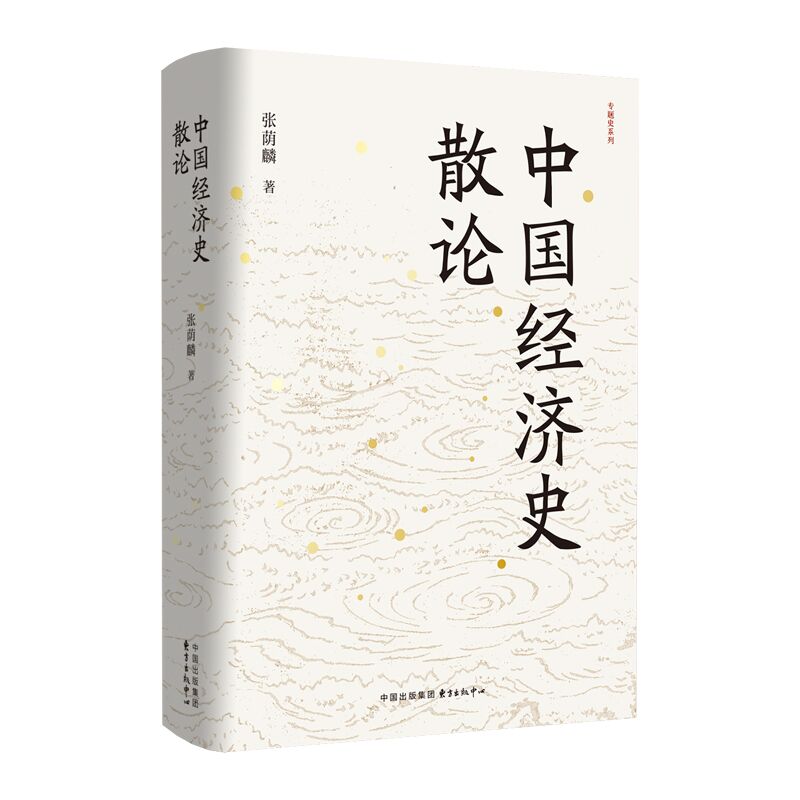
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其治学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和梁启超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两个开山大匠”。
《孟子》所述古田制释义 (一)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 一章中论述田制的一段,语甚迷离,与书中滂沛的辞令殊不类,疑有夺句错简。近考周代封建社会史,越读此章越发生问题。 第一,是段开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不管“贡”“助”“彻”的意义如何,这里明说周人的田制是“彻”而非“助”,但不一会却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又明说周人的田制是“助”而不是“彻”(彻不能有公田)。于此我们有两个可能的说法: 甲、 孟子头脑糊涂,在几行之内自相矛盾;乙、 孟子本意以为周代曾同时并行“彻”制和“助”制,或曾先行“助”制,继改“彻” 制,却没有把话说清楚。这两个设想都不好接受。头一个设想和孟子的智力不类。至于第二个设想,孟子既然没把话说清楚,我们怎好判断他的原意?而且孟子是这样不会说话的人么? 解释这个困难的钥乃在本章中“请野九一而助”的话和另一章(《孟子·梁惠王下》第五章)中“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的话。显然所谓“虽周亦助”是指克殷以前的周,文王治岐时的周;而“周人百亩而彻”承殷人而言,则指克殷以后的周。如此则本段文义毫无格扞矣。 此文之解释若对,则近人以为孟子认为“九一而助”的井田法是周代的制度,而引经据传去反驳他的,简直是无的放矢;而另一方面,用孟子这段话去证明周代实行过井田法的更是谬中之大谬了。 第二,本段中“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的规定,与下文所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各私百亩,同养公田”的制度有什么关系?如没关系,它在本段所描写的田制中的地位是怎样?后世读此段的人,自韩婴、何休以下,多不得其解,误认此“请野九一而助……”以下一节为叙述史事,并且误把“余夫”混入井田制里去。韩婴认为:“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何休认为:“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分之,一夫一妇授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授田二十五亩。”其实,“请野九一而助……”只是提出一种办法,而不是陈述历史(虽然所提出的办法被认为有历史的根据)。“请”之云者,正明此意。孟子此处所提出的是“彻”与“助”的混合制,故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什一使自赋”即是“彻”制。“国中”是指国都附近的地方,“野”是指边鄙的地方。“彻”与“助”各是孟子所认为历史事实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孟子的创议。下文叙井田制的一节是承“野九一而助”言,而解释之。故叙述完了,跟着说“所以别野人”也。中间关于“圭田”“余夫”的规定,则是承“国中什一使自赋”言而解释之。否则何以“野九一而助”的办法有了下文,而“国中什一使自赋”的办法却没有下文?依说话的层次,叙“圭田”“余夫”的一节应在叙井田的一节之后,今本殆有错简,又脱去若干字,遂不可解。但无论如何,“余夫”的规定决不能混入“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的井田制里去。孟子明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下》第七章)就平均言,八口尽可包括一家的老幼,而安用更有“余夫”?而安得更有“多于五口”的“余夫”?兹将上面所涉及今本《孟子》一段的原文和现在所拟的订正并列于后,以供参考。 原文: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拟正: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中缺)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没有本子的依据而颠倒古文,宜与程朱之擅改《大学》同讥,但我相信知言的人当不以此为迕的。 (二) 明乎所谓“什一使自赋”是述“彻”制,则孟子所谓“贡”“助”和“彻”的意义更无翳碍。兹略为疏释如下: 1. “贡”的意义本无问题。孟子引龙子的话道:“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样: 于每一区(分区的单位不可知),农田几年间的收成,求得一年的收成的平均数,然后于这平均数中取百分之若干(依下文“其实皆什一也”的话,则是取百分之十),以为每年的税额,不管各年实际的收成多少。因此丰年则嫌征收的太少,歉岁则嫌征收的太多。 2. “彻”制就是要补救“乐岁寡取,凶年取盈”的弊病的。以前解经的人因《论语》有“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的话,因以为“彻”制的要素在于什一而税。但依孟子所说,“贡”“彻”“助”皆可以“什一”,则此点绝非“彻”制的要素可知。在“什一使自赋”的一句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使自赋”三字。这就是说,让农夫每年于实际的收成中,取其十分之一以供税,而不是由公家规定年年一律的税额,如“贡”的办法。孟子所谓“周人百亩而彻”,是说周人行一夫授田百亩制而用“彻”法征税。孟子所提议在“国中”实行的是一夫授田五十亩,其家中的余夫二十五亩,而用彻法征税。 3. “助”的意义,我们若不把“圭田”“余夫”的一节羼入,也无甚问题。如孟子所说,“助”制的要素是有所谓公田和私田的分别。至于公田和私田的比率却没有一定。公田和私田的分配也不必成“井”字式。井田制只是助制的一种,助制不一定即是井田制。孟子所提倡而认为周文王曾实行过的是“九一而助”,他认为殷人所实行的是“七十而助”,比率显然不同。“七十”大约是说一夫授田七十亩,但若干人合耕若干公田则没有提到。 上面只释《孟子》所述和所提出的田制的意义,至于他所述与历史事实符合与否,另是一问题。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2期,1935年7月5日) 1本书系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开创者之一、史学家张荫麟先生的经济史文集。分四辑,收录其《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中国古铜镜杂记》《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等经济史学论文20余篇, 2 作者号称“天才史学家”,享有极高的学术威望。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 其治学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和梁启超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两个开山大匠”。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3全书逻辑严密,阐述清晰,作者透彻又睿永的思想,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问,尽以体现。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 4清华大学经济史名教授龙登高、邢菁华主持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