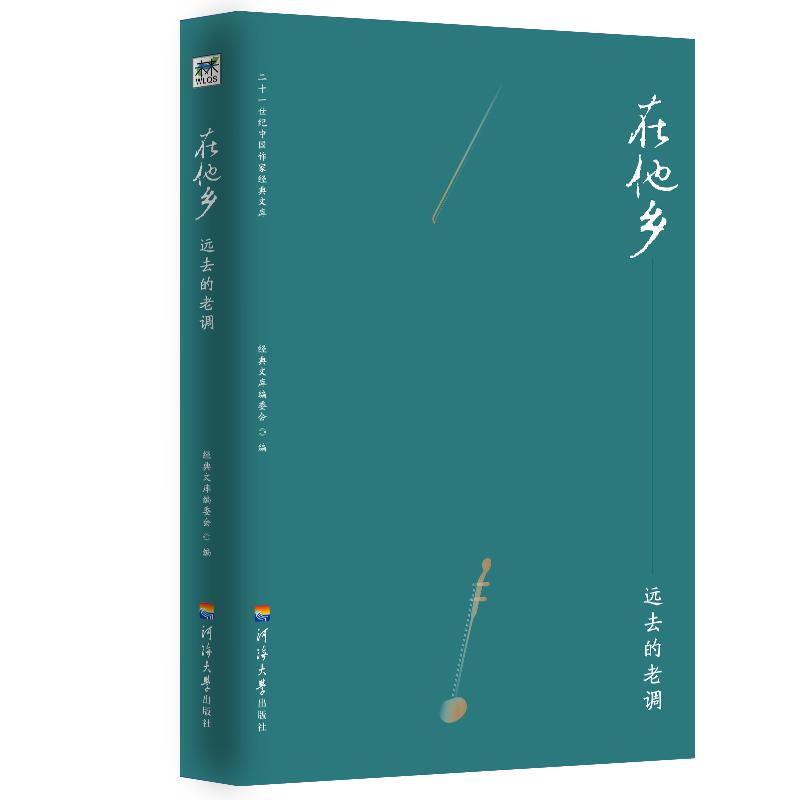
出版社: 河海大学
原售价: 59.80
折扣价: 32.30
折扣购买: 在他乡(远去的老调)/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63060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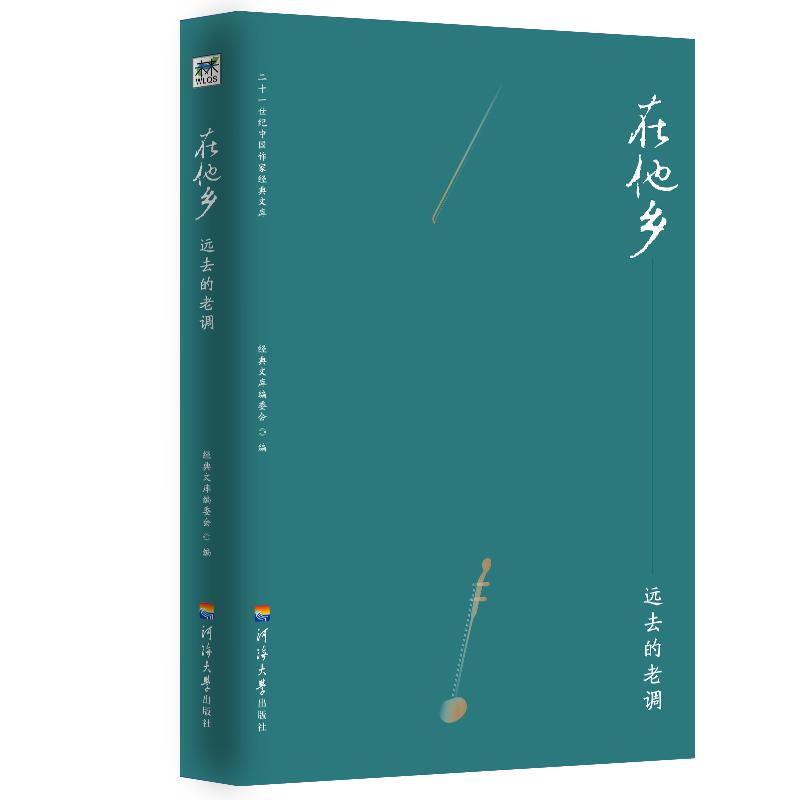
竹风萧萧纸乡行 朱仲祥 出夹江县城往洪雅方向行十余公里,便进入著名的纸乡马村。 其实在夹江,成片的竹子有数万亩,分布在青衣江的东西两岸,包括南安、迎江、中心和马村等地,形成莽莽苍苍的无边竹海。于是,一千多年来,夹江人便传承蔡伦的手工造纸工艺,利用丰富的竹资源生产文化用纸,也使夹江成为蜚声中外的纸乡。而今保持传统手工造纸技术的地方就在马村。 离开公路主干线,车沿绿竹簇拥的小溪而行,两边的竹子苍翠欲滴,构成一道绿色长廊。这里的竹以清秀婀娜的慈竹为主,夹杂着秀挺繁茂的苦竹、潇洒多情的斑竹、纤细柔媚的水竹和金竹,偶尔还可见到粗壮如椽的楠竹,高低错落, 多姿多彩。而用来造手工书画纸的主要是柔韧细致的慈竹。 据记载,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就曾寓居夹江。葛洪《抱朴子》“ 逍遥竹素, 寄情玄毫” 中的“ 竹素” 被认为是竹纸。唐代天宝十五载(7 5 6 年),“ 安史之乱” 中跟随唐明皇进川的大批工匠,将中原已臻成熟的“竹纸”制作技术带到了夹江。 其实, 长江流域和江南很多省份盛产各种竹类, 故竹纸多产于南方。《天工开物· 杀青》中“ 造竹纸” 一节, 开篇就提到:“ 凡造竹纸, 事出南方, 而闽省独专其盛。” 一千多年来, 夹江手工纸就因其种类多、品质优、产量高而名扬海内外。史载康熙二十年( 1 6 8 1 年),该地一种名为“长帘文卷”和“方细工连”的产品被钦定为“文闱卷纸”(科场用纸),每逢科举之年, 如数上贡朝廷, 历时两百多年。到了清代中期,夹江造纸产量进一步增加,《嘉定府志》曾这样记载:“今郡属夹江产纸,川中半资其用……”由此可见,夹江纸在清代同治年间已具备相当规模。其间, 夹江全县一半以上的乡镇从事或曾经从事手工纸生产。有一段时间,夹江因此被誉为“蜀纸之乡”,名扬全国。而今,夹江手工造纸继承了古代造纸技艺,从选料到成纸共有十五个环节、七十二道工序, 与明代《天工开物· 杀青》所记载的生产工序完全相合, 这种技艺凝结了中国古代人民伟大的科学智慧, 具有鲜明的民间特性和地域特征。夹江手工竹纸与安徽宣纸一道被称为“国之二宝”,而且被列入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粗犷有力的竹麻号子, 引导我们穿过茂密的竹林, 来到纸农造纸的作坊。只见九位孔武有力的汉子, 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指挥下, 围着一个约三米高的大铁锅, 吼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 有节奏地一下下用力舂捣着, 阳光照在他们赤裸的臂膀上, 闪闪发光。竹麻号子衍生于手工造纸环节中的劳动号子,具有节拍明确、韵律感强的特点,槽户(纸农)手握杵杆,边杵边唱,保证了动作的整齐划一,有效地激发了槽户的劳动激情。竹麻号子多为“ 恨杵” 即兴发挥, 内容多诙谐欢快, 一领众和。打竹麻的劳动单调而繁重, 竹麻号子的歌唱题材却谈天说地、多种多样,歌词具有极大的即兴成分,好的歌词因此流传开来, 成为槽户中的“ 流行歌曲”。爱情题材是竹麻号子歌唱的重要内容,比如,“纸槽加药水滑滑哟,妹儿心思哥难料吔! 只怕水随竹帘过哟,捞起愁思淌帘笆哦! ”歌词或含蓄委婉或率真泼辣。 他们唱着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的号子, 所做的是造纸工序中最基本的一道程序:蒸煮竹麻,就是把选取的竹料经过捶打后进行蒸煮, 那口大铁锅就是蒸煮竹麻的篁锅。此时锅下的火正熊熊燃烧, 锅上水汽蒸腾袅绕。已经蒸煮过的竹麻被汉子们用木杵使劲舂捣着, 他们要把竹麻捣成细细密密、碎烂如泥的纸浆。据说, 每年五月砍竹子时, 人们就边喊号子边围着篁锅填料, 一般的篁锅能装两三万斤原料( 竹子), 据说最大的篁锅能装下十万斤竹子。蒸煮的时间一般一次一周,还要反复地发酵、清洗, 然后才能捣碎、抄成纸, 再贴在墙上阴干。如今, 篁锅被高压蒸锅代替了, 一批原料只需蒸煮一天时间,大大缩短了造纸工期。 砍竹水浸、捶打浆灰、二蒸煮熟、浸洗发酵、捣料漂白、抄纸脱水、焙纸切割……在竹海深处的金华、石堰等村,传承千年的手工造纸工艺正在这里天天上演。夹江手工造纸工艺,从原料竹子到一张完整的纸, 整整需要十五个环节。前人概括为二十四个字:“砍其麻、去其青、渍其灰、煮以火、洗以水、舂以臼、抄以帘、刷以壁。”即砍竹麻、捶打、蒸煮、漂洗、 沤料、捣料、漂白、抄纸、压榨、刷纸。其中, 造纸工具主要包括纸槽、纸帘、纸臼、纸刷、撕纸标、竹麻刀、纸槽锄、竹麻锤、抓料耙、料刀、纸矛刀、切纸刀和割纸刀等。夹江古佛寺中立于清代的蔡翁碑, 对夹江的造纸技艺有更为精练的描述。透过千年历史的厚重尘埃, 夹江造纸这一原生态的技艺似乎并没有从先民那里消解掉文化的内涵, 在夹江那些造纸槽户人家的院坝里, 竹子青青, 蒸汽蔓延, 槽户们在一道道复杂的工序里,延续着先民们的光荣和梦想。 在这里, 除了唱着竹麻号子捣竹浆外, 其成纸环节也很吸引人眼球。只见师傅将竹帘在纸浆池中轻轻一舀, 再缓缓筛动, 待纸浆在帘子上分布均匀后小心揭起, 往一旁的纸墩上一倾倒, 一张湿漉漉的手工纸便成型了。然后再将这些纸轻轻揭起, 一张张往纸墙上刷上去, 经柔柔山风一吹, 宜书宜画的手工纸便完成了。当然, 最后还要用刻好了花纹的模板, 在一张张纸上印上福寿团花、瓦当图案之类的暗纹。这最后两道工序一般由妇女来做。她们无论手拿刷子将湿漉漉的纸刷在墙上,还是手拿印模在洁白绵柔的成纸上印上暗纹,都如舞蹈一般,娴熟而优美。 石堰村有一处完整的四合院, 坐落在青山下竹海中, 被当地人称作大千纸坊。这个典型的川西民居, 见证了国画大师张大千同夹江国画纸的一段特殊情缘。 张大千先生曾经到重庆寻找纸源, 这时有人给他推荐了夹江手工纸。张大千听说后来到夹江马村, 发现夹江纸虽总体不错, 但存在拉力不足等缺陷, 便与当地槽户石子青一起反复试验,在纸浆中适当加入棉麻之类,以增强纸的柔韧性,经过反复试制、试写、试画,新一代夹江国画纸问世了。而且,当时张大千还根据绘画的需要, 亲自定下了夹江纸的大小规格“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亲自设计了宽纹纸竹帘,并巧妙地制成暗纹印在纸上,在纸的两端做上云纹花边和“大风堂造”的字样。经过这番改进,一车车洁白细腻、浸润性好、书画皆宜的夹江书画纸走向了山外, 成为文人们争相追捧的书画用纸。如今, 大千纸坊内完整地保留了夹江纸制造所需要的器械, 如镰刀、石槽、筛子、刷纸墙等, 甚至很多已经过时的工艺器材,大千纸坊依然保留着。 在“ 青衣绝佳处” 的夹江千佛岩, 坐落着全国唯一一家手工造纸博物馆。它前临青衣江, 后枕千佛山, 风景优美,环境宜人。博物馆共分四个展厅: 功垂千古、作范后昆、古泾流风和蔡伦纪念馆。馆藏文物和实物标本两千三百多件,并陈列有数百个品种的古今中外名纸和全国著名书画家的数十幅夹江书画纸作品。功垂千古展厅, 进门首先看到的是蔡伦的塑像, 并有再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图画。以文物图画和实物标本, 展现了纸前时代人类记事的各种方法和造纸术在中国的发明发展。作范后昆展厅, 以夹江手工造纸的工具、原料等实物,表现了手工造纸的工艺流程,对七十二道工序、十五个环节都有所介绍。同时,这里还形象地展示了造纸工具,包括料池、篁锅、石臼或石碾、纸槽、纸帘、大壁、纸架等。古泾流风展厅, 展示的是夹江造纸的悠久历史, 以及夹江生产的各类纸品、纸加工品, 使用夹江纸的各类书画作品、报刊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明代以来手工造纸的八十六个品牌、一百三十多个花色样纸,张大千2 0 世纪3 0 年代在夹江研制、改良并监制的“ 大风堂造” 书画纸和古契约也弥足珍贵。第四展厅是蔡伦纪念馆, 塑有蔡伦坐像。夹江人把造纸之师蔡伦奉为纸乡之神。馆内还有碑刻, 纪念蔡伦以及为纸乡做出贡献的人们。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悠悠长河中, 总有一些曾经闪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中华绝粹无法穿越历史的迷雾, 悄无声息地陨落。然而历史在带给我们更多遗憾和迷惑的同时, 却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莫大的惊喜。四川夹江马村一带, 其传承古法的手工舀纸制造技艺,上承晋代的“竹纸”生产工艺,又与明代《天工开物》所载工序完全相合, 几乎原版地复活了造纸术,至今仍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华光! 元宵节里高桩会 朱仲祥 每年春节,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夹江父老乡亲们的最爱,也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而高桩彩会就是其中的保留节目之一,也是人们每年春节之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高桩彩会是峨眉山下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造型表演艺术。这一传统的民俗表演,反映了故乡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需求,更展示了父老乡亲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水准,被称为巴蜀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元宵节里高桩会高桩彩会是一种空间造型艺术。它把各种造型的演员(一般都是小孩)高悬、支撑在空中,构成立体精彩的艺术画面,产生奇特惊险、不可思议的视觉艺术效果。如一台名为《踏伞》的高桩造型, 装扮成剧中人物的女演员, 凌空站在撑开的油纸伞上,摇摇欲坠但就是不坠,很是惊险奇特;再如一台《活捉王魁》的高桩,那扮成穆桂英的女孩站在鬼卒手持的提牌上,居然就是掉不下来。当然, 我还见过更刺激的, 就是让演员置身在刀锋之上摆造型。这些风格各异,惊、险、奇、美的造型,使不少观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夹江的父老乡亲, 就是通过这种表演方式,鲜明地展示自己的审美和爱憎。 高桩彩会的造型内容, 取材于中国传统戏剧、历史小说中的精彩场面, 而故乡人喜爱的川剧故事是其中的首选。单是一部与故乡峨眉山有关的《白蛇传》,就能够衍生出“水漫金山”“船舟借伞”“断桥相会”“盗灵芝”等不同的高桩造型。此外,《水浒传》中的“十字坡”、《封神榜》中的“哪吒闹海”、《说岳全传》中的“朱仙镇”等,都是高桩彩会造型的惯熟题材。夹江高桩彩会, 将戏剧情节中的精彩场面, 由真人表演 定型为立体画面伫立于空中, 既神秘又真实, 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每逢元宵夜,家乡的民众社团都要举办高桩彩会。每年的元宵节,夹江城里或者一些乡镇,人头攒动, 盛况空前。人们老早就等候在街道两旁, 翘首以待。每当运载着一台台造型奇特美观、被装饰得五光十色的高桩车队缓缓驶来,人群就会发出阵阵喝彩,伴随礼花升空,锣鼓喧天,热闹的气氛升到了高潮。 高桩彩会绑扎技艺是夹江、峨眉山一带民间长期以来开展各项节日文化活动的结晶, 展示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水准。 夹江高桩彩会活动历史悠久, 在川内, 特别是乐山市颇负盛名,在中国民俗文化大花园中独树一帜。它由清末夹江乡间的平台、地会民俗表演逐步延续演变而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的故乡峨眉山下青衣江畔,平台、地会和高桩,原来是三种不同的民俗表演形式, 后来人们逐渐用高桩取代了平台和地会,但吸取了后者的精华部分。早期的高桩彩会,是在八人抬的方桌上表演, 称作高桩平台, 行话叫会墩, 相当于演戏的舞台。那时受制作材料、表演道具和器材等因素的限制,整个造型只能固定在方圆一平方米左右的大方桌上。这样的弊端是,只有孤独的人物造型,没有相应的背景衬托,显得较为淡薄简陋; 且只能人工费时费力地抬着走, 路程长了受不了, 就要停下来歇会儿再走, 影响了活动的连贯性。更谈不上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的运用,虽然古朴,但显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夹江高桩彩会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故乡的高桩彩会表演的改变,首先从运输方式的进步开始。从2 0 世纪7 0 年代开始,由原来人工抬着走,逐渐变为用手扶拖拉机载着走, 其优势是行走更加平稳, 平台面积上也有较大突破, 可以给民间艺人们更大的发挥空间。这种尝试得到社会一致好评后, 他们又大胆创新, 过渡到用农用货车或载重平板车运载。平台变大了, 造型内容就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场面更加壮观恢宏。特别是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将原人力抬着游行的会墩改在汽车上, 场面容量大, 增加了人物配景, 夹江高桩彩绘绑扎技艺制作更加完美、精湛, 形体表演从静止到动感,从无声到有声,从无照明到灯光布景。搭建平台和绑扎手段的改变, 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艺人们在节目取材上, 不仅继续保留传统的戏曲经典场景故事, 也大胆采用一些反映现代生产生活的内容, 比如登月计划、航空母舰、龙舟大赛等, 将传统艺术和时代气息相融合,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总之, 运载方式的改变, 带来绑扎技艺和艺术创作方式的改变, 使夹江高桩彩会更具稳固性、安全性、艺术性, 审美效果也更好。 高桩彩会在追求惊、险、奇、巧、美等艺术魅力的过程中,非常讲求力学原理,达到惊而不险、奇中有巧的效果,是艺术和力学的完美统一,其奥妙就在于民间艺人高超的绑扎技艺。我的父老乡亲们, 就是通过奇巧大胆的艺术构思和精巧娴熟的绑扎技艺, 把看似不可能的空间立体画面, 展示给节日里参加庙会的人们,实现他们求新求变、求巧求奇的艺术追求。大俗才能大雅, 大美藏于民间。这些艺人们, 都是民间艺术的传承者和创造者。长期以来,他们都在追求美、创造美。表现在高桩彩会上, 则是将传统戏曲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人物,通过服装、道具、化妆等艺术造型,使其成为所要表现的对象。对参与表演的小孩的挑选,有两个主要标准:一是年龄、个头要相宜,不能太大太高,否则不好支撑;二是身体结实,性格坚韧, 要能够和愿意在支架上坚持一个多小时( 如果加上绑扎的过程, 时间就会更长)。还有就是要与所饰演的角色接近。因为年龄等条件相对苛刻, 一个小孩最多参加两次表演就会被淘汰。听说我有次成为表演的候选人, 被母亲一口拒绝了。理由是我身体不行, 怕坚持不下来。但那些日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一上戏装就变了个样, 特别是扮作小生花旦的,美得不行,让人羡慕。 挑选到合适的小演员后, 再将这些小模特高悬、腾空于会墩之上, 成为元宵节里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或站在指尖上,或吊于刀尖下,以示其“险”;将人物或立于转动轮上,或立于飞带之中, 扮演动物生动逼真, 以示其“ 奇”; 小模特的服装道具制作精良, 加之整体造型大方、协调, 以示其“美”;整台高桩造型藏其机关、隐其锐角,通过暗藏转动滑轮、播放录音等秘密手段,以示其“巧”。 观看高桩彩会的人们总在思索追寻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探访高桩绑扎老人, 我才略知一二。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支撑模特的一根根铁棍上。这些铁棍不大也不小, 但足以支撑表演的孩子们。铁棍一头固定在平台上, 一头绑扎在模特腰间,看似很危险,实则牢靠安全。这些起到固定作用的铁棍,被戏服和道具巧妙地挡住了,一般人看不出来。不过,过去用人工抬着走时,出现过失误,因不堪负重而将演员颠下了平台,露出了里面的铁棍机关。近年来采用汽车运载着沿街慢行,这种掩饰的效果就更到家了,一般外乡人更不容易看出名堂。 近年来, 故乡夹江的高桩艺人们, 又把灯会和杂技的一些技法运用到高桩彩会中来, 创新了高桩彩会的表现形式,所使用的不仅是铁棍和布条, 还有光学、电学, 参与制作的人也年轻化了。故乡的新老两代人一起努力, 让这一民俗艺术彰显出更加迷人的魅力。 《远去的老调》一书聚焦于那些曾经存在过、却正在消失着的旧物事,在渐渐远去的乡风民俗中,感受岁月无声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