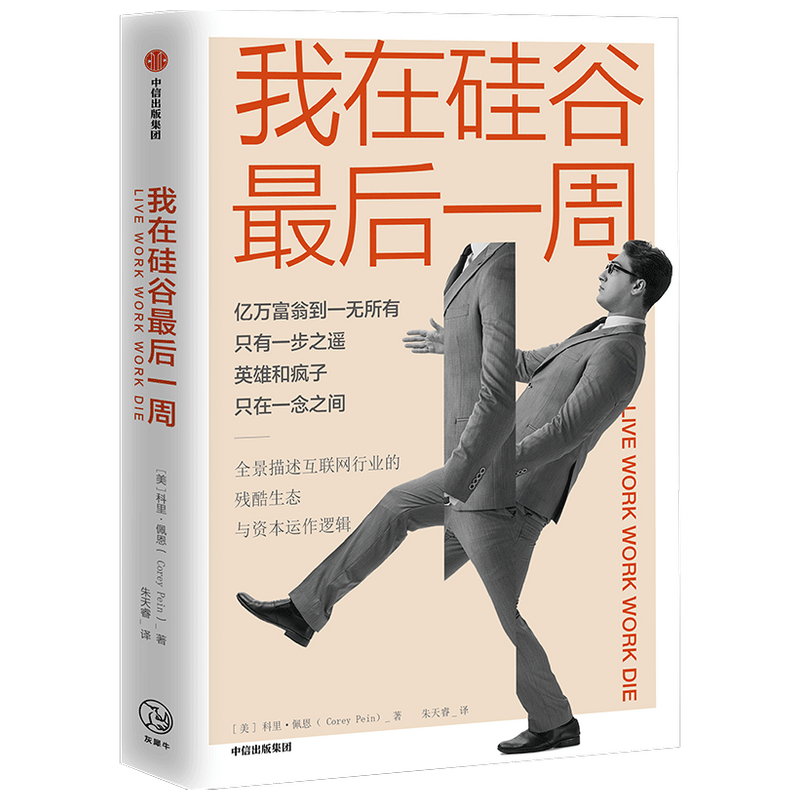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8.40
折扣购买: 我在硅谷最后一周
ISBN: 9787521716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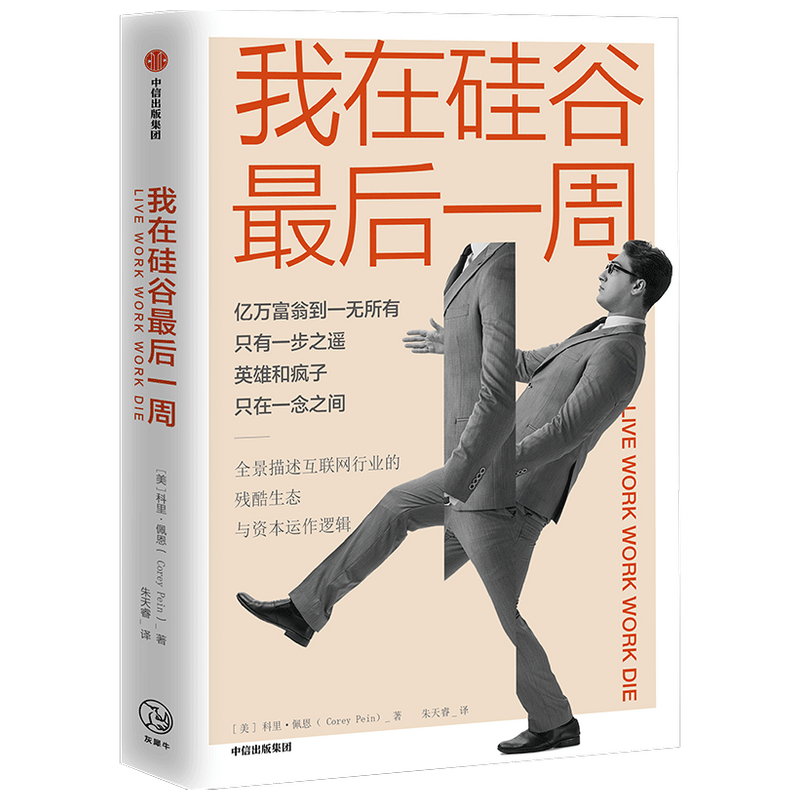
科里·佩恩是《The Baffler》科技杂志的调查记者。他也曾在《维拉麦特周报》(Willamette Week)供职。还曾为《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以及其他出版物供稿。现在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在硅谷创业热潮的鼎盛时期,佩恩作为资深调查记者,失败的内容创业者身份前往硅谷,寻求二次创业成功。他深入硅谷食物链的底层,了解真实的创业企业在硅谷的生存状态。 佩恩言辞流利、嬉笑怒骂,自称要追求财富、改变世界。。但是当他通过爱彼迎的招租广告,住进了描述和实际严重不符的创客空间时,受到了印度班加罗尔和挪威来的其他租客们不冷不热的欢迎……在体验了硅谷的奋斗和心酸后,佩恩最后决定离开硅谷。
谷中篝火 我意识到,倘若选择和无家可归者们一起住在帐篷里,我就不需要再向“爱彼迎”缴纳房租了,就在这时,我在硅谷的这场鲁莽的磨难也就宣告结束了。我忍受了这场竞赛中的各种羞辱和 折磨,但是在性格塑造、社会地位提升和财富积累方面都一无所获。这就像电影《战争游戏》(War Games)里操控美国核系统的超级电脑所说的那样,创业游戏中唯一的制胜之道就是不参与。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回家,见到了我那耐心的妻子后,我立刻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解脱感。 但我真的逃出来了吗?又有谁真能从中解脱呢?谋生越来越意味着在科技行业设定的条件下榨干自己的精力,而整个就业环 境所鼓励的自我商品化的强制性味道也越来越浓。产自硅谷的电子仆从在你的口袋里如影随形地监视着你,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它们搜集一切信息,然后全部上报。通过各种数字记录,它们最终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他们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遗忘的,他们替你记着。你找寻的,它们帮你储存。我们像牧场里的小牛和母牛一样被标记,被跟踪,在记录中变成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存在,被来自以太的成千上万条紧急却毫无意义的指令戳着,驱赶着。创建帐户,登录,继续,点击同意。叮!你收到了通知。难道是你的老板?你此时不应该在工作么?你为什么在阅读这个?点击,滑动滚轴,分享。我们努力坚持着。感到焦虑?那就来点多巴胺吧。叮!更多的通知。过去,对工作感到厌倦也没啥大不了,一些懒汉也做成了大事。如今,你找不到闲人。即便人们都在告诉自己,你需要休息,但还是不停在工作。有人说 “数据就是新的石油”。“可数据的本质就是我们自己,新的石油就是我们本身。与石油不同的是,我们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创业泡沫从2005年左右开始,在大约12年后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对于半生不熟的初创公司们来说,容易钱已经被赚完了,就跟那些被过度炒作的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遭遇的尴尬境地一样。曾经宣称“要么在旧金山发财,要么就破产”的那些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如今越来越倾向于去匹兹堡或底特律这类开销更低的城市积累财富。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结果很明显:跟前几年不同了,硅谷造不出独角兽来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的泡沫并没有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那样骤然崩塌。实际上,泡沫的表面像茧一样逐渐凝固起来。于是我们看到另一种荒谬的美国式的过度消费——“高科技郁金香狂热”(a hightech tulip mania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瞥见:一场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性的经济转型。金融危机时对华尔街的救助使美国政府转变成了资本的仆从,这是自1929 年大萧条后前所未见的。而在我们目前经历的这场创业泡沫 中,举着网络 2.0(Web 2.0)大旗的独角兽公司们对经济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他们将表面上的的顾客变成了一种宝贵的数据来源和免费的劳动力,这可能,或者说实际上,也意味着更加深入的剥削。 毋庸置疑,华尔街的浮华和贪婪可与硅谷相匹敌,但说到控制世界的宏伟野心,鲜有人能同硅谷的那群技术宅相匹敌。他们赌的是,未来的几代人寄希望于兜售各种小玩意的商贩们解决面包、正义和安全,而非政府。这并非牵强附会。数以千万计的美 国人实际上已经是苹果、优步和亚马逊的公民;这些公司的政策 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而且这些 品牌的标识也肯定比国家和政府更能激发人们的忠诚。这些科技 大亨们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心中,他们目光敏锐,工作勤奋,善于解决各种问题,奋斗在传统的最前沿,为美国人提 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两样东西:认可和希望。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被培养成了一群乐观主义者。但正如一位著名企业家所说的,这也意味着美国大众被培养长了一群傻瓜。美国人无法理解许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事情已经非常糟糕了,而且总还会变得更糟。 我知道科技公司们设想的未来可能会很丑陋。可无论我如何 靠近他们,去观察他们,我都无法想象,为了建构他们心中的乌托邦,这个新的精英阶层准备给全世界的民众施加多大的痛苦。因为这个阶层时而古怪却人畜无害,时而又幼稚得让人恼火,而在面对别人时,他们又总是一副自鸣得意。未来,这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将被利益所驱使的单一主义引向疯狂的争夺,离开湾区后,2016 年 9 月我一边写书一边与妻子来到东印度的农村。她在一所由亚洲各地的达沃斯级别的富豪资助的新建 大学里任教。比哈尔邦(the state of Bihar)差不多是一个人从硅谷逃出来后,能跑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我们住在一间大学征用的 旧旅馆里,整修后,这栋楼变成了学生和教员的宿舍。就在这栋楼周围,当地居民们用油布支起帐篷,住在泥地里,养着骨瘦如柴的山羊。通常,他们共用一个手摇井,一部手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新的技术一无所知。走在泥泞的路上,旁边的铁皮小屋里,小贩们在打折出售SIM卡,自带不限流量的高速网络套餐。所有的孩子都会用 WhatsApp。假如让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这种科技乐观主义者看到这一切,他们肯定会为这座现代化的灯塔惊叹不已,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和繁荣指日可待! 结果并不尽然。颠覆旧世界的力量来到了印度,它带来的却是一股恒河泛滥般的巨大力量,横扫一切。2016 年,印度总 理(Modi)以进步的名义,在一群所谓的专家和唯利是图的 科技公司的建议下,推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破坏性极强的经济改革——“去货币化”(demonetization)。在既无事先警告,也未经公开讨论的情况下,**政府宣布, 500 卢比和 1000 卢比纸币将不再被视为法定货币。而印度流通现金中有近 90% 是这两种面额 的纸币。人们不得不把这些纸币存入银行,兑换更大面额的新纸币。但政府解释说,这项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带来的效益很大。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货币流通中更多地选择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进行数字支付,而不再使用现金。 废钞的公告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印度全国性的银行挤兑,并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囤积。自动取款机前的人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而各类商业活动也几乎陷入瘫痪。面对潮水般的批评,印度政府找出了各种各样、往往相互矛盾的理由为政策辩解:“去货币化”将重新平衡现金供应、提振经济、打击腐败(普及数字支付后,行贿或避税将很难不留痕迹)。有一条理由,政府始终在大加宣传:“去货币化”就是现代化。在这些人脉广泛的科技创业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印度正在向“数字化和无现金经济” 跃进。 在印度政府做出这一突然决定的同时,政府支持的移动支付程序的宣传攻势也展开了。他们买下了所有主流报纸头版的整版广告,上面印着展示莫 迪的笑脸,以及他对“印度支付宝” (Paytm)这款应用的支持。这款应用的推出利用了印度政府强制 实施的“去货币化”政策所造成的混乱。莫 迪的政治对手声称, 其政党与这家此前默默无闻的创业公司有牵连。确实,“印度支付宝”乍看下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实际上其大股东是中国投资者。该公司由一个喜欢参加派对的印度技术人员领导,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来自宝莱坞中心(Bollywood central),还曾为参演过 “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音乐翻拍版。(莫 迪的政党 和该公司均否认了任何此类指控。) “印度支付宝”可以说得到了硅谷的真传——程序设计混乱, 漏洞百出。因为纸币被宣布无效了,这个程序瞬间拥有了十亿客户,但是它根本无法处理每天巨量的交易。与此同时,在印度,有数亿人无法使用这款程序,印度政府却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备用方案,更何况这款程序也不好用。在我们小镇上,很多店主和菜贩连鞋子都穿不起,用智能手机就更甭提了。在这些地方,“印度支付宝”根本不存在。这一年冬季收获之后,因为很多人没有纸币去购物,大量的农作物被扔在地里,任其腐烂。莫 迪强制推行移动支付系统的结果,可以准确地被描述为一片混乱。在城市里,许多病人和老人死在长长的自动提 款机队伍中。至少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医生在索要现金无果后拒绝治疗病人。为什么付不出现金?因为大家都在排队等着取钱呢。人们整天在一台又一台的提 款机之间穿梭着,最终发现哪台机器都取不出钱了。然而印度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们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都会派佣人去购物,由此避开了这场意志力和耐力的比拼——“去货币化”后的日常购物。不但如此,他们还对莫 迪谈到的“去货币化”能反腐这一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们眼中,印度支付宝纵然有着繁多的缺点,但这种生活方式也能给他们带来自豪感,因为它体现了印度的崛起。外国记者们也普遍错过了“去货币化”的灾难性后果,或者说至少是错过了一开始的部分。他们大多只是尽职尽责地报道了印度政府“去货币化”的立场,以及紧随其后的移动支付革命如何对外界释放了强烈的信号,象征着印度已经“打开了大门”。可以说,莫 迪把印度变成一个实验室,将有史以来科技创业公司最欠考虑且破坏性最强的实验,强加给了对这一变革最不情愿的一群人。印度支付宝已经表明,彼得·泰尔(Peter Thiel)最初的设想的“贝宝”(Paypal)“统治世界”(他的原话“World Domination”),即货币的数字化和私有化,想要实现的话,可能除了通过法令之外,别无他法。“印度的‘去货币化 ’ 可能成为第一个现金被抛弃的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块。”《福布斯》评论员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印度的废钞实验会在其他地方重演。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国际媒体的报道没有准确传达这一实验的后果。相反,他们纷纷采用了科技媒体的风格,重复着印度官 方那套移动支付将“释放”印度经济增长潜力的宣传口径,并称 赞莫 迪为印度的未来押下了“高风险、高收益”的赌注。那么在印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印度政府以公司的形式批准了一批贵族的垄断行为,以铸造全新的货币。有一天我在一台提 款机前排队,机器旁有一个持*的守卫,他一直没等来现金,于是开始咒骂起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说这玩意简直毫无用处,买点吃的都做不到。当时我就在想,让程序员们统治这个世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陌生,且动荡逐渐加剧的世界。我不打算像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那样扮演预言家,但我确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将承受硅谷的科技公司带来的进一步“冲”。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阿姆斯特丹遇到的那些技术奇点主义者们都是一笑了之。因为我必须承认,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新技术终将成为现实,然而这个世界已经深陷各种政治和环境危机,这之外还要应对这些技术带来的冲击。最为可怕的是,这些发明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摆脱了人们的控制。正因为如此,改变世界的技术该如何分配,又该如何发展,这类大问题不能只由少数几个斯坦福出身、自信心爆棚的富人来决定,因为他们对历史、政治、语言和文化漠视的程度令人震惊,更不用指望这群人会去体察穷人们的求生之艰了。 技术奇点主义者的幻想可以牢牢吸引住全世界最狂热而利己的商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幻想有望赋予他们终极且永久的力量。美国科技寡头们的野心透着浓浓自我意识过剩,他们的设想简直有点可笑了——超人的力量、专属个人的超高速交通。在想象中,他们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更优越的种族。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实现想象中的一切,但不幸的是,这个超级精英阶层可以从这个发展出的任何新技术中获益,而成本则将一如既 往地落到我们其他人的头上。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过去,那些腐朽的国王们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复杂的问题往往有一个颇为简单的解决办法,比如砍掉他们的头。 1. 全景展示硅谷初创企业、初创者的奋斗和心酸。 2. 独特的视角。写作者以调查记者、首次创业失败的身份前往硅谷,全程体验硅谷的创业生态。读者跟随写作者,更有代入感。 3. 语言风格诙谐幽默,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硅谷科技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