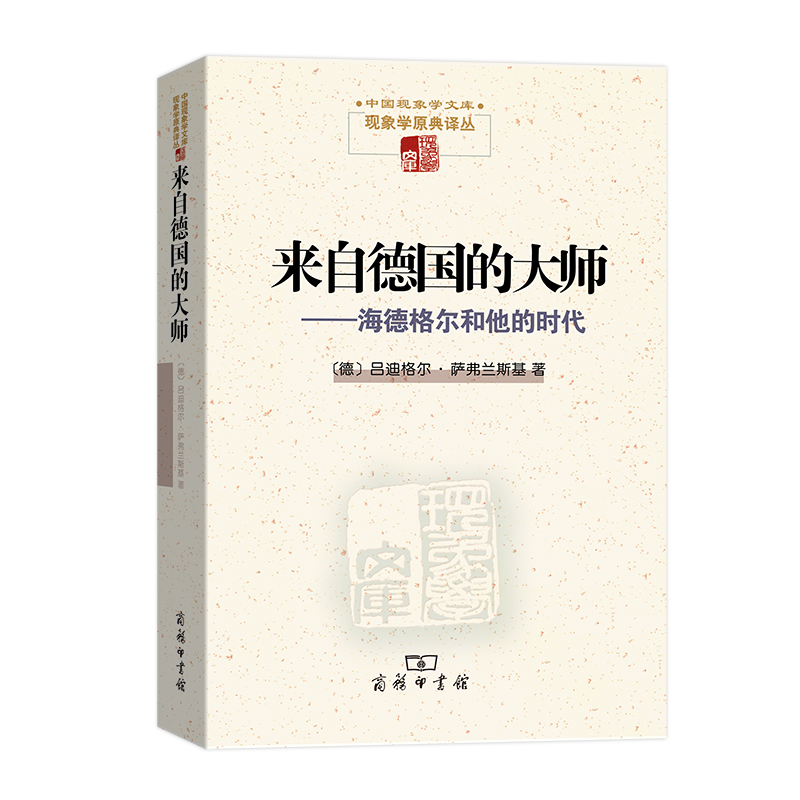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3.20
折扣购买: 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
ISBN: 9787100055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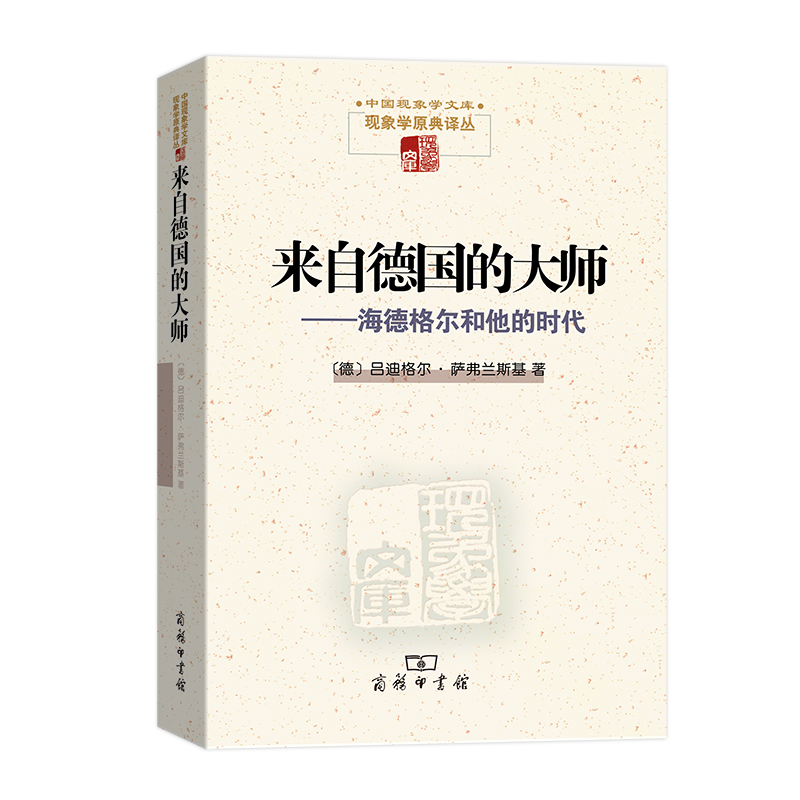
1928年已经成为名人的马丁·海德格尔,在给他以前在康斯坦茨天主 教寄宿学校上学时的班长的信中写道:“也许哲学以最强烈、最持久的方 式向人们指出,人总是一个刚开始的新手。哲学探讨最终无非就是意味着 当一个刚开始的新手。” 海德格尔开端的赞扬具有多种含义。他想当开始开端中的大师。他到 希腊这块哲学的开端中去寻求已经逝去的未来,而在当代他却想在生活中 找到使哲学持续涌流之源。而这些恰恰发生在“人生之心境情调 [Stimmung]”中。对那些硬性规定必须从思想开始哲学思考的哲学,他持 批判态度。海德格尔说,哲学应该始于“人生之心境情调”,始于惊异、 畏惧、忧虑操心、惊叹好奇和狂欢。 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人生之心境情调”把生活与思维联系在一起。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断然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本人思维与生活之 间的联系做任何研究探索。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某堂课上,海德格尔用下 面十分简练的话作为开场白:“他诞生、工作而后死去。”海德格尔希望 后人也能这样谈论他自己,因为他的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哲学生活,甚至 消失在自己的哲学之中。这当然和他的人生心境情调有关:他急于(也许过 于急切)发现现存东西中最紧迫的东西,以便稽查出其中的隐秘。也许,最 紧迫者莫过于生活本身。海德格尔的人生之心境情调使他自己言道:“人 生此在即是被抛”,存在[Sein]则“被揭示为负担”。因为“对于它是否 愿意进入‘人生此在’一事,作为此在本身的人生此在何时曾自己自由作 过决定?或者有朝一日能自己决定?”(《存在与时间》,第228页) 海德格尔喜欢作大动作。所以人们从来弄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在谈论 西方世界还是在谈论他自己,是就存在本身还是就他自己的存在进行辩论 。但是,如果“哲学不是起源于思维,而是起源于人生之心境情调”这条 基本原则的确有效,那么便不允许我们把一种思想只放到同其他思想的较 量中,即置人思想传统的高原之上。当然海德格尔同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传统显然不允许把 他自己的人世[Zur-Welt-Kommen]作为偶然馈赠[Geschenk],或者作为承诺 甚多的莅临来体检。所以那一定是一场大变故,他的人生之心境情调所向 往的就是这种大变故。 他感到,自己“被抛”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他1889年9月26日出 生在那里,在那里度过童年的上世纪末的麦氏教堂镇。但这块土地毕生令 他魂牵梦绕。当那个作为他对现代性吹毛求疵的后盾的故土世界将他抛了 出来时,他方才感到自己是被抛了。我们不要忘记,出生并不意味着人世 的完成。在人的一生当中,人必须反复诞生多次。而且可能永远不能完全 贴近世界。现在我们先谈海德格尔的第一次诞生。 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个箍桶匠兼麦氏教堂镇的天主教 圣·马丁教堂的司事,于1924年去世。他肯定经历了儿子与天主教的决裂 ,但却未能赶上经历儿子哲学上的成功。母亲死于1927年。海德格尔在她 的灵柩里放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存在与时间》。 他母亲的家族世居邻村格根恩。每当凛冽的寒风从施瓦本山的高原上 袭来的时候,麦氏教堂镇的居民们便说,“从格根恩刮下来的……”。母 系祖上几代都生活在村里的国有庄园“窿洞农民田庄”。。1662年西妥教 团修道院准许海德格尔的一位高外祖雅克布·肯普夫在位于普福伦村附近 的这所森林庄园中务农为生。1838年海德格尔的另一位外祖用3800古尔登 将田庄赎为己有。但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教会子民的身份。 海德格尔父系的祖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在18世纪从奥地 利移居此地的。麦氏教堂镇的镇史研究者发现,海德格尔血缘可以上溯到 麦格勒尔和克罗伊策尔家族。17世纪最著名的布道者亚布拉罕·阿·桑克 塔·克拉拉就出身于麦格勒尔家族。而另一个家族中则诞生了作曲家康拉 丁·克罗伊策尔[Konmtin:Kreutzer]。海德格尔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 校时的宗教指导教师、后来的弗赖堡教区大主教孔拉德·格勒贝尔也是海 德格尔的远房亲戚。 麦氏教堂镇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坐落在博登湖、施瓦本山和上多瑙河 之间,是阿雷曼地区和施瓦本地区交界处的一块贫瘠而穷困的土地。阿雷 曼人天性持重,性情忧郁,好冥想沉思。而施瓦本人性格爽朗,坦率,耽 于梦想。前者倾向于冷嘲热讽,后者更乐于驰骋激情。马丁·海德格尔两 种天性均沾。约翰·彼得·黑贝尔是阿雷曼人,荷尔德林是施瓦本人,两 人都被海德格尔选作自己的庇护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两人均受到各自乡 土民情的陶冶,而后都出脱为大世界中的伟人。海德格尔对自己持同样的 看法:“向太空的广阔自由开放,同时又生根于大地的幽冥之中。”(《思 想的经验》,第38页) 1942年,有一次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解释荷尔德林的多瑙河赞歌《伊丝 特尔》。在他的讲稿中夹着一张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未予收录的字条,上 面写着:“也许诗人荷尔德林,注定要成为一位思想者的有决定性意义的 赠品:其祖父于《伊丝特尔赞歌》诞生之时在位于上多瑙河激流之畔、山 岩峭壁之下的牧场羊圈中出生。”(珀格勒:《海德格尔对自己的政治理解 》,第41页) 是自我神化吗?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确定自己出身的 尝试。在威尔登施坦山巅城堡之麓、麦氏教堂镇脚下、多瑙河畔的一所房 子上,闪烁着荷尔德林的光华;18世纪海德格尔家族生活在这里。这所房 子还在。房子现在的主人向来人叙述着,头戴巴斯克圆帽的教授如何频频 光顾此地。 在多瑙豪斯和威尔登施坦城堡附近静卧着一个小镇博伊隆,它环抱着 一所天主教本笃会的修道院。这里过去曾是奥古斯丁教团唱诗班的男修道 院,里面有牲口栏、粮食垛以及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这个静谧的修 士世界一直吸引着马丁·海德格尔,即便是在他和天主教决裂之后亦是如 此。在20年代,寒暑假期间他间或光顾修道院,在僧房中盘桓数周。1945 年到1949年间,盟军禁止海德格尔从事任何教学活动。那时,博伊隆修道 院是他能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的唯一场所。 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