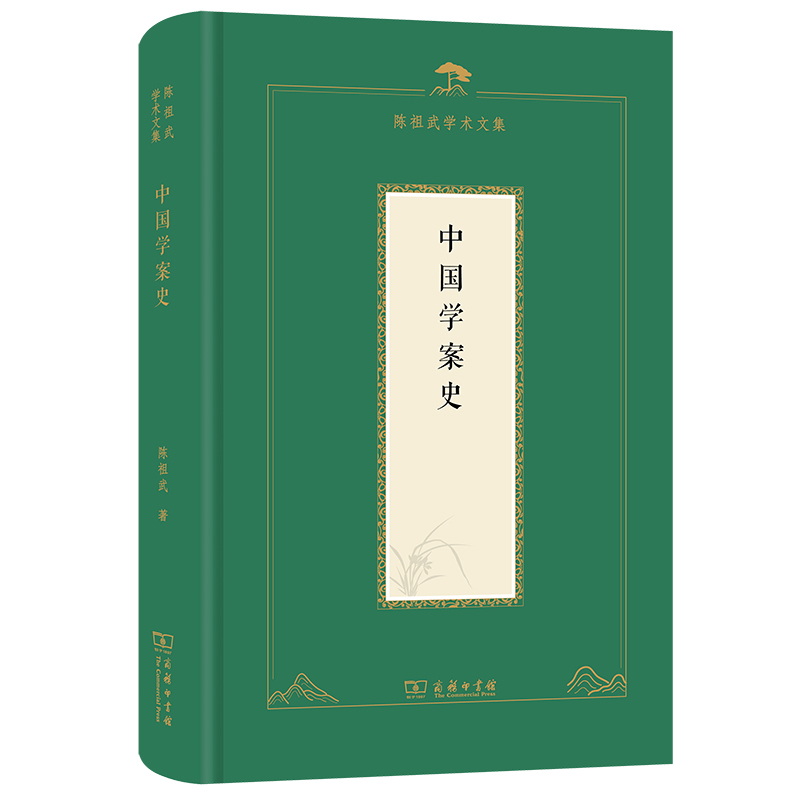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6.00
折扣价: 67.20
折扣购买: 中国学案史(精)/陈祖武学术文集
ISBN: 9787100211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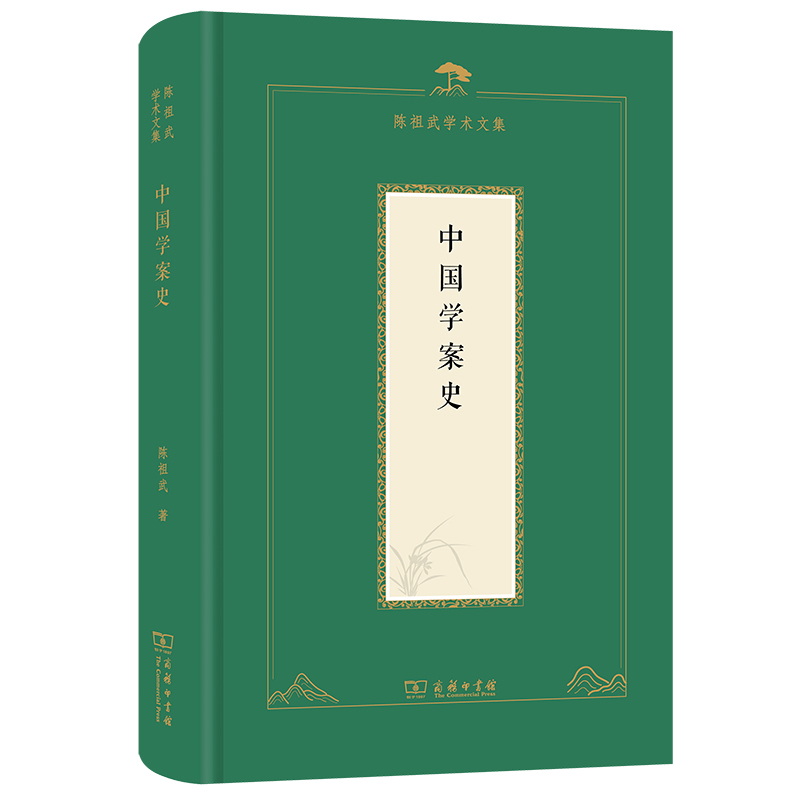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认同,迄今已成史学界的共识。然而较长时间以来,却少有学人去对这部开风气的著述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伊始,卢钟锋先生在《孔子研究》撰文,阐幽发覆,钩沉索隐,做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以下,拟接武卢先生之大作,就《伊洛渊源录》的撰述背景、成书经过、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及学术价值等,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撰述背景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遁翁等,学者以其所居,尊为紫阳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后定居福建建宁府建阳县,遂为建阳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岁。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时年十九岁。后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军、漳州、潭州,至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止。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仅四十日。其他岁月则多以祠职虚衔,课徒乡里。庆元二年(1196),以倡“伪学”落职罢祠。四年(1198)致仕,两年之后即溘然长逝。嘉泰间,学禁弛除,赐谥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奉诏从祀孔庙。朱子一生,弟子满门,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生撰文及论学问答,后人辑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谱长编》,于朱子一生学行,记之最详,亦最可信据。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现存朱子的有关文字而言,最早议及这部书的文字,为孝宗乾道二年(1166)写给友人何镐的书札。在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谈到了正在结撰的《伊洛渊源录》,他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朱子时年三十七岁。何以朱熹要在此时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由于该书与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并无序、跋一类文字,因而对这部书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体说来,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另一个则是朱子个人的学术师承。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术环境。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诸家首倡于前,至周敦颐崛起,援佛、道学说以入儒,著《太极图·易说》《易通》,提出“主静”“无欲”“无极”“太极”“理气”“心性”诸范畴,以“性与天道”的讲求,开始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过程。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程氏兄弟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道学自北宋中叶形成,迄于北宋亡,它并未取得学术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苏轼、苏辙兄弟的诗文之学相颉颃,又有讲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学的压制,尤其是荆公新学凭借其政治势力而风行于世,更对程氏道学的能否立足构成一大威胁。程颢去世,时值元祐更化,程颐之学虽一度抬头,但哲宗亲政之后,伴随党派政治的风云变幻,它屡遭黜斥。徽宗崇宁间,程颐竟因“学术颇辟,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被“尽逐学徒”,置身于奸党名籍之中。宋室南渡,政局反复,元祐奸党名籍明令废毁,王安石被逐出孔庙,褫夺王爵,程颐学术亦渐得褒扬。但是,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据《续资治通鉴》载,直到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犹上疏请求禁绝“伊川学”,他说:“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党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转相传授。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公辅言出,程门弟子后学纷起驳斥。绍兴七年(1137),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正是在这篇奏疏中,胡安国提出了明定道术的问题,他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与之同时,程颐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则拒不就任经筵讲官,以示抗议,且理直气壮昌言:“学程氏者焞也!” 后来,陈公辅虽被贬为外官,但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门后学魏掞之应召赴杭州,进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结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响。 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 以上,我们对迄于南宋初的学术环境,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接下去,拟谈一谈朱子的学术师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渊源录》去述道学统绪,这是与他作为程学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朱熹为学之初,即因家学濡染而自程学入。其父朱松,师从南剑罗从彦,得闻程门高第弟子杨时所传程氏兄弟之学。十四岁以前的朱熹,随其父所讲习者,即为二程关于《论语》的解说。父卒,托孤于刘子羽,遗命从父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问学。胡宪为胡安国从子,刘勉之早年于杨时曾亲承教言,勉之课督朱熹如子侄,并妻以长女。二刘胡氏之学,皆近承杨时而远宗程颐,为东南程门后劲,所以朱熹青少年时代的为学根柢,就大体而言,应是以程学为矩矱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刘子翚、胡宪皆喜禅学,朝夕相随,使早年的朱熹亦与禅僧道谦、圆悟等过从甚密,为禅学长期习染而不自觉。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问学于其父生前同门友人李侗,迄于三十年(1160)与李侗正师弟礼,朱熹始毅然摆脱禅学羁绊,成为程氏道学的笃信者。 关于朱熹早年皈依程门学术的过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据称:“初师屏山(刘子翚——引者注)、籍溪(胡宪——引者注)。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李侗——引者注)。”朱熹还回忆早年住刘子翚家时,与一禅僧的交往,他说:“一日在病翁(刘子翚——引者注)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原注)。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著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自问学李侗、皈依程门之后,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谢良佐语录肇始,朱熹为护卫程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八月,应诏上疏,力谏孝宗讲求程氏兄弟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不可为佛、老之书所惑。朱熹疏中有云:“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旋即取二程及其门人友朋关于《论语》的解说,辑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随后,朱熹潜心于二程学说旨趣的阐发,先是于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学说中,“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史称“丙戌之悟”。继之得湖湘学派著名学者张栻启发,于三年后推翻前说,专意弘扬程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史称“己丑之悟”。其间,他在乾道二年撰成《杂学辨》,以明苏氏兄弟之学非儒学正统。四年(1168)四月,又校订二程门人所记程氏兄弟论学问答语,成《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并附以所辑《伊川先生年谱》等合为一书。在该书后序中,朱熹写道:“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复取先前未予收录的二程论学语,于乾道九年(1173)六月,辑为《程氏外书》十二卷刊行。与之同时,他还致力于与二程在师友之间的周敦颐、张载诸家学术的表彰,先后撰成《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访朱熹于武夷山,二人携手合作,分类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论著为《近思录》十四卷。至此,朱熹成为程氏学说的权威解说者,显示了他作为程学干城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间,为确立二程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他以《伊洛渊源录》去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便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旧日读朱子书,蓄一疑问于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当年何以于《伊洛渊源录》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后来将朱子《文集》与《语类》《渊源录》等比照而观,个中缘由始渐悟出大半,原来这同该书的结撰过程颇有关系。尽管代远年湮,文献有缺,关于成书的若干具体细节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脉络可以说已经清楚。以下,拟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经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而福建邵武学者何镐,则是最初促成该书着手编纂的一个重要人物。镐字叔京,福建邵武台溪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仅四十八岁。其父兑,字太和,号龟津,学者称为龟津先生。兑以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南渡后官至辰州通判,后因表彰程氏弟子马伸忠节,忤权相秦桧而去职。其学自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学最称专精。镐妻叔父李郁,传杨时之学于乡里,一时学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镐承家学,贯穿经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学为归,著有《易说》《论语说》及史论、诗文等数卷。乾道二年(1166)夏初,何镐慕名访朱熹于崇安,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镐长熹二岁,自初识迄于何镐去世,朱熹始终事之以兄礼。大概正是在何镐的这次过访中,朱熹与之议及《伊洛渊源录》的结撰。只是由于朱子当时正忙于辑录校订《程氏遗书》,很可能大致陈述著录人选的初步构想之后,便委托何镐先行草拟一个详细的大纲。因而这年秋天,朱子致书何镐,才会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这里所说的邵氏,当指邵雍。何镐接书,即遵嘱将所拟之大纲寄朱熹,于是同年冬,朱熹有书答何镐,告以“《渊源》《闻见》二录已领”书所言《闻见录》,当是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伯温书乃《伊洛渊源录》的重要史料来源。而《渊源录》,或许就是何镐代朱子所拟之大纲初稿。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揣测?除方才所引述朱子与何镐的两封书札外,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今本《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有关马伸生平行实的材料,皆出自何镐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为何兑撰《逸士状》,一为何镐撰《续记》。而何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为《逸士状》所写跋,即全文附于状末。跋文避何兑名讳,而屡称“先君”,文末落款亦直书“男镐谨书”。这与同书卷十录朱松撰《遵道墓志铭》,朱子所做题注语气略同,朱注云:“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显然,倘若何镐不是最初的大纲拟草者,或者说撰稿人之一,这样的行文方式是不会出现于书中的。第二,书中著录的程门弟子,每有朱熹以题注形式提出的异议。譬如卷七所录范祖禹,朱注即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同卷之杨国宝,朱熹亦据程颐所撰祭文及吕希哲《吕氏家塾记》考订:“国宝宗应之,无他叙述,独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诸书记其言行之一二。然详祭文,亦先生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吕氏言其元丰中已老,则年辈与先生亦相若云。”又如卷十四所录王岩叟,朱熹则认为:“盖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说明《伊洛渊源录》的最初拟目者,并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时朱子的交游而言,与上述诸条合观,则何镐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渊源录》虽于乾道二年冬即已初成大纲,但是一则因为朱熹此时著述头绪太多,不能专意于该书的结撰,再则大纲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时又难以确定下来,所以时辍时续,历时数年而未见大的进展。此处所谓难以确定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二程学术的师承,即与周敦颐学说的关系不明,此其一。其二,该书既以专记二程及诸弟子生平行实为职志,以期彰明程学源流,而大纲著录的程门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订等工作要做。其三,则是对一些拟著录者的究竟是否程门弟子,还需予以澄清,因而难作定论。为此,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长途跋涉,访程门后学张栻于湖南。乾道四年、五年两年间,又就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事,与前辈学者汪应辰屡有书札往复。迄于乾道九年(1173)初,尽管托友人刘清之等所收集的资料间有寄来,结撰工作亦已加紧进行,然而上述三个问题中,除第一项因得张栻、吕祖谦等人赞同而可告解决外,后二项则终属悬案。 面对这一状况,朱子显得缺乏耐心,急于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书友人吕祖谦,征集程门弟子李吁为同门友好刘绚所撰墓志铭,信中即告以正结撰《伊洛渊源录》的信息,并托吕祖谦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温州)籍程门弟子的传记材料。朱子此信写道:“刘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两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就《伊洛渊源录》结撰事,书札往复,多所商榷。这些书札成为了解该书成书经过,以及朱子何以于此书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的重要依据。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吕祖谦遵嘱将刘绚墓志铭寄来。朱熹及时作复道:“刘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类文字,此间所已有者旦夕录呈,切告。据此以访其所无,异时得一书,亦学者之幸也。”随即又寄出辑录初成的《程氏外书》和《伊洛渊源录》初稿,请吕氏订正,并请为《渊源录》撰序。吕祖谦接二书稿,于同年冬再度致书,信中说:“《渊源录》《外书》皆领,旦夕即遣人往汪丈处借书,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渊源》序次,本非晚辈所当涉笔,然既辱严诲,当试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尝作文字,须俟来春祥祭后,乃可措思也。”吕祖谦的父亲于乾道八年(1172)春故世,此时他尚在居丧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尝作文字”答复朱熹,并表示来年春天大祥之后,可望为《渊源录》撰序。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接祖谦札,甚为欣喜,当即复书:“《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两处文字,告更趣之。”三月,朱熹将新刻《弟子职》《女戒》二书寄吕祖谦,并附札敦请早日完成《渊源录》序文。信中说:“《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吕祖谦接书,随即复书,通报所询情况,他说:“《外书》《渊源录》亦稍稍裒集得数十条,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屡督之矣。”同年秋,吕祖谦寄还《渊源录》《外书》二书稿本,并就《渊源录》写了详尽的商榷意见,建议不可急于求成。祖谦于信中指出:“《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的来信,不啻给朱熹的急于求成之想泼了一瓢冷水,顿时使之清醒过来。于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复书吕祖谦,表示接受建议,信中说:“《渊源》《外书》皆如所谕,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c随后,朱熹又专就吕祖谦的商榷意见,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答复。这就是著录于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在这一封答书的末了,朱熹同样表示:“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 综上所述,足见从乾道二年《伊洛渊源录》拟就大纲,到九年得一初稿,迄于淳熙元年冬,全书并未取得定本形态。因而今人谈《伊洛渊源录》,每以清初王懋竑辑《朱子年谱》为据,判定该书成于乾道九年,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实上,如果将朱子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与今本《伊洛渊源录》比照,我们即可发现,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违。谨依朱子答书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后。 朱子答书所论凡十五条,或解释辑录初衷,或提出修订意见,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渊源录》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诸卷内容。第一条论卷三所引《胡氏传家录》语,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修订原稿,信中表示:“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因虑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而今本既未删所述之八个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为‘赠’,显然与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条论卷四《伊川先生年谱》所述讽谏哲宗折柳事,吕祖谦主张删除,朱子则维持己见,并进而提出一折衷方案,于折柳事后注如下数字:“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今本无“某人云”句,仅有“恐无此事”四字。第六条论卷四遗事第四则所引《涪陵记善录》事,吕祖谦指出程颐制西京国子监时,文彦博并未任洛阳尹。朱熹认为言之成理,“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而今本并无此注。第九条论卷七记吕希哲从学佛、老事,朱熹认为“似不必载”,而今本依然载之甚明。第十二条论卷八蓝田吕氏兄弟编次,朱熹指出:“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而今本于吕大忠、大钧并未别立两条,仍旧与吕大临一并编录。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渊源录》,并未按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所述加以修订,因而它当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经朱子亲手定稿。 关于《伊洛渊源录》通行本的乖违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论学文字中,亦能寻出有力的直接佐证。绍熙二年(1191),朱子时年六十二,他于《渊源录》谈了两条否定性的意见。一是否认书中卷五邵雍传记材料为己作;二是邵武印本《渊源录》系后生传出,并非己愿。第一条意见,见于《朱子语类》卷六十答门人郑可学语。可学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朱子答道:“书坊自增耳。”第二条意见,则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吴斗南》中。朱熹于此信中写道:“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见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须作。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朱熹的这两条意见表明,直到朱子晚年,由于他对程门诸弟子的能否光大程学深致怀疑,因而不唯无意去修订《伊洛渊源录》初稿,而且于他人的擅自将“编集未成”的稿本刊行而引为憾恨。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之下,迄于逝世,朱子于《伊洛渊源录》始终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我们赞成清代雍乾间学者全祖望的看法,即《伊洛渊源录》实为一部“未成之书”a。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伊洛渊源录》虽是一部“编集未成”之书,但是自南宋绍熙间初刊,历元、明诸朝,代有镂板。至清代乾隆中叶,且著录于《四库全书》,迄于民国间,续经重印,其影响经数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理学风行、朱子学术地位日渐尊荣的背景,另一方面同该书独具一格的特殊内容和编纂体例也是分不开的。 《伊洛渊源录》凡十四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书中所著录之四十九人,大致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合卷。卷帙分合,次第如后。 卷一周敦颐。朱熹推尊周敦颐,取以冠于全书之首,旨在彰明二程学术的师承所自。卷二、三程颢,卷四程颐。此三卷一意表彰二程倡明道学之功,确立程氏兄弟承接孔孟儒学统绪的正宗地位,实为全书核心。卷五邵雍。全书所录诸多学者中,邵氏年辈最长,不惟长于二程,且亦长于周敦颐。他虽与程氏兄弟为忘年交,故世之后,墓志铭亦为程颢所作,但二程并不传邵雍最为自负的象数之学。程颐于此有过明确申述,他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渊源录》中如何处理二程与邵雍的关系,看来颇费周折。早年,一如前述,朱熹曾就此与友人何镐有过商量,表示《渊源录》中的邵雍资料“且留不妨”。后来大概主意变更,于是晚年又否认此卷为己录,断言系“书坊自增”。卷六张载、张戬兄弟。张氏兄弟为二程表叔辈,张载病卒,程颢写有《哭张子厚先生》一诗以志哀悼,诗中即尊载为夫子。张氏门人吕大临为其师撰行状,内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程颐见此文,当即令吕氏删除前述文字。程颐晚年,弟子尹焞就此提出质疑,他再度予以否定道:“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朱熹既尊程颐说,指出吕氏行状后有改本,已将“尽弃其学”改作“尽弃异学,淳如也”,因而书中著录即以改本为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所以张氏兄弟虽为长辈,而录中依然载诸二程之后。 大体而言,以上六卷可以归为一类,即专记二程及与之在师友之间的前辈学者。而之后各卷,除个别例外,则多属承学于二程的南北诸门人。 卷七所录凡四人,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四人年辈皆与二程相当,用程颐的话来说,就叫作“同志共学之人”,然而却并非都属门人之列。所以朱熹于范祖禹即明言:“不云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于杨国宝则断定:“亦先生之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此卷所录,实可视为与二程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同辈。 程颐一生,门徒甚众。早年与其兄倡学之初,最为得意的弟子莫如刘绚、李吁。刘、李皆先于程颐去世,颐所撰祭刘绚文有云:“呜呼!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祭李吁文亦称:“呜呼!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所以《渊源录》卷八,即率先著录刘、李二人。随后,同卷所录二程门人,为陕西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程门诸弟子中,继刘绚、李吁之后,吕大临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故《渊源录》卷八载吕大临于刘、李之后,无可非议。但因大临而并载其兄大忠、大钧,则实属不妥。吕大忠、吕大钧皆年长于二程,虽有与二程论学问对,但与其弟大临不同,未可一概视为二程弟子。唯其如此,所以淳熙元年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对此加以修订,将吕大忠、吕大钧与吕大临分立。卷九所录凡三人,苏昞、谢良佐、游酢。谢、游皆为程门高足,编入同卷,理所当然。而苏昞则不然,他为陕西武功人,与吕大临情况类似,先师从张载,后卒业于程门。倘合大临作一卷,倒也顺理成章,而此处则与谢、游同编,且先于谢、游,实是不伦。于此,似亦可见今本《渊源录》之为不成熟初稿。卷十所载,为杨时、杨迪父子。杨时早年从学于二程兄弟,后辞师南归,程颢曾欣然期许道:“吾道南矣。”宋室南渡,杨时传学东南,俨然一时程学正宗。朱熹一如其父,皆为杨门后学,故录中载杨时传记资料最详,除二程之外,远非他人所可比拟。杨迪既承家学,又师从程颐,深得器重。故世后,朱松为之撰墓志铭,文末订铭诗有云:“屹屹龟山,源渊伊洛。”朱熹与友人合作著书述程学源流,而以《伊洛渊源录》题名,当启发于此。 程颐晚年,弟子满门,其中最为惬意者,则数尹焞、张绎二人,所以他每以“晚得二士”而自慰。《伊洛渊源录》分载尹焞、张绎于卷十一、十二,同入此二卷者,为程颐晚年门人刘安节、马伸、侯仲良、王苹四人。王苹故世,已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4),《渊源录》所载之四十九人,即以王苹故世为最晚。宋室南渡之后,以朝廷大臣而护卫程氏道学最力者,首推胡安国,故朱熹专取安国为一卷,编为《渊源录》卷十三。至此,程氏道学自北宋嘉祐间倡立,后迭经盛衰,屡遭压抑,迄于南宋绍兴中,不绝如缕的发展源流,已在录中载之甚明。由于收集材料的困难,全书的编纂又不可旷日持久地延宕下去,因此凡未能在短期觅得传记资料的二程门人,朱熹皆集中于《伊洛渊源录》卷十四,统名之为“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计所录为王岩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周恭先、唐棣、谢天申、潘旻、陈经正、陈经邦、李处遁、孟厚、范文甫、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等凡二十二人。此卷所录实为一待访名录,宗尚未明,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同之前诸卷相比,无非附录而已。朱熹于此本不满意,所以他后来致书答吕祖谦,才会表示“诚觉旷阙”,亟待吕氏及诸友朋襄助,以期早日得成完书。全祖望之所以判定《伊洛渊源录》为一“未成之书”,其依据亦即在于此。 以上,我们从卷帙分合着眼,就《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梳理程学源流的编纂特征做了介绍。接下去,准备以前四卷为例,就所录传记资料的排列,来看一看该书的编纂体例。 卷一所录为两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状》,二是《遗事》。《事状》为朱熹撰,文成于乾道五年(1169),专记周敦颐生平行事、学术好尚。《遗事》则以记述传主言论及他人称述为主,与《事状》浑然一体,相辅而行。所记凡十五条,分别取材自《程颐文集》、《程氏遗书》、邵伯温《易学辨惑》、吕本中《童蒙训》诸书。卷二、三载程颢传记资料,犹如卷一,亦作两部分。卷二为程颐撰《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吕大临撰《哀词》、程颐撰《墓表》、陈恬撰《赞》。以上诸篇碑志传状合而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遗事》,凡二十七条,所录亦多系传主言论,材料分别出自《上蔡语录》《程氏遗书》《龟山语录》《侯子雅言》《二程文集》《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程氏外书》《击壤集》《涪陵记善录》及《陈忠肃公集》等书。体例与卷一略异者,则是关于材料来源,改正文称述为文后夹注。对所录有别本异文,亦于夹注中略加征引,并作必要考订。譬如《遗事》第八条记程颢与宋神宗论王安石学术一段,语出《程氏遗书》卷二,而《龟山语录》所载略异。朱熹于引述杨时书后,即考订:“恐当以《遗书》为正。”再如第二十七条述陈瓘以不识程颢而自愧语,文末既注“见《陈忠肃公集》”,又据《范公遗事》补注:“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而后读之。”卷四所录程颐传记资料,亦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载朱熹于乾道四年所辑《伊川先生年谱》、尹焞等所撰《祭文》及胡安国绍兴初所上奏状节略。第二部分为《遗事》二十一条,录文所出著述,皆一一夹注于文末。 就上述四卷传记资料的构成而言,《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已甚明朗,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第一,所录皆为两大部分,一为碑志传状,二为遗事,前者记行,后者记言,言行一体,相得益彰,遂成传主一翔实的传记资料汇编。第二,所录资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于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来源,以示求实可信。第三,凡有异文歧辞,皆于文末注明,并作必要考订,以明历史真相。卷五以后诸卷,无论所载内容详略,亦无论人自为卷或数人合卷,上述三条,皆首尾无异,始终如一。凡因资料收集有缺,一时难觅传状者,作者则有题注说明。如卷七之范祖禹、杨国宝,卷八之吕大忠、吕大钧,卷九之谢良佐,卷十二之张绎、侯仲良等皆是。这样,一部《伊洛渊源录》,除卷十四待访之二程诸门人外,全书以贯穿首尾的严整体例,立二程为中心,合百余年间诸家传记资料于一堂,在南宋初叶的学术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记录了二程道学的承传源流。 四、学术价值 在朱熹繁富的学术著作中,《伊洛渊源录》尽管只是他思想发展早期的著述,不仅尚未取得定本形态,而且朱子在其晚年,还对该书发表过否定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之而忽视这部著述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时期以后,随着赵宋王朝对道学的褒扬,尤其是入元之初统治者的推尊,朱熹学说高踞庙堂而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学正统。诚如元代名儒虞集所论:“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而不衰,从而显示出它重要的学术价值。拂去理学中人陈陈相因的门户之见,历史地去考察《伊洛渊源录》,其学术价值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在理学发展中所显示的巨大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它对宋元以后历史编纂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前者是从理学史角度来讲的,后者则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着眼。 关于《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史价值,一如前述,它是以为二程道学争儒学正统地位为职志而结撰问世的。南宋初叶,形成伊始的程氏道学,面临能否立足的严峻局势。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祖,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虽未成完书,著者的编纂目的则已经得到实现,因而它无疑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学史。至于这部书在尔后的理学发展中,能够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则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朱子逝世前夕,已届宁宗初政,由于党争复炽,局势出现反复,程氏道学再遭厉禁,朱熹亦以伪学首倡者而声名狼藉,最终悄然辞世。宁宗末,禁网松弛,政局再变,于是道学又告复苏。理宗继位,朱门后学真德秀、魏了翁并世而鸣,于程朱道学再事表彰。以淳祐元年(1241)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奉诏从祀孔庙为标志,为朱熹所确立的道学统绪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朱熹本人,也以二程学说,尤其是伊川之学无可争议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延续道统的卓然大师。宋亡,元代统治者接受既成格局,一意表彰程朱道学,并于顺帝至正五年(1345),据以完成官修《宋史》的纂修。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所确立的道学统绪,便成为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述理学源流的定规。 同理学史价值相比,我们以为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的《伊洛渊源录》,它的史学史价值恐怕是更应该予以重视的方面。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迄于南宋初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书相继问世。这些史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逾越纪传体断代史的樊篱,在通古为史中打破旧有格局,实现了史籍编纂形式的创新。朱熹为旷世大儒,他虽不以史学名家,但在这样一个学求创新的史学风气影响之下,不惟其道学思想表现出非既往成说所能羁绊的鲜明个性,而且他的史学思想也在对传统的错综会通之中,展示出求新的可贵历史特征。惟其如此,所以朱子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作跋,既盛赞《资治通鉴》的编年系日,誉为“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同时更取袁书与先秦时代的《国语》后先比美,充分肯定其以事命篇、各成始末的创辟之功。朱熹就此写道:“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其结撰略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同时。如果说袁枢在错综司马光著述的过程中,创立纪事本末体史籍,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三体鼎立的格局,那么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是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以对史籍编纂传统形式的错综会通,兼容并蓄,别张一军,从而为学案体史籍的编纂开了先河。 一如前述,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甚早,先秦诸子述学即已开其端倪,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则规模粗具。然而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则无疑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朱子深厚的学术素养,使他谙熟历代史籍编纂形式的变迁。《伊洛渊源录》的以人物传记汇编形式叙述学派源流,显然导源于《史记》《汉书》以《儒林传》述学的传统。不过,倘若《伊洛渊源录》之于《史记》《汉书》,只是恪守矩矱,亦步亦趋,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创辟路径的学术价值了。朱熹著述的可贵,就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同时又博采佛家诸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自《伊洛渊源录》出,历元、明、清诸朝,学术史著述接踵朱书,代有成编。其间,不惟有遵其旧辙,沿例而成的《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洙泗源流》《心学渊源》《洛学编》《道南原委》《闽中理学源流考》《道学渊源录》等,而且还有变通旧例而成大观的众多学案体史籍。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发轫,中经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承先启后,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再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而加以发展,迄于民国初叶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而臻于大备。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终于形成源远流长的专门学术史编纂体裁—学案。 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从梳理洛学源流的角度而言,《伊洛渊源录》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著述。然而,两宋间繁富的学术演进历史,毕竟非是洛学一家升沉所能赅括,一部早期理学史,也不是单一的洛学史所能取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又是很不完备的史书。其中,对于两宋学术的奠基人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几乎未作任何反映。而对在赵宋一代学术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等,《伊洛渊源录》或视作附庸而语焉不详,或屏为异己而多所贬斥,皆未有如实记录。时起时伏的党派斗争,与北宋一代相终始。沿及南宋,痼疾铸成,不可逆转。愈演愈烈的党派角逐,不惟给一时政治投下浓厚阴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其间的学术发展。朱熹既非超凡脱俗,沉浮于党争之中,就难免成见障目,入主出奴。因而《伊洛渊源录》拘囿门户、党同伐异之见,亦在所多有。凡此种种,都是毋庸讳言的。朱熹当年于该书所说的“诚觉旷阙”,实非言不由衷的谦辞,而是一个杰出学者实事求是的反省和自责。于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朱子。总结北宋道学史,乃至整个一代学术史,在朱子生活的南宋初叶,条件实未成熟。《伊洛渊源录》筚路蓝缕,在这方面开了一个良好的端绪。始为之者难,继述之者易,朱子在以史昌学中所建树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把握学术史脉络的拓荒之作 。“学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中国学案史》曾于1994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被当时学者评为“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曾获第三届中华出版物(图书)奖。十余年后,2008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再次推出经过修订本《中国学案史》。修订本,学理上更趋缜密,议论更显开阔。本次纳入陈祖武先生个人文集中,底本选用此修订本,经陈祖武先生再次亲自修订,编辑同陈先生共同协作,力图为读者再次呈现陈祖武先生这部力作。本书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