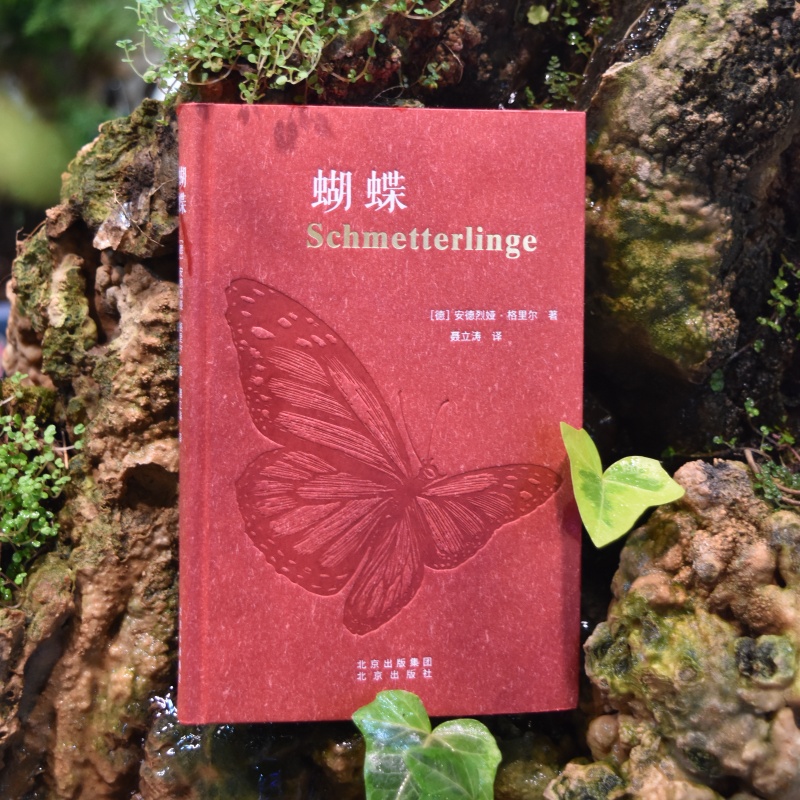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5.29
折扣购买: 动物肖像 蝴蝶(精)
ISBN: 9787200136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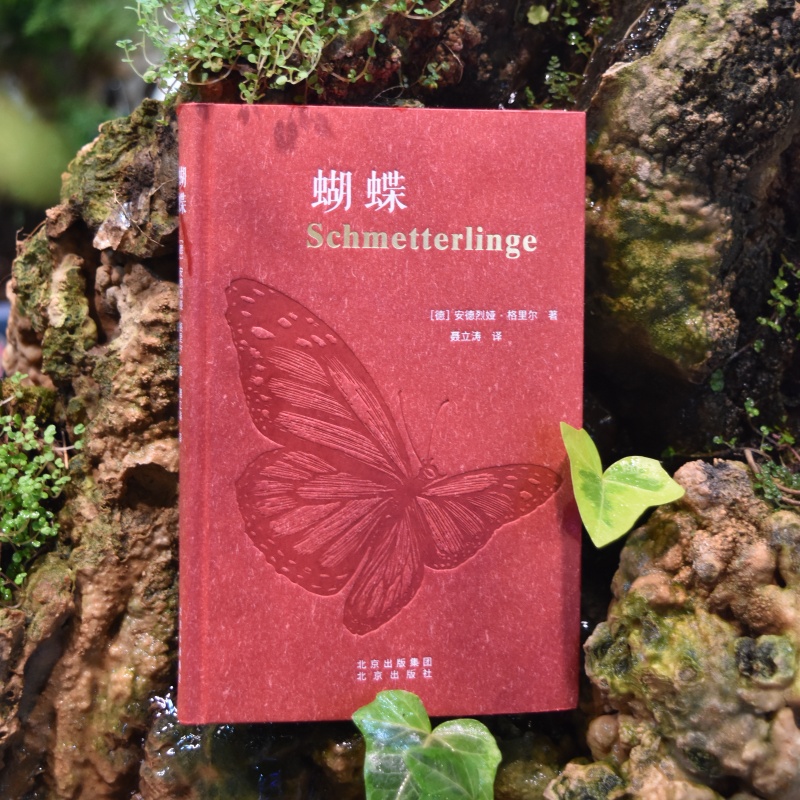
作者:安德烈娅·格里尔(Andrea Grill)在萨尔茨堡学习生物学,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时研究的课题是撒丁岛地方蝴蝶的进化。她还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能翻译阿尔巴尼亚文作品,目前在维也纳大学研究并教授进化生物学。 译者:聂立涛,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现为媒体从业者。
我在过去15年里用大部分时间研究了一种蝴蝶,第一张流传下来的关于它的画像可以在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油画中看到。耶罗尼米斯·博斯1 (Hieronymus Bosch)1490年前后创作了《人间乐园》(Gartens der Lüste)三联画,其中一个场景叫“地狱之翼”,画的是一只长着蝴蝶翅膀的鸟或者说是一只长着鸟头的蝴蝶正在攀爬一把梯子最底下的横杆,但它临时停住,把头转向了一个裸体小人。小人的身高和这只“蝴鸟”或者说“鸟蝶”的身高相仿,他有些绝望地把手挤在两腿中间。那只动物似乎在和他说话并安慰他。它的翅膀显然和雌莽眼蝶(德文名:Ochsenauge,学名:Maniola jurtina,英文名:Meadow brown)的翅膀一样。翅膀画得很逼真,好像这只动物接下来就能飞向空中。博斯的油画用这样不太引人注目的细节展示了人和蝴蝶之间关系的一些本质。 曾经有一个色彩斑斓的东西, 即所谓的蝴蝶, 它飞起来和其他所有同类一样, 对自己的年龄一点也不感到忧伤。 就像大约500年后海因茨·艾哈特1 (Heinz Erhardt)所作诗歌描写的那样,博斯画的蝴蝶似乎在某些方面胜过了它面对的小人。同时清楚的一点是,它只是短暂停留:这只动物长着鸟头和翅膀,预示着它能以两种方式飞走 —尽管我们看到它的那一刻,它被画家固定到了梯子底端的地面上。 它这儿吸一口,那儿吸一口, 吸饱后就继续飞走, 飞向风信子,不再回头。 我们羡慕蝴蝶无忧无虑。在我们的想象中,它象征着生命之轻、夏天、温暖。几乎没有人憎恨蝴蝶,尽管极少数人患有蝴蝶恐惧症。他们看到蝴蝶会吓得大喊着逃跑。他们或许认为,谚语所说的无忧无虑只能是指蝴蝶的重量:一只欧洲蝴蝶重约100 ~ 200毫克,比一片生菜叶还轻。 蝴蝶感觉怎样?它能以某种方式感知吗?“我觉得怎样?”我们人类总是问这样的问题,“我还好吗?”因此,人类认为其他生物也能“感知”。 结果, 当这只蝴蝶被捉住, 它感到非常惊讶。 艾哈特的这首诗好像是为诗集或类似东西所作。该诗以喜剧性的方式,或许以悲剧性的方式结尾。我们还不知道那只蝴蝶后来怎么样了。它暂时感到惊讶。蝴蝶能够感到惊讶吗?它能像第一段所说的那样无忧无虑吗?能像它的行动方式预兆的那样无忧无虑吗? “Ψυχη”是蝴蝶的古希腊文写法,意思大概指灵魂、呼吸、气息。但蝴蝶有灵魂吗? 蝴蝶曾经被视为死者的灵魂。那还是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色彩斑斓的“飞动花朵”和草丛中的绿虫子是同一种生物的时代。“ Πεταλουδεζ”是蝴蝶的现代希腊文写法,意思是“飞动的花朵”。直至17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只有少数仔细研究蝴蝶的人才知道它的各个变态阶段。收集和喂养蝴蝶的研究者在广大民众眼中就像疯子和巫婆。1647年生于法兰克福的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就是这样的人。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自然写实画家之一,因为细致描绘了蝴蝶的各种形态 —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刚刚羽化出的蝴蝶 —而出名。 但是,像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这样的人也为下列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蝴蝶在分类学上所属的昆虫种类在生命过程中要经过变化,即我们常说的“变态”。因为梅里安的大部分图书是以德文而非拉丁文出版,而且作为刺绣图案和绘画图案是以妇女为目标读者的,所以其读者通常缺乏这种专业知识。而她在专业圈最初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并被视为业余爱好者。 也因为她是女性,这才使她没有立即得到承认。蝴蝶研究者、德国戏剧作家和导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特赖奇克[Georg Friedrich Treitschke (1776 — 1842)]在1840年写到了梅里安。即便她属于“更温和更安静的女性”,特赖奇克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她表示赏识: 我们也遇到少数充满激情去搞上述研究的女性,她们始终拥有堪比男人那样强大的精神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虽然这在女性中只是例外,但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却具备这些秉性…… 特赖奇克在他所著的《欧洲蝴蝶自然史I.蝴蝶》(Naturgeschichte der europ?ischen Schmetterlinge. I. Tagfalter)卷首加上了一张“肖像”和一篇《M.梅里安生平事略》。他还发表她的绘画;作为对她的崇敬,他甚至把她的名字加到标题中。 特赖奇克本人和他的朋友 —演员费迪南德·奥克森海默(Ferdinand Ochsenheimer),都是18世纪和19世纪最重要的鳞翅目学科即蝴蝶学科的重要研究者。两人在特赖奇克的出生地莱比锡相遇,当时奥克森海默在宫廷剧院当演员。奥克森海默自童年时代起就对蝴蝶表现出极大兴趣,而特赖奇克的这种激情却主要受到朋友激发。因为医生建议两人呼吸新鲜空气以便从疲劳状态中恢复过来,所以他们移居到维也纳。在那里,他们受雇于当地的宫廷剧院,其中一人当导演和舞台诗人,另一人当演员。他们经常到维也纳郊外旅行。奥克森海默因为健康原因减少了演出,同时致力于编写多卷本《欧洲蝴蝶》(Die Schmetterlinge von Europa)。但该书内容太为丰富,直至他死后多年才由朋友特赖奇克编写完毕。特赖奇克在1811年至1814年间除了受雇于宫廷剧院(今天的维也纳城堡剧院)外,甚至还担任维也纳剧院的院长。两人都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有过至少算是松散的联系。奥克森海默本人也会见过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奥克森海默在席勒所写的一个戏剧中扮演角色后,席勒对他的演技大加赞扬。 两人给歌德和席勒寄过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舞台剧、音乐剧和歌剧,特赖奇克为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所写的剧本是当时最出名的版本。尽管如此,他在昆虫学领域的名声显然比在戏剧界更持久。 奥克森海默从1817年开始整理维也纳自然博物馆收藏的蝴蝶。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他的朋友特赖奇克继续这项工作,并在他死后把这项工作做完。这样一来,他们就通过描述蝴蝶及其幼虫、寄主植物和生活方式,让人们系统地了解了当时对欧洲蝴蝶的认知程度 —不仅能了解蝴蝶,而且还尤其能了解蛾子的多样性。 我本人和他们相遇是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两人的手稿中。该馆收藏了这两位鳞翅目研究者出版物的大部分手稿,例如1840年出版的带有梅里安插图的那部作品。他们两人收藏的蝴蝶标本加起来超过1万件,都卖给了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家博物馆。 早在梅里安之前2000年就有另外一个业余爱好者仔细描述了昆虫的变态: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即便我现在满怀敬意地称他为“业余爱好者”—因为蝴蝶只是他所研究的大量事物和问题中的一个对象,他也是我们知道的首位动物学家:据说他是首位系统研究生物多样性并尝试把它们与类似个体进行分类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创立了分类学,即把生物按照相似性原则进行类别划分的系统学。大象看上去更像海牛而不像蚊子,因此与前者而非与后者有更近的亲缘关系。生物学至今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 我们把类似的生物划为一类并统一命名。蝴蝶的德文写法是“Schmetterling”,这是一个怎样的名字啊!这个词来源于德国东中部地区词汇“Schmetten”和德国南部地区词汇“Schmette”,它们都是指高山牧场上用来制作黄油的乳脂。因为草地上竖起的黄油桶中的白色乳脂吸引来蝴蝶,所以人们给这种昆虫取名为“Schmetterling”,其字面意思就是黄油飞虫,和蝴蝶的英文写法“buttery”有异曲同工之妙。 亚里士多德对昆虫有很大兴趣,把它们称为“εντομα”。他是首位把昆虫从其他生物中单分为一类的学者:“但我把所有身体上不论背面还是正面有分节的动物都称为εντομα。”从根本上说,昆虫“业余爱好者”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昆虫学家。他对昆虫变态有很深的理解。但他在教人们了解昆虫变态的同时也教授自然生殖理论,认为昆虫(也是)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生成的。这两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很好地并存,但对他来说却不存在矛盾。 虽然他观察到昆虫会变成一种蛋 —他指的是蛹 —且从中羽化出蝴蝶,但昆虫从何而来对他来说是个谜,就像他也显然没有观察到蝴蝶的交配。他在论文《动物之生殖》(De geneoatione animalium)中写道: 所谓“仙女蝶”(蝴蝶)是从“蠋”生成的,蠋是生长在绿叶上的,主要是在“拉芳诺”—有些人称为“包菜”—叶上。原先,不够一颗稷粒那么大;继而成为一条小蛆 ;三日之内这又变为一条小蠋 ;随后它继续长大,而又骤然静息,换却形貌,这时改称为一只“蛹”。蛹的外皮是硬的,你倘予触动,它也有感应。它自系于网丝 ;不具备口和其他明显可识的器官。隔一会儿,外皮开拆,一只有翼的生物飞出来了,这个我们就叫它“仙女”(蝴蝶)。当它原先是一条蠋时,它既进食,也要排泄 ;但一朝转成了蛹,它便不饮不食,也不排泄。 可能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认识存在矛盾,故而后来就被人们遗忘了,无论如何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流传开来。它们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昆虫变态的知识绝非毫无意义。蝴蝶是否无忧无虑这个问题也同样不是没有太大意义。或许在人类观察者看来它是无忧无虑的,这种观察导致了本文开头引用的海因茨·艾哈特诗歌的第二段。 像昆虫这样的动物和我们是如此不同,关于它们的任何想法都会给一位科学家带来更多问题而非答案。我在过去15年里研究耶罗尼米斯·博斯所画的漂亮的莽眼蝶时,情况也是如此。 一幅关于蝴蝶变态过程的演变图卷:文中借由作者的经历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完整且清晰地阐述了——蝴蝶从幼虫阶段到突然羽化,从择偶到产卵的过程。这是全书最核心的部分。书中有大量精美的手绘、照片和画作,以及蝴蝶的分布图,是不可多得的精细之作。 独特的叙述方式:在这本关于蝴蝶的小书中,从相遇到兴趣的发生,到第一次真正的触摸,再到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探究过程,每一步,作者都将自己的经历、感受,与以往或者同时代的“业余爱好者”及研究专家的一同拿来陈述。相似的经历,因不同的视角而丰富起来,如同众多蝴蝶的爱好者相聚一团,各自娓娓道来。一本简单的科普读物,更像是众多亲历者在分享自己的所得。 汇集近现代以来著名蝴蝶研究者的成果: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稀有蝴蝶收集,昆虫学家阿瑟·弗朗西斯·亨明和卡尔·冯·林奈关于蝴蝶的命名,澳洲神经生物学教授布莱恩·基的启发性见解,等等。小小篇幅聚集众多专业学者的谈论,并恰到好处地放置在作者成长的每一阶段里,对作者是一种启发,对读者同样也是。 发掘蝴蝶在人文历史中的有趣含义:出现在博斯《人间乐园》中的“地狱之翼”,是展示人与蝴蝶之间关系本质的细节;古希腊语中“蝴蝶”指死者的灵魂,现代希腊语中“蝴蝶”意为“飞动的花朵”,赋予人们太多的想象……古往今来人们对蝴蝶这个生命体的理解如何?又被赋予了多少人文含义? 引发发人深省的思考:这样一个被视为灵魂象征的小小生灵,它的生态环境如何?是否可以在完全忽略蝴蝶品种的前提下只以数量就能成为物种良性发展的指标?不仅是蝴蝶,其他物种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如何生活才能把对蝴蝶的打扰降到最小?”这是对生物生存轨迹与人类关系的发问。 博物学始于热情,终于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