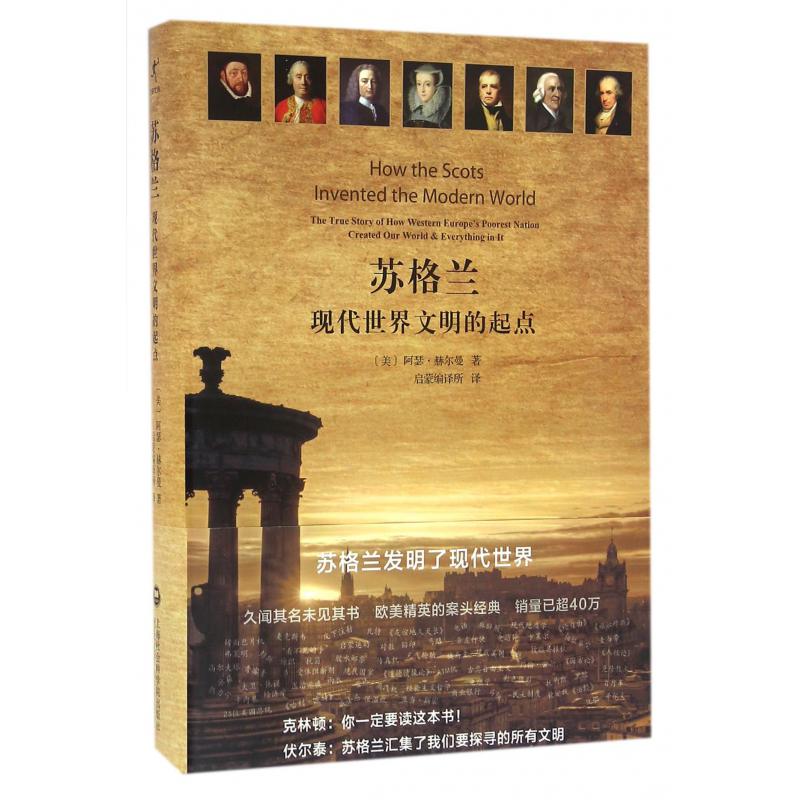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售价: 89.80
折扣价: 51.70
折扣购买: 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精)
ISBN: 9787552011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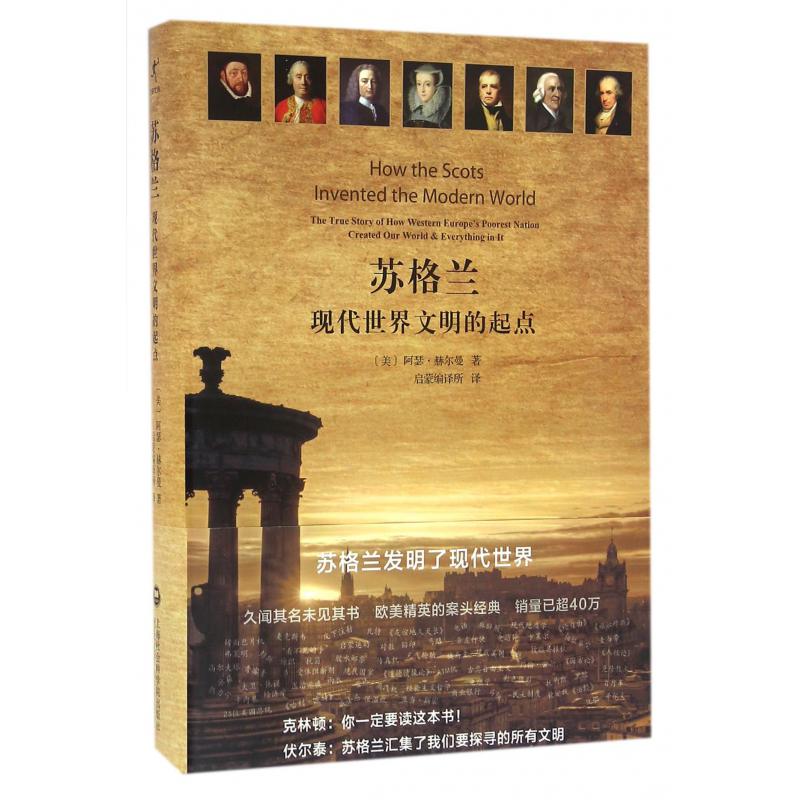
阿瑟·赫尔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学博士,曾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访学。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他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7年至2009年,他作为第一个非英籍人士被任命为苏格兰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甘地与丘吉尔:对抗与妥协的壮丽史诗》《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等多部畅销历史读物。赫尔曼的著作主题宏大、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畅销不衰,深受各界人士的推崇。
导读 陈正国 这是一本有关苏格兰近代历史的好书。 “苏格兰”一词在中文世界不大受关注,主要原 因当然是因为其父兄之邦——英格兰过于耀眼,几乎 就要完全掩盖了苏格兰的地位与成就。然而事实上是 否如此?自从大清帝国被迫认识西方以来,清朝文献 就学会了清楚区分“英格兰”与“苏格兰”。当年在 清帝国领地上的大不列颠子民,有许多其实来自苏格 兰。例如文献上被称为义律与懿律的海军统帅,以及 帮助过清廷对付太平天国的戈登。但是到了20世纪, 中文文献逐渐以英国笼统指称所有英伦三岛的事物, 甚至以“英格兰”代表“英国”。以“英国”指称、 转译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或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如果不是错误,至少是严重不妥 :因为英国的“英”字很容易让中文世界误以为是英 格兰的别称,是英吉利的现代名词。英语、英吉利、 英格兰、英国的类似性,使得中文世界容易将苏格兰 甚至北爱尔兰边缘化。例如我们说“英美法系”的“ 英”其实只能指涉英格兰。因此,严格说来,所谓“ 英国的习惯法传统”或“英国国教”都是错误的陈述 。同理,如果我们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或“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我们就不可能同时说“英国 的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我们的翻译作品常将 History of England误译为“英国史”而非“英格 兰史”。长期以来,我们学院里的“英国史”课程其 实都只讲述“英格兰史”加上以伦敦为主要观点的“ 大不列颠”史。这些错失根源于我们对苏格兰历史太 不清楚。自从1707年英苏《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生效之后,苏格兰(Scotland)就失去了议 会以及单一主权国家(state)的地位,而仅是文化 地理的国家(country)。可是和英格兰人(the English)一样,苏格兰人(Scots,the Scotch or the Scottish)自认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a nation)。如果以主权国家的观点来写作历史,苏格 兰史到了17世纪就画下了休止符。但是如果以民族或 社会观点来看,苏格兰的历史则绵延至今。假若以所 谓英伦三岛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民在18世纪以后经 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习惯的转变,并 且逐渐发展出了不列颠人(Britons,or the British)的新认同。此后苏格兰与苏格兰人就成为 大不列颠史里不可或缺的元素。本书处理了16至19世 纪近三百五十年苏格兰民族史。在这三百多年中,苏 格兰经历了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产业结构等方面的 巨大变动。紧接而生的社会风俗、文化创造、思想学 术当然也与时流转、胜义迭出。 法国的学术传统告诉我们,地理决定了文明的走 向。苏格兰虽然勉强可算孟德斯鸠所谓的文明摇篮— —温带地区——但绝对不是上帝应许之地。它的土质 过硬而且贫瘠,更兼有占总面积约三分之二只宜粗放 经营的高地。当欧洲通过地中海与东方贸易往来,邻 近地区产生所谓文艺复兴的荣景时,当海上新航路陆 续被发现,西、葡、荷、英等国开始纵横海外时,苏 格兰的贵族几乎不知道新财富、新艺术、新学术的滋 味。经院传统依然主导着贵族与大学的学问。文字经 典的传统虽然持续发展(例如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 —同时也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被人认为就是一 位古典学者与政治理论家,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则是当地望重士林的学者与 史家),但有关视觉艺术的开发则相当匮乏。不过到 了18世纪中叶,苏格兰突然散发惊人的创造力。它开 始相信自己有杰出的画家如拉姆齐(Allan Ramsay, 1713—1784),剧作家如侯姆(John Home,1722— 1808),建筑师如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 ),以及伟大的诗人拉姆齐(Allan Ramsay,1686— 1758,画家拉姆齐的父亲)、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当然它还有一群才华横溢的文人、哲 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如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亚 当·斯密(Adam Smith,1721—1790)、弗格森 (Adam Ferguson,1721—1816)、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3—1794)等等。为什么天才总是成 群而来?因为天才也受限于地理、文化条件。 苏格兰固然错失了“地中海时代”,但它却能及 时积极参与“大西洋时代”的建立。本书作者详细说 明了苏格兰人如何参与早期美国与美国企业精神的建 立。不过除了北美,18世纪苏格兰人的足迹早已随着 大不列颠帝国的船只踏遍了从几内亚到刚果,从印度 孟加拉到中国西藏,从中国沿海到澳洲等世界各个角 落。这些经验除了让苏格兰社会的物质文明大有斩获 ,更开启了苏格兰人的世界观。与吉本、休谟齐名的 罗伯逊(后人统称为英国18世纪史学三雄)著有《苏 格兰史》、《查理五世统治史》、《美洲史》。他强 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历 史的进步表现在心智的开展。可是少了经验,少了物 质世界的涉入而谈心智的开展,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这种物质主义式的论调竟然出自一位长老教会的大会 主席之口,不啻令人称奇不解。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 ,他的好友,也就是后来敢于批判法国大革命激进主 义而名垂青史的保守主义健将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在议会发表强烈言论批评当时印度总督 海斯汀(Warren Hastings,1732—1818)。柏克花 了十年时间指责海斯汀擅权专制,欺压印度人民。罗 伯逊知道以后,写了一本论欧洲早期对印度文明看法 的小书以为呼应。书中阐释,商业是宽容的基础。事 实上罗伯逊的次子就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美洲独立战 争爆发之后,弗格森应政府之邀赴美洲与革命军谈判 ,希望对方悬崖勒马。(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