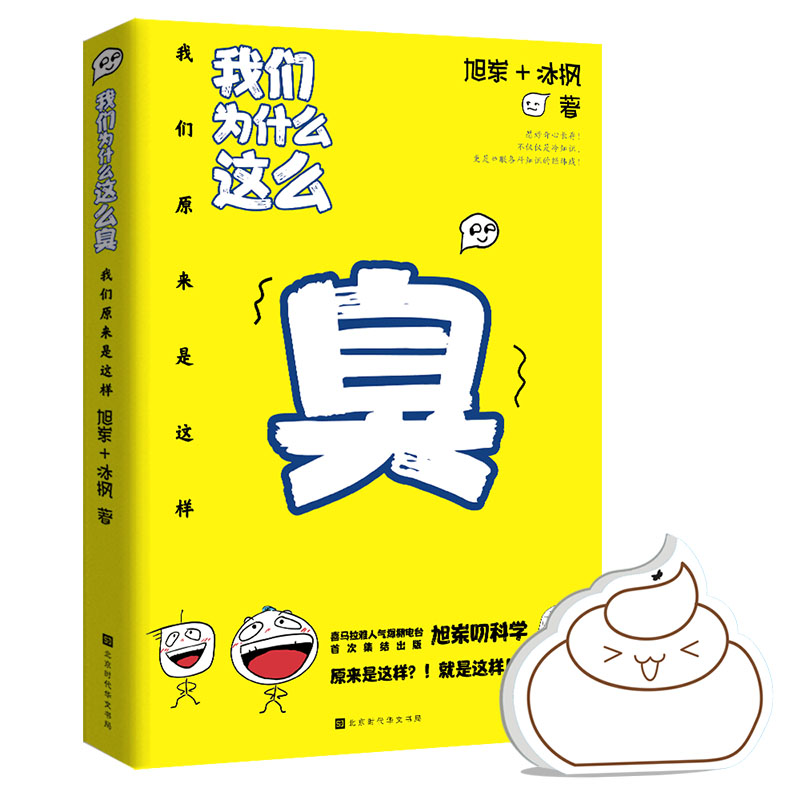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28.40
折扣购买: 我们为什么这么臭:我们原来是这样
ISBN: 9787569931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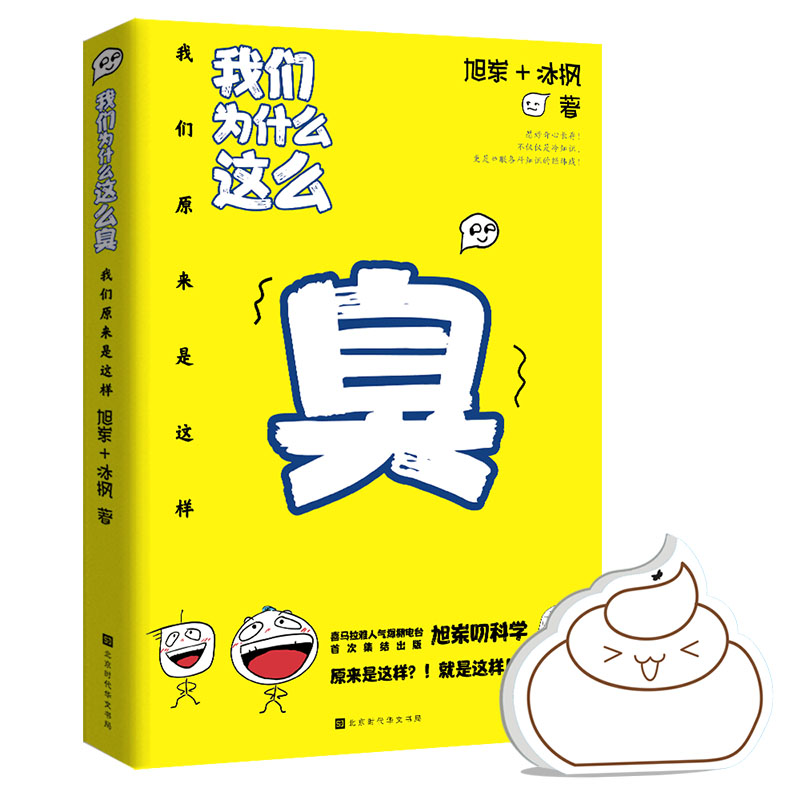
旭岽,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工作室总监、首席主持人,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上海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会员。主持有《十万个为什么》《科学魔方》《极客秀》等多档高热度科学类节目。访谈过数百位科技领域工作者,撰写的科普节目文案超200万字。多次获得上海新闻奖、广电奖、科技新闻奖等奖励、2017年获颁上海科普贡献奖(个人)一等奖。2014年,利用业余时间创办科普自媒体“旭岽叨科学”,以严谨又有趣的内容吸引了众多听众、五年多的时间《原来是这样》专辑,全平台已累计收获近200万订阅,总播放量近三亿。”五年多的时间,全平台已累计收获近200万订阅,总播放量近三亿。 冰枫,香港大学心理学硕士,**认知科学学会(CSS)会员,曾在“注意力、脑与认知”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并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15年加入科普自媒体“旭岽叨科学”,2017年创办心理学科普自媒体“Outside?In”,带领公众重新认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业余时间坚持MOOC学习,*邀加入EdX中国学员俱乐部,同时也是Coursera**翻译者社区成员。作为上海电台科学工作室**科学编辑,多次获得上海新闻奖、广电奖、科技新闻奖等荣誉。
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是我? 先思考两个问题,**个问题:用一支蜡烛的火焰引燃另一支蜡烛,这两支蜡烛的火焰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坪里的*在冬天全部枯萎死去了,但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又再次生机勃发,去年和今年的*坪是什么关系呢? 在寻找答案前,我们先思考一个古老却**的问题——“我是谁”。 人格面具 很多人会觉得,代表我的是我的人格。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一种特有的统和模式。这种独特的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类型。而我想说的是与人格有关的另一个词——人格面具。 无论你是否承认,只要在社会中生活,我们都会戴上各种面具。人格面具(person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本意是指演员在一出剧中扮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人格面具是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一。怎么解释呢?它是指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一种外在表现,但是在面具背后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这个真我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自我,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作时的我和生活当中的我虽然都是我,却又都是我的不同侧面。 弗洛伊德认为我包含了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包含了要求得到满足的一切本能**,按照快乐原则形式急切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本我当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本能和**。自我就是现在能想到我是我的这个我,而超我,superego,则代表着良心、社会准则、自我理想等等,可以理解为人格的高层领导,按照至善原则形式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超我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对于美好或者理想中的我的追求。 所以,本我和超我是不是我呢? 自我意识 我们先把这个思考放在一边,再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如何产生的?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从卵子和精子的结合,再到新的生命呱呱坠地,这时“我”似乎就诞生了。但是,这时的小生命会有“我”这个概念吗? 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不用感*外界的不适刺激,不会感到肚子饿了、尿布湿了。这是一个**安全,相对封闭的环境。但是当婴儿出生之后,人生的**个所谓的创伤也便开始了,因为婴儿诞生到了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里。但是这时婴儿会以为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不知道自己和妈妈的区别,也不知道自己和其他人的区别。总有**婴儿会发现自己和妈妈、和其他人都是不一样的。 镜子测试是一个有关“自我意识”的测试,用来判断动物是否有能力辨别自己在镜子当中的影像。在测试当中,实验者在动物身上标记两个没有味道的颜色斑点。一个是测试斑点,位于动物身体上在镜中可见的部分,另一个是对照斑点,涂在动物身体上可触及但不可见的地方。通过观察动物的反应来判断它们是否意识到测试斑点是在自己身上,而同时忽视对照斑点。 已经通过镜子测试的动物包括所有的类人猿、猕猴、大象等,但是猫、狗以及*大部分鸟类都不能通过镜子测试。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通过镜子测试,要等到大约18个月大的时候才能通过。当然,这个研究也简化了大量的复杂问题,不能确定没有通过测试的原因,到底是因为没有自我概念还是没有认识自己的面貌。 婴儿从刚刚开始会说话到两岁左右,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还不会说“我”。婴儿只会说“宝宝要什么”,或者用小名来表述 “东东要什么”,不会说“我要什么”。如果遇到了另一个也叫东东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困惑。之后,儿童才会逐渐掌握人称代词。这在儿童自我意识的形成上是一个质的变化。 关于自我意识的产生有无数争论和假说。不妨先换一个角度,用数学的反证法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了什么,我就不再是我了。 我为什么是我? 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会说到一个人的肉体,这就是身体理论,认为你的肉体就是你。这种理论是有道理的,思想需要一个肉体作为载体。如果肉体停止了工作,“我”就死了。 “我”到底是否等于我的身体?我现在是短发,如果剃成光头,我还是我。如果我不幸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比如换了一个肾,又或者科技发达了,我把一只手换成了功能强大的机械手,大家都会觉得,不管换一个肾还是两个,就算把四肢都换成了机器,我还是我。 如果换的不是别的,而是脑子呢?先不考虑技术是否可行,假设我和别人互换了脑子,“我”会是谁? 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是互换了脑子,可是从脑子的角度来看,就是互换了身体。换了脑子之后的人,从法律和生物识别的角度来看,身份应该是身体所决定的,指纹、虹膜都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意识的角度,似乎是脑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这就是另一个关于“我是谁”的理论,大脑理论。大脑理论认为,你的大脑去了哪儿,你就去了哪儿,哪怕是去了别人的身体里。 大脑这个器官是不是真的就能代表“我”呢?换了脑子之后的我,该如何向别人证明我还是我呢?比如一些电影里有这种情节,和亲密的朋友说一些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细节。不过要让别人信服,还是挺难的。 如果黑科技继续发展,可以不换脑子,仅仅是把脑子里的信息记忆互换,肉体没有变化,但是行为记忆全都改变了。哪个才是你?哪个才是我呢? 来看一个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令人抓狂的折磨测试。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疯狂的未来科学家抓住了我和你,交换了我们大脑中的数据,当我对着你的身体,也就是对着我原先的身体说:“接下来我要折磨我们其中的一个。”我该折磨谁呢? 第二个情景:疯狂的科学家抓住了两个人,但是他动手前先问了这样几个问题:我会折磨你们中的一个,你认为我应该折磨谁呢?不管我折磨谁,我都会把你们两人的大脑清空。所以当我折磨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不会记得你之前是谁。进一步,在折磨这个人之前,我不但会把你们的大脑清空,还会改造你的大脑,改造完之后,你就会相信你是对方,而且会拥有对方的全部记忆、人格、感知和知识。改造之后的甲将拥有乙的记忆,也将会记得乙现在所做出的一切决定。等甲被折磨的时候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时身为乙的我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但是反过来,如果乙选择折磨乙的大脑所对应的那个身体,乙现在这颗大脑的未来也注定要经*痛苦。 哲学家洛克的个人身份记忆理论认为,“我”是由关于“我”的经历和记忆决定的,“我”是由“我”大脑中的数据决定的。那么,这些关于我的回忆、性格等等的数据集合在一起,到底是不是我呢?别着急下结论,来看看一个古老的思想实验——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早出自于普鲁塔克的记载,描述了一艘船,由于不间断地维修和替换部件,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一块木板*烂了就会被替换掉,一颗钉子坏了也会被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功能部件都被*换。*终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忒修斯之船吗?还是一艘**不同的船呢?如果不是原来的船,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呢?英语中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叫祖父的斧子,斧柄坏了换斧柄,斧头坏了换斧头。换来换去,祖父的斧子似乎还是祖父的斧子,但它还是原来那一把吗? 用数学角度看忒修斯之船,把忒修斯之船看作一个集合,船上的部件就是它的元素。当*换部件的时候,集合中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原来船上的木板有木板A、木板B……木板Y,假如把木板A换成了木板Z,忒修斯之船这个集合的元素就变成了木板B、木板C……木板Z。当我们*换部件的时候,忒修斯之船的定义已经改变了。就像一支足球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可它还是叫着原来的名字。虽然名字没变,但是本身一直在变。 忒修斯之船的情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真实且时刻发生着,我们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每**我们都会呼吸、上厕所,失去一部分原子,又通过吃喝得到新的原子,全身的原子完成一次*替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所说的“我”和五年前的“我”可能**不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原子是一样的。 所以想一想,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我是谁?我还是我吗? 虽然看上去我还是我,但我却一直在悄悄变化。五分钟前的我和现在的我虽然肉眼看起来区别不大,但是因为发生了原子的*替,因为拥有了新的记忆,所以虽然我还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了,是这样吗? 关于忒修斯之船还有一个*疯狂的可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做了一个延伸:忒修斯之船的每一块老木板拆下来之后,并没有损毁或者烧掉,而是被用来搭了一艘船。于是就出现了两条船,只是一条看上去比较新,一条看起来有点旧。这两艘船当中,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传送机思想实验 相对于船,人还有思想,于是事情就变得*加复杂。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在他的书《理与人》中描述过一个类似思想实验的现代版本,那就是传送机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在遥远的28世纪,人类发明了传送机,可以把人以光速传送。某天你要从上海去北京,传送机会扫描你的全身,把你身体里的分子组成详细到每个原子和每个原子的准确位置,全部收集起来。在扫描你的同时,也会摧毁你,一边扫描一边把你的每个细胞都摧毁掉。收集到的信息发送给北京,另一台机器利用这些数据把你的身体重新构造出来。当一切完成之后,你出现在北京,感觉就和刚刚出发时没有区别。你的心情没有改变,肚子还有点饿,连手指上昨天晚上的划伤都还在。整个过程大概只花了五分钟。但是这一切对你来说是即时的,你按下按钮,然后眼前一黑,就到北京了。 有**,你又要从上海去北京了,按下按钮,听到仪器扫描的声音,却发现原本的眼前一黑没有发生,自己依然在上海。工作人员告诉你:扫描设备工作正常,收集了你的全部数据。不过原本和扫描设备同步工作的细胞摧毁设备好像出了故障。他打开监控录像,上面是你在北京的监控画面,你已经到达北京。所以,只要把你摧毁就好了。 这时候,哪个才是真的你呢?你认为在北京的你只是一个复制品,目前的你才是真实的,如果摧毁了这里的你,不就代表你死亡了吗?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瞬间传送是移动过程,还是死亡和重生的过程?类似的桥段已经被无数的科幻小说或电影演绎过。 如果在故事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可能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瞬间传送明明是一种很安全的移动方式。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它越来越像一种死亡的过程,每天往返于北京和上海的时候,你都是被细胞摧毁设备杀死,又创造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对于所谓原版的自我而言,可能早就死亡了。可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认识你的人来说,你经历了瞬间传送,安然无恙。 回到那个问题,“我是谁”,这依然取决于我是什么。认同数据理论的人认为,到达北京的你和从上海出发的你是相同的,瞬间传送并没有杀死你。但是大家都能够理解故事结尾时那个仍在上海的你的恐惧。 *进一步说,如果传送器可以把你的数据送到北京去复制,是不是也可以把同样的数据送去南京、广州、西安,再造出三个同样的你呢?要承认这四个你全都是你就很难了,传送机思想实验是对数据理论很有力的反驳。 我是谁,这要看从什么角度回答。从法律的角度,我就是这具肉体,哪怕大脑或者数据被调包,肉体还是在法律上代表我。哪怕我被复制了许多个,可能每一个肉体都还代表我。仔细想一想,我或者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其实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故事,一个不断发展的主题。你就好像一个装满了东西的房间,有些东西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有些你知道在哪里,有些你都不知道。房间里的东西一直在变,每天都不太一样。 同样的,你不是一组大脑数据,而是一个内容一直在变换的数据库,不断成长和*新。你或许不是一组原子,而是一套告诉这些原子该怎么组织的指令。从庄子的角度来看,我是谁,是庄子还是蝴蝶,也没有区别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关于自我意识也好、我是谁也好,这都是**问题,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它可能现在、以后,都没有答案。 就像大家读我的书,你怎么能确定我是真实存在的呢? 1, 喜马拉雅、蜻蜓、网易、企鹅FM、凤凰FM、苹果播客、荔枝FM人气爆棚电台《原来是这样》**结集出版,不仅是冷知识,*是串联各科知识的经纬线。 2,为什么数字2是*绿色的,而5是天蓝色的?我们到底使用了20%的大脑还是全部大脑?耳朵不止能听到声音,还能发出声音?我们的舌头到底能尝出多少味道?“拖延癌”能治吗?“既视感”是什么?我——是谁?…… 3,24个问题,为你解答关于我们自己的情绪、感官、大脑和神秘力量,让你了解以前不知道的自己。这不是板着面孔的科学问答,而是脑洞大开的科学真相。那些匪夷所思和疑惑未解,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我们,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