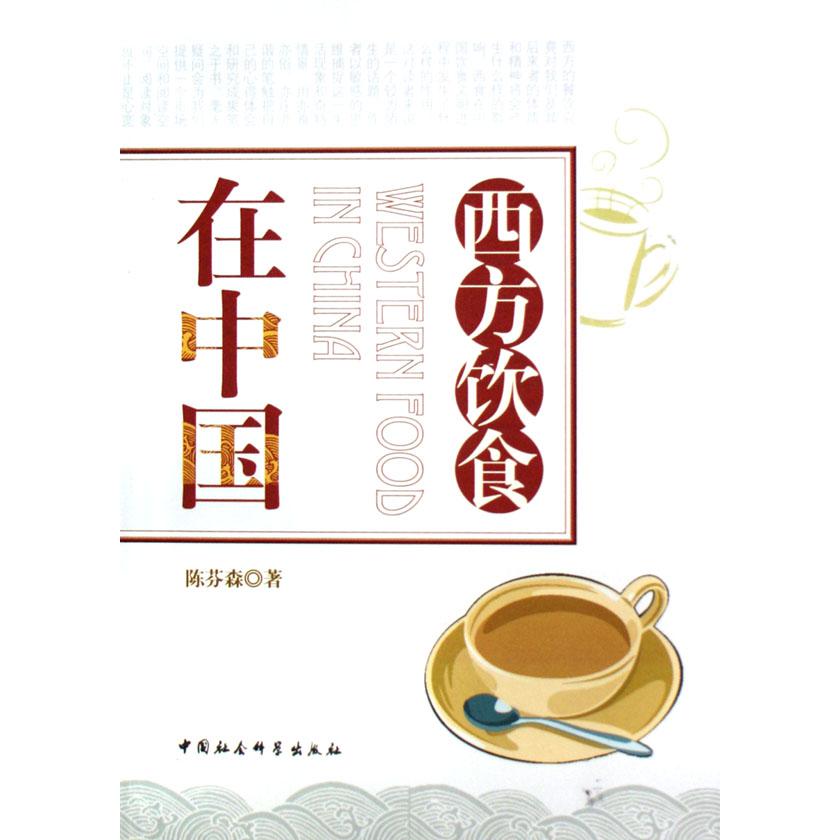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社科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20.00
折扣购买: 西方饮食在中国
ISBN: 7500455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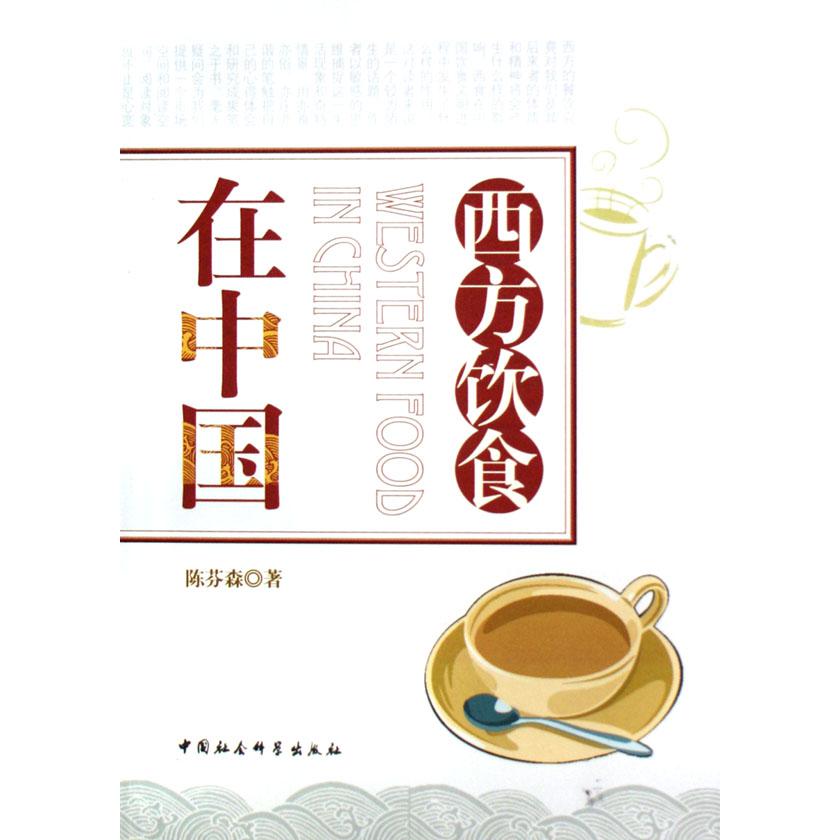
陈芬森男,汉族,湖南安仁县人。1985年大学毕业,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后读研,1993年硕士毕业,在某国有企业工作。已出版《国有企业改革沉思录》、《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市场竞争策略》等专著。
昔日的西餐 西餐不是近年从西方传来之物,大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他 就带来了西餐的烹饪技术和西餐的进食方法,明中叶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中 国传经布道,将基督教教义向东方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饮食文化。清 末鸦片战争之后,五大通商口岸正式流行西餐,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到 国外游历求学频频,伴随国人思想的革新,中华饮食文化加快了现代西食东 传的文明历程。当时有名的西餐馆有六国饭店的西餐厅,张森隆西餐馆等, 辜鸿铭先生就常在那里吃西餐,并在西餐厅里教训过洋人,辜鸿铭自己是个 典型的西化人物,他在西洋留学十多年,对西方的文化非常认同,但是他却 更喜欢国粹,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东西文化的混合。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袍 大褂拖着长辫去吃西餐可能只有他一人而已,所以会遭到嘲笑,这使得他气 不打一处来,非得把嘲笑者骂一通才舒服。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一身民族打扮 的东方人在西餐厅吃西餐,也许一点都不惊奇。但是在辜鸿铭时代,吃西餐 毕竟是一种时髦,并非当作家常便饭,只有外交场合以及试图进入外国人的 饮食生活圈子的有钱者才进入西餐馆,那是很正式的事情,平民百姓不可能 把西餐当正餐的,西食在广大的乡村和中小城市并不流行。 即便如辜鸿铭时代,北平的西餐馆有一些,但是也并不正宗,可能是受 到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的影响,怕是太正宗了要挨骂的,说你想全盘西化。孙 中山先生在他著的《建国方略》中就有批评西餐而肯定中餐的言论:“中国 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 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胜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 所可并驾。”“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之一道,法国为世界 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不过孙中山先生是从革命的 立场出发,要求中国人在其他建设方面也都像在餐饮方面一样领先世界,并 不是否定西餐。不过,西餐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不多见。直到后来也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好几处写自己在红色西北地区因为 采访的劳碌,经常想喝一杯洋咖啡啃一块面包而不可得,为此一再感叹,可 见西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不普遍。 那时一味吃西餐的人也没有几个,除了礼仪场合的需要,有头有脸的官 员和士林也仅仅是将西餐当作一种时髦而已,否则难免被人攻击为西化派。 “五四”之后,能背着全盘西化的名可能只有胡适受得起,因为胡适大名鼎 鼎,不怕,一般人要是主张西化就有崇洋媚外之嫌,有卖国主义之恶,谁敢 不加入一点中国的东西?所以那时的西餐很带点中国式西餐的味道。就是说 ,中国的西餐总是做得不伦不类,吃西餐的人不像西人,这也情有可原。关 键是菜味儿不像,西餐里要求乳酪,中式西餐里没有;西餐面条里加“芝士 ”,中式西餐没有;西餐里牛羊肉除了红烧之外,一般都是半生不熟,带着 血迹,中式西餐都炖得烂熟;西点的主要成分是奶油,而中式西点为了减少 成本,不肯加奶油。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就谈到吃一顿名副其 实的西餐的不易,他说只有逃难到青岛才能吃上正儿八经的西餐,但是一旦 青岛的西餐搬往内地,恐怕也要本土化,否则就肯定不会受欢迎。这是当时 国人对西餐的心理。 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政,拒绝西方国家的政治干扰,西餐也就随着 帝国主义的滚蛋而滚蛋,但是在外交场合,西餐是必不可少用来招待外宾的 主餐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是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 除了这两家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西式餐厅了。吃西餐成为上等人的享受, 有幸吃一顿西餐那是平民梦想成为贵族阶层的一个活动。这种活动当然成本 计价很高,首先你吃不起,其次你请不起,第三你吃了请了但消受不起。所 以一般平民百姓向往着西餐,请客做宴的时髦活动还是放在中餐厅。 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孩子是这样描述对莫斯科餐厅的体验: 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 牛鱼排、罐焖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 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老莫”(六七十年代北京人对莫斯科餐厅的 称谓)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 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7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 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 ,盛罐焖牛肉、罐焖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 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儿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 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 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 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以至于或同学 ,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已经构 成一种现象,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 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 ——刘仰东,《红底金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改革开放后,国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国外人口进入家门,进来后你得招待 他们,首要的是得给他们准备吃的,虽然入乡随俗是中西文化共同恪守的准 则,但是好客的中国人总是尽可能满足客人的胃口,当然就要做西餐给外人 吃。西餐和西食在中国之盛开始于这个时候,并在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 渐渐流行起来。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已经不再是青年人追求的时髦了。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