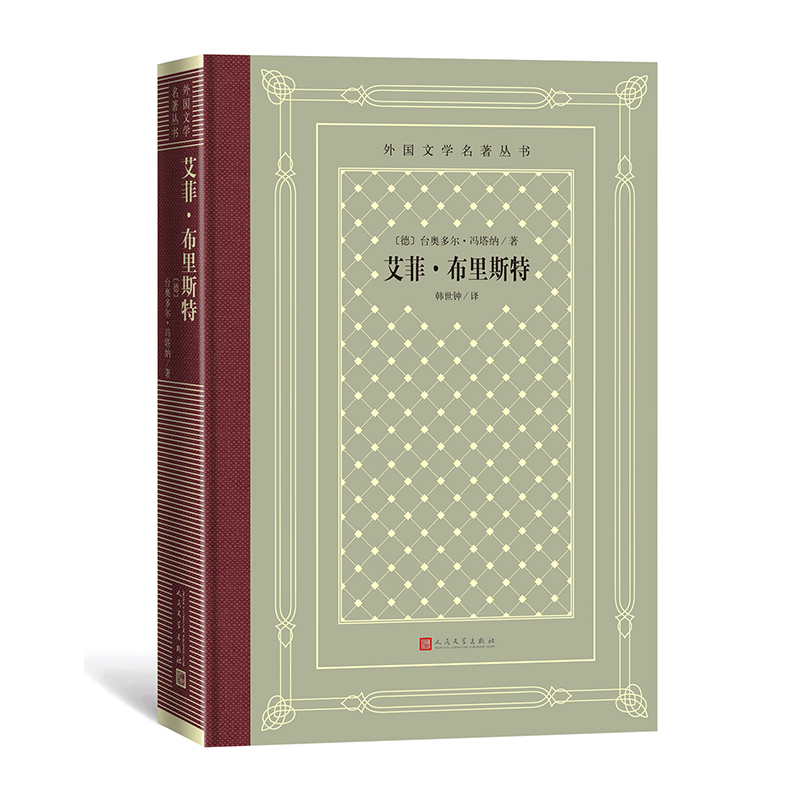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6.00
折扣价: 41.10
折扣购买: 艾菲·布里斯特/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6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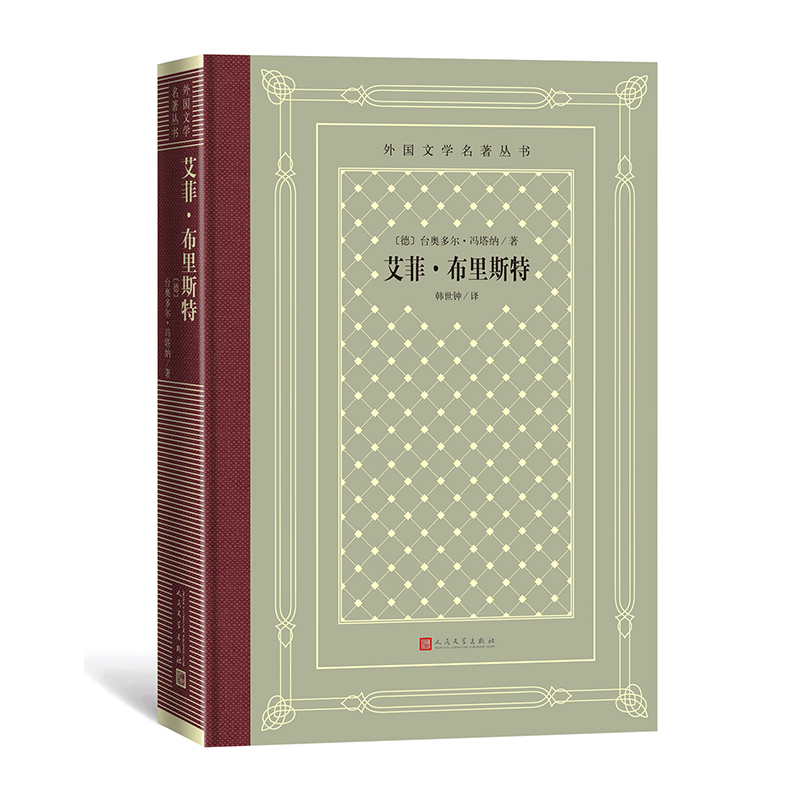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德国作家。生于德国诺伊鲁平。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教徒。职业学校毕业后,进药房当学徒。后对文学发生兴趣,开始发表诗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沙赫·封·乌特诺夫》《迷惘、混乱》《施蒂娜》《燕妮·特赖勃尔夫人》和《艾菲·布里斯特》等。 译者简介: 韩世钟(1928—2016),浙江桐乡人。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译有海涅的《卢卡浴场》《卢卡城》,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霍普特曼的《织工》等。
译本序 《艾菲·布里斯特》是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晚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既是冯塔纳的代表作,也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作品通过对普鲁士贵族女子艾菲一生遭遇的描绘,深刻揭露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社会道德的虚伪及其破产,对这个必然覆亡的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 一 台奥多尔·冯塔纳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于德国诺伊鲁平。他的祖先原是法国胡格诺教徒,于一六八五年定居德国。他的父亲路易斯·冯塔纳于一八一九年初迁居诺伊鲁平,在那儿开了一家药房,因此,冯塔纳的童年最初就在该地度过。一八二七年他随父母搬到斯温内明德,在那儿上了小学,后在家庭教师和父亲的辅导下学习。一八三二年回到诺伊鲁平,成了当地文科中学的学生。下一年,父亲把他送往柏林,进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他在那儿一直读到一八三六年。同年毕业后,进罗泽施药房当学徒,一八三九年通过满师考试。这时他对当代文学发生兴趣,经常阅读“青年德意志派”出版的刊物《电讯》,参加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普拉顿俱乐部和雷瑙协会举办的集会。此时,冯塔纳开始在柏林报刊上发表最初的诗作。 次年冯塔纳离开罗泽施药房,时而在马格德堡,时而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工作,后又回到柏林。与此同时,他对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一八四三年在莱比锡参加海尔维格俱乐部,公开表明他对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向往。下一年五月他成了柏林“施普雷河隧道”诗人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给他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他得以在斯图加特和柏林等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纪念古代普鲁士将军的诗歌《七个普鲁士将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问世的。 一八四八年他在柏林经历了一场革命,他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参加了街垒战,支持民主力量的兴起。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拥护共和政体和国家的统一。革命失败后,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面对普鲁士国家的军事暴力一筹莫展。一八五○年同埃米莉·罗昂纳特·库默尔结婚,随后出版了一些诗集。一八五二年四月至九月耽在伦敦,给柏林报纸写通讯、翻译英国诗歌,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个散文集《伦敦的一个夏天》,不久又写了歌谣《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后来回到了柏林。 此后三年,他为柏林《普鲁士报》工作。后去伦敦,发表了《德英通讯》。一八六○年重返柏林,在普鲁士报《十字架报》工作。次年发表《歌谣集》,同时又写下了《勃兰登堡漫游记》。一八六二年作为随军记者,跟着普鲁士军队上前线,写了若干描写战争的书籍。一八七○年离开《十字架报》,集中精力为《福斯报》写评论文章,同时修改一八六二年开始写作的长篇小说《在风暴前》。该书于一八七八年发表,作者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是“介绍一八一二年冬至一八一三年间一大批勃兰登堡人物”,其目的“不是为了描绘冲突,而是着意刻划产生于当时的各类人物所具有的伟大感情”。小说出版后,他又致函出版商,说明这部作品的倾向。这本书表达了一定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它偏袒宗教、习俗和祖国,但它痛恨普鲁士军国主义和虚伪的爱国主义,痛恨“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作者从这本书开始,在创作上走上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又写出二十来部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自传,开辟了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后来由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继承下去,一直通往当代的某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在冯塔纳的晚年作品中,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沙赫·封·乌特诺夫》《迷惘、混乱》《施蒂娜》《燕妮·特赖勃尔夫人》和《艾菲·布里斯特》等。其中的《艾菲·布里斯特》,则是冯塔纳的杰作。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冯塔纳于柏林逝世。 二 冯塔纳的一生创作活动,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以一八七八年发表《在风暴前》为其重要的分界线。前一阶段的创作,主要写些诗歌和散文。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歌谣集》,大抵是一些以民间叙事谣曲形式写成的歌谣,其中多数以英国苏格兰民间故事为题材。散文方面主要写了一些游记,《勃兰登堡漫游记》共有四卷。到了后一阶段,作家才从普鲁士民谣歌手发展成为普鲁士制度的批判者。冯塔纳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存在决定意识,冯塔纳的这一转变,应该说跟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变迁有一定联系。 大家知道,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封建专制割据阻碍了经济政治的进步。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在欧洲英、法诸国后面。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才有了显著的转变,工业革命的迹象逐渐显露,机器生产日益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形成。四十年代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斗争的序幕。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德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革命终遭失败。及至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实现德国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 德国统一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早在一八六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告成立。一八七四年国会大选时,“帝国的朋友”仅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帝国的敌人”。在此后的年代里,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合并以后的这个党在一八七七年大选中获得五十万张选票。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蓬勃发展,容克贵族感到威胁,于是俾斯麦在一八七八年搞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的法令,妄图扑灭工人运动。然而“好景”不长,在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下,法令不得不废除,俾斯麦本人也不得不下台。凡此种种,都给了冯塔纳以重大影响。当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开始执行时,冯塔纳就赞赏工人阶级,对俾斯麦开始采取否定态度。这年六月他给妻子的信中说: “……千百万工人跟贵族和市民一样聪明,一样有教养,一样值得尊敬,有的还远比贵族和市民高明……所有这些人同我们的出身完全相同……他们不仅代表反抗现存制度一方,代表起义一方,而且也代表若干思想,其中部分思想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决非人们所能扼杀和禁锢得了的。” 后来,他给一位伯爵的信中说: “人民中间逐渐酝酿着一种反俾斯麦的风暴……他满以为自己深孚众望,其实他弄错了。他的这种威望一度是巨大的,但现在已经不多了。眼下是与日俱减,每况愈下……” 除了上述种种客观因素外,在冯塔纳转变为普鲁士制度批判者的过程中,也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第一,冯塔纳无论在普鲁士容克还是在霍亨索伦皇朝中,很少得到他们的赏识;第二,不管是他的《勃兰登堡漫游记》还是关于普鲁士战争的著作,都遭到了贵族和国王的冷遇。正因如此,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普鲁士统治阶级。这种清醒态度特别在一八七六年有了飞速发展。这一年他出任过皇家艺术研究院秘书。但三个月之后,这种为普鲁士皇朝当雇员的活动使他感到屈辱,他于是辞职不干。他情愿追求独立思考,而不愿出卖思想和灵魂;他宁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个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自由作家,也不愿在普鲁士官场中混太平日子。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是在不幸的七六年,方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在此以前,我只是一个曾经写过一点东西的富有才华的人。但是作这样的人是不够的。” 在此前十一天,他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说: “我现在看清楚了,我实际上是在七十年代写了战争著作和小说(《在风暴前》)之后才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也就是说,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干的是艺术这门手艺,他懂得艺术的种种要求,而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歌德曾经说过:‘一个正直的诗人和作家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符合他认识的尺度。’他的话讲得非常正确。一个人也可能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写出一点好作品来,也许这些作品是这样的好,连他日后用带有批判眼光写的作品也赶不上。这一切当然毋庸争论。然而这些作品只是‘上帝的馈赠’正因为是‘上帝的馈赠’,那是极为罕见的。一年里面出现那么一次,而一年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剩下来的三百六十四天,理当由批判的眼光,也就是认识的尺度来决定。” 应该说,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地“观察,检验和衡量”,是作者晚期创作的真正基础。而他晚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是这种批判地“观察、检验和衡量”生活的产物,这些产物主要针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 三 冯塔纳写的小说,大多以当时柏林生活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成了封建军事帝国以后的社会现实。《艾菲·布里斯特》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正好是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前前后后,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晚年的力作,初稿完成于一八九○年,出版却在一八九五年。内容写一个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出身的美丽少女艾菲,十七岁那一年由父母做主嫁给母亲旧日的情人男爵殷士台顿。殷士台顿在海滨城市凯辛当县长,艾菲结婚以后,就跟丈夫去那儿生活。艾菲年轻、热情,喜欢玩乐,而殷士台顿则已年近四十,公务繁忙,有时不免把妻子冷落一旁。这样,艾菲渐渐感到日子过得寂寞无聊,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再加上那幢县长公馆阴森可怕,曾闹过鬼,这更使艾菲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每逢丈夫因公离家,她就疑神疑鬼,心惊胆战。后来她要求丈夫掉换房子,殷士台顿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对她讲了一番大道理。就在艾菲这种寂寞无聊无以排解的当儿,殷士台顿的一位友人少校军官克拉姆巴斯认识了艾菲。两人从此常常一起出外郊游,不久发生了关系。六年以后,殷士台顿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发现此事,为捍卫名誉,他和克拉姆巴斯进行了一场决斗,决斗结果,克拉姆巴斯被打死,艾菲被退婚,亲生女儿离开了她。艾菲一个人和女仆罗丝维塔孤零零地住在柏林。最后她身患重病,父母才允许她回娘家居住,不久,就死在那里。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以艾菲的婚姻为中心,着重描写这个贵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婚姻关系,剖析赖以维持这种关系的道德观念的虚伪、陈旧和腐朽,从而对这个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 艾菲和殷士台顿的结合,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门第、地位、金钱等的考虑。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艾菲的母亲路易丝早年为了门第、地位、金钱,情愿抛弃殷士台顿,嫁给布里斯特,就连她亲生女儿的亲事,也得由她和她丈夫做主,许配给业已获得县长地位的殷士台顿。这里的一弃一取,充分证实了“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这句话也适用于贵族之间的联姻。事实说明普鲁士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只是一种机械的僵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束缚下,即使像艾菲向往的那种单纯的爱情生活,也无法得到满足。相反,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使她感到痛苦,感到寂寞,只要有一个比较了解她心情的人闯到她的生活中来,她就无法抗拒了。个人与这种制度如果发生冲突,最后总是个人的毁灭。造成艾菲个人悲剧的原因也在于此。再看殷士台顿,他虽然一时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由于决斗和离婚,感到内心空虚,意志消沉,生活极不幸福。自从艾菲离开他以后,他觉得功名利禄是过眼烟云,不择手段追求幸福无异是捕风捉影。他认为“外表上光彩夺目的事物,往往其内容极为贫乏可怜;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的话,那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来他跟维勒斯多夫的一席谈话,更说明他对功名利禄的一些看法。他说:“人们越是表扬我,我越是感到这一切一文不值。我心里暗自思量,我的一生从此毁了,我不得不跟这种往上爬和虚荣心从此一刀两断,我不得不和大概最符合我本性的教师爷行径从此分道扬镳,而这种行径却是一个更高一级的道学家所习以为常的。” 这里所谓的“教师爷”和“道学家”,实际上是指殷士台顿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卫道士角色;这个“道”,也就是普鲁士社会的传统道德。这种道德观念早已陈旧过时,而殷士台顿却“死守条文”不放。艾菲和克拉姆巴斯的私通事件,殷士台顿是在六年以后偶然发现的。六年以来他和艾菲之间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他是不是要为六年前的事情进行一次决斗,以洗刷名誉的污点呢。为了这件事,他曾和友人维勒斯多夫作了一席谈话,他问朋友要否为了六年前的一件事而进行决斗,因为他此时并不感觉嫉妒、愤怒,也不想复仇。但是他还是决定和克拉姆巴斯决斗。他所依据的理由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仅是单独的个人,他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我们得时时顾及这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在殷士台顿的眼里,维护个人的名誉,是普鲁士制度下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为了保护名誉,他下决心决斗。他还说,一个人“和人群共同生活时,就形成了某种东西。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习惯于按照其条文来评判一切,评判别人和自己。违犯这些条文,是不允许的;违犯了这些条文,社会就要看不起我们,最后我们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直到完全受不了舆论的蔑视,用枪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止。”这里所谓“条文”,无疑是普鲁士式的教育和传统习俗。小安妮后来受的也就是这样的教育:不认母亲,冷酷无情。维勒斯多夫听了殷士台顿的一番话以后,马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咱们的名誉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但是只要这个偶像一天还起作用,咱们就得向它顶礼膜拜。”维勒斯多夫的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机器所需要的是人们的盲目服从、偶像崇拜,这种盲目服从,后来也在艾菲身上表现出来。殷士台顿恰好成了这种偶像的俘虏。不仅是殷士台顿,就是艾菲的父母,开头也做了这个偶像的俘虏,他们不许艾菲回家,害怕舆论的压力,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这种捍卫名誉的虚伪的荣誉心,是造成决斗,造成杀人,造成艾菲死亡的真正原因。在这场决斗以后,殷士台顿虽然有所省悟:“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捍卫一个概念的一场戏,一个人为的故事,一出演了一半的喜剧。这出喜剧我现在还得继续演下去,还非得把艾菲遣走不可,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但他并没有回头是岸,迷途知返,而是执意要把这出“喜剧”,不,应该说是“悲剧”演到底。一句话,名誉崇拜,是普鲁士社会的道德核心,不论艾菲,殷士台顿,还是艾菲的父母,他们都是这个偶像的俘虏。正因为大家把捍卫名誉看作是最高原则,这才产生那样一个悲剧。小说通过艾菲的不幸遭遇,展示了这个以过时的道德观念作为精神支柱的容克贵族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 然而,《艾菲·布里斯特》尽管揭示了普鲁士贵族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性,指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冯塔纳笔下的女主人公艾菲,对于这个社会丝毫不敢反抗,她始终是痛苦绝望,听天由命。书中的其他人物,在反抗旧制度上也无所作为。而作者对于像殷士台顿这样一个人物,并没有加以鞭挞,到了全书末尾,还要通过老布里斯特的嘴称赞他“气量大”“心地总是光明磊落”,对他寄予同情。连艾菲在临终前,也要表示忏悔,认为殷士台顿做得对,主动要同他和解。 四 《艾菲·布里斯特》这部小说,结构非常紧凑,情节单线发展,它不像某些小说那样,一条主线以外,还穿插着若干支线。本书的情节自始至终沿着一条线向前发展,情节的中心是艾菲的婚姻。这婚姻发展到最后成了一个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是人们在事先所能预料到的。全书的顶点不是艾菲的私通,不是私通事件的被发现,也不是殷士台顿和克拉姆巴斯的决斗或艾菲的死亡,而是殷土台顿在准备决斗前和他的朋友维勒斯多夫的一席谈话,这席谈话点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展示了作者批判锋芒所向。 全书出现的人物虽然不算多,但情节的发展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小说从艾菲订婚开始,随着艾菲婚后生活这条线索的进展,社会场景从乡村到小城,从外省到首都,从县长公馆到部长官邸,从圣诞晚会到林务官的家宴,作者都以细腻的笔触作了不同程度的刻划。读者如果细细研读,就会觉得好像身历其境,看到了俾斯麦执政时期普鲁士德国的种种生活画面。从俾斯麦统一德国到俾斯麦下台,其间虽然不过一二十年,但这一二十年,却是德国向封建军事帝国的过渡时期,什么“时代精神”,什么“保护关税”,什么“殖民主义”,书内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反映;作者在这几个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颇能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正是作者艺术技巧的杰出之处。 其次,关于人物形象的刻划,冯塔纳也有其独特的手法。像艾菲这个人物,不仅是作者自己最喜爱的形象,也是德国文学中塑造得最出色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善于用陪衬对比的手法,使艾菲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艾菲本来是人们比较同情的一个人物,作者通过鬼屋的描绘,使人们更加同情弱小者艾菲的处境;同样,作者把艾菲和书中其他女性置于对比的地位,从而突出艾菲那种天真、纯洁的少女性格,这样能使读者对她寄予更多的同情。当然,今天看来,她毕竟是一个贵族少女,在她身上有许多贵族女子的弱点和缺点。 又如罗丝维塔这个人物,作者在她身上是着墨较多的。这个人本身是劳动妇女,手工匠家庭出身,为人忠心耿耿,善良,憨直,在她身上保存了若干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这个人和约翰娜、克丽斯特尔一比,更显得她的形象高大;作者通过维勒斯多夫之口,称赞她比贵族们“高明”,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现实主义者的冯塔纳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 冯塔纳的艺术技巧,还表现在书中穿插的大量对话上面。作者通过对话,刻划了书中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那个阶级的想法、愿望和要求;通过对话,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突出人物的性格。这些对话都十分精彩动人,它们可把无法用行动描绘出来的东西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同时每个人的对话各有特点,各自符合这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例如,老布里斯特常常把不能理解的问题,用“这是一个太广阔的领域”来表示;艾菲之死,他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也用了上述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他的口头禅,也可以说是他这个人物的心声。又如罗丝维塔这个女仆,喜欢讲她那个老掉了牙的初恋故事,说话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这正符合她那憨直的性格。艾菲去世前不久,她为了索取爱犬洛洛给女主人做伴,曾致信殷士台顿直陈己见,打动了殷士台顿的心,这又体现出她对女主人的一片忠心。她和女主人之间的若干对话,读了之后,令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作者有时通过罗丝维塔这个人物的语言,表达他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冯塔纳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善于典型地塑造形象,反对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某些情节写得极为含蓄,某些场面只是一笔带过。比方像艾菲跟克拉姆巴斯的私通,他不作赤裸裸的描绘,不花大量笔墨,而是通过情节本身合乎逻辑的发展,使读者感到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又如,关于殷士台顿枪杀克拉姆巴斯的决斗场面,作者也只是简单交代几句,不花大量篇幅作自然主义的刻划。书中关于自然景色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其目的或加强情节的发展,或衬托人物的心境,都限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是冯塔纳的又一特色。 德国文学批评家保罗·里拉稍稍改动了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话,用来评论这位作家:“冯塔纳不得不违反自己普鲁士保守派的感情行事;他看出了自己以嘲讽的保留态度所偏爱的勃兰登堡贵族必然没落,把普鲁士世界的制度描写成一种偏狭固陋的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习俗;他在那些为傲慢的新德意志社会所不齿的地方看出了才干、灵魂的伟大和未来——这一切可说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冯塔纳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保罗·里拉:《文学·批评与论战》,德文版,柏林亨舍尔出版社,1952年版。 可以认为,这些论断很能概括冯塔纳创作方面的成就和特色。 韩世钟 一九七九年六月 第一章 自从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当政以来,封·布里斯特一家就在霍恩克莱门村定居了。邸宅的正厅面临大道,中午时分,岑寂的大道上洒满了明亮的阳光。正厅旁边是公园和花园,那儿造有侧厅,与正厅构成曲尺形,侧厅的硕大阴影起先投在用绿白两色方砖铺成的走道上,接着日斜影移,便笼罩在一个圆形的大花坛上。花坛四周为美人蕉和一丛丛大黄环抱,中央立有一口日晷。离此数十步,教堂庭院的一堵围墙在望,墙与侧厅平行,墙上爬满小叶常春藤,墙中仅有一处设有一扇白漆小铁门,墙后是霍恩克莱门村木板铺顶的钟楼。钟楼尖顶上装有一只风信鸡,新近才重新镀过金,闪闪发亮。正厅、侧厅和那堵围墙,从三面围成一个马蹄铁形的小巧精致的花园。空旷的一面,有一口池塘,塘边筑有一顶水桥,桥畔泊着一叶小舟,用铁链拴住。靠近池塘,还能看到一个秋千架,架子踏板的两侧上下,各用两条绳索缚住,架子的立柱已经有点儿倾斜。池塘和花坛之间一对高大、蓊郁的老梧桐,却遮住了半个秋千架。 每逢白云蔽日、阴翳横空的时刻,哪怕在邸宅的正面——那儿有一个平台,台上摆着栽有芦荟的木盆和花园靠椅——略作小憩,也能使人悠然自得,心旷神怡;但是,遇上赤日当空的时分,花园那一边却是人们,特别是这家主妇和她女儿喜欢流连的地方;即使在今天,她们也坐在这浓影匝地、方砖铺成的走道上。她们的身后是一排敞开着的窗户,上面攀满野葡萄藤,旁边是一个突出在屋外的小台阶,台阶的四个石级由花园通向侧厅的高台。这时母女俩忙于把一方方小料,拼缝成一块教堂祭台台毯。一绞绞毛线和一团团丝线摊在一张大圆桌上,五彩缤纷,斑驳杂陈。刚才她们曾在这儿用过午餐,现在桌上还剩有几只装点心的碟子和一个装满美丽的大醋栗的马约里卡彩陶碗。母女俩手中的银针快似飞梭,一来一往,随心所欲。但是就在母亲专心致志地做女红时,名叫艾菲的女儿却不时放下手中的针线,直起身来,伸腿弯腰,做出种种柔美的姿势,操练各节健身操和室内操。显然她特别喜欢做出这种略带滑稽的动作来逗引别人。当她站起身来,把胳膊慢慢举到头顶、合拢双掌时,她的妈妈也会放下手中的女红,抬起头来张望,不过她总是偷偷地瞥上一眼,因为做妈妈的不愿别人看出自己由于孩子的矫健而在脸上露出的喜悦神色,也不愿别人发现她那应有的母性骄傲在她内心所引起的激动。艾菲穿一件蓝白条子亚麻布罩衫,一半有点儿像小伙子穿的褂子;腰间紧束一根古铜色皮带,胸颈袒露,肩背上方披一条水手领。她的一举一动,显得既高傲又优雅。一对笑盈盈的褐色大眼睛,泄露出天生的绝顶聪明、热爱生活和心地善良。人们称她为“小丫头”,她也乐意接受。因为她那美丽、窈窕的妈妈,还比她高出一个手掌宽哩。 正巧艾菲又一次直起身来,把身子时而朝左时而朝右转动的时候,妈妈恰好停下手里的女红,重又昂起头来,向她大声说:“艾菲,你本来应该进马戏团学艺,永远登云梯,在高空荡来荡去。我差不多相信,你是想干这一行的。” “也许是这样,妈妈。但是,如果是这样,又该怪谁呢?我这种性格是谁给的?还不是你。或者你认为,是爸爸吧?要是你这样想,那你心里也会好笑的。再说,你干吗让我这样打扮,穿小伙子的褂子?有时我想,我又穿短褂了。只要我一穿上这玩意儿,我又会像黄毛丫头那样行屈膝礼。一旦拉特诺地方的军官来这儿,那我就骑在格兹大校的膝盖上,嗬嘘嗬嘘把他当马赶着走。干吗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七分像叔叔,三分像求爱者。全要怪你。我为什么没有一套体面的衣服?你干吗不把我打扮成一个高贵的女士?” “你想当高贵的女士吗?” “不!”她说着就奔向妈妈,十分热烈地拥抱她,吻她。 “别那么疯疯癫癫,艾菲,别那么感情冲动。我看到你这样,心里就不安……”妈妈说这话,样子一本正经,看起来想要继续讲讲她的忧虑和担心。但她没有接着往下说,因为正在这当儿,有三个年轻的姑娘通过那堵围墙的小铁门来到花园,沿着卵石道走向花坛和日晷。三个女孩都举起阳伞向艾菲这边打招呼,然后急急忙忙地朝封·布里斯特夫人走去,吻吻她的手。夫人向她们问长问短,寒暄了一阵,然后邀请她们坐一会儿,或者请她们至少和艾菲再谈上半小时。“我反正有事要走,年轻人最喜欢跟年轻人做伴。你们好好聊。”她说着就跨上通往侧厅的石级。 现在的确只剩下年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