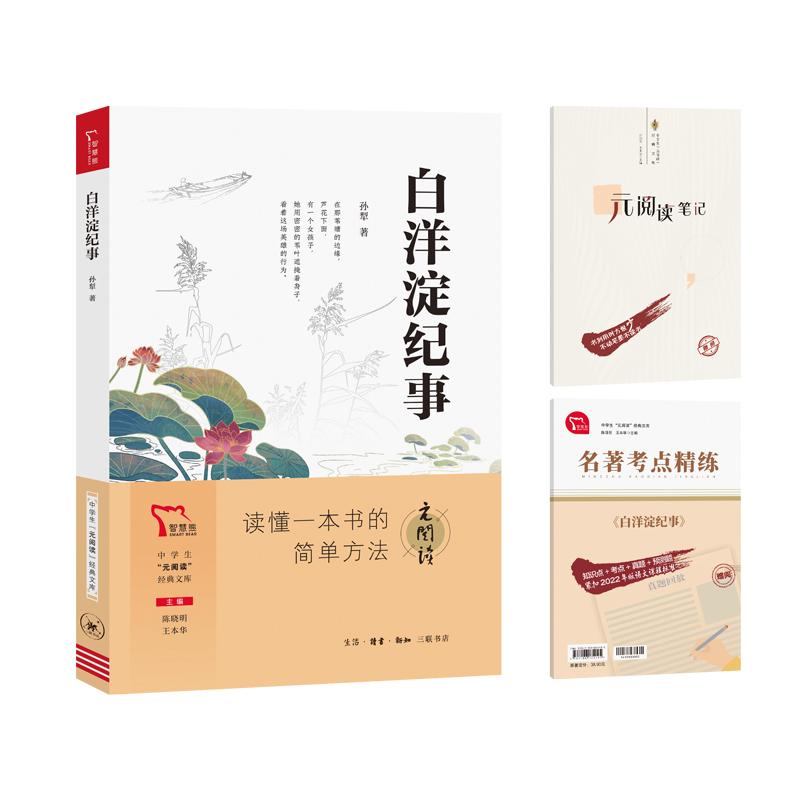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38.9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中学生“元阅读”经典文库 白洋淀纪事
ISBN: 9787108074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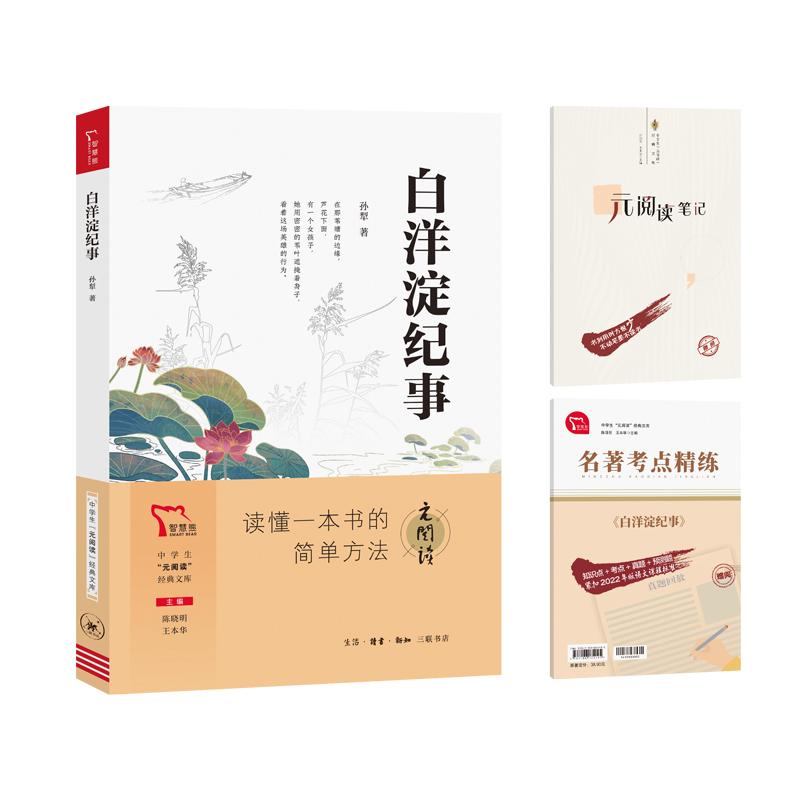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被认为是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孙犁于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集《白洋淀之曲》,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等。
"邢 兰 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叫邢兰的。 他在鲜姜台居住,家里就只三口人:他,老婆,一个女孩子。 这个人,确实是三十二岁,三月里生日,属小龙(蛇)。可是,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蒿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像有多年的痨症。眼睛也没有神,干涩的。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唱歌…… 去年冬天,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我的工作是刻蜡纸,油印东西。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这房子房基很高,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看西面,一带山峰,一湾河滩,白杨,枣林。到下午,太阳慢慢地垂下去…… 其实,刚住下来,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那几天正冷得怪。雪,还没有融化,整天阴霾着的天,刮西北风。我躲在屋里,把门紧紧闭住,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从门上面的空隙,从窗子的漏洞,从椽子的缝口。我堵一堵这里,糊一糊那里,简直手忙脚乱。 结果,这是没办法的,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脚更是受不了。正对我后脑勺,一个鼠洞,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起初,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吹着冷气;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山鼠出入的小洞洞。 我走出转进,缩着头没办法。这时,邢兰推门进来了。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来这里转转。我就请他坐坐,不过,我紧接着说: “冷得怪呢,这房子!” “是,同志,这房子在坡上,门又冲着西,风从山上滚下来,是很硬的。这房子,在过去没住过人,只是盛些家具。” 这个人说话很慢,没平常老乡那些啰唆,但有些气喘,脸上表情很淡,简直看不出来。 “唔,这是你的房子?”我觉得主人到了,就更应该招呼得亲热一些。 “是咱家的,不过没住过人,现在也是坚壁A着东西。”他说着就走到南墙边,用脚轻轻地在地上点着,地下便发出空洞的嗵嗵的声响。 “呵,埋着东西在下面?”我有这个经验,过去我当过那样的兵,在财主家的地上,用枪托顿着,一嗵嗵地响,我便高兴起来,便要找铁铲了。——这当然,上面我也提过,是过去的勾当。现在,我听见这个人随便就对人讲他家藏着东西,并没有一丝猜疑、欺诈,便顺口问了上面那句话。他却回答说: “对,藏着一缸枣子,一小缸谷,一包袱单夹衣服。” 他不把这对话拖延下去。他紧接着向我说,他知道我很冷,他想拿给我些柴禾,他是来问问我是想烧炕呢,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他问我怕烟不怕烟,因为柴禾湿。 我以为,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照例应酬,我便说: “不要吧,老乡。现在柴很贵,过两天,我们也许生炭火。” 他好像没注意我这些话,只是问我是烧炕,还是烤手脚。当我说怎样都行的时候,他便开门出去了。 不多会儿,他便抱了五六块劈柴和一捆茅草进来,好像这些东西,早已在那里准备好。他把劈柴放在屋子中央,茅草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拿一把茅草做引子,蹲下生起火来。 我也蹲下去。 当劈柴燃烧起来,一股烟腾上去,被屋顶遮下来,布展开去。火光映在这个人的脸上,两只眯缝的眼,一个低平的鼻子,而鼻尖像一个花瓣翘上来,嘴唇薄薄的,又没有血色,老是紧闭着…… 他向我说: “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 从此,我们便熟识起来。我每天做着工作,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类到房子里来替我生着,然后退出去。晚上,有时来帮我烧好炕,一同坐下来,谈谈闲话。 我觉得过意不去。我向他说: “不要这样吧,老邢,柴禾很贵,长此以往……” 他说: “不要紧,烧吧。反正我还有,等到一点也没有,不用你说,我便也不送来了。” 有时,他拿些黄菜、干粮给我。但有时我让他吃我们一些米饭时,他总是赶紧离开。 起初我想,也许邢兰还过得去,景况不错吧。终于有一天,我坐到了他家中,见着他的老婆和女儿。女儿还小,母亲抱在怀里,用袄襟裹着那双小腿,但不久,我偷眼看见,尿从那女人的衣襟下淋下来。接着那邢兰嚷: “尿了!” 女人赶紧把衣襟拿开,我才看见那女孩子没有裤子穿…… 邢兰还是没表情地说: “穷的,孩子冬天也没有裤子穿。过去有个孩子,三岁了,没等到穿过裤子,便死掉了!” 从这一天,我才知道了邢兰的详细。他从小就放牛,佃地种,干长工,直到现在,还只有西沟二亩坡地,满是砂块。小时放牛,吃不饱饭,而且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唤。……直到现在,个子没长高,气喘咳嗽…… 现在是春天,而鲜姜台一半以上的人吃着枣核和糠皮。 但是,我从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他愁眉不展或是唉声叹气过,这个人积极地参加着抗日工作,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邢兰对于抗日工作的热心,我按照这两个字的最高度的意义来形容它。 邢兰发动组织了村合作社,又在区合作社里摊了一股。发动组织了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代耕团是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的,互助团全是村里的人,无论在种子上,农具上,牲口、人力上,大家互相帮助,完成今年的春耕。 而邢兰是两个团的团长。 看样子,你会觉得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但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出人意外地英勇地做了。这,不是表现了英勇,而是英勇地做了这件事。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还是去年冬天,敌人“扫荡”这一带的时候。邢兰在一天夜里,赤着脚穿着单衫,爬过三条高山,探到平阳街口去。敌人就住在那里。等他回来,鲜姜台的机关人民都退出去。他又帮我捆行李,找驴子,带路…… 邢兰参与抗日工作是无条件的,而且在一些坏家伙看起来,简直是有瘾。 近几天,鲜姜台附近有汉奸活动,夜间,电线常常被割断。邢兰自动地担任侦察的工作。每天傍晚在地里做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我便看见他斜披了一件破棉袍,嘴里哼着歌子,走下坡去。我问他一句: “哪里去?” 他就眯眯眼: “还是那件事……” 夜里,他顺着电线走着,有时伏在沙滩上,他好咳嗽,他便用手掩住嘴…… 天快明,才回家来,但又是该下地的时候了。 更清楚地说来,邢兰是这样一个人,当有什么事或是有什么工作派到这村里来,他并不是事先说话,或是表现自己,只是在别人不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表示了意见,在别人不高兴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件工作担负起来。 按照他这样一个人,矮小、气弱、营养不良,有些工作他实在是勉强做去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从坡下面一步一步挨上来,肩上扛着一条大树干,明显他是那样吃力,但当我说要帮助他一下的时候,他却更挺直腰板,扛上去了。当他放下,转过身来,脸已经白得怕人。他告诉我,他要锯开来,给农具合作社做几架木犁。 还有一天,我瞧见他赤着背,在山坡下打坯,用那石杵,用力敲打着泥土。而那天只是二月初八。 如果能拿《水浒传》上一个名字来呼唤他,我愿意叫他“拼命三郎”。 从我认识了这个人,我便老是注意他。一个小个子,腰里像士兵一样系了一条皮带,嘴上有时候也含着一个文明样式的烟斗。 而竟在一天,我发现这个家伙,是个“怪物”了。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树修理枝丫,停下来,竟从怀里掏出一只耀眼的口琴吹奏了。他吹的调子不是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中国流行的曲调,而是他吹熟了的自成的曲调,紧张而轻快,像夏天森林里的群鸟喧叫…… 在晚上,我拿过他的口琴来,是一个“蝴蝶牌”的,他说已经买了二年,但外面还很新,他爱好这东西,他小心地藏在怀里,他说:“花的钱不少呢,一块七毛。” 我粗略地记下这一些。关于这个人,我想永远不会忘记他吧。 他曾对我说:“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这句话在我心里存在着,它只是一句平常话,但当它从这样一个人嘴里吐出来,它就在我心里引起了这种感觉: 只有经受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记到这里,我才觉得用不着我再写下去。而他自己,那个矮小的个子,那藏在胸膛里的一颗煮滚一样的心,会续写下去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记于阜平 战 士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废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废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小壶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 “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 “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 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 “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经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抬了一筐肉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 “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人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和小孩尿,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这不是一个十分妥当的女人,临完,她和我搅缠B着一毛钱,说我多吃了一毛钱的肉。我没办法,照数给了她,但正色说: “我不在乎这一毛钱,可是我和你丈夫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回来,你不要说,你和我因为一毛钱搅缠了半天吧!”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 “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 “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芦 苇 敌人从只有十五里远的仓库往返运输着炸弹,低飞轰炸,不久,就炸到这树林里来,把梨树炸翻。我跑出来,可是不见了我的伙伴。我匍匐在小麦地里往西爬,又立起来飞跑过一块没有遮掩的闲地,往西跑了一二里路,才看见一块坟地,里面的芦草很高,我就跑了进去。 “呀!” 有人惊叫一声。我才看见里面原来还藏着两个妇女,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不是因为我跳进来吃惊,倒是为我还没来得及换的白布西式衬衣吓了一跳。我离开她们一些坐下去。半天,那妇女才镇静下来说: “同志,你说这里藏得住吗?” 我说等等看。我蹲在草里,把枪压在膝盖上,那妇人又说: “你和他们打吗?你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有多少。” 我说,不能叫他们平白捉去。我两手交叉起来垫着头,靠在一个坟头上休息。妇人歪过头去望着那个姑娘,姑娘的脸还是那样惨白,可是很平静,就像我身边这片芦草一样,四面八方是枪声,草叶子还是能安定自己。我问: “你们是一家吗?” “是,她是我的小姑。”妇人说着,然后又望一望她的小姑,“景,我们再去找一个别的地方吧,我看这里靠不住。” “上哪里去呢?”姑娘有些气恼,“你去找地方吧!” 可是那妇人也没动,我想她是有些怕我连累了她们,就说: “你们嫌我在这里吗?我歇一歇就走。” “不是!”那姑娘赶紧抬起头来望着我说,“你在这里,给我们仗仗胆有什么不好的?” “咳!”妇人叹一口气,“你还要人家仗胆,你不是不怕死吗?”她就唠叨起来,我听出来她这个小姑很任性,逃难来还带着一把小刀子。“真是孩子气,”她说,“一把小刀子顶什么事哩!” 姑娘没有说话,只是凄惨地笑了笑。我的心骤然跳了几下,很想看看她那把小刀子的模样。她坐在那里,用手拔着身边的草,什么表示也没有。 忽然,近处的麦子地里有人走动。那个妇人就向草深的地方爬,我把那姑娘推到坟的后面,自己卧倒在坟的前面。有几个敌人走到坟地边来了,哇啦了几句,就冲着草里放枪,我立刻向他们还击,直等到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才停下来。 不久天也快黑了,她们商量着回到村里去。姑娘问我怎么办,我说还要走远些,去打听打听白天在梨树园里遇到的那些伙伴的下落。她看看我的衣服: “你这件衣服不好。”再低头看看她那件深蓝色的褂子:“我可以换给你。先给我你那件。” 我脱下我的来递给她,她走到草深的地方去。一会儿,她穿着我那件显得非常长大的白衬衫出来,把褂子扔给我: “有大襟,可是比你这件强多了,有机会,你还可以换。”说完,就去追赶她的嫂子去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女人们(三篇) 1.红棉袄 风把山坡上的荒草,吹得俯到地面上、砂石上。云并不厚,可沉重得怕人,树叶子为昨夜初霜的侵凌焦枯了,正一片片地坠落。 我同小鬼顾林从滚龙沟的大山顶上爬下来。在强登那峭峻的山顶时,身上发了暖,但一到山顶,被逆风一吹,就觉得难以支持了。顾林在我眼前,连打了三个寒噤。 我拉他赶紧走下来,在那容易迷失的牧羊人的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在乱石中开拔着脚步。顾林害了两个月的疟疾C,现在刚休养得有了些力气,我送他回原部队。我们还都穿着单军服,谁知一两天天气变得这样剧烈。 虽说有病,这孩子是很矜持的。十五岁的一个人,已经有从吉林到边区这一段长的而大半是一个人流浪的旅程。在故乡的草原里拉走了两匹敌人放牧的马,偷偷卖掉了,跑到天津,做了一家制皮工厂的学徒。“事变”了,他投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身子一弱就到了这样!” 像是怨恨自己。但我从那发白的而又有些颤抖的薄嘴唇,便觉得他这久病的身子是不能支持了。我希望到一个村庄,在那里休息一下,暖暖身子。 风还是吹着,云,凌人地往下垂,我想要下雨了,下的一定是雪片吧?天突然暗了。 远远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现一片白色的墙壁,我尽可能地加快了脚步,顾林也勉强着。这时,远处山坡上,已经有牧羊人的吆喝声,我知道天气该不早了,应是拦羊下山入圈的时分。 爬上那个小山庄的高坡,白墙壁上的一个小方窗,就透出了灯火。我叫顾林坐在门前一块方石上休息,自己上前打门。门很快地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我对她说明来意,问她这里有没有村长,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话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小庄子,总共三家人家,过往的军队有事都是找她家的,因为她的哥哥是自卫队的一个班长。随着她就踌躇了。今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妈妈去外婆家了,哥哥还没回来。 她转眼望一望顾林,对我说: “他病得很重吗?” 我说:“是。” 她把我们让到她家里,一盏高座的油灯放在窗台上,浮在黑色油脂里的灯芯,挑着一个不停跳动的灯花,有时碎细地爆炸着。 姑娘有十六岁,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没有那灯光和灶下的柴禾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间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我一时觉得我们休息在这里,有些不适当。但顾林躺在那只铺一张破席子的炕上了,显然他已是筋疲力尽。我摸摸他的额,又热到灼手的程度。 “你的病不会又犯了吧?” 顾林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牙齿的“嘚嘚”声,他又发起冷来。我有些发慌,我们没有一件盖的东西。炕的一角好像是有一条棉被,我问那正在低头烧火的姑娘,是不是可以拿来盖下。姑娘抬着头没听完我的话,便跳起来,爬到炕上,把它拉过来替顾林盖上去。一边嘴里说,她家是有两条被的,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把被紧紧地盖住了顾林的蜷伏的身体,她才跳下来,临离开,把手按按顾林的头,对我蹙着眉说: “一定是打摆子!” 她回去吹那因为潮湿而熄灭的木柴了,我坐在顾林的身边,从门口向外望着那昏暗的天。我听到风还在刮,隔壁有一只驴子在叫。我想起明天顾林是不是能走,有些愁闷起来。 姑娘对我慢慢地讲起话来。灶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像蔓延着火焰一样。 她对我讲,今年打摆子的人很多。她问我顾林的病用什么法子治过。她说有一个好方法,用白纸剪一个打秋千的小人形,晚上睡觉,放在身下,第二天用黄表纸卷起来,向东南走出三十六步,用火焚化,便好了。她小时便害过这样的病,是用这个方法治好的。说完便笑起来:“这是不是迷信呢?” 夜晚静得很,顾林有时发出呻吟声,身体越缩拢越小起来。我知道他冷。我摸摸那条棉被,不只破烂,简直像纸一样单薄。我已经恢复了温暖,就脱下我的军服的上身,只留下里面一件衬衫,把军服盖在顾林的头上。 这时,锅里的饭已经煮好。姑娘盛了一碗米汤放在炕沿上,她看见我把军服盖上去,就沉吟着说: “那不抵事。”她又机灵地盯视着我。我只是对她干笑了一下,表示:这不抵事,怎样办呢?我看见她右手触着自己棉袄的偏在左边的纽扣,最下的一个,已经应手而开了。她后退了一步,对我说: “盖上我这件棉袄好不好?” 没等我答话,她便转过身去断然地脱了下来,我看见她的脸飞红了一下,但马上平复了。她把棉袄递给我,自己退到角落里把内衣整理了一下,便又坐到灶前去了,末了还笑着讲: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 她身上只留下一件褶皱的花条布的小衫。对这个举动,我来不及惊异,我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的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 我凝视着那暗红的棉袄。姑娘凝视着那灶膛里一熄一燃的余烬。一时,她又讲话了。她问我从哪里来,尽走过哪些地方,哪里的妇女自卫队好。又问我,什么时候妇女自卫队再来一次检阅。一会儿我才知道,在去年,平山县妇女自卫队检阅的时候,打靶,她是第三名! 2.瓜的故事 马金霞又坐在那看瓜园的窝棚里了。已经吃过了晌午饭,肚子饱饱的,从家里跑来的满身汗,一到这里就干了,凉快得很呢。窝棚用四根杨树干支起来,上面搭上席子,中间铺上木板,一头像梯子一样横上木棍,踏着上去,像坐在篷子车里。 好凉快呀!马金霞把两只胳膊左右伸开一下,风便吹到了袖子里、怀里。窝棚前后是二亩地的甜瓜和西瓜,爹租来种的。甜瓜一律是“蛤蟆酥”和“谢花甜”种,一阵阵的香味送过来。西瓜像大肚子女人,一天比一天笨地休养在长满嫩草的地上。那边是一个用来从河里打水浇地的架子,“斗子”悬空着。 一带沙滩,是通南北的大道,河从中间转弯流过。 村边上,那个斜眼的铁匠的老婆,又爬上她那蔓延在一棵大柳树上的葡萄架了。从马金霞这里也会看见那已经发紫的累累的葡萄。马金霞给这个铁匠老婆起了一个外号,一看见她便叫起来: “馋懒斜!”是因为这个老婆顶馋(不住嘴地偷吃东西),顶懒(连丈夫打铁的风箱也不高兴去拉),顶斜(眼也斜,脾气性情儿也斜)。 那女人从葡萄架上转过身子来,用手护着嘴像传声筒喊: “金霞又卖俏哩吗?看过路的哪个脸子白,招来做驸马吧!” “放屁,放屁,放屁!”马金霞回骂着。 “你看你不是坐在八人抬的大轿里了吗?要做新媳妇了呢!”斜眼女人扯着嗓子怪叫。 马金霞便不理睬她了。理她干吗呢?狗嘴里掉不出象牙来,满嘴喷粪。 水冲着石子,哗啦啦地响着。 马金霞把鞋脱掉了,放在一边。把右腿的裤脚挽到了膝盖上面,拿过一团麻,理了一理,在右腿上搓起麻绳来,随口唱一支新鲜小曲儿: 小亲亲, 我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 我不要你的银, 只要(你那)抗日积极的一片心! 一架担架过来了,四个人抬着急走,后面跟着两个人挥着汗。马金霞停止了唱。 “住下,住下。”后面一个人望了一望瓜园嚷着。 “什么事?这里晒得很哩!”抬的人问着,脚也没停,头也没回。 “王同志不是说要吃瓜吗?这里又有甜瓜又有西瓜,住下,住下……” 担架住下了。在一床白布罩子下面,露出了一个脸。黄黄的,好大的眼睛啊。头歪到了瓜园这边,像找寻着什么,微笑了。一个民兵跑上来喊: “下来,小姑娘,买瓜。” 马金霞赤着脚下来了,快得像一只猴子。两步并作一步,跑到伤兵的面前,望了望那大眼睛,又看见那白布罩角上的一片血迹,就“咳呀”了一声。 她带那个人去挑选瓜了,告诉他还是给同志一个西瓜吃吧。受了伤吃甜瓜不好,肚子痛还不要吃甜瓜呢。那个人以为这女孩子要做“大宗买卖”,也便没说话。马金霞在瓜园里践踏着,用手指一个个地去弹打着瓜皮,细听着声响。然后她问: “是前两天那次大战受的伤吗?” “是,真是英雄呢。”那个人赞叹着,“可是你会挑选瓜吗?” “你瞧着吧。” 马金霞想起在西北角上那个血瓤的西瓜了,那是她前天就看准的,她把它摘下来,亲手抱过去。 抬担架的小伙子们还不相信,就地把那瓜用一把小刀剖开来。 瓜瓤是血红的,美丽的,使人想起那白布罩上的光荣的战士的血迹了。几个小伙子夸奖着,问价钱。 “送给同志们吃的,不是卖的。” 虽然那战士也用微弱的声音诉说着这不好,但马金霞跑上窝棚了。她对那远远的葡萄架上的女人喊: “馋懒斜,把你的葡萄送些来,有位受伤的同志呢。” 可是斜眼女人问了: “买几毛钱的呀?” 有什么意味呀!马金霞气恼了。总是“几毛钱”。她常见斜眼女人烦絮地和来买葡萄的同志们要着大价钱,赚了钱来往自己坏嘴里填,吃饱了和不三不四的坏男人嚼舌头,有什么意味呀! 3.子弟兵之家 从前,村里的人称呼她“三太家的”,现在,妇女自卫队分队长找上她的门子是喊: “李小翠同志!” 丈夫是子弟兵。临入伍那天,大会上小翠去送他;临走,三太用眼招呼她。小翠把手一扬: “去你的吧!” 两个人都笑了。李小翠便一边耍逗着怀里的孩子,一边想着心思,回家了。 在边区,时光过得快。打了一个百团大胜仗,选举了区代表、县议员、参议员,打走鬼子的捣乱……就要过年了。 天明便是大年初一了。 天还没亮,鸡只叫了两遍,“申星”还很高呢。 孩子闹起来,小手抓着小翠的胸脯,小脚蹬着肚子。 “他妈的!”小翠一边骂着,一边点起灯来。 窗纸上糊着用彩色纸剪成的小人们,闪耀着…… 小纸人是西头叫小兰的那女孩子剪的。那孩子昨天早晨捧着那些小人跑来,红着脸对小翠说: “小翠婶婶,我剪了两个戏剧,一个捉汉奸,一个打鬼子,送给你贴在窗子上。” “呀,你费了半天工夫,拿去叫你娘贴吧!”小翠客气着。 “为的是,”小兰睁大眼睛,“我家三太叔上前线了。” 小兰还怕她贴错,帮她贴好才走了。 小翠给孩子穿衣裳,打开一个小匣子,拿出一顶用红布和黄布做成的小孩帽,是个老虎头的样子,用黑布贴成眼,用白布剪成虎牙。 孩子一戴上新帽子,觉着舒服,便在小翠的腿上跳起来,小翠骂: “小家子气!” 小翠又想起心思来了。前年死了一个孩子,没戴过新帽子。这个孩子三岁了,这还是头一顶。虽说裤子还破着,可是今年过年没有别的花销,村里优待了一小笸箩白面、五斤猪肉、三棵白菜,便也乐开了。她把孩子举起来,叫孩子望着她的放光的大眼,她唱着自己编的哄孩子的曲儿: 孩子长大, 要像爹一样 上战场…… 孩子便“马、马”叫起来。小翠叫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接着: 骑大马, 背洋枪! 唱到这里,小翠又想起心思来了:“谁知道他骑上马没有呢?”三太那大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她笑了。她喃喃地好像对孩子说,又好像对三太说: “你呀!多打好仗呀!就骑大马呀!” 风吹窗纸动起来,小人们动起来了。她愿意风把这话吹送到三太的耳鼓里去……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自主阅读推荐图书。 ★文字清馨质朴,思想深刻,意味隽永,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自初版以来获得广泛好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配套教材使用,增设“名家导读”“梳理与探究”“精读旁批”“阅读·思考·生活”“读书短札”等栏目,帮助学生科学高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