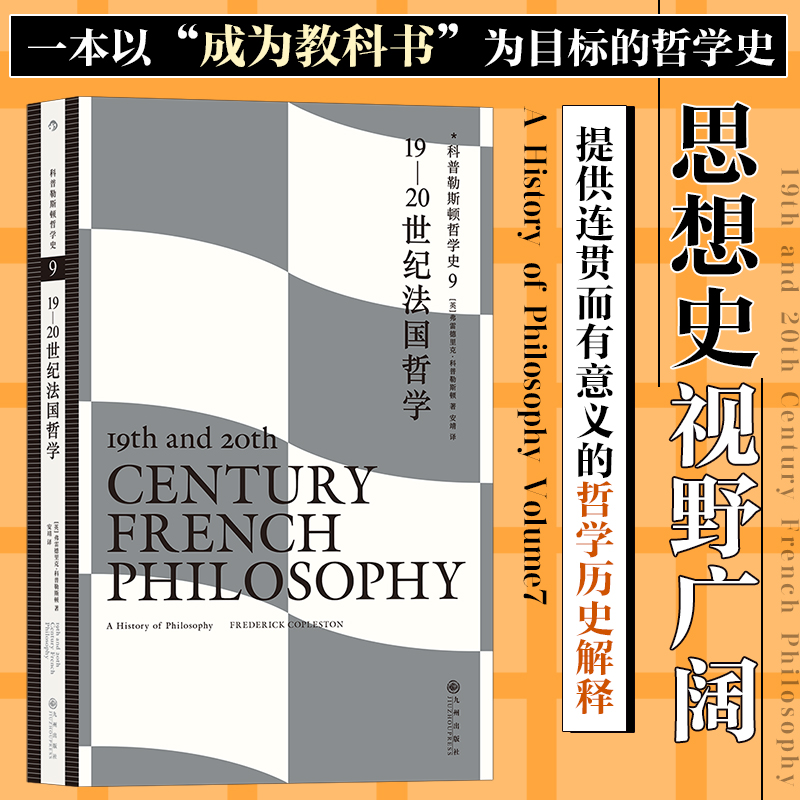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科普勒斯顿哲学史.9,19—20世纪法国哲学
ISBN: 9787522521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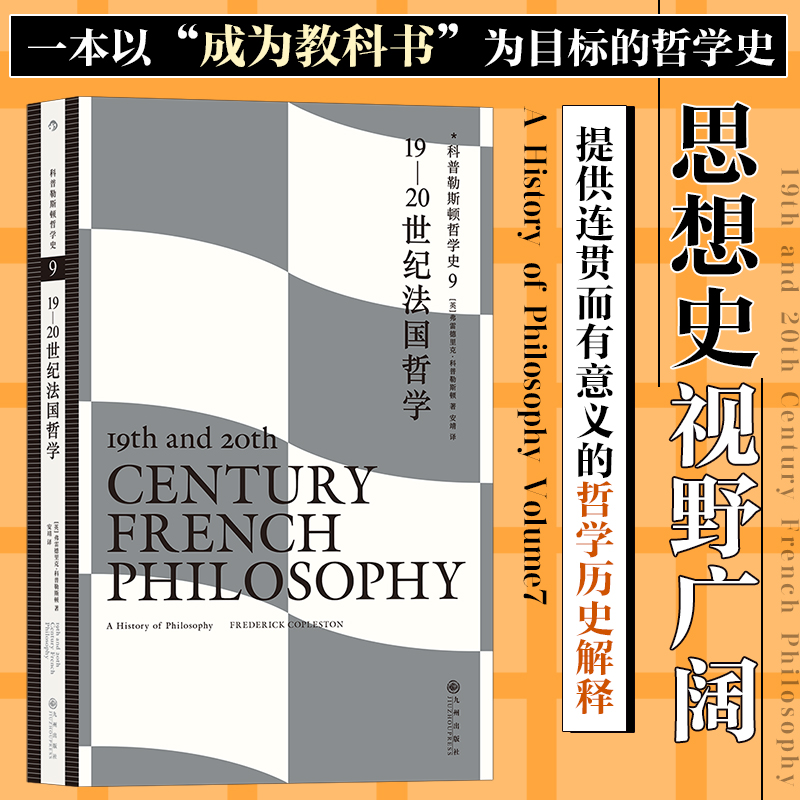
★著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著名哲学史家,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哲学学会成员、亚里士多德学会成员、伦敦大学海斯洛普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译者简介 安靖: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哲学博士,现于南开大学哲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为形而上学史与当代德法自然哲学。已出版的译著有《差异与重复》《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式革命》与《柏格森主义》。
第一章 传统主义者对大革命的回应 引言—德·迈斯特—德·博纳尔德—夏多布里昂—拉梅内—传统主义与教会 1. 法国大革命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冷静客观地研究它的起因、发展和结果。但在当时,显而易见的是,强烈的情感不但伴随着判断,而且还往往影响着人们做出的判断。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场革命不但表现为民族解放和法国社会的复兴力量,而且也表现为一场注定会给其他民族带来光明和自由的运动。恐怖统治当然会遭到谴责,或许也会得到原谅, 但大革命的理想得到了认可和欢迎,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对人类自由的肯定,而且它们在有些时候还被看作宗教改革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扩展,人们对此期盼已久。不过,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还有其他一些人,大革命对他们来说是威胁到社会根基的灾难性事件:它用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代替了社会稳定,它给法兰西传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它表达了对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宗教基础的拒斥。很明显,对大革命所抱有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私的动机激发出来的,但同样的判断也可以用在大革命的支持者身上。正如观念论可以用来支持大革命,同样,也会有反对者发自内心地确信大革命精神具有毁灭性和不敬神的特征。 在哲学层面上对大革命提出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的是所谓的传统主义者。无论是支持大革命的人还是反对大革命的人,全都倾向于认为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结出的果实,尽管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和态度有天壤之别。认为传统主义者是怀念过去并且对历史运动视而不见的反动力量,从而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无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多么的目光短浅,他们仍然是富有影响力的杰出作家。对19世纪早期的法国思想所做的分析不能简单地略过他们。 2. 第一位必须提到的作家是著名的保皇主义者和教皇至上论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德·迈斯特出生于萨伏依的尚贝利,他曾经在都灵学习法律,后来成了萨伏依的参议员。当法国人入侵萨伏依时,他首先逃到奥斯塔然后逃到洛桑避难,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关于法兰西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虽然德·迈斯特曾一度对自由主义抱有同情态度,但在这部著作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反对态度和重新恢复法国君主制的欲求。 1802 年,德·迈斯特被撒丁王国国王任命为派往圣彼得堡俄国宫廷的全权公使,并在俄国停留了14个年头。他在这段时间撰写了《论政治宪法的发生原理》(Essai sur le principe générateur des constitutions politiques,1814)。他同时还忙于《论教皇》(Du Pape)的写作,这部著作最终在都灵被完成并于1819年出版。他的《圣彼得堡的夜晚》(Soirées de Saint-Pétersbourg)出版于1821 年,而《培根哲学考》(Examen de la philosophie de Bacon)则在他去世后的 1836 年出版。 德·迈斯特早年间和里昂的共济会圈子有所来往,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路易-克洛德·德·圣-马丁(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1743—1803)观点的影响[而圣-马丁本人则受到雅各布·波默(Jakob Boehme)著作的影响]。这个反对启蒙哲学的圈子转向了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学说,后者表现为基督教信仰和新柏拉图主义信仰的融合。在圣-马丁看来,历史就是神意的展开,它是一个完全与神或太一联系在一起的连续过程。 在德·迈斯特的《关于法兰西的考察》中至少可以辨识出这类观点的回声,这或许不无道理。他的确因为革命、弑君、攻击教会和恐怖统治而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的历史概念又使得他无法对大革命做出彻底的否定性评价。在他看来,虽然罗伯斯庇尔和一些其他领袖人物是恶棍和罪犯,但他们同样也是神意的无意识工具。人的“活动既是意志的又是必然的”。他们仿佛是在以自己所意愿的方式活动,但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推动神意的设计。大革命的领袖们认为是他们在掌控革命,但他们不过是先被使用后被丢弃的工具,而且大革命本身是神用来惩罚罪恶的工具:“神圣者还从未在其他人类事件那里如此清晰地显露过自己。如果他使用了邪恶的工具,这便是出于革新之故而进行惩罚的情况。”如果卷入大革 命的各个派别试图毁灭基督教和君主制,“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努力只会带来基督教与君主制的强化”,因为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 德·迈斯特的这种认为“历史展现了神意的行动,而个人只是工具”的观点本身并不新鲜,尽管他把这种观点应用到了最近的一个或一系列事件之上。这种观点显然会遭到反对。不仅在调和人类自由和神圣目的之不容动摇的实现时会遇到困难,革命和战争作为神的惩罚这一概念还会催生这样一种反思:并不只是有罪者(或那些人类眼中的有罪者)才遭受这样 的大灾难。尽管如此,德·迈斯特试图通过一种国家团结、人类团结(这种团结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的理论来回应这种挑战。他正是利用这一理论来对抗被他视为错误和危害的启蒙个人主义。德·迈斯特坚持主张政治社会绝不是通过社会契约统一起来的个人的集合。一部行之有效的宪法也不能在不考虑国家传统和历经了数世纪发展的制度的情况下单凭人类理性而被先天地构想出来。“这个信奉一切错误的世纪中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相信一部政治宪法能够以先天的方式被写就、被创造,而理性和经验则一起告诉我们,一部宪法乃是神的作品,它恰恰就是国家法律中最根本的、最本质的宪法性的东西,是无法被书写的。”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英国宪法,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大量发挥着作用的因素和环境的结果,它们充 当了神意的工具。这种类型的宪法当然不是以先天的方式构建出来的,它始终与宗教结盟,始终表现为君主制。因此,这样一个事实就并不出人意料:如果革命者们希望通过法令来确立一套宪法,那么他们必然会同时对宗教和君主制进行攻击。 一般说来,德·迈斯特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因为后者只关心抽象的东西而不尊重在他看来展现了神意活动的传统。启蒙哲学家们的抽象人(abstract human being)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虚构,它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它不是任何一个有机统一体的成员。当国家被解释为契约或习惯的产物时,它同样也变成了一种虚构。当德·迈斯特对某位启蒙思想家做出赞美的评价,这乃是因为他认为这位思想家超越了先天理性主义的精神。例如,德·迈斯特就因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的人为性所做的批评而对他大加赞扬。如果德·迈斯特回到启蒙运动之前对弗朗西斯·培根进行批评,理由就在于在他看来 “现代哲学完全就是培根的女儿”。 在德·迈斯特看来,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虚构就是自然宗教—如果“自然宗教”这个术语被理解为一种纯粹哲学性的宗教,一种人类理性的自发建构。对于神的信仰实际上是由原始启示传给人类的,基督宗教是一种更加完全的启示。换言之,唯一存在着的宗教就是启示宗教。而且,正如人们无法先天地建构出一种宪法,人们也无法先天地建构出一种宗教。“上世纪的哲学在后人眼中将会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最为可耻的时代……它事实上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实践无神论体系。” 根据德·迈斯特的观点,18世纪的哲学在人民主权理论和民主那里得到了表达。尽管如此,人民主权理论是缺乏根基的,而民主的结果就是无序和无政府状态。解决这些疾病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在历史中得到奠基的、按照神意被构建出来的权威。在政治领域中,这就意味着重新恢复基督教君主制;而在宗教领域,这就意味着接受永远正确的教皇的最高的、唯一的主权。人类的本性决定了人类是必须被管理的,绝对的权力是无政府状态唯一的真正替代选项。“我从未说过绝对的权力—无论它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不会带来严重的不便。相反,我明确承认这一事实,没有想要弱化这些不便。我只是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两道深渊之间。”绝对权力的运行在现实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政治主权都是或应当是以教皇的法权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教皇有权从宗教和道德的视角出发来评判这些政治主权的活动。 德·迈斯特最著名的就是他对教皇至上论和教皇无误论的坚持,他的这种坚持远远早于对教皇无误论进行了界定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尽管如此,这种坚持并没有被所有与他一样敌视大革命、渴望重新恢复君主制的人们所接受。他对政治宪法和传统价值的某些反思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反思不乏近似之处。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论教皇》的作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 3.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的是德?博纳尔德(Louis Gabriel Ambroise, Vicomte de Bonald,1754—1840)。他曾经是皇家卫队的军官,而且还在1790年成为立宪议会的成员。但在1791年,他移居国外并且生活在困顿当中。1796年,他在康斯坦茨发表了《论公民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Théorie du pouvoir politique et religieux dans la socitété civile)。在回到法国后,他对拿破仑表示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有能力实现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但是当复辟之后,他开始支持君主制。他在1800年发表了《对社会秩序之自然法的分析性评论 》( Essai analytique sur les lois naturelles de l’ordre social)。在这之后出版的是1802年的《原初立法》(La législation primitive)。他的其他作品还有1818年的《有关道德知识之首要对象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premiersobjets des connaissances morales)和1827年的《对社会构成原则的哲学证明》(Démonstration philosophique du principe constitutif de la société) 我们不时会听到德·博纳尔德拒斥一切哲学这种说法。但这一陈述并不符合事实。的确,他强调社会的宗教基础是必要的,而且他还把这种必要性和哲学作为社会根基的不足拿来做对比。在他看来,“正如意志和行动的同时性对于构成人的自我来说是必要的”,宗教和政治社会的统一“对于构成民事主体或社会机体来说是必要的”,而哲学则缺乏执法赏罚的权威。同样真实的是,他不断思考着前后相继的、彼此冲突的体系,并做出了“欧洲……仍然在等待一种哲学”的结论。但与此同时,他对一些哲学家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推崇。例如,他认为莱布尼茨“也许是在人类中出现的最为全面的天才”。而且,他还区分了理念或概念之人(men of ideas or concepts)和想象之人(men of imagination),前者自柏拉图以降“致力于启世人之蒙”,而后者[如培尔(Bayle)、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卢梭]则使人误入歧途。把培尔和狄德罗这样的作者描述为想象之人似乎有些奇怪。实际上,德·博纳尔德所说的想象之人并不是指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而是指那些全部观念都派生自感觉经验的人。例如,当孔狄亚克谈到“变化了的感觉”时,这种说法可能会诉诸想象力,而后者可以随意描绘出各种变化和变动。“但是,当这种变化被引用到心灵的行动上时,它无非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空洞词语。而且,孔狄亚克本人会因为不得不对其做出令人满意的应用而感到羞愧。” 按照德·博纳尔德的理解,想象之人一般而言是感觉论者、经验论者和唯物论者。理念或概念之人主要是那些相信天赋观念并且要追溯这些观念的最终来源的人。因此,柏拉图“宣扬由最高理智置入我们心灵之中的天赋观念或普遍观念”,而亚里士多德“则使人的理智蒙羞,因为他认为观念只有通过感官的中介才能进入心灵之中”。“法国哲学的改革者是笛卡尔。” 德·博纳尔德的确提到,在《旧约》时期的犹太人和其他充满活力的民族(如早期罗马人和斯巴达人)那里并不存在哲学。而且他还从哲学史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家们无法为他们的种种思辨找到任何可靠的基础。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我们因而就要对哲学感到绝望并彻底拒斥哲学。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作为可靠出发点的“绝对原初的事实”。 德·博纳尔德当然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哲学寻找可靠基础的人。但有意思的是,他是在语言中发现他的“原初事实”的。因为哲学总体而言是“关于上帝、人和社会的科学”e,所以被寻求的原初事实必须是人和社会的基础,而语言就是这个基础。语言看似不可能是一个原初事实。但在德·博纳尔德看来,人类是不可能发明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的,因为动用了普遍概念的思想就是以某种语言为前提的。换句话说,人如果想要表达思想就必须已经是一个使用语言的存在者。语言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同样,人类社会也是以语言为前提,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社会。 德·博纳尔德将符号性表达视为人的一个根本特征,这种看法在今天并不会让人们感到惊讶,尽管它依然会引发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过,他接着宣称,人是在获得自身存在的同时收获语言这种恩赐的,因此,“在人这个物种产生之前就必然已经存在着这一奇妙结果(即语言)的第一因,也就是一个在理智上高于人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高于我们所能知道甚至想象的一切事物。人正是从这个最高存在者那里收获思想、收获语词的……”换言之,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如果人需要言语来学习思考,而他又只能在可以思考的前提下构造言语,那么他是不可能发明语言的。而这个事实正好可以充当上帝存在证明的基础。 当然,我们既没有必要指责德·博纳尔德忽视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没有必要指责他忽视了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发明了语言表达这个事实。他的论点是,如果我们把人描述为“首先发展出了思想,然后又发明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做法肯定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虽然现实的思考并不意味着要放声说出语词,但它已经动用了符号表达。因此,当德·博纳尔德反对将思维和语言截然分开时,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对思想和语言之间关系的论述能否作为证明上帝存在的依据则是另一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我们有关世界中具体事物的观念依赖于感官经验,但有一些基本概念(例如“上帝”)和基本原则或真理,它们代表的是上帝对人的原初启示。由于如果没有语言,这种启示就无法被掌握或化用,而人类自己又发明不出语言,所以它(语言)必须是上帝在创造人类时给予人类的一种原初礼物。德·博纳尔德显然认为上帝直接将人创造为使用语言的存在者,而我们则可能是在进化论的框架中进行思考的。 德·博纳尔德的社会哲学在如下意义上是三位一体的,即:他认为“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三个位格”。在宗教社会中存在着上帝、他的牧师和子民,子民获得拯救是上帝和牧师之间关系的目标。在家庭社会中存在着父亲、母亲和孩子。在政治社会中存在着作为权力代表的国家首脑、他的官员、人民或全体公民。 现在,如果我们追问,在家庭中权力属于父亲是否是协议或契约的结果,对德·博纳尔德而言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权力自然地属于父亲并且最终来自上帝。同样,在政治社会中,主权属于君主而不属于人民,而且这种归属是出自本性的。“公共权力的确立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强迫的,而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它是符合社会中存在者的本性的。而且,它的原因和起源都是自然的。”这种观点甚至适用于拿破仑。这场革命既是长期弊病积累的结果,也是社会试图恢复秩序的努力的结果。一个能够从无政府状态中恢复秩序的人必然应当掌握权力,这因而也是自然的。拿破仑就是这个人。 和德·迈斯特一样,德·博纳尔德坚持权力或主权的统一。主权必须是唯一的、独立的、明确的或绝对的。而且主权也必须是持久的。德·博纳尔德从这一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必要性。然而,他的思想的独特之处是他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以及原初的神圣启示(这种启示是宗教信仰、道德和社会的基础)以语言为手段得到传播的理论。这种原初启示之传播的理论是如何与德·博纳尔德对天赋观念理论的热情协调一致的,也许还不太清楚,但他大概认为先天观念是化用启示的必要条件。 4. 德·迈斯特和德·博纳尔德显然都是传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精神并坚持法国古老的政治和宗教传统。不仅如此,德·博纳尔德还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主义者,因为他捍卫传统或原初启示之传承的观念。他们都对启蒙哲学进行了抨击(尽管德·迈斯特做出的谴责更加全面和彻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反理性主义者(anti-rationalists)。尽管如此,他们严格说来并不能被单纯视为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的代表,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立场提供了合理的辩护,而且在对18世纪思想进行攻击时诉诸理性。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弗朗索瓦—勒内·维孔特·德·夏多布里昂子爵(Fran?ois-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相当不同的侧重点。曾经接受过百科全书派哲学教育的夏多布里昂在大革命期间流亡。他在伦敦期间撰写了《从历史、政治和道德出发论革命》(Essai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moral sur les révolutions,1797)。 在这部著作中,他接受了18世纪哲学家对基督教及其神意和不朽学说提出的有力反驳,并进而主张一种历史循环论。在历史的循环中,各种事件基本上都在重复发生—尽管涉及的人物和环境当然不同。因此,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将带来永久利益的全新开端是毫无根据的。从根本上说,它不过是重复了之前的革命。进步的教条是一种幻象。 夏多布里昂后来—无疑是正确地—宣称,尽管他曾经拒绝基督教,但他仍然保留了一种宗教本性。总之,他被基督教所吸引,并且于1802 年出版了他的名著《基督教真谛》(Génie du Christianisme)。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基督教的美”(“Beauté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精神,因为作者在书中最为强调的就是基督教的审美品质。“其他所有类型的护教都已被穷尽,它们在今天甚至毫无用处。现在,除了那些无须被说服的虔信者和已经被说服的真正基督徒之外,谁还会去读神学著作?”人们与其诉诸风格陈旧的护教学,不如努力证明“基督教是所有现存宗教中最富有诗意、最人性化、最有利于自由和文学艺术发展的”b。 这种说法会让人们觉得,夏多布里昂试图证明:基督教为“真”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美”的,就在于它的信仰可以抚慰人心,就在于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是基督徒。有些人可能会不赞同这种关于基督教之美的观点,除此之外,这种观点还会招来如下反对意见,即:基督教的审美品质和抚慰人心的品质并没有证明它的真理性。如果但丁和米开朗琪罗是基督徒,这除了揭示了一些关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的事实之外还说明了其他什么东西吗?如果“复活”和“天堂”的教义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这能证明它们是真的吗?就此而言,夏多布里昂被指责为非理性主义或“以审美满足的诉求代替理性论证”就不难理解了。 的确,在夏多布里昂那里,被人们用来证明基督教之可信性的传统哲学论证下降到了一个完全从属的位置上。他所强调的主要是审美层面上的考虑、感情和内心的理由。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他想到的是这样一些基督教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是令人反感的,基督教妨碍了道德意识的发展,它不利于人的自由而且是反文化的,总而言之,基督教起到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精神的束缚和扼杀。夏多布里昂明确表示,他不是为那些“从不寻求良好信仰所蕴含的真理”的“智者”写作,而是为这样一些人写作:他们由于受到智者误导而相信基督教是艺术和文学的敌人,是一种对人类幸福有害的、野蛮的、残酷的宗教。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诉诸人身论证(argumentum ad hominem),目的是表明基督教不是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5. 一个更有意思的人物是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1782—1854)。出生在圣马洛的拉梅内年轻时曾是卢梭的追随者,但他后来很快重拾了基督教信仰。当德·博纳尔德的《原初立法》在1802年问世时,这部著作给拉梅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09年,他发表了《对法国教会在18世纪的状况及其当下境遇的反思》,呼吁复兴教会。1816年,他被任命为瓦讷的牧师。1817年,他发表了《论对于宗教问题的漠不关心》(Essai sur l’indifférence en matière de religion,1817—1823)的第一卷。这部著作马上给他带来了基督教护教士的名声。 在《论对于宗教问题的漠不关心》的第一卷中,拉梅内坚持认为,在宗教、道德和政治领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我们可以对其持漠不关心态度的。“被视为灵魂的一种恒常状态的漠不关心不但与人性相冲突,而且还会摧毁人的存在。”这一论题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的:人没有宗教就不能发展为人,宗教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它是道德的基础,社会没有 宗教就会退化为试图扩张自身利益的人的集合。换言之,拉梅内一方面坚持强调宗教的社会必要性,另一方面对于在18世纪广泛传播的一种信念表示拒斥,即:伦理道德完全可以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实现自立,没有宗教并不会妨碍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针对这种观点,拉梅内宣称,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人们当然可以主张说:即使普遍的漠不关心是不可取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宗教信仰的所有方面都具有社会重要性和相关性。然而,根据拉梅内的说法,异端为自然神论铺平了道路,自然神论为无神论铺平了道路,无神论又为彻底的漠不关心铺平了道路。因此,这是一种一揽子交易。 拉梅内对宗教的重视看上去似乎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仿佛宗教信仰能够得到辩护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的社会效用。但这种看法并没有充分说明他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他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有其用处的建制,它在这种意义上成为普通人的必需品。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不仅有用,而且还是真理。事实上,它们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们是真理。因此,对拉梅内来说,人们没有理由去选择异端。 困难在于拉梅内如何能够证明,基督教教义是一种超越了纯粹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真理的真理。在他看来,由于我们的理性思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甚至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所以它不能产生确定性。我们当然可以声称自己能够从自明的真公理或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出结论。但事实上一个人眼中的自明真理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拉梅内为什么要拒绝一切将宗教还原为“自然”宗教或哲学宗教的企图。但如下问题仍然存在:他打算通过何种方式展示启示宗教的真理? 拉梅内坚持主张,克服怀疑论的方法不是相信某个人的私人推理,而是相信人类的普遍赞同。因为这种普遍赞同或共同情感(sentiment commun)才是确定性的基础。无神论是错误哲学和遵循个体私人判断所导致的结果。只要对人类的历史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对上帝的自发信仰是所有民族的共同之处。 即便抛开拉梅内的主张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这个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如果他想要表达的是大多数人都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得出了“上帝存在”的结论,那么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所谓的普遍赞同就等同于个人得出的结论的集合,人们就会质疑拉梅内如何能够表明普遍赞同要比个人通过推论得出的结果具有更高程度的确定性。拉梅内实际上诉诸了传统主义理论。例如,我们之所以知道“上帝”一词的意义,是因为它属于我们已经习得的那种语言,而且,这种语言从根本上说来自一个神圣起源。“那么,必然是第一个人把它们(亦即某些语词或概念)传递给了我们,而且他自己是从造物主口中获得它们的。因此,我们在上帝那不可错的话语中找到了宗教的起源,以及保存了神圣话语的传统的起源。” 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我们是依靠权威知晓了宗教信仰的真理,而且一切存在的宗教事实上都是启示宗教。通常所说的自然宗教实际上是启示宗教,而且它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人类在未被错误的推理败坏和引入歧途时认为“人始终有义务服从他可能知道的最伟大的权威”。人类对于上帝存在的普遍赞同表现了对于原初启示的接受,而对于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则表现了对上帝在耶稣基督之中并通过耶稣基督做出的进一步启示的接受。 这种理论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我们在此无法对它们加以讨论。我们必须转而对拉梅内的政治态度进行讨论。鉴于他在宗教领域中对权威的强调,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会像德·迈斯特和德·博纳尔德那样强调君主制的作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拉梅内仍然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他也表现出了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他在《论宗教—以它和政治秩序、世俗秩序的关系为着眼点》(De la religion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ordre politique et civil)中宣称,虽然现实中的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被恢复的君主制是“对过去的珍贵纪念”。的确,“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的原初绝对主权这一无神论教条的基础上的”。但拉梅内对国家现状的反思并没有将他引向对于绝对君主制的追求,而是使他走向了教会中的教皇至上论。在当代法国,教会不仅得到了容忍,而且还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持。但是,国家的这种资助却对教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它倾向于把教会当成国家的一个部门,而这会妨碍教会自由地渗透国民的生活并将其基督教化。只有强调教皇的最高权威,才能防止教会成为国家的附庸,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具有普遍使命这个事实。对于君主制,拉梅内则有所疑虑。他在《论革命进程与反对教会的战争》(Du progrè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guerre contre l’église,1829)中指出:“由于加利刚主义(Gallicanism),人的力量在君主制末期成为真正的偶像崇拜的对象。”虽然拉梅内仍然认为瓦解了社会秩序的革命是基督教的敌人,但他开始相信问题始于绝对君主制的兴起。正是路易十四“把专制当成了国家的基本法”。法国君主制通过使教会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削弱了教会的生命力。而且,如果神职人员出于对国家的庇护和保护这种表面上的保障的渴望而默许教会成为后革命、后拿破仑国家的附庸,那么这将是灾难性的。只有明确承认教皇的权威才能为教会提供保障。 尽管拉梅内不断对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抨击,但他已经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包含着一个宝贵的因素,也就是“基督教国家固有的对自由的不可战胜的欲求,因为基督教国家不能容忍任意妄为的或纯粹属人的权力”。1830年的革命使他确信,不能依靠君主来恢复社会。必须接受民主国家的现状,确保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并在教会内部坚持绝对正确的 教皇的最高权威。换言之,拉梅内把对于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理念的接受和在教会内部对于教皇至上论的坚持结合了起来。然希望教会能够在基督教化的社会中取得成功,但他逐渐相信,除非教会放弃国家的一切资助和特权地位,否则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拉梅内在1830年创办了《未来报》(Avenir)。这份报纸支持教皇的权威和绝对正确,而且表示接受当时的法国政治制度与政教分离。它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如蒙塔朗贝尔伯爵(Comte de Montalembert,1810—1870)和著名的多明我会传教士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尔(Henri-Dominique Lacordaire,1802—1861)。但《未来报》所提出的观点绝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能接受的。拉梅内试图获得教皇额我略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的认可。但在1832年,教皇发布了一封通谕信(Mirari vos),谴责漠不关心主义、良知自由和政教分离学说。这封信里并没有提到拉梅内的名字。尽管教皇对漠不关心主义的谴责可以被视为对拉梅内早期的《论对于宗教问题的漠不关心》(Essai sur L’indifférence)的认可, 但《未来报》的编辑显然受到了通谕的影响。 1834 年,拉梅内发表了《一个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他在书中支持所有受压迫和受苦难的人民和群体,并主张所有人享有完全的良知自由。事实上,他赞同在宗教背景下被解释的关于革命、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1834年6月,教皇额我略十六世在给法国主教的信中谴责了这本书,但拉梅内当时已经和教会相当疏远。在两年后的《罗马事务 》(Affaires de Rome)中,他放弃了通过君主或教皇来实现社会秩序的想法。他已经成为人民主权的信奉者。 在后期的著作中,拉梅内认为具有组织形式的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但他仍然认为,如果宗教被视为存在于人的内心当中并且将人的内心与上帝和他人联系起来的神圣元素,那么宗教就是有效的。1840年,他发表了一本针对政府和警察的小册子并因此被判处一年监禁。在1848年革命后,他被选为塞纳省的代表。但在拿破仑三世掌权后,拉梅内退出了政坛。他于1854年去世。他在去世前没有与教会达成任何正式的和解。 6. 从广义或宽泛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些人称为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对其国家宝贵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传统的灾难性攻击,并且主张恢复这些传统。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即人们在叙述大革命之后几十年的思想史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传统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人类的精神和文化发展与福祉所必需的那些基本信仰并不仅仅来自人的理性思考,它们源自上帝的原初启示,并通过语言媒介代代相传。显然,广义的传统主义并不排除狭义的传统主义,但前者并不包含后者。毋庸赘言,某个法国人完全可以在支持恢复君主制的同时不诉诸原初启示理论,不对哲学证明的有效范围加以限制。同样,接纳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主义理论而不要求恢复旧制度(ancien régime)同样是可能的。两种意义上的传统主义可以并行不悖,但它们却并非密不可分。 由于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主义既抨击启蒙哲学又强调神的启示,而且还倾向于教皇至上论,所以它初看上去似乎会得到教会权威的高度接受。但是,尽管教会至上论的倾向肯定会得到罗马教廷的赞许,但传统主义哲学却招来了教会的责难。通过指出某种18世纪哲学在前提或论证上的问题来对其加以攻击完全没有问题,这事实上还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以人 的理性无法获得确定无疑的真理为由来攻击启蒙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上帝的存在只有依靠权威才能为人所知,那么人们是如何知道权威具有可信性呢?就此而言,第一个人是如何知道被他当作启示的就是启示本身呢?如果人的理性像立场更为极端的传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无力,a那么人们怎样才能证明基督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明 白为什么教会权威虽然同情传统主义者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攻击,但却并不热衷于那些使教会的主张除了人的赞同外得不到任何理性支持的理论。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对此做出说明。拉梅内《论对于宗教问题的漠不关心》的第二卷对《基督教哲学年鉴》(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的创办人奥古斯丁·博内蒂(Augustin Bonnetty,1798—1879)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内蒂在《基督教哲学年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开始理解整个宗教是基于传统,而不是基于理性思考。他的总论点是:启示是宗教真理的唯一来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神学院中盛行的经院哲学是异教理性主义的表现,后者败坏了基督教思想,并最终在启蒙运动的破坏性哲学中结出了果实。1855年,禁书审定院(Congregation of the Index)要求博内蒂支持“人的理性能够以确定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灵魂的属灵性和人的自由”“理性思考会导向信仰”“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所使用的方法并不会导向理性主义”等一系列论点。欧仁·玛利·博坦(Louis Eugène Marie Bautain,1796—1867)已经在 1840 年对一系列类似的主张表示支持。 读者很可能会想到,尽管教会权威强制人们接受“上帝的存在可以在哲学上得到证明”这一论点,但这无助于说明这种证明是如何被完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教会站在了博内蒂所认为的理性主义一边。而且,1870 年举行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教皇至上论的胜利)就此问题发表了明确的声明。至于法国只有通过与教会结盟恢复君主制才能再生这种一般观点,它是通过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发起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aise)找到新的生机的。但莫拉斯本人和他的一些亲密伙伴一样是无神论者,而不是像德·迈斯特或德·博纳尔德那样的信徒。而且,如果他那种利用天主教达到政治目的的犬儒主义企图最终导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谴责,这显然不足为奇。顺便说一句,在《论对于宗教问题的漠不关心》中,拉梅内认为,把宗教视为一种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有用的工具也是一种漠不关心。 ◎广阔的思想史视野 本书以其详尽的内容在哲学史界占据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力图破除哲学简史类书籍对哲学家、哲学思想漫画式的理解,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哲学史上耀眼的“明星”哲学家们及其哲学思想,还对那些通常被史书忽略的哲学家们给予一定关注。 ◎细致的哲学流派谱系研究 科普勒斯顿以深厚的学养勾勒出各哲学体系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联系,试图以“永恒哲学”的原则完成历史材料的挑选工作,提供连贯而有意义的哲学历史解释。 ◎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引用 作为一本以“成为教科书”为目标的哲学史,其中广泛吸纳了各种古代、近代、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鼓励学生在学习哲学史之后去阅读哲学原典,拿起书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