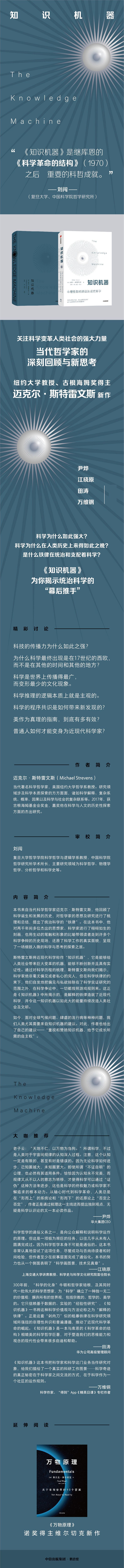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3.10
折扣购买: 知识机器
ISBN: 9787521743388

迈克尔·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当代科学哲学家,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到科学本质探索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解释、复杂系统、概率、因果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复杂联系等。2017年,斯特雷文斯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以嘉奖他在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性探索方面的杰出研究。
如果你穿越到人类历史上某个随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那你很可能会住在一个没有家具的潮湿的洞穴里,靠捡拾小如针头的谷物,以及用一根一头削尖的木棍狩猎猛兽维持生活。 不过要是你非常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穿越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穿着希腊世界的富人才能拥有的凉鞋。依靠这种特权地位,你可以享用差不多所有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有价值的文化发明。你可以从荷马和萨福的诗歌中获得快乐,去剧院观赏《俄狄浦斯王》和其他古典戏剧杰作,然后雇一位音乐家在晚餐后为你的朋友们演唱小夜曲。你生活的城市可能受到法律和法院体系的约束,由创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中某些杰作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一手建造,并由沿用至今的政治模式(君主制、寡头制、运转平稳的民主制)治理。如果你有天赋和意愿,你还可以从事几何学或哲学方面的高级研究。 而你很快就会注意到,这片文化乐土上缺少了一些东西。这里既没有传播速度比最快的马还要快的X射线和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也没有让生活在百里香香气中的地中海人了解世界大事的音视频报道。最令人震惊的是,这里没有让我们的先进医学、运输和通信技术成为可能的东西,也就是被称为近现代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器。 文明始于几千年前,但这台机器却直到几百年前才出现。怎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呢? 古代人并不是不想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大约在前580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港口城市米利都眺望着蔚蓝的爱琴海,看到大海与天空在夏日的薄雾中融为一体,于是提出万物最终都是由水构成的。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几十年后,住在西西里岛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而与此同时在米利都,我们同样不太了解的泰勒斯的另一位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万物都由潜能无限的无形物质组成,他把这种物质叫作“阿派朗”(apeiron),也就是“无限”的意思。 尽管这些思想家、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后继者—包括中国学者、伊斯兰教大师、中世纪的欧洲修士—都巧妙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但这之中却没有一种观点能脱颖而出,打败其他所有观点。尽管他们探索了大自然的深层结构,也提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极具智慧的原始假设,但他们对于知识的储备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原因很简单。尽管前现代的自然研究有时也会提出正确的想法,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让自己的想法脱颖而出。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的时候,有关地球、行星和太阳之间关系的几乎所有可能的假设都已经被提出了:行星和太阳围绕着固定的地球旋转,或者地球和行星围绕着固定的太阳旋转(由古希腊哲学家阿利斯塔克在前3世纪提出),又或者部分或所有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而太阳又围绕着地球旋转(这个想法通过古罗马作家传给了中世纪的哲学家,后又于15世纪在印度被独立提出)。然而,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1 000年之后,人们才在这些理论中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而且不久之后就明确了最终的结论。 这次巨大的突破发生在1600年至1700年这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当时,经验主义探究从过去随心所欲的猜测热潮,演变为在全新的层面上展现出发现力的研究方法—知识机器。驱动这台机器的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过程,它会利用观测得到的证据对理论进行无情的“拷问”,支持某些理论,并推翻其他的理论。尽管偶尔会出现偏移或者倒退,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还是会取得明显的进展。在泰勒斯曾经观察过地平线和海水的地方,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在外太空看到了暗物质。 正是为了纪念这种新发现涌现的速度与发现方式上的突变,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科学革命”,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则把革命取得的成果当作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这样,他们就把“近现代科学”与之前的古代以及中世纪科学(有时为了强调显著的不连续性,也称其为“自然哲学”)区别了开来。在科学革命之前,自然哲学的创造性并不逊于近现代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推动下,它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同样重视感官方面的证据。不过,似乎还是缺少了某个特殊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特殊的东西迟迟未能到来呢?在哲学、民主制度和数学接连闯进古代思想家的意识之门后,科学为何还徘徊在起点?为什么不是古巴比伦人将零重力观测站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不是中国汉族人在黄河沿岸的平原上制造出粒子加速器,不是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种植出转基因玉米,也不是古希腊人研制出流感疫苗并完成心脏移植呢? 像革命、选举、宣言和解放这样的事件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了。但是像“科学方法尚未出现”这样令人失望的事情却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近现代科学并没有出现在民主制的雅典,没有被亚里士多德发明出来。它也没有出现在 1 000年前的中国,尽管当时的中国有凝聚力,具有学术传统,也具有技术方面的实力。古时的伊斯兰医学和欧洲医学都没能成功地发展为真正的科学。至于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还有高丽王朝和柬埔寨的高棉帝国,以及先后建立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我们视他们的庙宇和金字塔有如奇迹,也为他们多姿多彩的戏剧和舞蹈传统而惊叹,但是这些富饶、强大而精深的文化也都不是科学的发明者。 因此,科学长期的缺位不能通过一连串特定的事件,或者风俗与环境间某种特定的组合来解释。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神权政体,东方还是西方,泛神论者还是圣书之民a,都没有孕育出科学。似乎是科学本身的某些性质让全世界的人类都难以接受。 我认为答案就是:科学是一种陌生的思想形态。要理解它为何在人类活动领域中姗姗来迟,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方法固有的陌生性。 1. 颠覆范式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革命性,揭示了塑造了近现代科学与现代世界的铁律。作者在书中回望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历程,找出了科学的“铁律”。这是当代科学哲学家对于人类智识的深刻总结,是足以比肩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后的思想性陈述,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型,告诉我们为什么近现代科学成为不断创新并具有实证性的知识机器,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 2. 作者重磅。作者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也是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3. 中文译稿特别邀请刘闯教授审校。刘闯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史等,在国际科学哲学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 学界与企业界联袂推荐。推荐人尹烨、江晓原、田涛、万维钢。本书对于科学界、思想界乃至业界的广泛启发意义。重新理解科学的结构与逻辑,发现其深层的动力源泉。最后,思考如今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利用科学(即知识机器)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