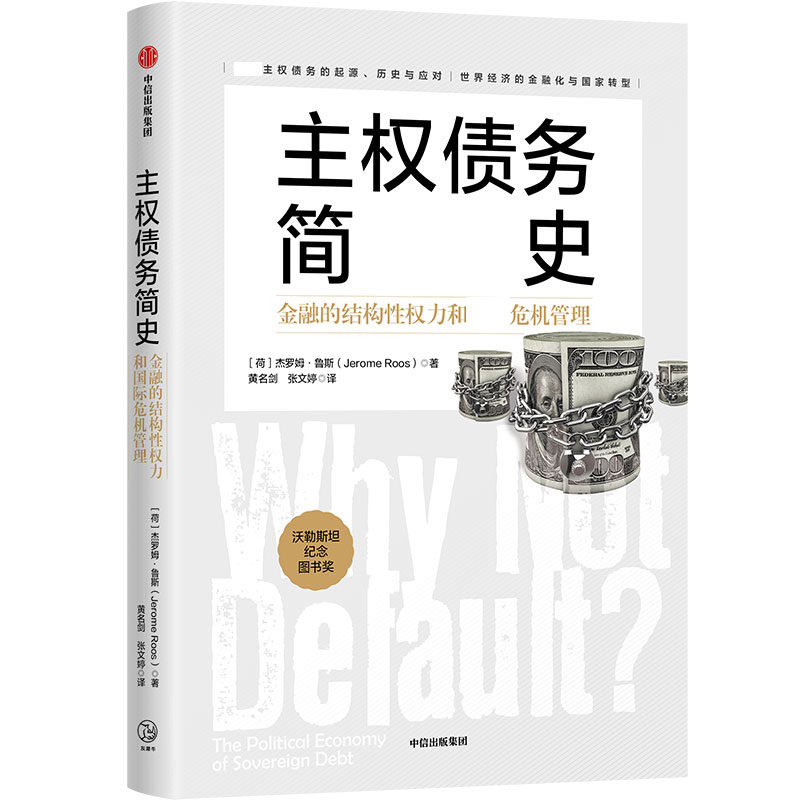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0.70
折扣购买: 主权债务简史: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危机管理
ISBN: 9787521721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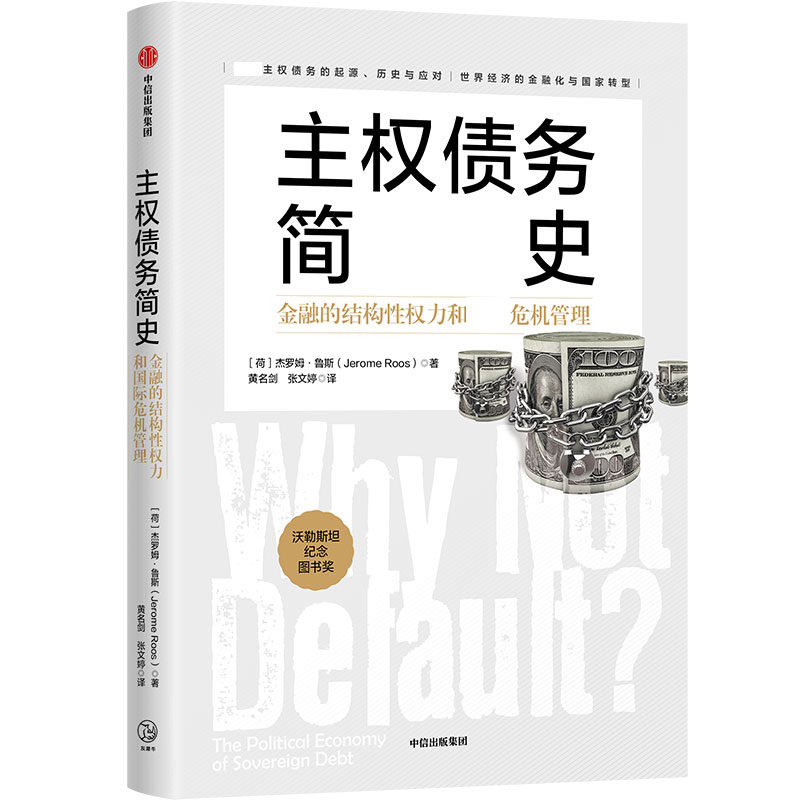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LSE研究员。他经常为各种国际媒体提供有关世界政治和时事的评论。它为我们提供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债务危机的全新视角,展示了全球经济的转型如何导致国际和国内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
富人获得贷款,穷人获得债务。 墨西哥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成功避免了单边违约和早期多边债务重组的国际债权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上毫发无损,甚至获得了巨大收益。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国际上对债务危机的反应并非为拉丁美洲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主要为债权人和主要的华尔街货币中心银行的利益服务。的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全球南部作为一个整体,稳步向全球北部进行资本净输出,发展中国家向国外支付的还本付息费用比它们从新的外国贷款和投资获得的回报多 520 亿美元。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外债比率和还本付息费用总额在 20 世纪 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都有所上升,尽管认真偿还债务和布雷迪协议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使这些数值在 1987 年后 下降。 除了高度不对称的国际维度外,债务国内部调整成本的分配也非常不均衡,因为国内精英阶层和富裕公民成功地将偿还债务的负担转移到社会中特权较少的阶层身上。在墨西哥,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连续的结构调整方案下付出了特别沉重的代价,而富裕的国内精英阶层通过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摆脱了通货膨胀、连续贬值和高税收的影响。1983—1987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93.1%,1988年达到177%,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工资控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这使得平均生活水平在过去的十年里急剧下降。1983—1988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下降 5%,而实际工资则下降 40%~50%。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从 1982年的35.9%下降到 1987年的 26.6%。 这种对穷人生计的侵蚀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结构调整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偏见。例如,曼纽尔·帕斯特找到了证据,表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和基金扩容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持续大幅下降”。后来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 策条件对再分配的影响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墨西哥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危机开始前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在危机期间下降了 66%。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个四口之家需要 4.8 倍的最低工资才能满足基本需求,但现在 80% 的家庭必须靠 2.5 倍的最低工资或更低的收入生活。因此,营养不良的现象在穷人中蔓延开来。官方债权人最终认识到了危机带来的不公平结果:例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承认,“大部分负担是由债务国的工薪阶层承担的”。一项评估世界银行明确提出的减贫目标的内部研究得出结论:“贫困问题很少在这类对话中作为突出问题,对结构调整方案的分析也很少考虑谁将承担最沉重的调整负担。” 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对墨西哥的穷人来说代价高昂,但对富人来说是恩惠。1982年银行国有化失败实际上有效地将银行家的“负债”社会化了。到1988年,收入前10%的人群设法向国外转移了640亿~ 800亿美元(或更多)资金,其中大部分资金在外国投资(如股票、债券和存款利息)中获得了利润。这允许墨西哥富人“在频繁的货币贬值最大化精英阶层的购买力时,利用这些资产的收入将资金转换回墨西哥比索来获益”。根据一项估计,回流到当地富裕精英手中的资本外逃的利息约占债务总额的40%,这些私人利润不用被墨西哥政府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坚持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贷款先决条件非但无助于阻止资本外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随着工资的下降,私人利润猛增,而对外汇市场的控制和危机中期异常的股市繁荣为精英阶层提供了充足的投机机会。最后,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所总结的那样,“富人获得贷款,穷人获得债务——这并不是太过简单的 说法”。 因此,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结果与20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形成鲜明对比。首先,战前债券融资较低的债务集中度和分散的贷款结构使债权人协调困难,削弱了市场规则的力量。债券融资被债务集中度高、信贷结构相互关联的银团贷款所取代,从而降低了债权人的协调难度,使信贷中断的威胁更加可信、更具破坏性。其结果是促成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债权人卡特尔,并大幅增强市场规则的权力。其次,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没有国际官方债权人和积极的国家干预,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了积极的 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行了国际官方债权人、财政规则执行者和债权人卡特尔协调员的职能,使债务人保持偿债能力,同时迫使它们采取最大限度偿还债务的政策。最后,来自底层的压力和大萧条时期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后者曾鼓舞民族民粹联盟,使大都市银行家联盟边缘化——被政府对信贷的日益依赖和 20 世纪 80 年代相对温和的反紧缩对抗所取代,加强了银行家联盟及其技术官僚盟友的权力,他们被认为对外国债权人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能够以更好的条件吸引信贷,从而在经济决策中获得特权地位,将规则内化至国家机 构中。 20 世纪 30 年代的普遍条件增加债务人在全球金融中的自主权,最终导致单边违约,以及紧随其后的债务人主导的激进重组。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条件则减少了债务人的回旋余地,导致债权人主导的软重组,从而使调整成本的分配更加不均。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结果表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国际权力平衡(赋予货币中心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相对于外围债务国的权力)以及金融精英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国内权力平衡(赋予债务国中对外国债权人起桥梁作用的社会群体以权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种潜在权力关系的转变解释了为何 20 世纪 80 年代没有显著的单方违约,而不像 20 世纪 30年代那样普遍单方违约。正如曼纽尔·帕斯特在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结束时总结的那样,“如果不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任何更激进的提议(全部或部分拒绝偿还债务,限制债务偿还,或动用当地精英的外国财富)都不会被采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来看看权力重新分配显然确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权力的重新分配对该国偿还外国债券持有人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的意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主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危机管理的广泛历史比较调查,回答了经济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债务累累的国家即使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仍然会继续偿还外债?我们如何解释大萧条之后如此高的债务人履约程度?为什么金融市场是一个“全球超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直至解除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三驾马车中的尴尬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不断演变的作用? 本书意在发展在主权债务危机中金融结构性权力的一种动态理论,解释债务人的抵制和社会及政治结果的变化,揭示私人债权人和官方债权人权力实际运作的确切机制,以及这种权力产生效力和失效的确切条件。同时作者提出了债务人履约的三种执行机制,识别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三个具体发展特征,之后回顾和复盘了各主权国家的偿债和违约历史,最后重点介绍了墨西哥、阿根廷和希腊的特殊案例。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观点:主权债务问题有社会和政治属性,“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富人获得贷款,穷人获得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