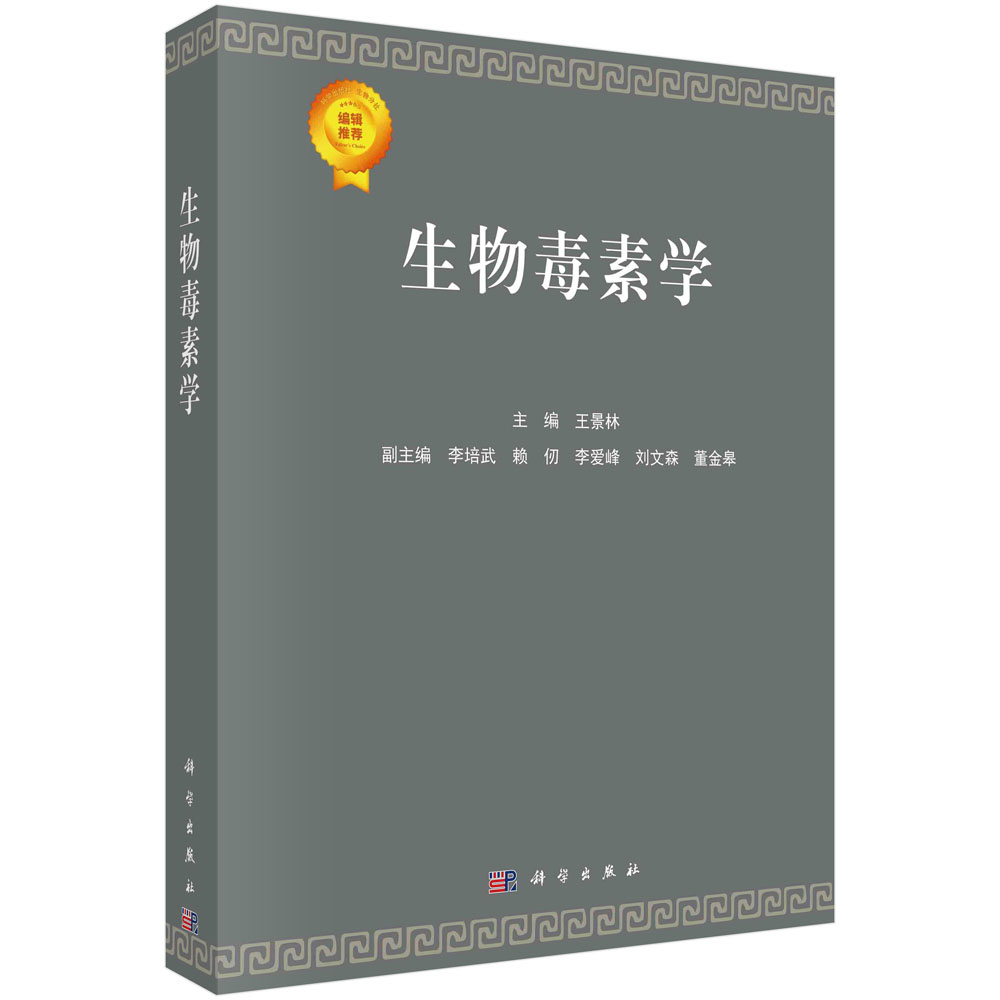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698.00
折扣价: 551.50
折扣购买: 生物毒素学
ISBN: 9787030689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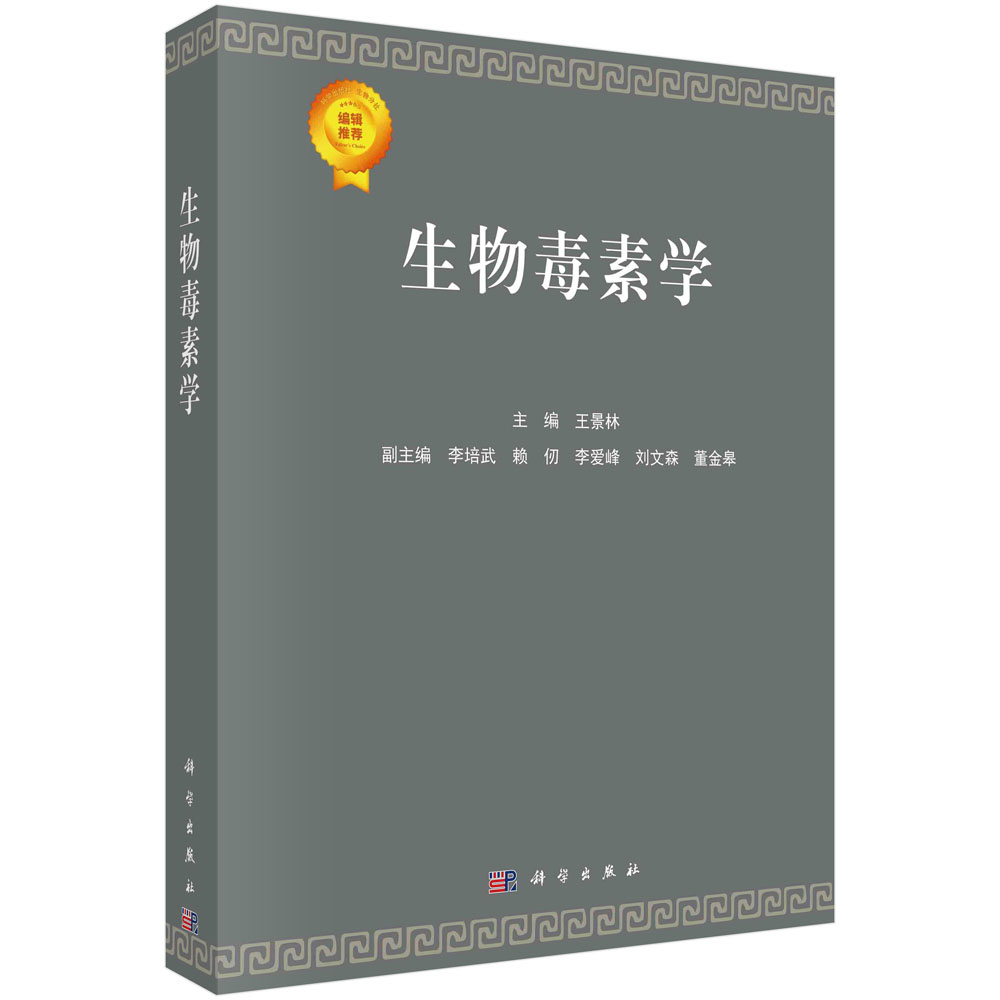
绪论生物毒素
引言
生物毒素(biological toxin/biotoxin)广泛存在于陆地、湖泊和海洋的动物、植物与微生物中。动物的储毒器官是腺体或特殊组织,植物的贮毒或有毒物质的富集器官是种子、根叶和植株等,微生物毒素则是由染色体或质粒编码产生并储存在细胞中。人类对生物毒素的认识、研究与利用源于古人在寻找食物和药物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误食中毒甚至死亡的教训,慢慢积累了经验,从漫长的感性认知逐渐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不但学会鉴别有毒动植物,避免误食中毒,还学会以毒攻毒,治疗疾病。甚至还学会将动物或植物的毒液涂抹在箭头上制作毒箭,以猎杀动物获取食物,或在战斗中作为特殊武器射杀敌人。我国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镞”就是古人使用的一种毒箭。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著人使用毒箭狩猎也有数千年的历史。 1536年,意大利学者 Autonio Pigafetta出版的书中描述:“一名白人士兵在 Pitagoman行走时被当地土著人射来的毒箭所杀”。1859年,东印度群岛的土著人在与英军交战时,就手持涂有箭毒木(Antianris toxicaria)树皮毒液的毒箭,射向英军,很快导致英军士兵倒地身亡,其杀伤力令英军惊骇万分。
伴随毒箭的制作与使用,人们也开始研究治疗箭毒的方药,因此发现了一些毒物的药用价值。如汉代《马王堆医书》记载的“毒乌嚎”就是治疗箭毒中毒的方药。唐代的《日华子本草》中记载:“土附子 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填、晒干取膏,名为射罔,猎人作毒箭使用;中(毒)者,甘草、蓝青、浮萍、芥痆等皆可御也。”马钱子是制作箭毒的有毒植物之一,我国古代中医对马钱子毒性和药性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无毒”到“有毒”,再到“大毒”的逐步认识与不断发展的过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谓马钱子为“苦寒、无毒”,李中立的《本草原始》中则载“味苦、寒,有大毒”,之后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言其“有毒”。清代张锡纯著《医学哀中参西录》指出“其毒甚烈,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功远胜于它药”。1925年以后,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开始用箭毒治疗肌肉张力亢进症和痉挛症;后来又有人将箭毒作为肌肉松弛剂,成功地用于外科手术的浅麻醉。
1888年,人类发现了**个细菌毒素 ——白喉棒状杆菌的主要致病因子白喉毒素(diphtheria toxin),从此开拓了微生物学与细菌性疾病的新领域。随后人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细菌性疾病都是由毒素导致的,如破伤风、肉毒中毒、百日咳、炭疽和气性坏疽等。 1956年发现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杀虫活性物质是它的伴孢晶体蛋白(insecticidal crystal protein),在昆虫体内转化为一种蛋白毒素,可杀灭特定种类的昆虫。1962年首次鉴定出黄曲霉产生的有毒代谢物质——黄曲霉毒素(aflatoxin)。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黄曲霉毒素列为Ⅰ类致癌物,主要引起原发性肝癌。1973年发现人轮状病毒后,人们对其致病机制提出过多种假说,但都不能充分解释其引发腹泻的具体机制。直到 1996年,美国科学家 Ball等在制备轮状病毒非结构蛋白 NSP4的抗血清时,意外发现将 NSP4注射到乳鼠腹腔内会引起腹泻。据此,提出轮状病毒的 NSP4可能作为一种肠毒素(enterotoxin)在轮状病毒引发腹泻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这一推论已获得学术界的公认, NSP4也是**个被发现由病毒编码的肠毒素。
生物毒素是生物在自然界长期进化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动攻击或自我防护的“化学武器”,发挥着捕食、防卫和抵御物种之间的同化等多种功能。如蛇、蜘蛛、蝎子等专门靠毒素攻击对手获取食物;蜂类、蚂蚁、毒镖蛙等借助毒素防御敌害入侵,确保自身安全;对于植物而言,植物毒素也是植物本身拥有的特殊化学防御武器,起着防御敌害,攻击对手的作用。实际不同产毒生物可抵御物种之间的同化,即抑制竞争对手,确保自身的生存环境。而有些产毒生物又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如石房蛤毒素(saxitoxin)、西加毒素(ciguatoxin)、海葵毒素(sea anemone toxin)等许多海洋毒素分别是石房蛤、西加鱼、海葵通过滤食产毒藻类而富集产生的。一些有毒蘑菇如毒蝇鹅膏/毒蝇伞(Amanita muscaria)、绿盖鹅膏/毒鹅膏(A. phalloides)和春生鹅膏 /白毒伞(A. averna)等,无论怎样清洗、煎煮或冷冻,都不能去除其毒性,可谓“死毒不怕开水烫”。马铃薯本身是无毒之物,但一旦变绿或抽芽后,居然“翻脸不认人”,食用后会中毒,究其原因是变化部位产生了一种植物毒素——龙葵素(solanine),也称龙葵碱。基于生物进化观点,产毒生物拥有的毒素是其抵抗其他生物侵袭、吞噬和保护自身物种世代繁衍而形成的一种化学防御能力,同时毒素也成为它们生命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奥妙复杂的生物学信息,甚至影响着整个自然界生物物种间生存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toxin一词来自古希腊语(toxikon),是德国有机化学家 Ludwig Brieger最先提出的,指由生物体或活细胞产生的有毒物质。此后,有关毒素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对蛇毒素的纯化和化学成分,以及咬伤后的中毒救治等研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Findlay E. Russell(图 0-1)等的积极推动下于 1962年成立了国际毒素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oxinology,IST),F. Russell教授因在蛇咬伤与多价抗响尾蛇毒血清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被选为**任 IST主席。该学会的宗旨是“增加对来自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毒素和抗毒素性质的认识,并通过 IST把关心这类有毒物质的研究者团结起来”。同年 F. Russell等在美国创刊了毒素专业杂志,并用希腊文 toxikon拉丁化的 Toxicon作为杂志名称,其创刊词为“助力医疗,用科学征服未知”。1966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召开了**届世界毒素学大会,之后每 3年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举行一次大会,最近的一届是 2017年 10月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第 19届世界毒素学大会。到目前为止,已有 19人担任了 IST主席,中国台湾李镇源教授因其在利用银环蛇毒素(bungarotoxin)鉴定乙酰胆碱受体及蝎毒、蜘蛛毒素等方面取得的卓著成绩,于 1985年当选为 IST的第 10任主席。
图 0-1 芬德利 尤文 罗素 Findlay E. Russell(1919~2011)
我国的生物毒素研究工作开始较晚。1978年 5月,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次召开了全国的蛇毒研究与利用学术会议,围绕蛇分类、生态、蛇毒生化和蛇伤治疗等进行了报告交流。1981年在云南昆明又召开了第二届蛇毒研究和利用学术研讨会。之后又分别在福建厦门(1983年)、江苏苏州(1984年)和福建邵武(1985年)召开了全国的生物毒素会议。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20世纪 80年代初,有关生物毒素的学术组织也纷纷成立。1981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毒素专业委员会首先成立,随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毒物学分会(1991年)、中国毒理学会的毒素毒理专业委员会(1994年)、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微生物毒素专业委员会(1997年)和中国菌物学会真菌毒素专业委员会(2014)等几个二级学会也陆续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成立中国生物毒素一级学会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伴随着毒素研究、学术交流和相应的学术组织成立,我国有关毒素的专业刊物也先后创立。1986年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之全国兽医毒物检验协作组在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刊了我国**个有关毒素的期刊《动物毒物学》,史志诚教授任主编,至 2004年停刊,共 28期。1990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毒素专业委员会决定创办《中国毒素研究》刊物,舒雨雁教授任主编,由广西医科大学蛇毒研究所负责印刷出版,1996年《中国毒素研究》停刊,共出 4期。
20世纪 80年代,生物毒素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毒素个体的化学、生物学、毒理学、药理学研究,而是从生物化学、免疫学、药学、临床医学和分子生物学多学科角度对生物毒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基础与临床应用探索,并奠定了毒素研究的学科基础,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即毒素学(toxinology)或也被称为生物毒素学(biotoxinology)。狭义的生物毒素学是关于动物毒素、植物毒素和微生物毒素中毒救治的一门基础与应用学科;广义上讲,生物毒素学是关于生物体中产生或蓄积的有毒物质及其性质与生物学意义的科学,主要研究产毒生物及其毒素的结构与功能、化学组成和作用方式、中毒救治与预防、毒素开发利用及其生物学基础、生态学意义等。目前,生物毒素学多学科交叉的性质越来越突出。例如,对有毒生物的生物学特性研究,涉及解剖学、化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对毒素成分及中毒机制的研究,涉及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药理学及毒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等;对中毒的救治,涉及临床急救医学、免疫学、中医药学和预防医学等;对生物毒素的应用研究,涉及分析化学、分子生物学、药学和基础医学等。因此,生物毒素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
本绪论将阐述生物毒素的相关术语与定义、分类与特征、危害与开发利用等科学与应用问题。
一、生物毒素的相关术语与定义
与“毒”有关的术语较多,包括:毒素、毒物、毒液、毒剂、毒药等,同时,与“毒素”有关的术语也是不胜枚举,例如,生物毒素、天然毒素、动物毒素、昆虫毒素、植物毒素、微生物毒素、海洋毒素、细菌毒素、真菌毒素、霉菌毒素、蘑菇毒素、贝毒素、藻毒素、致病毒素、环境毒素、食品毒素、免疫毒素,以及内毒素和外毒素、类毒素和抗毒素、寄主专化性毒素和非专化性毒素、植物抗毒素等等。
(一)与“毒”有关的术语
1. 毒素(toxin)
toxin一词来自古希腊语(toxikon),是指由生物体或活细胞产生的一种有毒且不可自我复制的物质,毒素可以是小分子化合物、多肽或蛋白质。在英国《牛津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词典》中,毒素是指生物源的具有特定毒性的各种有毒物质(any of various specific substances that formed biologically)。根据《美国法典》,毒素是指有毒的物质或植物、动物、微生物(包括但不限于细菌、病毒、真菌、立克次体或原生动物)等产生的有毒产物,或感染性物质,或重组或合成的分子,不论其来源和生产方法如何。
2. 毒物(poison/toxicant)
在一定条件下,可引起生物体和细胞损伤、中毒、疾病或死亡的任何物质,包括生物源和非生物源的,以较小剂量进入机体就能干扰正常的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
3. 毒液(venom)
顾名思义就是有毒性的液体。由有毒动物体中高度进化的细胞器或腺体产生,在叮咬或刺蛰时排出的有毒物质。有毒动物在防御或攻击其他生物时,通过某种通道排出毒液,使受害对象中毒。如蛇毒、蝎毒、章鱼毒及蜂毒等均为毒液。
4. 毒剂(poison agent)
军事上指专门用来毒害人、畜、植物的化学物质,大多是毒气,如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和窒息性毒剂等。
5. 毒药(toxicant/toxic drug)
在中国古代,毒药并非有毒之药,而是指味道浓烈、药性强的药,即重药。神医扁鹊曾认为遇到重症患者,便得下“毒药”,药效才够。随着历史的变迁,毒药一词本身也经历了演变,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有毒之药”,即泛指能通过各种途径使人畜中毒甚至死亡的药物,而非最初的重药良方。
(二)与“毒素”有关的术语
1. 生物毒素(biological toxin/biotoxin)
生物源的毒素,即由微生物、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