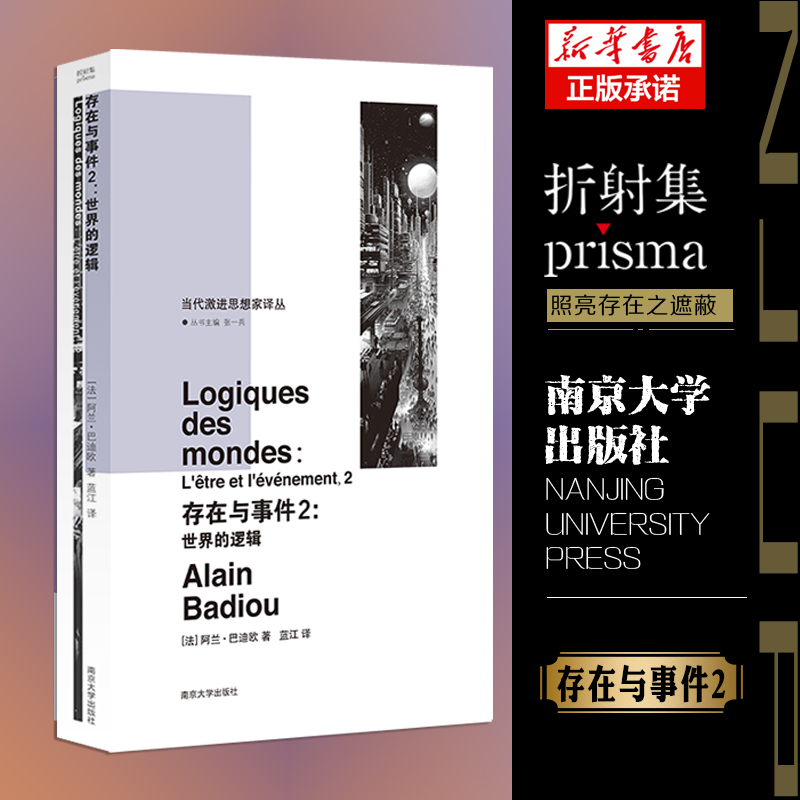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20.80
折扣购买: 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ISBN: 978730520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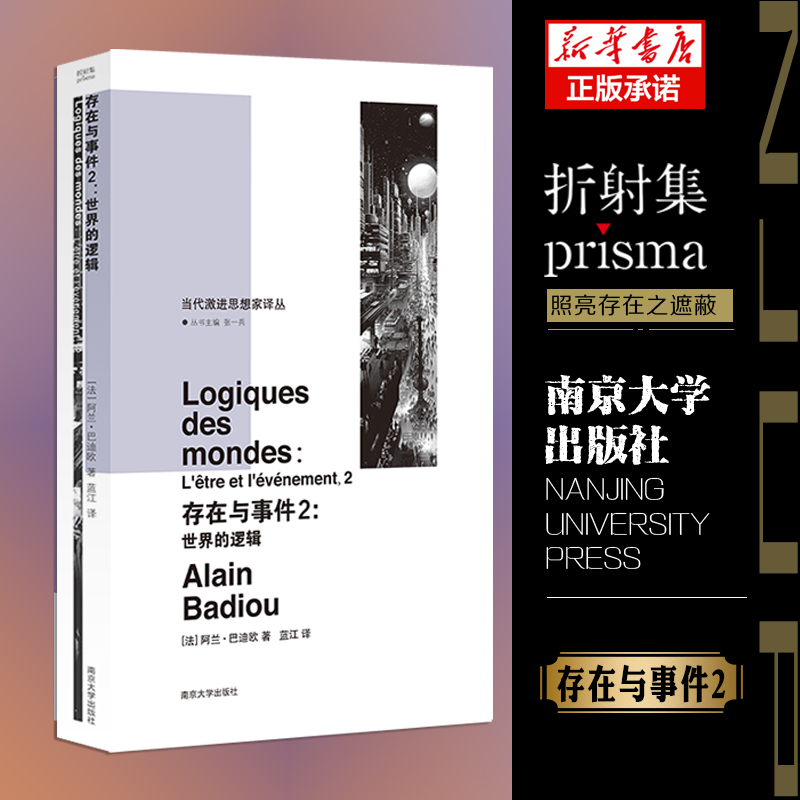
阿兰?巴迪欧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前哲学教授,法国哲学家。师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路易?阿尔都塞,并参与了阿尔都塞为科学家举办的哲学讲座班。20世纪80年代之后,巴迪欧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先后发表了《主体理论》(1982)、《存在与事件》(1988)、《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2006)、《存在与事件3:真理的内在性》(2018),宣告了他以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为根基的新哲学的诞生。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我们能思考政治吗?》《元政治学概述》《伦理学》《爱的礼赞》《非美学手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德勒兹:存在的喧嚣》《圣保罗》《瓦格纳五讲》《柏拉图的理想国》《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法国哲学的历险》等。 关于译者 蓝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社会科学杰青,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主要研究当代欧陆左翼激进思潮,尤其是引介和研究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维历史轨迹》《阿甘本五讲》《忠实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主要译著包括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世纪》《哲学宣言》《数学颂》《小万神殿》,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敞开》《宁芙》等。
4. 艺术的例子:马 我们来看四幅画,在画中,马是最显著的角色,这些画大约出现于30000年前。一边是肖维岩洞(Grotte Chauvet)中用白色线条画的马和黑色的“马的底板”;另一边是毕加索的两幅画[1929年和1939年],第一幅是灰色的,两匹马拖拽着第三匹死掉的马,在第二幅画中,一个人掌控着两匹马,其中一匹马佩着辔头。在这里,所有东西会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表达要素。毕加索不可能受到肖维岩洞中大师的启发,在他的时代,还不知道肖维岩洞,当然,毕加索给出了他自己在岩画艺术认识方面的最充分的证据——尤其是他画的公牛的形象,像1945年画的黑色的模糊的克里特人的轮廓。但他的这个认识与肖维岩洞中的大师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因为毕加索所用之技艺也影响了很长一段历史,如果不算肖维阿特里耶岩洞,还包括比它晚10000年到15000年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岩洞和拉斯科(Lascaux)岩洞。若看到了这些差别,相对主义者会再一次宣布胜利。我们知道,他们会说,毕加索所画的马头的风格以及对腿部的几何学上的处理,只能理解为用现代手法画出的带有“写实”倾向的马。古代的画家描绘的是体量、肌肉组织和动感。毕加索反而试图描绘出原始的“淳朴”——包含了一种前历史的模态——将马变成一种装饰力的符号,以后腿直立,并试图摆脱其生理机能。在那里有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个是野兽那高高昂起的头颅,似乎仰天长啸,呼唤着上天的拯救,另一个是经常会施加在马背和马蹄上的重负。它们就如同天使般的佩尔什马(Percheron)。在它们的“仰立”(cabrure)中——这个“仰立”是如此的缓慢,也如此猛烈——对应着那绝望的呼喊。 相反,肖维岩洞中的马是一个顺从的标志。毫无疑问,里面有猎人的形象:所有的马都低着头,26尽可能保持温顺,立即投入我们眼帘的是它们那巨大的前颅,正好在它们的鬃毛之下。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马的底板”上的四个马头的布局[正好是另一个视角的效果!],似乎要说的是,它们是按照一种神秘的等级秩序来安排的,不仅仅是马的高度——头的大小从左到右逐渐减小——还有色泽[从明亮到黯淡],尤其是看的角度:我们从一个睡眼惺忪的马走向一个有着很明确表象强度的最小的马。事实上,这些被展现出来的、顺从的、明显可见的马的举止,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毕加索讲述的带有矛盾冲突和呼唤救赎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把握用白色勾勒出来的马的整个轮廓,它的腿过于细长,腿部也比较瘦弱。与毕加索在这些动物中所了解到的乡村的天真无邪不同,肖维岩洞中的艺术家,即艺术家猎人,在这些动物的不确定的定型中,看到了一种征服的野蛮,一种同时被展现出来的和隐秘的支配性的美。 于是“马”在两个例子中的意义不同。随着情境的彻底改变,动物的客观性在30000年的跨度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我们如何将这些猎人们的无法解释的模仿能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画完全是枯燥无味的,我们要想象一下,在光影摇曳的火光或火把中,百折不挠地将这些巨幅的绘画镌刻在洞穴的岩壁上]与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所有艺术家中最为著名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创造新的形式,或者为绘画思想的快感而再创作, 而在他的画室中,所有的化学和技术都可以用来服务于他的画作]相提并论?此外,对于前者而言,动物,如马,就在他们生活的中间:马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的对手、他们的食物。猎人们自己所身处的危机四伏的丛林与他们日日夜夜观看、捕猎、观察的动物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从这些动物之中,他们提炼并绘制出华丽的符号,这些符号历经漫长的岁月流逝,在数千年的时光里从未被人触及,径直来到我们的面前。相反,对于毕加索而言,动物是一种日益没落的农民和前技术时代世界的象征[在那个时代里,有他们的淳朴,有他们的欲求]。后者说,他们就是已经在景观中被捕捉到的人物形象,这样他们就像让这位画家如痴如醉的公牛和马一样,在绘画之前就被预先构想(préformée)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些“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肖维岩洞中大师的马是对他们参与其中的27纯粹生活形式的升华,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将这些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合为一体。毕加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只能引述这些形式,因为他已经退出了所有直接接近生活底层的直接路径。对于这些引述,如果毕加索表现得要像远古的猎人那样以纪念式的风格来生活下去,那么就会成就与他对立的意义:乡愁,徒劳的祈求,而在这里值得分享与赞美。 然而,我在这里坚持认为,事实上,其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同时贯穿于肖维岩洞和毕加索的画作。当然这个主题并没有包络它自己的变量,那么我们关于马的意义所说的一切仍然是正确的: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世界。事实上,由于这个主题是从各个变量中抽取出来的,所以马的主题让其变得清晰可辨。这自然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直接就被它的美所感动,在没有欲求的意义上,这种美就是肖维岩洞中的作品的美。同样,我们强行将这些画作与毕加索的进行比较,超越了纯粹反思的层面,也超越了毕加索自己对史前绘画风格的认识。我们同时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和真理的永恒性,而真理在多元的世界中不同的点上表象出来。 这种永恒不变的真理是由什么组成的?假设你涉及与动物的思想关系,而这种关系让动物成为那个世界中的稳定成分:那里有马,有犀牛,有狮子……现在设个别生物在经验上和生理上的差异从属于这种稳定性。那么东西就是一种可识别的范式,对动物的再现就是大写观念可能的最清晰的标记。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类型[或名称]的动物,从感觉经验的连续体中被切分出来。用这种特别形式的可认识的特征来将它们十分明显的有机体统一起来。 这意味着——正如在柏拉图的神话中,但是相反的——画出洞穴岩壁上的动物,就是要逃出洞穴,并上升到大写观念的光芒之中。这就是柏拉图假装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图像就是阴影的对立面。这证明了在绘画符号中的变化的不变量的大写观念。与从存在的大写观念下降到可感物的过程不同,这就是大写观念可感的创造。“这是一匹马”——这就是肖维岩洞的大师所说的话。由于他所说的远离了活生生的马的可见性,他证实了马是外在于思想而存在的东西。 然而,这在技术上的效果,28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这二者同样深刻,同样富有创造力——后者是为了将一匹马的肌肉线条和毛色的细节光彩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主要的结果是,就其对马的再现而言,一切东西都与线条有关。绘画必须刻画出可以识别的分隔,即由所有画出的马展现出来的对马的单独的凝思。但是,这种凝思——证明了与观念统一体相一致的马的观念——就是最原初的直观。它只有通过没有润色过的线条的确定性来加以固定。在一次行为中,在一次涂抹中,艺术家在分离出马的观念时,也画出了一匹马。正如——这样肯定了这种真理的普遍性——中国画的画家一样,经过严格的训练,一笔下去,就能把握住在一头牛与牛的观念、一只猫和猫的笑容之间难以分辨的东西。 我们只能赞同马尔罗的说法。例如,当他[在他的《反回忆录》(Antimémoires)中]写道: 艺术并不会让人们依赖于那些生命短暂的东西、依赖于他们的房屋和他们的家具,而是让人们依赖于他们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大写真理。艺术并不依赖于坟墓,而是依赖于永恒。 毕加索用他的非凡技艺所指向的永恒真理,可以概述如下:在绘画中,动物只需要借助各个彼此分离且十分明确的线条,这意味着在大写观念和实存之间,在类型和例子之间,我们可以进行创造,因此也可以思考那些仍然无法辨识的点。这就是为什么说,尽管在没有共同尺度的情形下,两个绘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意义完全相反,肖维岩洞和毕加索画的马却是一样的。从轮廓的角度来思考一下,三角形的头颅,圆柱形的脖子,画家不辞辛劳的努力夹杂着甜蜜,这种辛劳消失在画家对动物的凝视之中:整个形式工具,在所给定物基础上,汇集成对不可化约的马的凝思,它拒绝将其消弭为无形式的东西,从而保持了它的可以识别的独特性。于是,我们有信心说,30000年前,肖维岩洞的大师[当然,他或许是另一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的师傅的学生:我们也没有来源知道这一点]所开创的东西,也就是他所遵循的东西,也是我们在其中所遵循的东西,29以及毕加索提醒我们说:这不仅仅在事物之中,在身体之中,也在我们生活和言说的东西当中。这就是大写真实带来的惊喜,而我们有时也需要参与到这种惊喜之中。 一种非常著名的犬儒思想家会在柏拉图背后嘲笑说:“我只看到了马,我根本没看到马的观念。”从火炬光芒下的猎人到现代的百万富翁,在绘画创作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真的只有马的观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系列文本,从1988年的《存在与事件》到2006年的《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到2018年的《存在与事件3:真理的内在性》,前后历时近30年,是其以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为根基的事件哲学的宣言性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身体定义,将其理解为真理之身体,或可主体化的身体。正如存在之所为存在是通过数学来思考的,表象,或者在世界中存在,是通过逻辑来思考的。《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说明了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对象是什么,以及世界上的关系是什么。 ☆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以康托尔-事件为前提,通过多的数学理论彻底变革了真理的本体论;而在《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则通过层的逻辑理论彻底改变了超验和经验的结合。 ☆哲学最终需要解答的问题:什么是活着?活着,就是“成为不朽”。世界的无限性就是让我们摆脱所有有限的不幸。我们开启了世界的无限性。活着成为可能。 [重新]开始生活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