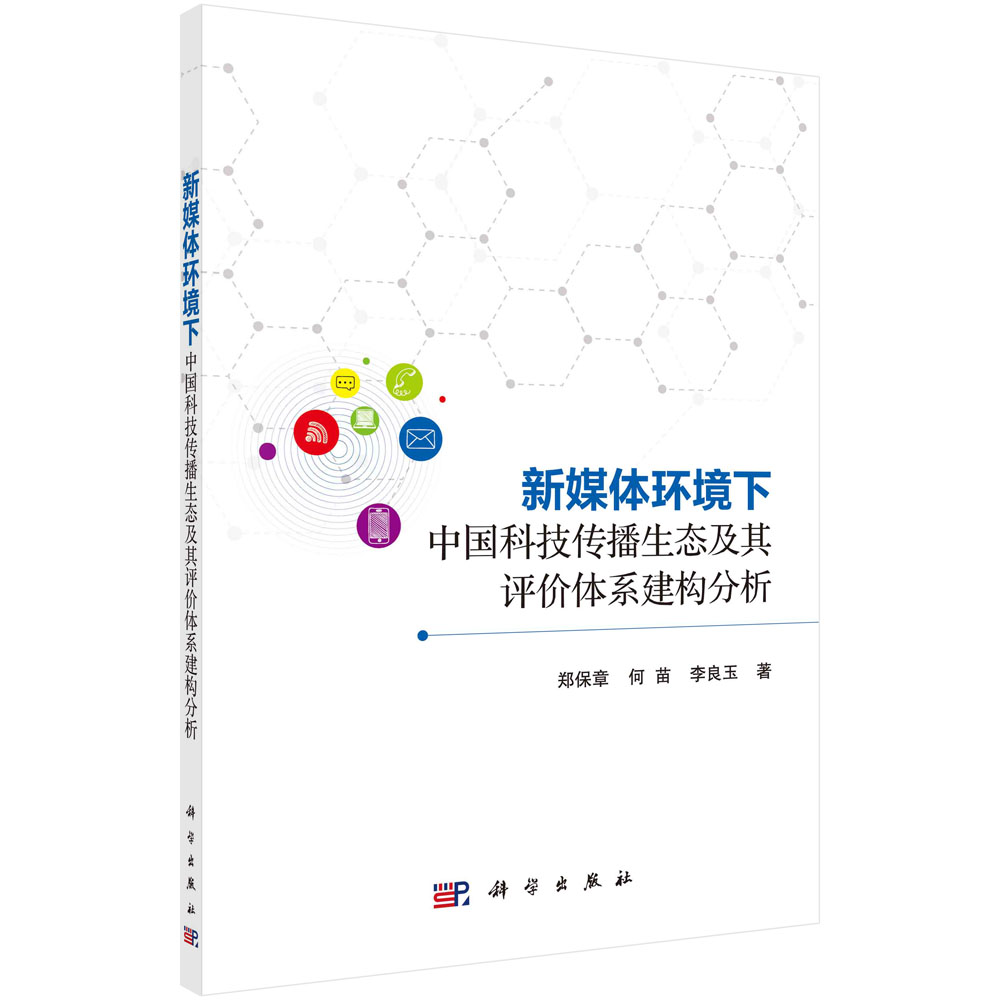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77.42
折扣购买: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科技传播生态及其评价体系建构分析
ISBN: 9787030674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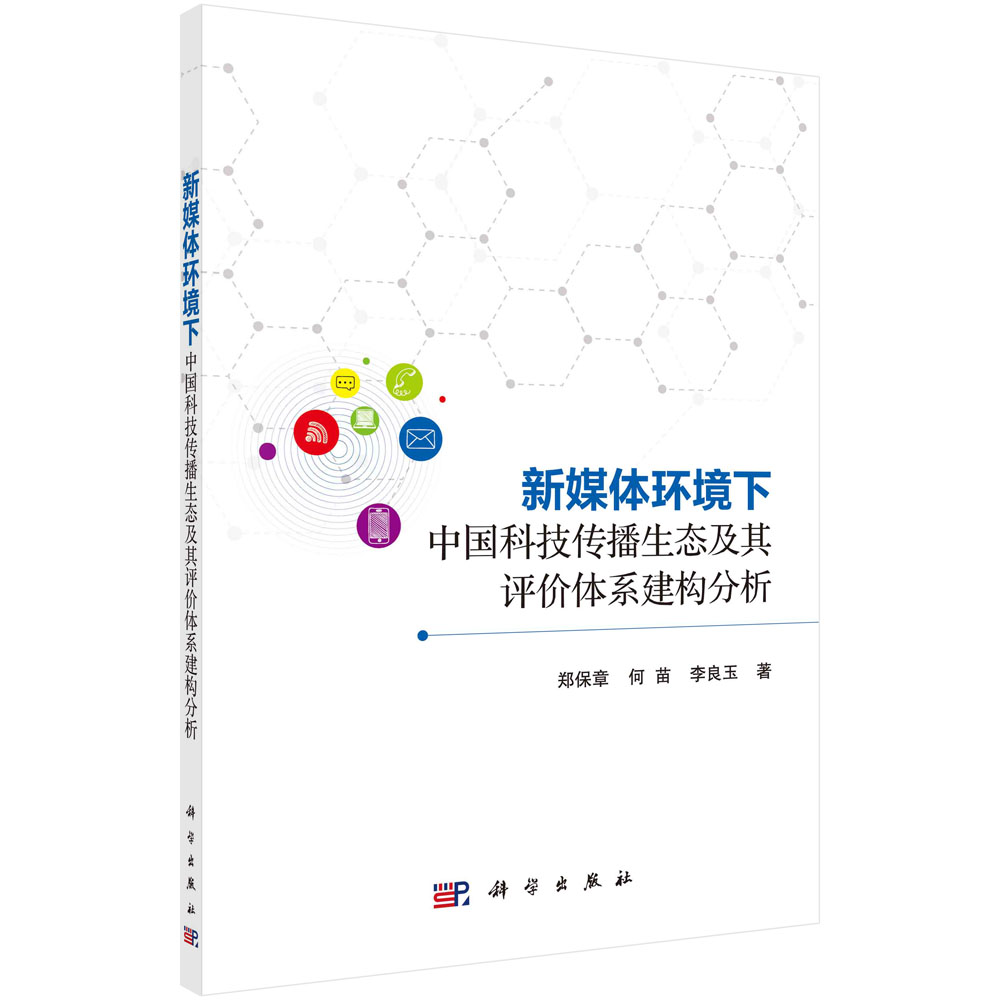
绪论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不再是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而是主要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以及知识和信息的运用,特别是依赖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依赖国家创新系统的良好运作。”①科技传播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科技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技传播过程中传播的知识信息成了连接科技与社会的桥梁。
科技传播环节的不畅,将减缓知识创新的产生、知识成果的应用、知识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的进步。科技进步才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科技知识在不同传播主体之间传播并向社会扩散,科技内容从知识的拥有者和发明者传播到广大受众,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共享,从而使科学技术本身得到延续、积累和发展。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平台的传播网络呈现“围观”的效应,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社会事件,不论是科技传播还是科普教育,不断增多且无法确定其变量的庞杂信息迅速充斥到传播过程中。尤其当发生热点事件时,新媒体渠道为受众搭建了传播信息昀快速、昀广泛的平台。但与科技知识传播的求实严谨不同,新媒体平台或追求轰动性效果,或重视与生活的相关性,或强调戏剧化情节,直接影响着科技传播的内容本身。面对林林总总的新媒体平台上不断增加的、各抒己见的、众声喧哗的科技信息,受众有正向的关注、评价,也有质疑、戏谑、迷茫,这甚至演变成类科技传播,造成了科技传播生态的无序化。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格局,改变了原有的科技传播格局,科技传播同样也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如何运用新媒体开启科技传播新阶段的任务?科技传播在新媒体平台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新功能?人们在新媒体时代享受着更高级的视听效果,这种需求促进新媒体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带动社会进步,促使人们掌握更丰富的科技知识,新媒体与科技传播不是平行线,它们都与社会发展产生必然联系,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研究,将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从生态学思维中关联性与整体性、动态性与平衡性的视角出发,将生态学从作为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领域,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在科技传播研究中强调生态学的可持续发展性,正是科技传播生态研究的本质所在。科技传播是一种传播实践活动,它集中反映的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科技信息作为科技传播的主要内容,以媒介为渠道,在社会环境中于主体与受众之间传播,并追求动态平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传播具有生态性。因此,在比较科技传播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基础上,以生态学的视角分析科技传播情境的范围和复杂性,揭示科技传播的本质与规律,可以更好地考察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失衡的新问题。剖析其根源,提出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维度。
科技传播是一种具有生态学特征的社会活动,结合新媒体时代媒介特点,我们运用生态视角审视科技传播中传播主体、受众、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科技传播客观规律和发展逻辑,运用生态系统特征来审视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平衡的原则与失衡的原因,可以促进科技传播研究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新媒体时代的科技传播生态构建。
其一,丰富和发展科技传播学理论。科技传播生态系统是科技传播固有属性和构成要素动态变化的结果,是以其内在本质特征和固有结构属性为深层动因的复杂生态系统。结合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与媒介生态的理论基础,从生态学角度对科技传播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和构建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的理论体系,深层次认识其生态结构、构成要素和生态功能,理解其生态平衡与动态循环,拓宽和挖掘科技传播学术研究在生态学视域的广度和深度,丰富和发展科技传播学理论。
其二,揭示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本质及运行规律。科技传播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特定功能并可以产生整体综合效应的社会活动,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科技传播系统内部的诸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通过能量和信息的相互联结构成有机整体即构成了科技传播生态。从一种单纯的社会活动演变为组织多元、功能完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的动态生态系统,可以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科技传播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
其三,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维度构建。新媒体时代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格局,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科技传播格局,科技传播同样也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带来了科技传播新阶段的紧迫任务。以传播科学文化为己任的科技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新功能,需要深入探讨,在新媒体冲击下的科技传播生态失衡的表现多样,需要分析其主体、技术和社会的失衡原因,分析科技传播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结构失衡根源,提出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维度。
目前针对国外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生态的文献综述,从新媒体的界定、科技传播研究和媒介生态研究三方面进行梳理。
“新媒体”(new media)的概念是 1967年美国人 P.戈尔德马克( P. Goldmark)率先提出的。所谓的“新媒体”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它们是相对于没有计算的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互动媒介,涉及计算并包括双向传播,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计算机、手机等终端,向客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 ①这里加引号的“新媒体”表示它们的身份是互动式的数字媒介,而不用引号的新媒体则表示,它们是刚刚引入讨论语境的媒介,二者的区别在于,现在一切的“新媒体”都是新媒体,而 20世纪 50年代的电视是当时的新媒体,电视与网络结合的网络电视则是“新媒体”。新媒体的定义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它的相对不确定性,也在技术、媒体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交织影响中带来了媒体的变革。国外对新媒体的定义大同小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定义聚焦于新媒体的媒体形态和技术特性。例如:有学者将新媒体描绘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或始于计算机,或倚重于计算机而流通,所倚重的设备和平台有人机界面,也有虚拟世界等。也有人描绘的新媒体集很多要素于一身,将文本、音频、视频、互动多媒体、虚拟现实、电子邮件、聊天功能、计算机应用等各种客户端能够获取的信息和实现的功能结合起来,正如伊锡尔 德 索拉 普尔( Ithiel de Sola Pool)将新传播技术定义为当时的“大约 25种传播设备的简称”。他重点强调的是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如新媒体利用网络的双向传播能力,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可以允许传播主体之间针对内容进行互动。也有人针对新媒体的技术形态变化,提出补救的概念,用以区别新媒体和旧媒体,如杰伊 大卫 博尔特( 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 格鲁辛( Richard Grusin)提出,新、旧媒体是互相补救和相互重塑的,新媒体是旧媒体被重塑之后的展现方式,同时,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旧媒体也在不断重塑自己。如果将一种媒体在另一种媒体中的再现称为补救,那么可以认为补救是新、旧媒体的界定性特征。 ②这种描述虽然无法回答哪些是新媒体,哪些是旧媒体,但适用于从古至今一切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另一类定义则超越了对新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受到“社会形成观”的影响,认为新、旧媒体的界定应该关照媒体技术与人类行为在社会结构中的交互影响。斯蒂夫 琼斯( Steve Jones)在《新媒体百科全书》的导言中写道:对于新媒体的**完美的定义无疑来自对历史、技术和社会的综合理解。这种理解框架认为新媒体不仅包括传播技术的进化,更包括与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层面的变化,如延伸我们传播能力的设备装置,使用这些设备进行的传播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与实践形成的社会组织与惯例。 ①通过对新媒体的文化意涵研究来界定概念的框架也逐渐完善。新媒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聚合概念,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分析。理解“新媒体”的关键即新媒体“新”在哪里,这也是国外新媒体研究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新”是指媒体形态质方面的变化,即首次出现了新的媒体形态,还是媒体形态的量方面的变化即新媒体对原有媒体传播方式的延续延伸,抑或是媒体形态所引发的社会法律、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方式的新变化?无论是哪种界定方式,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区别不是内容,而是思维方式。正如我们所见的互动媒介比如互联网不仅是创新的结果,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机制和过程。 ②在对新媒体衍生的历史语境及新媒体研究领域的形成进行追溯后,每一种媒体对“新媒体”挑战的回应,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新媒体”改变了旧媒体的运行背景,改变了旧媒体的影响性质,描绘传统的旧媒体成为某些“新媒体”的内容,或者旧媒体自己变形蜕变为一种“新媒体”的形式,更适合用“功能重组”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转化。正如尼尔 奥利 费尼曼(Niele Ole Finnemann)表达的,旧媒体的功能重组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它们有了新的用途:一种形式是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旧媒体完成了数字化,但其功能如故,数字照相机和电视机就是这样的;还有另一种形式是很多旧媒体完成功能重组,实现了数字化,结果蜕变为一种新东西,录制的音乐数字化,制成光盘以后,或者下载到 iPod播放器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③“功能重组”也好,“数字化”也好,旧媒体被“新媒体”改变了。理解“新媒体”时,研究它与其他媒体的互动与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伴随着媒介数字化,媒介融合的趋势使媒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对媒介的文化认知不仅来自其自身的运行方式,而且也来自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媒体构成一个网络,并在技术、社会、经济的环境中运行,每一种媒体的界定都依赖其在媒体网络中与其他媒体的互动。正如语词可以用它们与其他词的关系来界定,同理,媒体也可以用其与其他媒体的关系来界定。
科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翰 德斯蒙德 贝尔纳( John Desmond Bernal),他在 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的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问题,他认为,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经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并解决科技传播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 向公众传播的问题。贝尔纳将科技传播问题“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并特别强调了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对推动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让公众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了解科学对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贝尔纳将科技传播分为“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面向公众的传播”的观点后来在科技传播领域也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①在国际科技传播领域有着广泛影响的《科学传播》将 science communication划分为研究共同体内的传播( communication within research communities)和面向公众的科技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两个方面。马丁 W.鲍尔( Martin W. Bauer)在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综述中用三个范式论述了公众对科学发展的理解过程,包括“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三种范式呈递进关系深化。 ②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 T. W.伯恩斯(T. W. Burns)给出了一个可以简称为“ AEIOU定义”的科技传播定义:即使用适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个人对科技的这样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awareness)、愉悦( enjoyment)、兴趣( interest)、意见( opinion)、理解( understanding)。③相比上述的定义,这一定义更符合定义理论和定义方法的基本要求。这个定义从“科学传播所引发的个人对科学的反应”视角描述了科技传播的基本特征,形式上符合定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