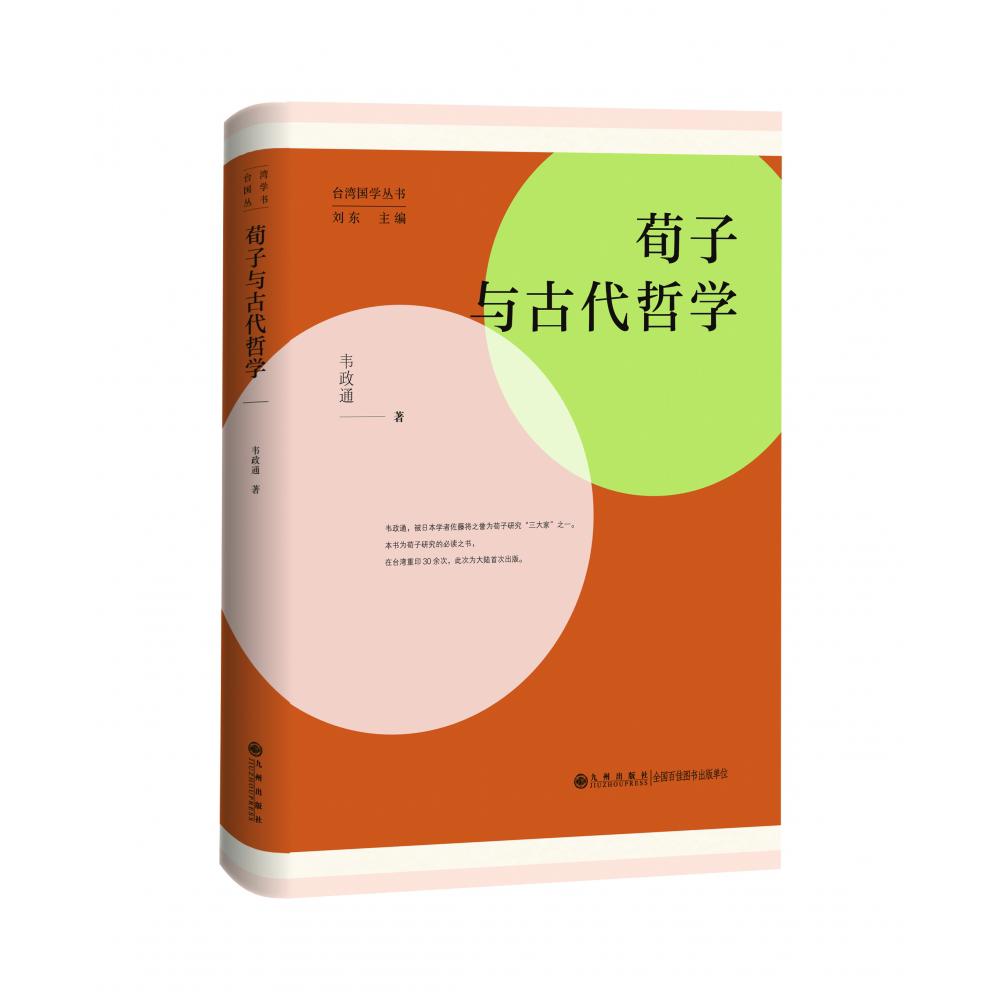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荀子与古代哲学
ISBN: 9787522507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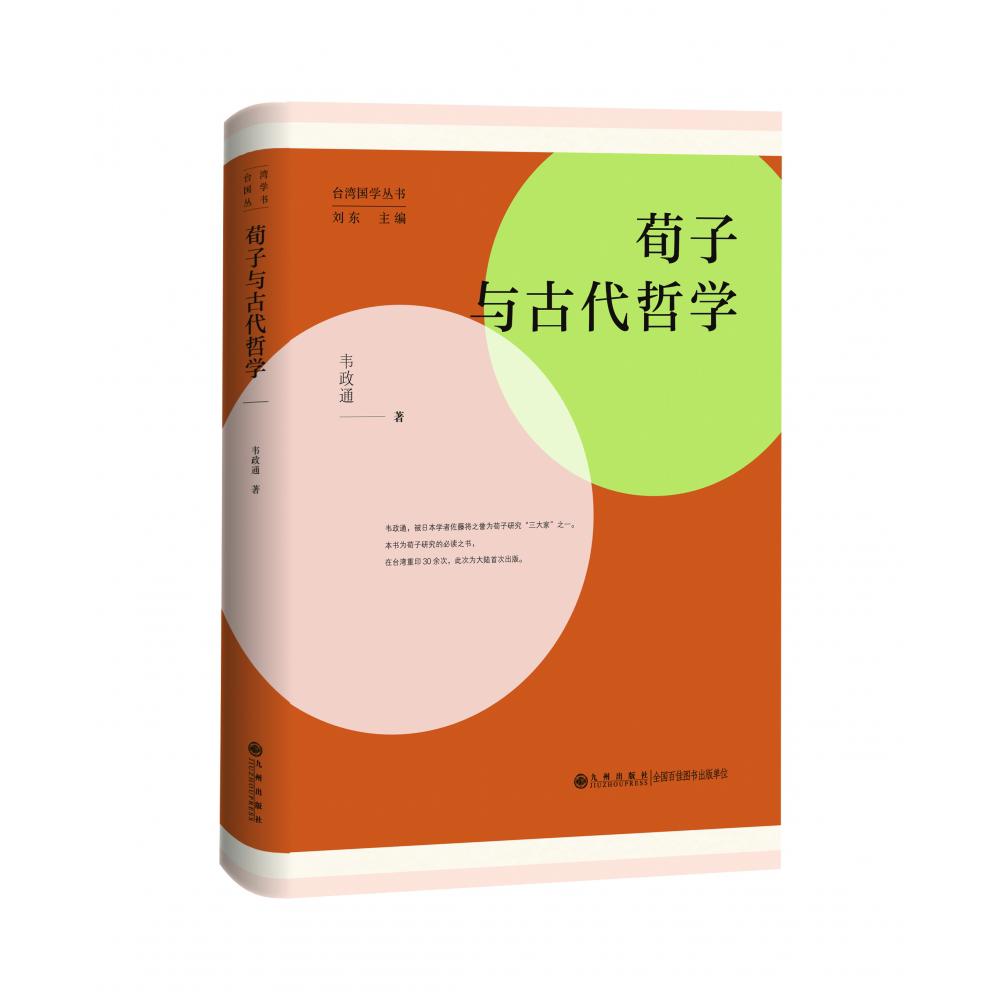
韦政通(1927—2018),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曾任台北《中国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世界中国哲学学会学术顾问等。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现代知识分子品质的塑造等方面多有创见。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董仲舒》《中国思想与人文关怀》《伦理思想的突破》《儒家与现代中国》等近四十部著作,编有《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等。
第二章 荀子“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 一 “天生人成”一原则之引出 “礼义之统”是荀子思想系统的基础,“礼义之统”所涵的一系列观念,是荀子思想系统的基层观念;通过这些基层观念,很清晰地表露了荀子系统的特质;这特质表示荀子思想自始就是一客观的路子, 他所要完成的系统,亦是一客观的系统。这系统的基本架构,是以“周文”作引子,以“礼义之统”作基础,到“天生人成”一原则构造出,才表现它的完成。因此,在“礼义之统”系统的解析之后,进一步必须对“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予以理论的陈述与展示。 要构造一个系统,第一步必须先形成一中心理念,荀子思想系统的中心理念即“礼义之统”。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主要领域,大体不外是对人、对事、对天的三个方面;中国历代的大思想家的系统,大都是根据他的中心理念,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及其关系所作的陈述。荀子亦不例外。荀子思想的主要部分,即是以“礼义之统”为基础,并于礼义效用的思考中,决定了礼义与人、与事、与天的关系;这一关系确定了,性、天的意义也就同时确定。这种由客观礼义的效用问题,导引到对天人关系上来的思考方式,即是由荀子思想系统的特质所决定的方式。 要了解这一特质,及此特质所决定的特殊方式的意义,与孟子的思路对照起来看,就很明显。孟子思想系统的中心理念是性善,这是就人之本然之善,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它是众善之源,理想之根;孟子的一切思想都是本此中心开出的。性善心亦善,孟子即是以心善作例证(如“四端”之说),建立其性善论,故尽心知性则可以知天。在此一标准下所了解的“天”是“生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此一标准下所了解的“事”是“修德”(《中庸》格、致、正、诚、修、齐,即修德之事;治、平亦莫不以修德为基础)。在孟子的系统中,一是皆以成德为主;孟子的宇宙,亦是道德的宇宙,这宇宙的基础在性善。表现道德的心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所以孟子的思想系统是必然由主体入的。亦即可本此义确定孟子思想的特质是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上;这与荀子的系统是由客体(礼义)出,并以“礼义之统”为基础而构造的客观系统是迥然不同的。 牟宗三先生,曾经在他《中国哲学的特质》一讲稿中,对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上,有如下的论断:“中国的哲人多不着意于理智的思辩,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的。这些人物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字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是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联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做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这一段说明两点:(1)中国哲学是,重实践重主体的;(2)政治理想的实现,是以内省修德作基础的。这两点即是以表示中国哲学的特质。很显然,此一特质的陈述,是以孔孟一系的人文思想为典范的,并不能概括荀子的系统。在这一特质的陈述下,荀子当是一个例外。而后来历史上的儒家哲学,是以孟子的心性论与《易传》《中庸》为主流、为正统的。明白这一点,荀子其人其学一直不被重视而遭湮没,便不足为怪了。荀子不入主流,不为正统,并不表示其哲学思想无价值;而是向来哲人在孟子思路的拘囿下,无人能了解其价值,无人能察觉其系统乃代表孟子思路以外另辟的一个新方向;反而在两千多年以后,中国文化百弊丛生要求新出路的今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总不免局限于主体的一面,终于转不出来;今天的新哲学精神的要求,重点在如何开出客观精神,要开出客观精神必须重客体。这正是荀子的思路,荀子客观系统所代表的精神。这一精神在前章“礼义之统”系统的解析部分,已有相当的展现;在“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中,而后能全体透出。 “天生人成”一原则是透过“天”“性”“伪”“心”等观念所组成;因荀子构造系统的思路不是由主体入,而是由客体之礼义出,故其所言性天之意义与孔孟所述者大异其趣。由主体入,故肯定心性皆善;心性善,则由尽心知性而知之天亦善;一向儒家所说成德的基本工夫,即以具有价值意义的心、性、天为本,对治人的私欲,荀子则不然。荀子系统由客观之礼义出,故其价值标准不在主体之心性,乃在客体之礼义。价值标准既在客体之礼义,则实现价值唯在尊礼隆义,及发挥礼义的效用。荀子即以其所尊所隆之礼义为能治之本,返而治性亦治天;则性天在礼义之对治中,皆屈服而为被治的、负面的。众善之源、理想之根唯在礼义,性天只是自然义。 在孔孟,礼义由性分中出,礼义乃表现性天价值之客观化,性天与礼义之关系是谐和的。荀子的礼义乃“由人之积习以成,由人之天君(智心)以辩”,它是人为(伪)的,与人的性分无关,礼义与性天之关系遂成为能治与被治之关系。能治之礼义,与被治之性天之对局,即“天生人成”的基本架式。“天生”之“生”,非“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生即自然而然之义;“人成”者,即通过礼义之效用以成。荀子“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即纯由礼义之效用问题之思考中而导引出。故“天生人成”的理论,实即荀子效用论的主要部分;荀子的基本精神,亦即由礼义效用的追逼下而步步彰显。在《荀子》书中有两段重要的话,已说明“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所以构成及必须构成之理由。在这两段话中,不仅提到组成“天生人成”一原则的几个基本观念,且启迪了构造这一部分理论的思路,此即本书对“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之所本。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篇》)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篇》) 这两段话颇具概括性,可视为“天生人成”一原则理论构造的一个纲领,下文即本此纲领而予以一一展现。 1. 韦政通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是早期“治荀三大家”之一,《荀子与古代哲学》为其荀子研究的代表作。是书一九六六年初版后,常销不衰,迄今已有十多个版本,印次不下三十。其人其书,魅力与价值,于此可见一斑。此番出版者,为五十多年来首部简体本。 2.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思想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本书特别着重与各家的比较,从比较中显现荀学的特色。 3. 本书写作的方式,是“叙述”与“判断”并重的。叙述的部分,把荀子的思想系统做了一次重建的工作;判断的部分,不仅一再断定了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且对每一点的重要观念的是非得失,都不放过对它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