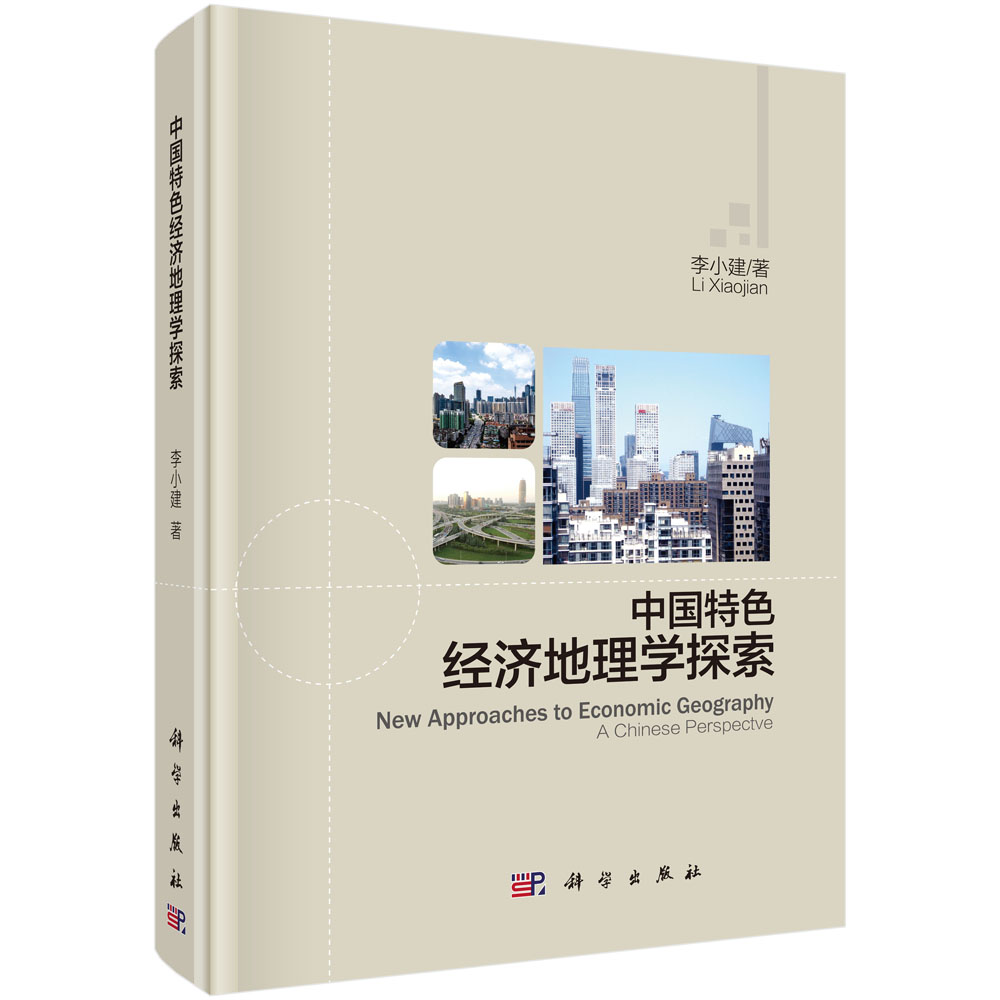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258.00
折扣价: 180.60
折扣购买: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探索
ISBN: 9787030461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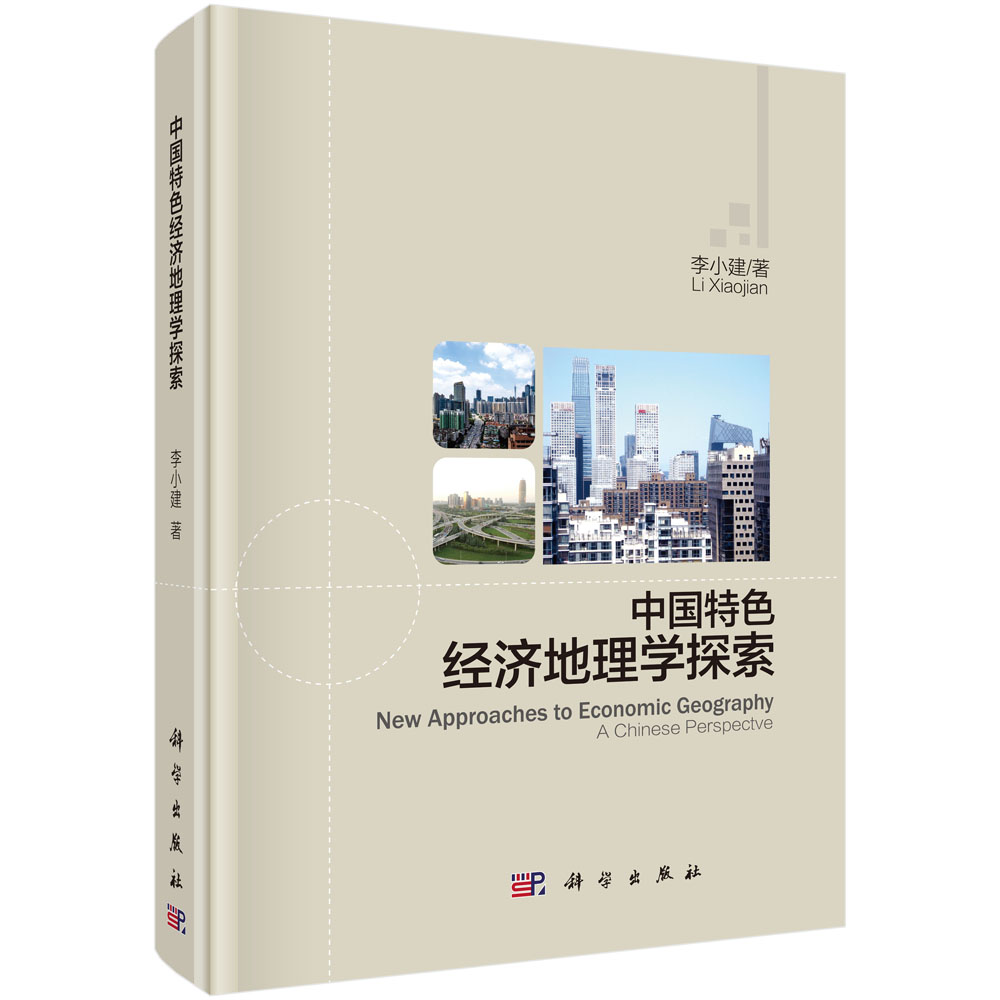
第一篇 经济地理学理论探索
第1章 西方经济地理学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出现的系列新特征,西方经济地理学家相继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差异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同时,由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分析的深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重新发现了“经济地理”的重要性,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要,在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传钧,1998;陆大道,2001)。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地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还相对较为薄弱。本章拟在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新进展的基础上,对我国该学科的理论研究方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促进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1.1 地理学家的“多维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理论视角的多元化,与此相应,一些学者用“复数”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取代过去作为“单数”的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Barnes,2001;Yeung,2003)。该阶段的多元化可概括为“多维转向”,包括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苗长虹,2004)。
1.1.1 制度转向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中,“计量与理论”革命时期的经济地理学将其理论大厦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其中心是空间科学与系统分析,这种地理学把经济主体的行为看做是理性的,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社会政治情景被忽视;而之后的激进地理学,则将其理论大厦建立在结构主义,特别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其中心是空间不平等发展理论,这种地理学将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看做完全是由经济过程所决定的,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置于被动和次要地位。也许,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马西(Massey)所引领的“劳动地域分工”和“地方性”(locality)研究率先将资本主义空间不平等发展的现实同历史上所继承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Massey,1984)。但制度主义或制度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的真正发端,是一些学者对70年代末期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市场自由化体制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所出现的新时空变化,特别是区域经济复兴的研究。例如,皮埃尔(Piore)和赛布尔(Sable)对弹性专业化和新产业区的研究(Piore and Sable,1984),加利福尼亚学派对新产业空间的研究(Scott,1988;Storper and Walker,1989),欧洲GREMI小组对创新环境的研究(Aydalot et al.,1988),库克(Cooke)等对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的研究(Cooke et al.,1988;Morgan,1997)等。所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资本主义经济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解。这种“制度转向”大体有4方面的来源(Martin,2000):①法国管制学派对“社会管制模式”的强调;②经济地理学对社会文化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认识;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对“制度主义”的研究;④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所发生的实际巨变。实际上,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来源为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苗长虹等,200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制度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快速复兴的产物。它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传统,但在分析视角上,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从多种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最新发展中寻求思想源泉,它不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资本主义空间动态中的作用,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经济及其演化的方法。2002年布伦纳(Brenner)等对“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及其空间动态的研究(Brenner and Theodore,2002),其理论视角就深深扎根于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中。
1.1.2 文化转向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研究是可以明显加以区分的。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经济的?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辩证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经济地理学远较制度转向意义更为宽广和深远的关于“文化转向”的讨论。倡导“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苗长虹和王兵,2003),“与其削弱经济,还不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Lee and Wills,1997)。因此,重视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的作用,着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把握世界、国家和区域的时空变化,强调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来认识一个具体区域的基本特征,真正把握区域发展的本质,更准确、全面地认识地方多样性和地理差异,进而希望用地方性文化来抗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庞效民,2000),就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后现代社会,人们在关注生产与经济的同时,消费与文化也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讨的核心(Featherstone,1991)。西方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发生虽然源于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侵入和经济地理学者的积极回应。由于文化概念内涵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视角的多元性,决定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视角的多元性。
文化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促成了西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创新和变革。在研究对象上,文化转向促使经济地理学重视对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并关注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文化转向不再寻求决定性的因果规律,而是探索支持如果A成立则B成立的机制。同时,文化转向还对相关的区域研究和规划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苗长虹和王兵,2003)。但另外,文化转向也使原本内涵明确的一些常用概念定义模糊化,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内涵模糊的新概念,并严重削弱了经济地理学与政策实践的相关性,从而引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Markusen,1999)。
1.1.3 关系转向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伴随着公司地理研究的兴起和区域研究的深化,产业联系和区域联系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生产联系。与此同时,结构马克思主义虽然关注生产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决定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其忽视经济行为者的能动作用,因而其对“关系”理论的建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与“文化转向”,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有关劳动空间分工、地方性和弹性专业化的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不断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变,从而使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日益成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倡导经济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关系视角”或“关系经济地理学”(Amin,1998;Dicken and Malmberg,2001),杨伟聪认为,经济地理学这种“关系转向”的分析框架主要有3个方面(Yeung,2002):①地方与区域发展中“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涉及新产业空间、产业区、集群、学习型区域、全球城市中的马歇尔节点等热点领域。②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这种框架围绕着“网络”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一核心,涉及全球地方关系、组织空间的差别化生产、路径依赖、社会网络的关系杂合性与片段化(relational hybridity and fragmentation)、空间行动的多元逻辑与多重轨迹(multiple logics and trajectories)等研究领域。③关系的尺度(relational scales)。这种框架涉及长期困扰地理学研究的尺度地理问题,也涉及作为当前研究热点的全球化、城市与区域治理、地方劳动市场的社会管制等问题。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表明,“关系”、“网络”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之一。由于行为者关系网络的多中心性和杂合性,“关系转向”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新时空最为基本、最为通用的分析工具。它使经济地理学能够通过对各种行为者及其之间关系网络的分析,透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建构过程、各种行为者(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在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网络机制的演化,以及空间经济的管制和治理模式。
1.1.4 尺度转向
尺度是地理学领域一个无法回避并具有本体性质的关键问题。美国国家研究院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在其出版的?重新发现地理学?(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1997)的报告中强调,“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的方法,是地理学对科学认识的重要贡献。在地理学观察世界的三个“透镜”(地方的综合、地方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尺度间的相互依存性)中,对尺度的认识构成了地理认识论的基础,因为“谈论空间而不谈论尺度是不可能的”。但长期以来,作为空间科学的地理学一直用欧氏距离定义“空间尺度”,并将“空间”看做是地理过程的平台;而早期一些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则将“空间”看做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直到21世纪初,一些政治经济地理学家在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的争论中,才明确提出“尺度的地理学”(geographies of scales)和“尺度转向”问题(Brenner,2001)。这些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制度分析等学术思想中吸取营养,提出了“地理尺度是一种关系建构”、“社会关系是一种尺度建构”、“尺度重组”(rescaling)和尺度的“相对化”(relativization)等理论视角,并将尺度的社会政治建构看做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地域结果、城市与区域的管制和治理的关键。这些学者强调尺度的过程、演化、动态和社会政治竞争等性质,认为地理尺度是社会建构的,它本身也是参与社会建构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空间”不仅是不变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事先给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更是社会空间实践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和层级组织(hierarchy)。因此,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尺度”的“本体论”革命,它使经济地理学从关于尺度的“空间科学”而转向尺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e)。进而,有关尺度的层级、关系、过程和动力的研究,便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整个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论题之一。
1.2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
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相比,主流经济学则一直以其简洁、有力的理论预设及一贯的、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公认的首尾逻辑一致的分析方法著称。由于地理学的区域性和综合性,其自身严谨规范的理论建构向来较为薄弱,因而在地理学特别是经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