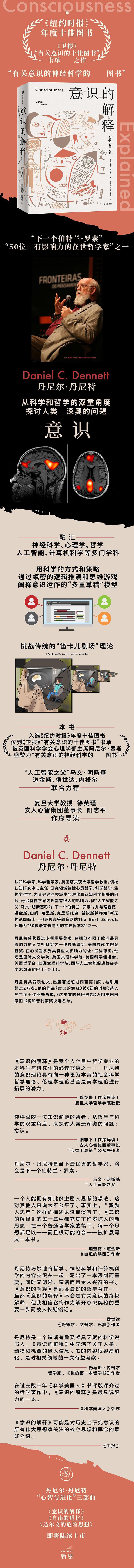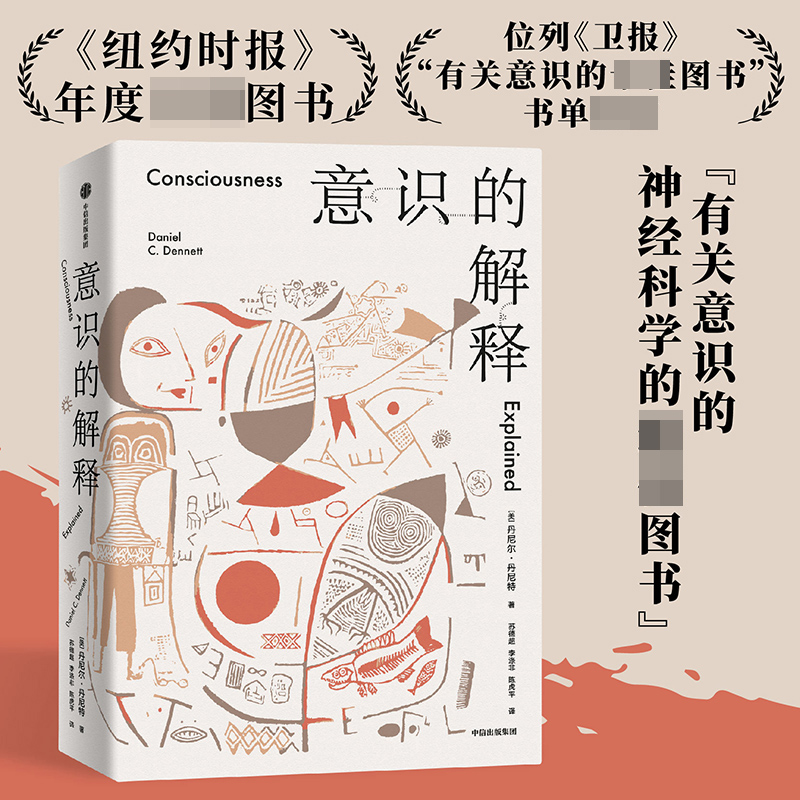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118.00
折扣价: 75.60
折扣购买: 意识的解释
ISBN: 9787521742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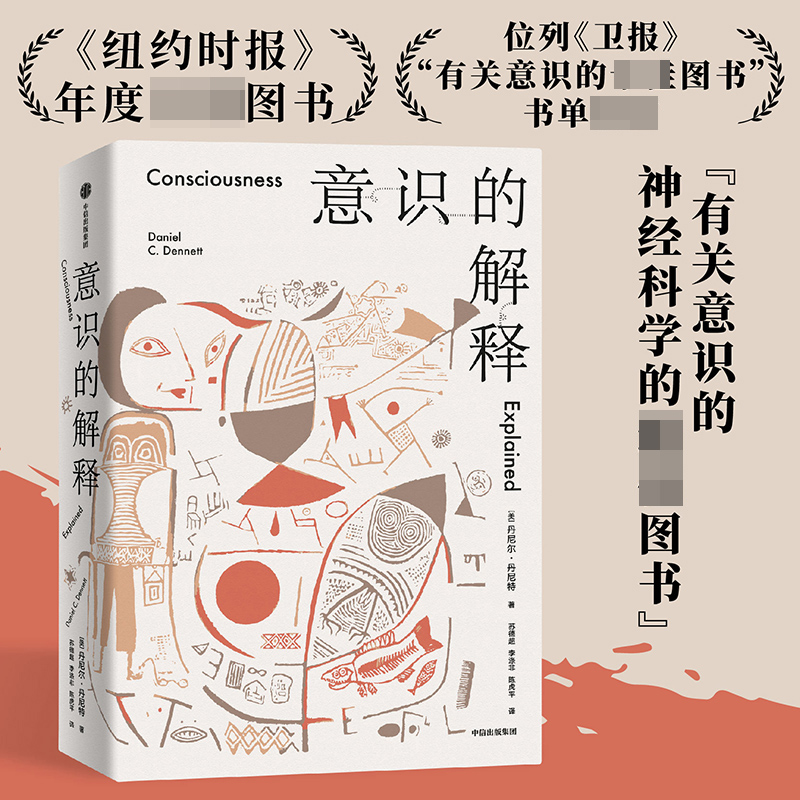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该校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进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丹尼特在学界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并与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并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他还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丹尼特曾获得过多项重要奖项,包括但不限于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文社科奖伊拉斯谟奖、美国成就学院金盘奖、在心灵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让·尼科德奖。他还是国际人文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哲学会、欧洲文理科学院、国际人工智能促进协会等学术组织的院士(会士)。 丹尼特共发表论文、出版著述超过四百篇(部),被引用超过2万次。他的作品《意识的解释》被《纽约时报》选入其年度十佳图书书单,《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决选名单。
第2章 解释意识 这儿有树,我知道它们粗糙的树皮;这儿有水,我感觉到它的味道。野草的气息,深夜的星星,心情放松的夜晚——我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力量与活力,我怎能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呢?然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我的。你向我描述这个世界,你教我对它进行分类。你列举这个世界的规律,在我渴望知识的时候,我承认这些规律是真的。你解剖它的机制,我的希望也随之增长……在如此多的努力中,我到底需要什么?这些山丘柔和的线条和抚平这颗受伤心灵的黑夜之手,教给我的反而更多。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 甜美是大自然唱出的歌谣; 我们理智,我们惹事 扭曲了事物形式的美好:—— 我们分析,我们凌迟。 威廉·华兹华斯,《把书桌掀翻》 人类的意识大概是最后尚存的谜团。所谓谜团,就是人们至今还不知如何去思考的现象。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别的重大谜团:宇宙起源之谜,生命与繁殖之谜,在自然中发现的设计之谜,时间、空间和引力之谜。在过去,这些谜团并非只是科学无知的地带,也是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和惊奇的领域。对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分子遗传学和进化论方面的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最后的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如何思考它们。这些谜团虽未消失,但已被驾驭。它们不再摧垮我们思考这些现象的研究活动,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分辨拙劣的问题和正确的问题,就算在目前公认的一些答案上,我们还犯有致命错误,但我们也知道如何着手去寻找更好的答案。 然而,对意识,我们却仍处在一种可怕的混乱状态之中。今天,唯有意识还是这样一个话题:它常常让哪怕是最为老练的思想家也张口结舌、无所适从。而且,与所有早先的谜团一样,还有许多人坚称并希望,意识绝不会被揭秘。 谜团毕竟是令人激动的,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乐趣。没人会喜欢一个扫兴的人把电影情节透露给等候入场的观影者。一旦真相大白,你就再也不能重新获得那种一度让你心驰神往的美妙神秘状态了。所以,读者要小心啊。如果我成功地解释了意识,那些继续阅读本书的读者就会失去神秘感,得到有关意识的初级科学知识。这种交换对某些读者来说可不是一场合算的交易。因为有的人视揭秘为渎神,所以我预计他们一开始就会把本书看作对理智的恶意破坏和对人类最后避难所的攻击。我想改变他们的想法。 加缪说,他不需要科学,因为他可以从山丘柔和的线条和黑夜之手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考虑到加缪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不会去挑战他的说法。科学并不回答所有的好问题。哲学也是如此。但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必保护意识现象,使之不被科学研究,或者不为我们正在从事的这类揭秘性质的哲学所研究;这个现象本身就令人迷惑,与加缪关注什么无关。有时,一些人由于害怕科学会像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分析,我们凌迟”,因而会受到一些哲学信条的吸引,这些信条据说可以提供这样那样的担保,抵挡科学的入侵。无论这些哲学信条是强是弱,他们的这些疑虑不安当然都有根据。的确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揭秘意识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不会出现:如果有什么损失,理解上的收益也完全可以抵消它;一个好的意识理论可以提供收益,既有科学的收益,也有社会的收益,既有理论的收益,也有道德的收益。 不过,意识的揭秘怎么会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呢?或许它就像失去孩提时的天真,就算这种失去得到了很好的补偿,那也确实是一种损失。例如,考虑这种情况:当我们变得更加世故时,我们的爱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骑士时代的骑士会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公主的荣誉,哪怕他从未与公主说过什么话——这是我大概十一二岁时特别心醉神迷的想法,但这可不是今天的成年人随便想想就能进入的心理状态。人们过去谈论和思考爱的方式,如今几乎不可能再有了——当然,除了儿童和那些能以某种方式抑制成人识见的人。我们都爱告诉自己所爱的人,我们爱他们,我们都爱从他们那里听到,我们为他们所爱——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爱是很单纯的,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确信我们知道爱是什么意思。 伴随着这种视角转变,我们是过得好些了还是坏些了呢?当然,这种转变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天真的成年人继续追捧哥特式浪漫文学,使其成为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而我们这些世故的读者,却发现自己已经根本不会为这类书的预想效果所动:看到它们,我们会咯咯发笑,而不是失声痛哭。如果这种书真让我们哭了——有时它们的确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哭起来——我们会觉得很尴尬:自己还在为这些廉价的把戏所感动。原因是我们无法轻易地处在女主人公的心智状态,她整天都在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找到“真爱”——好像真爱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就如黄金感情与黄铜感情一样不同)。这种成长不只体现在个体方面。我们的文化也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或者说,无论这种复杂是否有价值,都至少在整个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对爱的看法已经改变,这些改变又带来感性的转变,这些转变让我们无法再拥有那些曾经令我们先辈激动过、挫败过或充满活力的经验。 意识的情况与此类似。今天,我们也谈论我们有意识的决定和无意识的习惯,谈论我们享受的有意识的经验(我们跟自动取款机不同,那些机器就不具有这种经验),但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再确信,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还有思考者不依不饶地坚称,意识是一个真切的、珍贵的东西(就像爱,就像黄金),是一个“清楚明白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但是,人们的怀疑也在不断生长,我们怀疑这是一个假象。也许,共同诱发人们对某个神秘现象的感觉的各种现象,与让人认为爱是一种单纯的感觉的各种现象相比,也没有什么终极的或本质的统一性。 1. 与道金斯、侯世达齐名的思想家从科学与哲学的双重角度探讨人类最深奥的问题。 2. 本书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书单,位列英国《卫报》“有关意识的十佳图书”书单榜首,被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盛赞为“过去数十年间《科学美国人》书评版评介过的哲学著作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本”。 3. 神经科学家、英国科学学会心理学部主席阿尼尔·塞斯盛赞本书是“有关意识的神经科学的最佳图书”。 4.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屡获欧美人文、思想界大奖,是多家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组织的院士(会士),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5.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安人心智集团董事长阳志平作序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