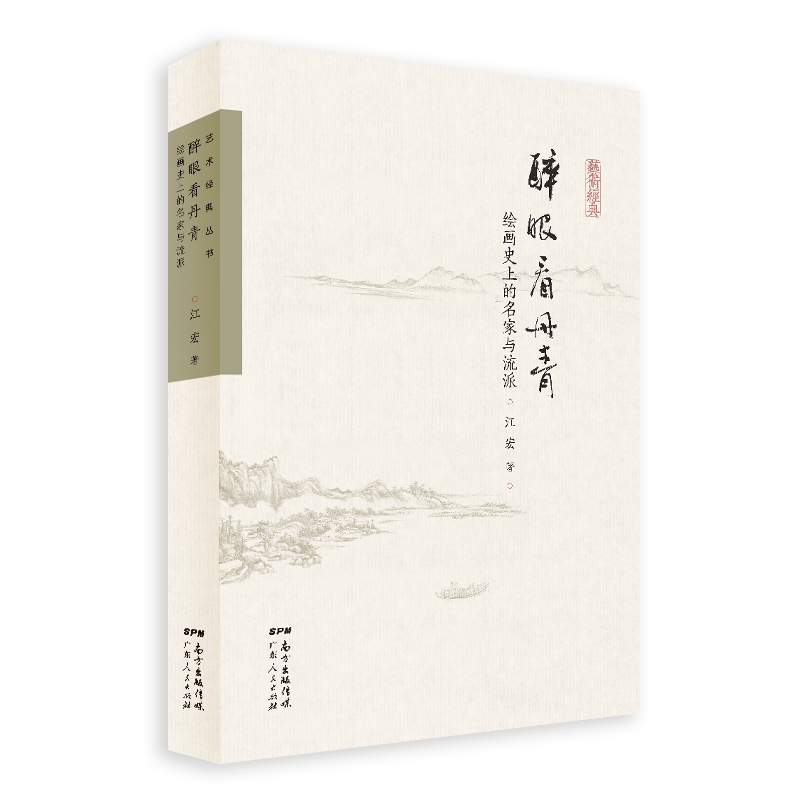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0.30
折扣购买: 醉眼看丹青--绘画史上的名家与流派
ISBN: 9787218134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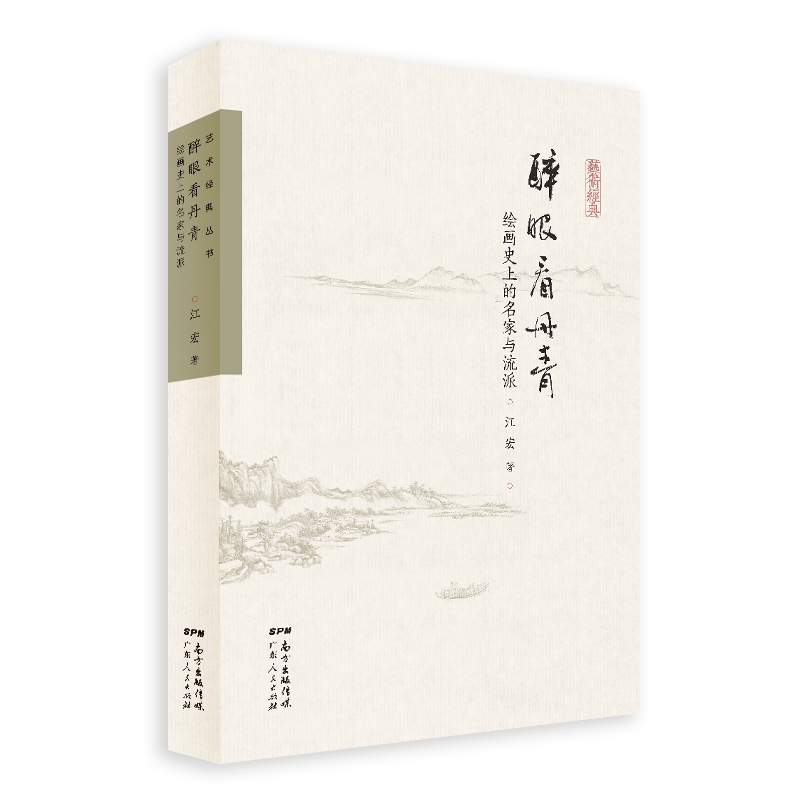
江宏,号恢翁,1949年生于上海书香世家,著名中国美术史学者、美术理论家、山水画家,曾任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现为上海美协理事、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江宏长年博研画论,创作出独具时代气息和个性的文人画。闲暇之余,江宏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生发过绘画意义的山川、古迹。
金农的画 金农,字寿门,又字司农,号冬心、稽留山民、耻在亭翁、昔耶居士、曲江外史、荆蛮民等,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金农一生经历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如此盛世,却没有给他敞开一条顺畅的仕途。其实,他不曾参加科举,唯一的一次被荐博学鸿词科,也不了了之。年轻时投何焯门下,原想借何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因何焯的罢官而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五十岁前,他东奔西走,“渡扬子,过淮阴,历齐、鲁、燕、赵而观帝京,自帝京趋嵩洛,之晋,之秦,之粤,之闽,达彭蠡,遵鄂渚,泛湘衡、漓江间”(金农《冬心画竹题记》),到处结交,用非凡的才能作触角去试探社会,并期望着权贵中的“伯乐”赏识自己,然而结果他还是以布衣终生。 五十岁后,金农在扬州和杭州两地生活,他的绘画生涯也开始于此。对金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大转折。常年的奔波,使他对社会、人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理想破灭后,他一方面安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采取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他既以绘画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又在绘画中澄其怀、畅其神,这个明智的选择,使他晚年凄凉的心境得以排遣。 记载上都说金农五十岁后开始作画,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下云: 金农“年五十余,始从事于画,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良由所见古迹多也”。《桐阴论画》、《墨林今话》、《清史稿》等均从此说。看来,金农五十岁后“从事于画”,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金农对绘画的兴趣,却由来已久。少年时,每逢上元节,随父亲去长时寺,观贯休十六轴《菩萨真形图》,这对他以后的佛像创作不无影响;二十岁那年,丁敬过其舍,金农以王翚《秋山行旅图》出示共赏;四十岁左右,他偶尔也舞弄画笔,曾作《兰竹图》,有诗曰: 写竹兼写兰,欹疏墨痕吐。一花与一枝,无媚有清苦。掷纸自太息,不入画师谱。酬人分精粗,妙语吾所取。钤以小私印,署名隶书古。半幅悬空斋,色香满岩坞。隐坐整日看,冷吟独闭户。饮水张玉琴,斜阳忽飞雨。(金农《画兰竹自题纸尾寄程五江二》,《冬心先生集》卷一) 从诗中看,画是属于兰竹小品一类,他自感“不入画师谱”,或是与行家尚有一定的距离,或是与时风相异,然而,他对此图是极满意的。“无媚有清苦”,当是金农的成熟画格,可见,这种画格,是他一直在摸索、追求的,经长期酝酿、发展,至五十岁以后,真正“从事于画”时,才让世人大开眼界。“涉笔即古”,原是一条有迹可循的绘画审美轨迹。金农的同乡钱杜说金农年四十始以己意学宋元写生,但这段时间金农无画迹留传,也不见其他记载。他会画却不常画。再往前看,康熙五十七年(1718),金农同厉鹗游吴兴,厉鹗有一首名为《督牛犁我田,欧阳圭斋句也。寿门为图,因题其后》的诗云: 高人思食力,所寄在扶犁。自是一生事,何知四体疲。乌犍行水浅,白鹭下田迟。缓缓逢邻叟,香秔问可宜。(《樊榭山房集》卷一) 这应是一幅农村风情画,由水田、农人、耕牛、白鹭众多形象组成,并不如兰竹那样是三两笔、五六撇所能了事的,画得如何,不得而知,但选择这样的题材,大概需要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当时金农三十二岁。 依我们的推测,金农很早就开始作画了,而且绘画题材不限于文人经常玩弄的兰竹之类。由于他不想在画上出头露角,只是在兴到情来时一展身手,也由于他能画,而画却不能像其诗文、书法那样让人心悦诚服,更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画会给生活带来何等光辉的前景。金农五十岁后“从事于画”,与其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不如认为是他大彻大悟的开始,与其说是他晚年的消遣,不如说是他人生辉煌的起点。金农在功名无望,前途迷茫时,已步入晚年,心境十分悲凉,他发现一片供自己尽情宣泄的土地,那就是绘画。他自跋《清风图》云:“老而无能,诗亦懒作,五七字句,谀人而已,可勿录也。然平生高岸之气尚在,尝于画竹满幅时,一寓己意。林下清风,惠贶不浅,观之者不从尘坌中求我,则得之矣。”(《画竹题记》)众所周知,金农最得意、最看重的是他的诗,诗也给他赢得了莫大的声誉。当年毛奇龄、朱彝尊、何焯、赵执信等诗坛学界的名流对他的诗推崇备至,他初到扬州时,就是以诗让时彦震惊,大名鼎鼎的陈壮履说他的诗:“如玉潭,如灵湫,汲绠之施,不息不穷。君非吾友,实吾师也,从此将执业称弟子云。”(《冬心续集》)而当金农在画中大大抒发自己平生的高岸之气时,他才找到了人的尊严,开通了通往人生至乐境界的路,以前引为荣耀的诗,竟成谀人之物。他不是在贬低自己的诗价,而是在反省。 应当看到,金农的诗,在诗家如林的清代也属佼佼者,他的画能够“涉笔即古”,和诗的渗透、书法的契入密切相关。可以说,金农的画,是诗意的笔墨化、书法的形象化。作为一个大诗人,他对事物的感觉是极其敏锐的。用诗的眼光、诗意的标准去衡量和把握事物的能力和他在佛、道哲学上的深厚功底以及书法的独创性等等,构成了他对美的悟性。如果说金农五十岁以前不常作画,那么,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备齐了不是所有画家都具有的画外功夫;如果说金农五十岁开始作画时在造型上尚欠火候,那么,他用素养构成的超一流的绘画感觉足以弥补此缺憾。而且,正是他在造型上的无法周全,才使丰富厚实的画外功夫水银泻地般毫无阻挡地进入属于绘画的领地,顺理成章地引发、开掘、拓展他独特的绘画语言。 因为发挥了画外功夫的优势,所以,画内的个性十分明显。我们知道,金农的时代,娄东、虞山两派已是强弩之末,新安派虽有些影响,但也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八大山人及石涛的余威尚在,时代在期待着有个性、有新意的画家。李鱓抛弃恽寿平、王武、蒋廷锡的画风,就是想在个性和新意上有所建树。李鱓是有造型基础和绘画功底的画家,他故意避开前人,选择与自己个性相近的狂放的风格,而金农则在绘画上几乎是张白纸,虽然也曾画过几笔,但终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他无法用绘画的因素去作绘画上的风格选择,他是用自己对绘画的理解,用自己的素养构成的绘画感觉,用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来树立自己的风格。这是一种纯粹的、不夹杂绘画偏见的,以个性为本、以情感为质的风格。他没有高举创新大旗,没有高喊创新口号,却画出了新意。别人梦寐以求的,他得来毫不费力,别人惨淡经营一辈子也未必可到的,他涉笔即成。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他只画自己想画的,不作旁骛。 根植在素养土壤里别开生面的画家,金农可称得上典型。他作画,完全依赖素养的发挥。当画情与诗意汇集到一处时,便有超常的发挥,他的山水小品,简直是无法用语言表现的诗: 景物寥落,却意境高妙,通过三五株长松,一两座奇峰,写尽万壑松风之趣。在狂风中凌乱飘舞的柳枝里,诉说无边春光;于拄杖老僧轻叩寺门的姿态中,见幽深寂静的山色;用采菱的轻舟,一展水乡生活的风情。在小天地里做大文章的画家,不啻低唱浅吟间见大手笔的诗人。蔬菜鲜果,这些寻常之物,经诗人手眼的拨弄竟清香四溢,充满着文人情调。金农七十三岁时画的自写真像,分赠朋友和学生,画自己的全身像,用极简的线描,精确地勾勒出自己的形象,神态更是惟妙惟肖。诗人捕捉形象的灵感,是如何转移到绘画上的?又如何达到这般出神入化的地步?真教人不可思议。这种超常的发挥,把金农推到了绘画奇才的位置。诗的影响,在画上无处不见,而书法的影响,却又是处处皆是。他选择梅、竹作为他绘画的主要题材,是因为这两种形象最适宜用书法笔法来表现。他擅长的隶书和独创的漆书,为他鲜明的墨梅、墨竹风格提供了笔法上的独特性。丰腴厚重的隶书笔法、清遒瘦劲的漆书笔法,能应付裕如地用作梅、竹的枝、干、花、叶,再加上画中可任意伸张、扩大的浓淡对比,金农的墨梅好作繁枝密花,在形象组合、堆砌中大过笔墨瘾,这是书法情怀的延伸,更有书法所无法达到的情感上的欢愉。金农的墨梅,可以说是他用书法素养营造的一个美轮美奂的黑白世界。金农的墨梅,尤其是繁枝密花式的作品,几乎没有败笔;金农的墨竹,没有常见的秀美劲挺,而是以他书法的特点为主导,甚至不惜闯入滞呆、木讷的禁区,我行我素。因为一旦偏离了他自己的笔法特性,就等于失去了他控制绘画的制高点。金农失败的作品,就在于没有或者根本无法发挥他书法素养的长处,当连诗意的支撑力也丧失的时候,他的画便不堪入目了。 然而,画再不堪入目,只要署上金农的名款,就会被人接受。金农以文学、书法的素养来调理绘画,而他在文学与书法上的名声,给他带来的社会效应,又帮助他解除了绘画上的窘境。他借着名声,借着社会对他的崇拜,借着大商贾附庸风雅的心理,用素养作画,跻身画家行列。文人参与绘画是由来已久的事,金农不因添上一个画家头衔而跌份掉价;文人画家参与经济,也由来已久,只不过金农所处的时代绘画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广泛。这种现象,是文人画家对他们曾不屑的金钱的就范呢,还是金钱把文人画家这尊神像请进了它的庙堂?也许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人画家的作品在金钱面前不会降格,他们可以依然故我地去作阳春白雪,经济阶层正以此来显示他们的风雅,从而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两者不是以经济关系的靠近来缩小审美差距的。因此,文人画家有着绝对的艺术自由,名声越大,自由就越多。“扬州八怪”的“怪”不正是个性适用艺术自由所致!又因此,金农的绘画成就,从某种角度讲,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绘画现象。这种现象集中在扬州,充分说明了经济与绘画合流是时代的潮流。 经济与绘画合流,引出了金农绘画的代笔问题。郑燮《高凤翰》诗: 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朋友交索予。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郑板桥集》) 当时求索名人字画的风气之盛,从诗中可见一斑。金农的作品“四方求索如云,得之珍同拱璧”(丁敬印跋),备受欢迎,他无暇应付众多的求索者,于是请自己的学生代笔,这是极其正常的事,他本人并不回避有代笔的事实。但是,近年来,金农代笔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危及金农画名的地步,有人认为金农不会画画,除那些不堪入目的作品外,都是罗聘、项均、陈彭的代笔。历史上大画家请人捉刀的为数不少,而金农受责难的症结在于他绘画基本功的浅薄。其实,金农绘画的好处和金农现象的重要意义,就是画外功夫在绘画上的成功,前面已作论述,不赘。金农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浙江风气,浙人的刚劲、奇崛成为金农绘画的基本格调,而这种格调,在金农以前的扬州是没有的,金农的同辈画家中也没有。金农的弟子罗聘是扬州人,项均是江都人,陈彭的籍贯不详,但陈彭为金农的仆人,在追随金农的十多年间,耳濡目染,接受主人的画风自不待言。罗聘、项均的画中有浙人风气,尽管稍嫌柔弱,但总由师传。再以罗、项两人的作品与金农相比,高下优劣相当明显。金农去世后,罗、项也没能拿出超过乃师的作品来。罗聘小金农四十六岁,金农“从事于画”时,罗聘还是个孩童,罗聘二十四岁入金农门,此前金农的画已具其成熟的格局。故宫博物院藏金农致罗聘的书札云: 是竹设色须鲜华而有古趣才妙,多留空处,以便题记复□一篇也。墨竹□前幅,不要过奇,墨汁半茶杯可了墨竹也。二马乘兴写之,必有可观也。幸俟秃笔扫骅骝,不足数矣。农小札,遁夫贤友足下。 请学生代笔的信中,仍可见老师的指导,指导的目的,当然是要代的笔像金农的画。所以,罗聘的代笔,始终没有脱离金农风格的笼罩。罗聘从金农中脱胎而来,是正常的。说老师的画像学生,那就本末倒置了。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画的文艺评论集,或读史、或言趣、或论法、或说论,杂中有序,条块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