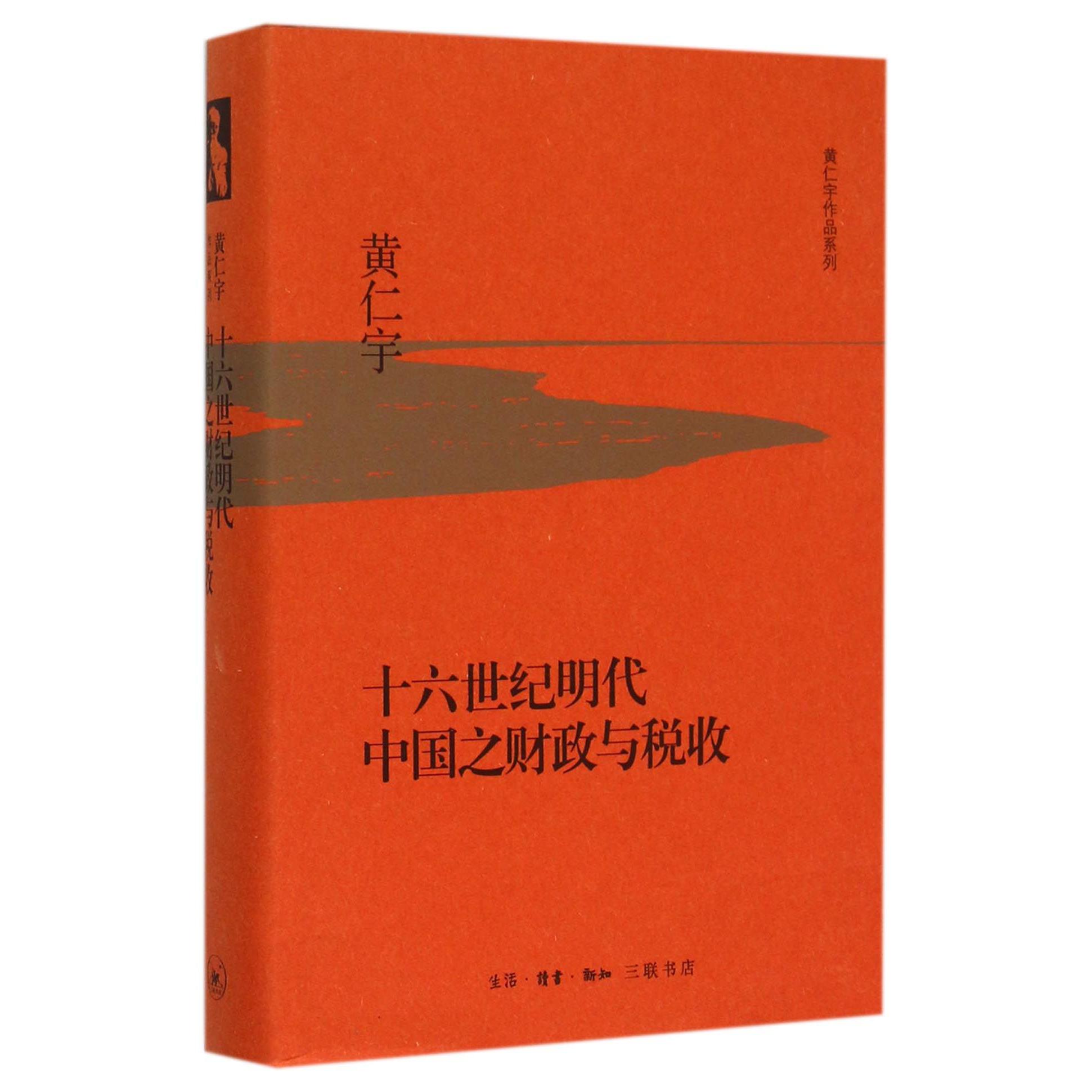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55.00
折扣价: 37.40
折扣购买: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精)/黄仁宇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53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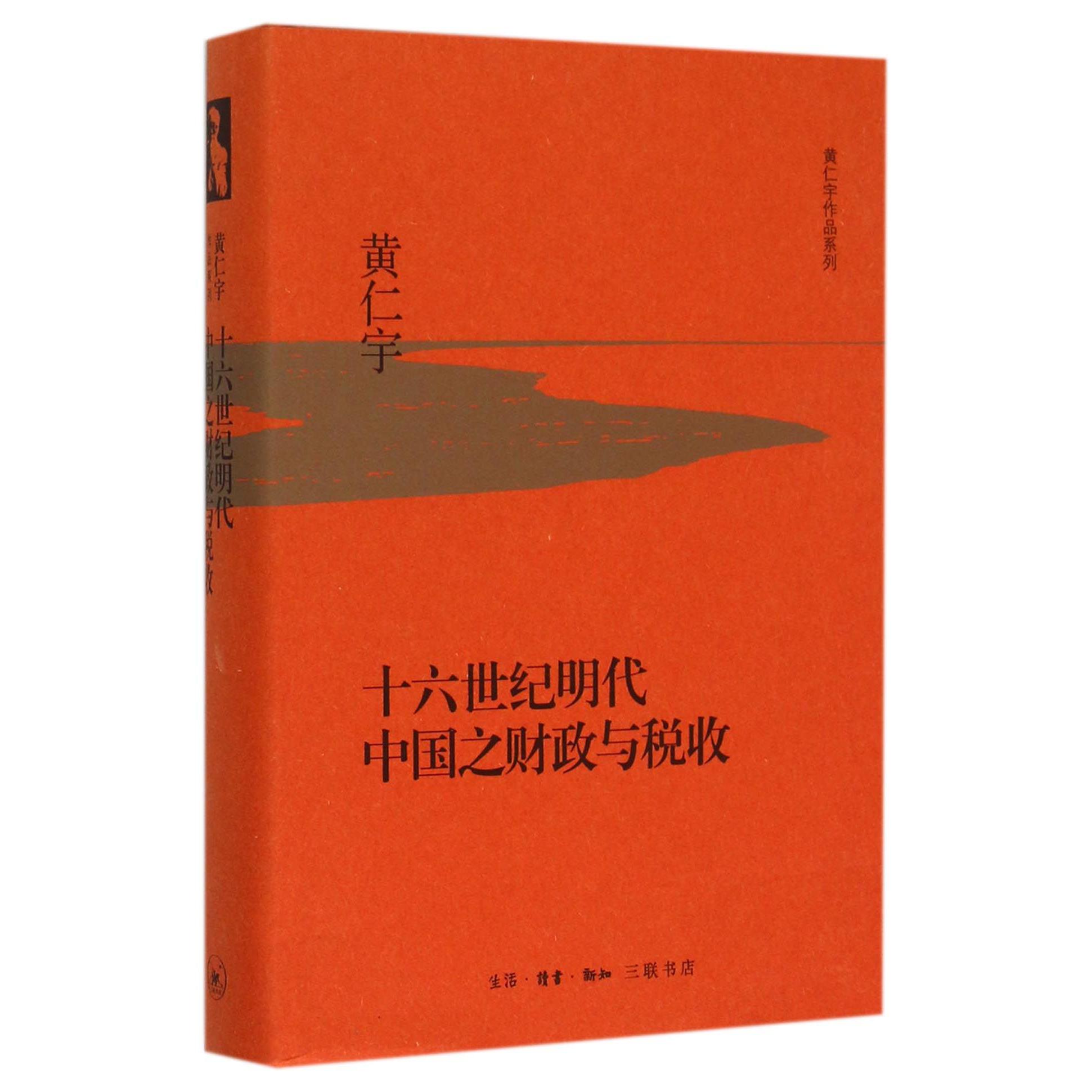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这种为了短期的政治目标而牺牲长期的经济发展 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明代的统 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 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欧小国,政府对工商业的 鼓励迅速地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在中国这样 的大国,却无法实现如此迅速而深远的变化。而且, 不像欧洲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也不像日本实力不断 增长的大名藩属,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 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 者自己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 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 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悲剧在于尽管他们提倡简明与划一,但是他 们的政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 所以明代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 国内部的多样性使得任何来自于中央的单一控制都是 不切实际的,在财政管理方面尤其如此。从农业方面 来讲,各地的气候、土壤、地形各异,劳动力情况不 同,农作物更是多种多样,还有市场、土地占有与租 佃关系的差异以及整个国家度量衡标准的不统一,朝 廷在首都制定法律,很难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宣布一 条统一的法律是一回事,但它是怎么贯彻到帝国的每 一个角落则是另外一回事,试图去弥合这种差异是没 有意义的。 按照许多晚明文人的观点:在王朝早期,帝国的 财政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仅仅到了晚期这种管理 才变得腐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部分。现在有充分 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帝国建立初期,政府的规定就已经 被变通执行了,皇帝的诏令打了折扣,官方的数据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篡改了。这不一定是官员不诚实造 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落 后的情况下,上层制定的财政方案无法与下层的具体 情况相适应,中央集权的愿望超出了当时的政府实现 这种愿望的技术手段。作为其结果,帝国的法律必须 进行调整,地方上进行改动与变通成为必要。确实, 在王朝后期,这种对规定程序的背离成为一种通行的 做法,对法律的普遍滥用则在所难免。 由于财政机构缺乏严格性,导致了很多恶果。一 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官员在财政上“拆东墙补西 墙”,一个项目的资金与物资短缺则由其他项目来填 补。我们所说的明代盐课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田赋。 而明中期以后,田赋与其他收入也混淆不清,无法分 开。明朝政府的收人与支出好像一条注入沼泽的河流 ,它有无数的分叉与会合。 这些复杂性不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明代的制度 多数难以准确地分类与定性,它们是不断变化的。这 种改变更多的是导因于外部情况的变化与管理者的操 纵与变通,而不是其自身的发展。在本书中,最大的 困难是把材料限制在—个主题之下而又不会令人眼花 缭乱,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选择依靠描述性语言而 不是数据表格。在这里,为了适应材料而对阐述问题 的顺序做了一些改动,各章节之主题也插入了互见式 引文。当然,这不是写财政史的理想方法,但这是一 种更现实的选择。 同样,本章也从多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我们可能 注意到,有明一代,除洪武朝以外,很少进行过官僚 机构改革。在它的二百七十六年中,实物经济转变成 货币经济,实物税收和强制徭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折 纳白银,佥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然而,令人惊 讶的是,即使到了明朝中期,很少建立起新的财政部 门,而被取消的财政部门则更少。做到这一点是可能 的,因为政府机构的职能并不总是被法规所固定住, 而是更多地依据习惯性做法。此外,管理措施很少被 新的法律所取代。新旧法令同时存在,有些荒唐的条 款完全被漠视,有些保存下来的条款根据隋况仍然应 用于个别的事例。事实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经历着 一种逐步变化的过程,他们的职能也不时进行调整。 有时候变化如此平缓以至于当时的人都无法察觉。因 此,这一绪篇不仅要讨论财政结构的形式,也同样要 讨论其变化。 P0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