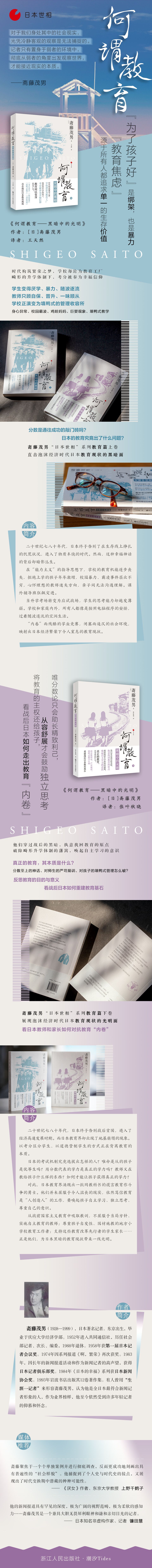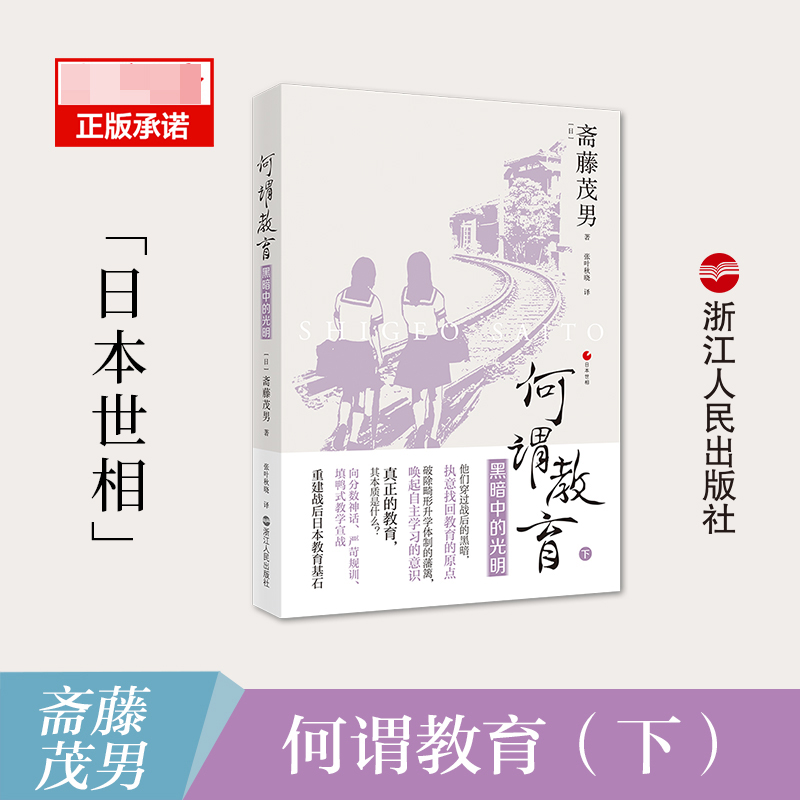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1.60
折扣购买: 何谓教育——黑暗中的光明
ISBN: 9787213105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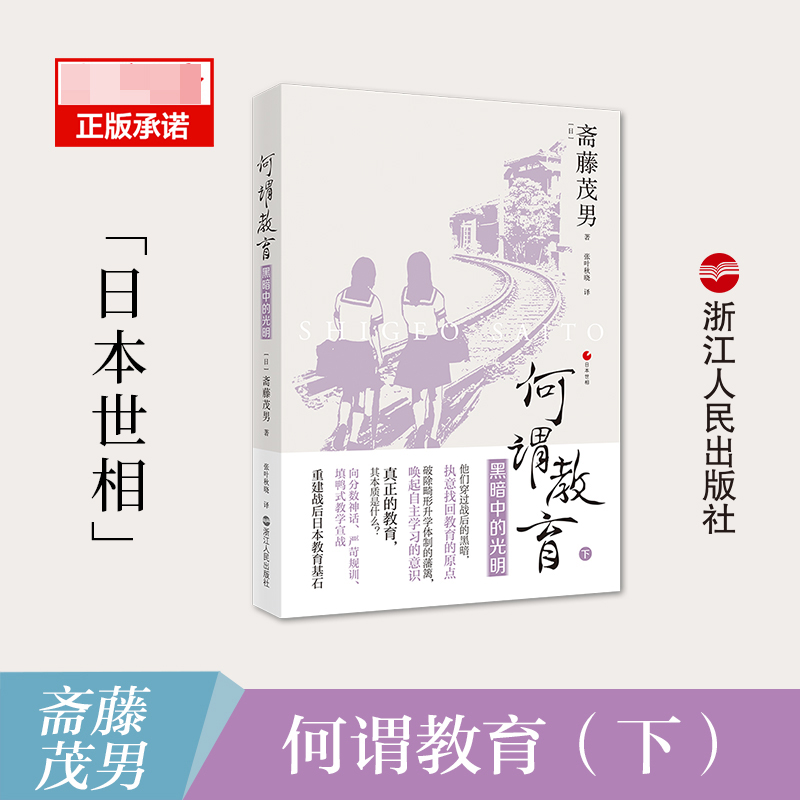
斋藤茂男(1928—1999),日本著名记者。东京出生,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1952年进入共同通信社,历任社会部记者、次长、编委,1988年退休。1958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奖。1974年因系列报道《啊,繁荣》再次获奖。1983年,因长年的新闻报道活动和作为新闻记者的高声望,获得日本记者俱乐部奖。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获日本新闻协会奖。1993年岩波书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对犹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实情的医生,斋藤说“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实情况”,让医生告知实情,像新闻采访一样用本子一一记录下自己的病况、还能做多少工作、延缓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选项等。这是他失去意识倒下的5天前的事。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
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神似配角的他 最开始,我们四处寻访着能成为采访对象的教师。 一位中年教师告诉我们:“盛冈的六太郎老师或许可以。可以采访他从战争时期开始直至今日的人生。嗯嗯,这个好……” 当我们随口向其他人问起“六太郎老师”时,对方竟也马上说“他可厉害了”。于是,我们拨通了六太郎老师的电话。 “哎呀哎呀,你们还得专门赶来多麻烦呀,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谈啊。行,行。”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六太郎老师骑着他的轻型摩托来到了我们在盛冈市内的约定地点。 头戴安全帽,一身西装,车后的行李架上固定着他那磨损了的旧包,六太郎老师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日本有一位叫西村晃的电影演员,是有名的电影配角,最擅长扮演那些妓院里物欲横流的老板、执拗的贫穷手工艺人以及市侩的小市民。如果抽出西村晃那股阴暗劲儿,再让他老一些,这和六太郎老师的形象就十分接近了。六太郎老师的眼睛很大,像是能看透世间万物,却丝毫不让人觉得藏着阴险,反倒有一种饱经风霜的温柔。 悲惨时代 吉田六太郎,五十九岁,盛冈市立上田小学校长。 他出身于盛冈市南部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现在的都南村)的一户穷苦农民家庭。幼时的他经常会拉着一车蔬菜去盛冈贩卖。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贫穷的小老百姓。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们,一心一意地为地主卖命就是我们唯一的生路。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请求地主能不能少收点地租,却总是被要求要送更多过去,也反抗不了。回到家里,一家人只能围在火炉边掉眼泪。父亲一边用火钳搅着灰,一边告诉我们,没办法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啊。” 夹在奥羽山脉和北上山地两大群山间的岩手县各村总是时不时地经历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六太郎上小学的时期正处于昭和初期,那时候正好赶上一战后的大萧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城市人口的回流使得农村生活雪上加霜。 来自当时日本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地区的进口便宜大米,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引起的蚕茧价格暴跌,这些都将当时的农民们推向了饿死的边缘。“岩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30%”“饥饿儿童剧增”——翻开当时的报纸,随处可见这样的新闻标题。女孩们被 迫卖身来养活父母与兄弟姐妹,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时代。 “死范”学校 “那时候,能进师范学校的都是认真的、学习好的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会给学生发拉舍尔毛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学校实行全寄宿制,伙食费、住宿费统统不需要,这些条件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毕业后还能当老师。” 那时候,相比从天蒙蒙亮开始就一直要劳作到深夜的农民生活,能穿拉舍尔毛制衣服、有饭吃的军队生活可要轻松多了。 将学生培养成“心地善良”“信人爱人”“德行高尚”的人 ,让为天皇国家奉献一切的“服从”精神渗透到每一个日本人的心中——这便是当时日本的师范学校肩负的特殊使命。 年少的六太郎在入学时就被教育“师范学校就是‘死范’学校”“教师的一言一行是所有人的范本,其终极意义便是死之模范”。 之后不久,学校便成了和军队一样戒律森严的地方,人们甚至说:“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师范学校是三大培养战争机器的地方。” 六太郎入学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五年战争的齿轮也由此开始转动。就在这一时期,一桩对于岩手师范的学生来说一生难忘的“事件”发生了。 “皇国教育”的脚步声 破型 六太郎入学时,岩手师范里有一位“不守规矩”的老师。他便是教授教育学课程同时身兼宿管职位的千喜良英之助老师(已故)。 在当时军事化管理氛围日渐浓厚的校园里,千喜良老师可以说是为学校带来了阵阵新风。 由于当时的学生大多出身于贫农家庭,总是接连不断地有人身患心肺疾病,他先是买下了十万平方米的农地,开始自己供应粮食,紧接着便新建了食堂、茶室,还破天荒地为清一色都是男生的宿舍招来了女宿管。他还开设保健室,请来护士,甚至让大家坐车去医院看病。此外,他还允许学生们使用大型电动洗衣机,让大家都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学校之前设有门禁,但千喜良老师认为,为人师、无信任、不教育,于是便废除了门禁。 “老师那时候经常喝了酒后,在晚自修时间来到我们学生宿舍,说:‘你们肯定没在学 习。’于是,我们就经常一起搞宿舍节的活动。所有学生都很崇拜他。”六太郎老师说道。 据当时最高年级(五年级)的级长、后来担任了盛冈市教育长的中村圭六说,千喜良老师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个你看书就知道了”。相反,他自己翻译了约翰?杜威的《教育学概论》,给学生讲授时也总是结合具体案例。“他引用的例子总是特别贴切,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血印请愿书 但是,这一自由主义式的教育终究还是被信奉“皇国史观”的县知事以及心怀不轨的学务课长给埋葬了。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面决定将千喜良老师派往冲绳。 消息一传开,都已经放暑假回家的全校学生立马赶回了学校。大家召开了学生大会,决议发起留任请愿运动。一夜之间,请愿书上就盖满了全校学生的血印。因不满校长、知事的回答,学生们还选出了代表,由他们去文部省直接上访。 当时有八名学生被选为代表,其中就包括中村级长 。由于车站里早已布满了县里的官员和便衣警察,八名学生换上了和服,藏在货舱与客舱之间,悄悄地前往东京。但是,东京上野站也早就被校长等人布下了眼线,上访文部省的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决心与县政府对抗到底的学生们一度聚集在学校的后山,誓不服从,最后还是千喜良老师亲自出面劝说,整件事才得以收场。紧接着的一天晚上,整个宿舍的同学为千喜良老师办了送别宴。六太郎老师回忆道。 “当时整个宿舍区有四幢宿舍楼,每一幢楼的代表都站起来致送别词。每个人都泣不成声。虽然学校禁止大家喝酒,但那天大家都喝了。南部牛方节《追马谣》,一首一首地接着唱。” 恩师出发的那天早上,学生们被禁止进入盛冈车站。 “我们呀,就去铁轨边目送老师。从车站一直到雫石川铁桥附近的整条铁路沿线,都是我们的人,大家都哭着喊着‘把老师还给我们’。” 暗转 早在那时,日本东北一带有志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教育运动的火苗——目睹着如此多穷困潦倒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高举“北方教育”的旗帜,通过生活作文让孩子们直面现实,即让学生们观察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努力培养他们批判、破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试图扑灭这一火焰的势头也在不断壮大。年少的六太郎在岩手师范里也目睹了不少学生被带走的景象。每当这种时候,千喜良老师都会悄悄和警察们交涉,将学生们保释出来。 “将这样一位好老师调走的势力,我们没理由不反抗它。”千喜良老师离开很久之后,不知道是谁在宿舍的墙壁上贴了这样一张檄文: ……距恩师离开已经过了多个春秋,可他留下的记忆却令人久久无法忘怀。当年岩手师范四百个因反对模仿西方衣着精致的风潮而衣冠不整的男生在人前流下了眼泪,可如今,恩师留下的赤诚之心是否正逐渐被大家忘却了呢? 以千喜良老师的下放事件为界,整个时代正以急促的脚步暗转。国家主义的思潮开始席卷整个教室与宿舍。 思考战后第三十一年的教育 地基崩塌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我们开着车奔走于岩手的各个村庄——见到了各位不同的教师、追寻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此过程中,许多老师都告诉我们,战后的日本教育界其实出现了地基崩塌的现象。变身、转向、背叛,他们用了不同的词汇,将自己在前辈、同事间看见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变化,生动地告诉给了我们。 X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变化起源于一九五五年,那时候战争结束不过十年。首先是学校的校长们,他们开始在学校运营的细节上主张用新的法律解释。每当和老师们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说这是‘理解不同’,这句话在当时甚至成了学校里的流行语。” 后来,在和罢工、国歌国旗相关的事情上,校长们开始滥用“职务命令”一词 。 X 先生告诉我们:“在那之前,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大家作为共同经历过战争的人,还总是有惺惺相惜的情愫在。每当提起当年作为‘军国教师’的经历,大家从不遮掩内心的歉疚。但是,从业务评定制度开始实施起,大家似乎逐渐与过去划清了界限。不仅仅是校长,一些日教组的干部也是一样。我亲眼见过一位干部在业务评定中钩心斗角,通过背后交易升为了教务主任。” 校长们不再说人话,他们如果继续说人话,就当不上校长——这句话也是出自当时。 就这样,战前的上命下服体制再次抬头,与此同时,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为学生排名的现代教育结构也逐渐形成。 发条娃娃 在六太郎老师的笔下,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以考试区分学生、以道德管制学生的结构”。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被视为优等生的孩子,他也给出了锐眼观察下的描述: (成为优等生的条件是) 对于朋友的失败与破灭能冷眼旁观,对于他人的冷漠眼神能麻木不仁,对于世间所有动态能不闻不问……可以说,优等生就是标准化产品的典型,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能极力迎合现代社会。他们会主动打磨自身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让自己成为一个圆滑的零部件……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些为其拧上发条就能按既定程式旋转的发条娃娃。 除了对优等生的形象作出的犀利刻画,六太郎老师也对当时教师们的模样进行了深刻描绘: 教师们让孩子们觉得自己的资质与能力都是从小就注定好的……将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民主的、尊重人权的教育,实属欺瞒……战败之前,教师们致力于为国家打造“忠孝之军”,而今,现代教师被迫培育出以优等生为代表的“平均水平的人”……若是想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让学生收获学习真理的快乐与感动,教师必须先从做回一个真正的人开始。 激情 同样作为战后的教师,有的以求自身安稳为行动最高准则,有的则完全相反,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事业之中。究竟是从哪个分岔路口开始,大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呢?对此,X 先生结合从战前时代继承下来的教师特质,这样评论道: “战前的教师,仅仅作为天皇的臣民存在着,通过自身的学问、伦理来思考、行动,都是不被允许的。当他们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激情时,却又不由得走向了对战争的热烈赞美。说起来,这也算是文学中日本浪漫派的想法吧。战败后国家支配教育的形式遭到否定,但教师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特质,也阻碍了他们去摘除那些自身应主动否定的部分。大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大概就是从‘八一五’战败体验开始的吧。是否将战败视作自身的责任,成了大家的主要分歧点。” 当时有一句口号是:“不要再把学生们送上战场了。”X先生 和我们讨论道,如果说这句口号在当今有什么现实意义,大概就是呼吁教师们要将每一个孩子、这些“未来”的体现者们,培养成能理解生命的尊贵与活着的喜悦、充满正义感、对同伴饱含善意、能体面生活的人。 岩手的各个村落终将迎来严峻的挑战。那个分校的孩子们,究竟过得怎么样呢?在和 X 先生聊起岩手的每一位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由得思考起了战后第三十一年的教育。 从壮丁村到流水线作业 壮丁产地 在长达十五年的战争中,岩手县为战争输送的士兵人数是全日本最多的。而岩手县送出的这些士兵,大多又来自坐落于北上高地崇山峻岭中的下闭伊郡各村落。从一九三四年各壮丁体格类别的数据来看,岩手县接受征兵体检的青年中,38.2% 为甲类合格,远超日本的县平均数据(30.8%)。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岩手作为贫困山区,婴幼儿死亡率极高, 而能在这种情况下存活下来的孩子们大多都有强健的体魄。后来,这些忠诚、勇敢的农民兵大多都战死沙场了。曾经的下闭伊郡安家村、现在的岩泉町大字安家也曾是这些士兵的故乡之一 。 从旧安家村的中心继续往里走六千米,在这里的一户农家, 我们见到了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婆婆。她的家人都在附近工作,见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娇小的身体几乎完全无法动弹。 她的儿子曾是独立步兵三〇三大队山崎部队的一员,一九四三年五月战死于美国阿图岛。关于儿子,她的手里只剩一张薄薄的遗书 。 遗书 母亲大人: 世事变化无常,小生如今即将离开祖国,留下告别之言。 正是因为从小被家人悉心呵护,小生才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作为军人在战场上出色地履行自己的光荣使命。 最后,小生立誓要报效天皇、报效祖国。 陆军二等兵 年年德藏 一九四二年十月吉日 二等兵德藏战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 教师的“本色” 作为壮丁产地的安家,如今正经受着高度增长的后果。一九六三年,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繁荣”的模式下,成长战争愈演愈烈。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和当时相比,整个安家的人口足足减少了三成。大家毫无例外地都是外出打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石田武夫老师(四十二岁)是在十年前来到安家中学的。 “作为父母,不再对孩子们留在农村抱有期待,任凭他们去喜欢的地方工作,但前提是不要给自己(父母)添麻烦。说要上大学的孩子自然是没有的,大家的学历也普遍偏低。孩子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否定了自己的可能性。这些因政策而被剥夺了生存基础的偏远山村的孩子们,要把他们培养成能直面现实且能迎面解决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难。说实话,当时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正如石田老师所言,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甚至关系到了教师们的生存状况。但是在安家这边听到的教师的“本色”,让我们陷入了沉思。 因被调到了偏远校区而退出组合的老师、拒绝参与罢工的老师,据说大家都是因为担心组合活动会推迟自己被“调离偏远校区”的日程,进而耽误自己的上升路径。据说还有老师身为组合委员却下指令让大家不要参加罢工,并以此为功帮助自己早日脱离偏远山区。 “买人” 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是“买人”的季节。曾经的校长们会接连带着印有企业人事主管头衔的名片来到安家。“你在这里也待了很久了吧,明年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你调出去”,这些校长以这样的话术让老师们去说服自己的毕业生。 我们找到了参与“买人”的一位老校长,宫五郎(六十七岁)。他原先担任过四所小学、中学的校长,现在在爱知制钢人事部工作。聊完了一些世间苦事后,他告诉我们:“有时候即使成绩好,比如那些学文学的孩子,因为不太能融入集体生活,企业也是不想要的。从这点来看,偏远地区的孩子正好。因为他们最听话,听话是最重要的。” 安家中学去年共有五十六名毕业生,今年春天是四十九名,其中有六成最后都去了企业。 “我以前也经常去送孩子们,一直会送到宫古的车站。集体就业的列车发车时心里的那种难受,真的受不了。孩子们也都忍 不住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作为消耗品去工作,用完就会被随手扔掉,但也没有别的办法。”石田老师说道。 那么,那些从安家出来的孩子们,现在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位当年的毕业生,Y子(十七岁),来到了她工作的地方——位于栃木县小山市的富士通小山工场。那是一家资本金为三百四十多亿日元、约有三万名员工的大型通信机器厂家,光是小山工场就有四千二百人。 Y子从事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作。每隔七分钟,传送带上就会送出一个小箱子,她要将里面的零件组装好。据说每天得经手六百多个零件,起薪五万六千二百日元。Y子住在员工宿舍,下班后会去非全日制的高中上课,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流水线上工作。她告诉我们:“其实我本来是想做幼儿园老师的,但可能不可以吧。” 晚上,我们去了Y子的宿舍。《Margaret》(集英社少女漫画杂志)、《周刊平凡》以及歌曲类电视节目,就像流水线上接连不断被送出的标准化零件一样,洁白的青春在空气中飘荡着。 ★ 将教育的主权还给孩子,拒绝为孩子的能力定价 ★ 唯分数论只会助长精致利己,从容舒展才会鼓励独立思考 ◎ 他们穿过战后的黑暗,执意找回教育的原点 ◎ 破除畸形升学体制的藩篱,唤起自主学习的意识 ◎ 真正的教育,其本质是什么?反思日本战后教育的目的与意义。 ◎ 斋藤茂男“日本世相”系列教育篇下卷,展现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教育现状的光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