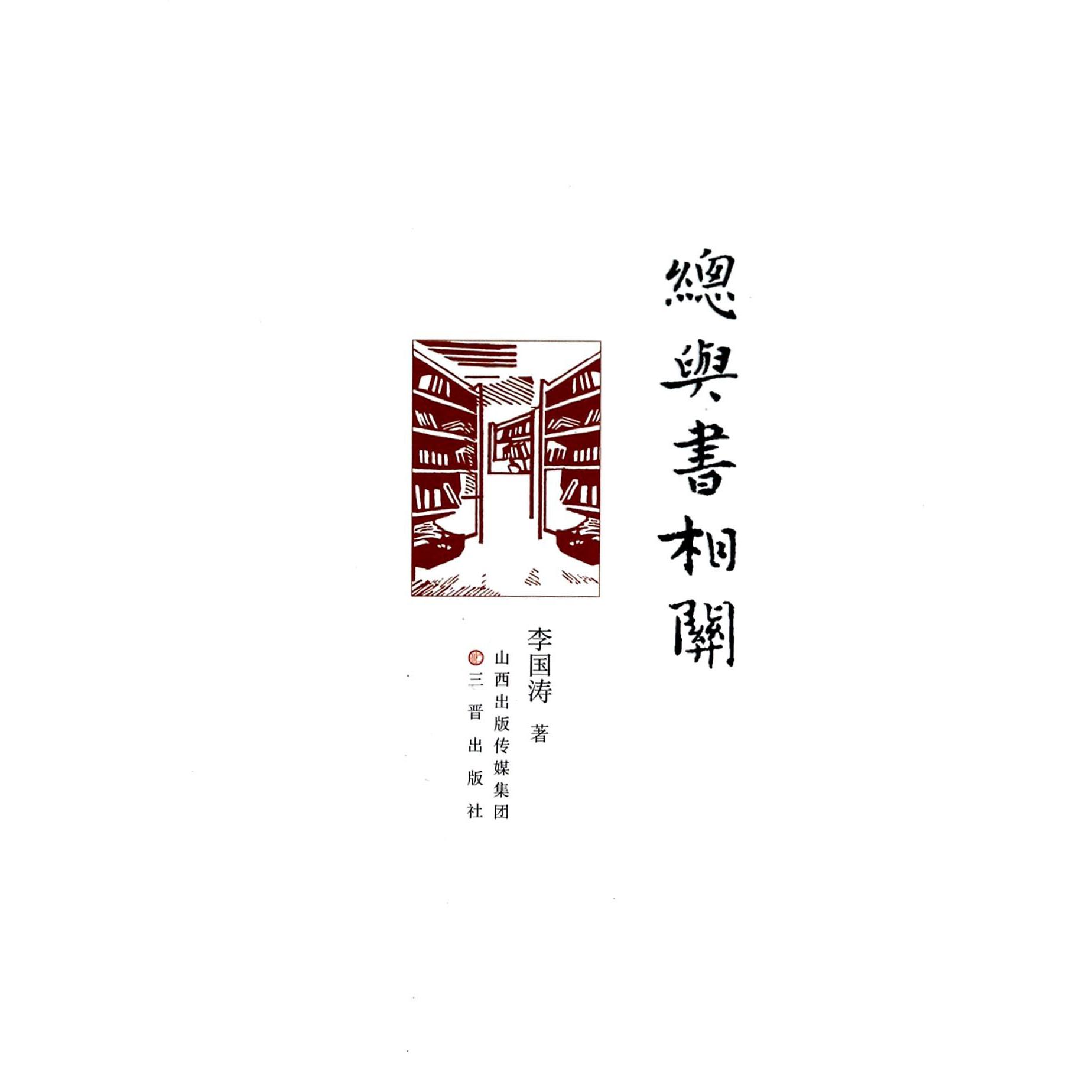
出版社: 三晋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2.80
折扣购买: 总与书相关
ISBN: 9787545707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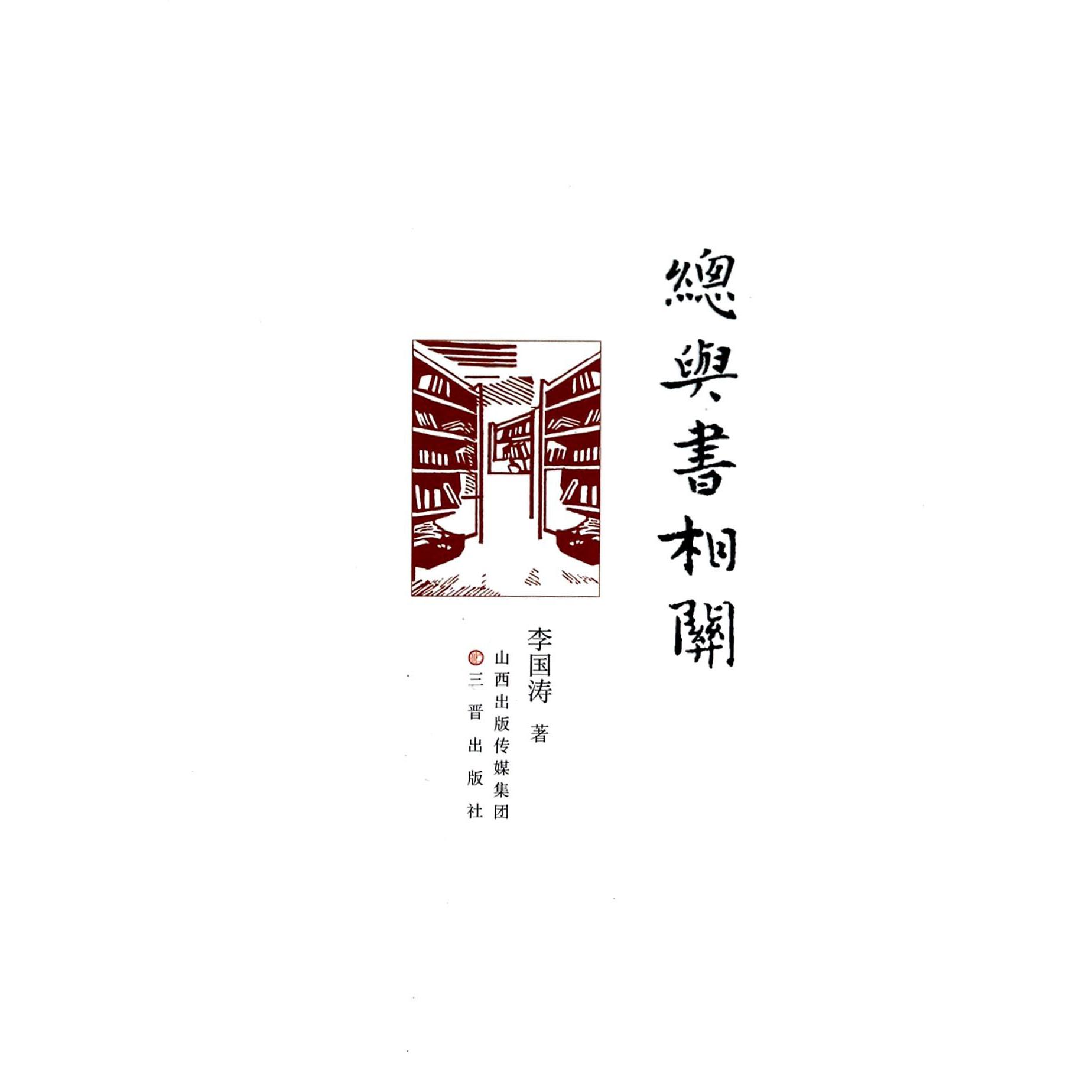
李国涛,男,一九三○年十一月生,江苏徐州人。喜写稿,乱投稿,偶发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任《山西文学》主编:一九九四年退休。
最近山西纪念傅山诞辰四○○周年,开讨论会, 出有关傅 山著作。我在此时读了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交往和应 酬》。该书 资料丰富,主要是谈傅山的“应酬”性的画作,其实 也是遗民当 时的社会处境。我就想到其他的遗民和一般的知识分 子与官 场。 明末清初的“遗民”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它实际上 突出了读书人的社会处境,,说明他们必须“应酬” 于世,必须与 官员交谈。凑巧我读到当时南北两位大遗民大学者, 在晚年为 他们自己的孙子写的托孤信,更有此感受。 南方的是黄宗羲。一六八0年,也就是康熙十九 年,黄宗羲 七十一岁。他写信与朝中官员徐干学,比之为宋代大 儒范仲淹, 继而说道:“又小孙黄蜀,余姚县童生,稍有文笔。 王公祖岁总科 考,求阁下预留一扎致之,希名案末。”这也就是说 ,孙子要考秀 才,他请徐干学给主考官一信,使小孙子榜上有名。 差不多同 时,康熙二十三年,北方大儒傅山,在二子傅眉死后 ,没过几个 月他自己也死去。他自知将死,死前上书朝廷大员魏 象枢托孤, 信中云“两孙孱少,内外眷属无可缓急者……(请求 您)使此两 孱少得安田亩间……”同时还给李振藻一信云:“愚 父子怛焉长 逝,特以两孙为托。孱弱无依,穷鸟不能不投长者之 怀也。”这些 信就写得十分哀凄动人,眷念弱孙,以托长者庇护。 而且托孤之 信,同时都附上傅山自己珍藏一生、不愿示人的最得 意的书法 作品,以表敬意。 它说明,遗老、贤士,不管多么清高孤傲,但是 那种态度和 处世方法,用于一时可以,也就是说,以刀兵相见, 义旗招展的 时候可以。但清政权稳定后,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 年以后呢? 遗民也要生活。全家活,子孙活,柴迷油盐,住家耕 地,官司税 务,你免不了就要托人办,或讨一个公道公平。比如 傅山家中来 了一位亲戚,打秋千,猝死于秋千架下。有人告,你 要洗去罪名, 这时你就要托人求情。找什么人?找平民穷光蛋行吗 ?不行。你 就少不了要找绅士,最好是官员,大官更好。要找人 ,临时抱佛 脚行吗?也不行。就要先拉关系,也就是“应酬”; 对许多人,由应 酬而生友谊,也是有的。因为官员中也有一代大儒、 一代文人, 他们也想与遗民相近。所以,应酬是少不了的。 傅山与山西当地官、商的关系非比一般,赠书法 ,看字画, 赠诗赠文,许多都是“应酬”,黄宗羲不写字,但写 文章“谀墓”, 也是少不得的。一个以画卖钱.一个以文卖钱。他们 也要生活! 实际上,康熙一朝开始不久,所谓明末遗民也就只以 不在清朝 做官为底线。子孙要科举,子孙要做官,自己交接官 员,都是可 以的。顾炎武在跋《石道人别传》(作者为傅山好友 戴廷拭)一文 中说:“行藏两途,人生一大节目……一失身百事瓦 裂,戒之戒 之。”所谓行、藏,就是当官与不当官,也即最后底 线。所谓遗民, 此后也就只此而已。你不能“应酬”于世。 上面说到的徐于学,就是一个例子,不但黄宗羲 找他,而且 遗民傅山与他也有关系。而徐干学正是大儒顾炎武的 外甥。说 来也巧,徐干学同顾、黄、傅都有关系,从徐干学身 上可以体会 到遗民们不得不应酬这样的人,甚至不单是应酬。徐 干学弟兄 三人在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分别考为状元和探花 ,每个人 都居高官。而这三位里,尤其是徐干学,在当地地方 上,近于恶 霸。当时朝中上下,议论颇多。可是谁不想依靠他呢 ?顾炎武有 这么三个外甥,才得以辞掉“博学鸿辞”的应试。并 且也因此,他 晚年居无定所,畅游黄河南北,每到一处都有地方官 员接待。这 与他的这一门亲戚大有关系。当然,必须说明,顾炎 武的成就和 文名,在海内早已确立,有点文化的官员还想巴结他 ,借他的光 为自己增色呢(黄宗羲、傅山也是如此)。于是黄宗羲 这样的高 人也向徐干学请托人情。傅山呢?也与徐于学有关系 ,当然很可 能是“应酬”。徐干学在为傅山的友人刘体仁的书写 序时曾说: “颖川刘公勇先生,天下骏雄秀杰士也……经太原特 访傅青主 于松庄,坐牛屋下对赋诗移日,其高尚如此。”如果 与傅山素无 往来,他能这样说吗? 傅山研究专家白谦慎说的很俏皮:“在这里,赋 的什么诗, 赋的好不好并不重要,只要能和傅山一起在牛屋下赋 诗移日, 在清初便已经是‘高尚如此’了!”傅山谈及那些官 员,也就难免 有些过头的话。黄宗羲后来也是称清为“国朝”,称 康熙为“圣天 子”,与当年大大不同了。顾炎武经济情况好像好一 点,不必多 求人,但每到一地,对官员们说几句好话,怕也是难 免的。明清 的恩仇和界线,在遗民身上和心理,也慢慢淡出了。 二○○七年九月三日P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