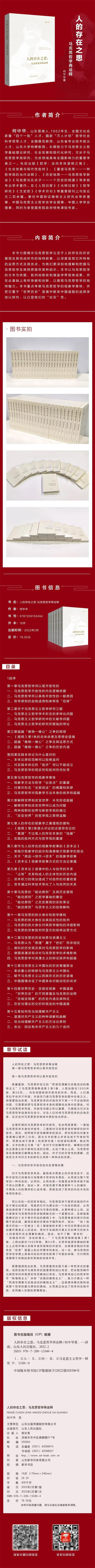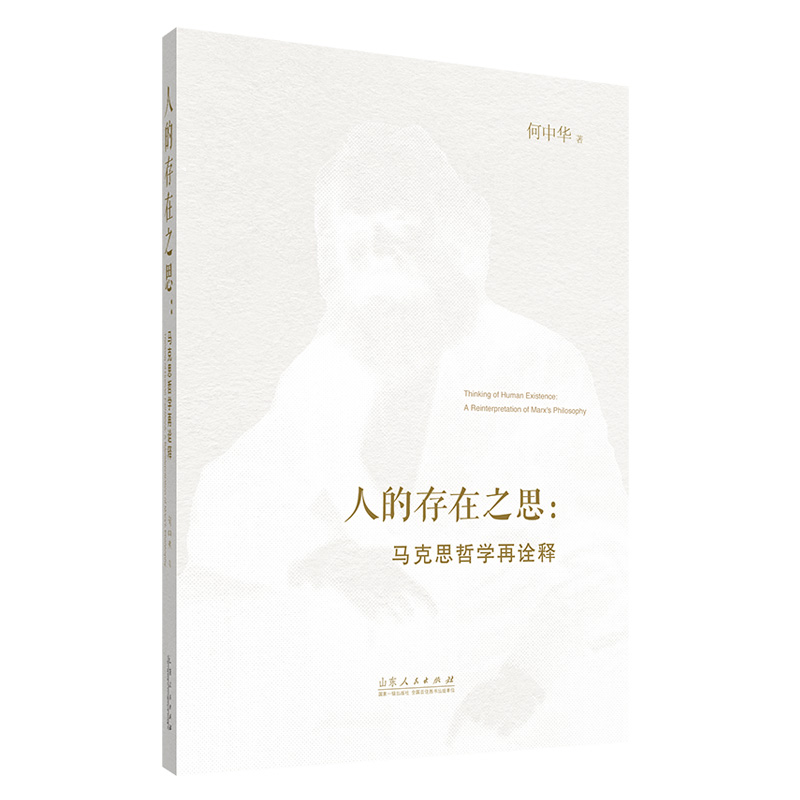
出版社: 山东人民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34.00
折扣购买: 人的存在之思:马克思哲学再诠释
ISBN: 9787209133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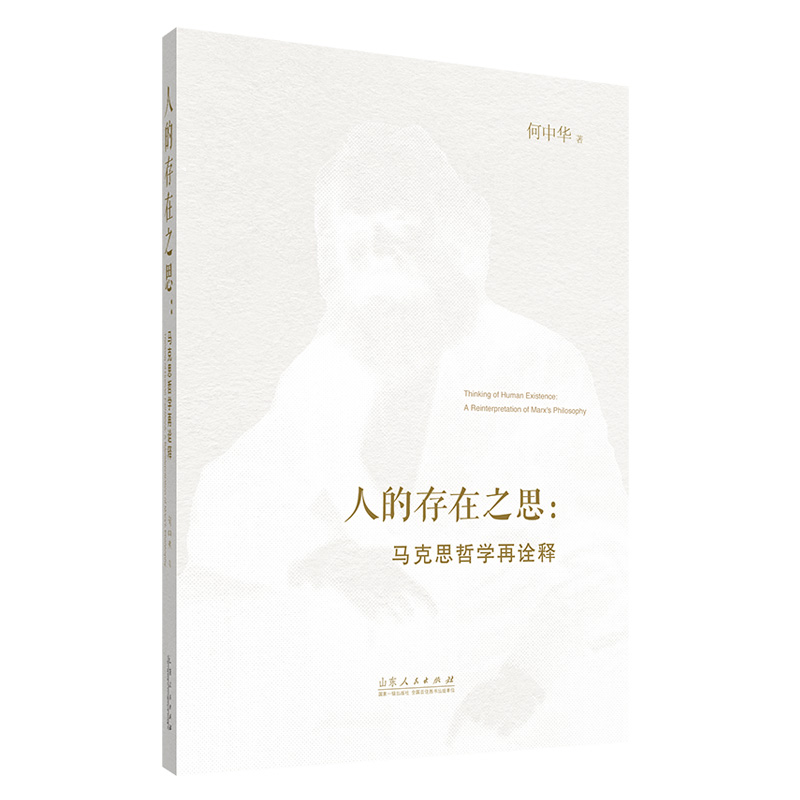
何中华,山东莒南人,1962年生,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大学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研究,尤长于马克思哲学观研究,为该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之一。先后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等重要报刊上刊发论文二百余篇。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同时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人的存在之思:马克思哲学再诠释 第一章马克思哲学何以是开放性的 第一章马克思哲学何以是开放性的 毋庸置疑,马克思所创立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内在地固有其开放性的诉求。而且,人们通常似乎也并不怀疑,开放性乃是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它需要按照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理路给出其内在理由。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开放性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涉及马克思哲学自身的生命力,涉及人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应有态度,还涉及对马克思哲学独特本质的恰当领会。 这里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开放性,二是指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研究的开放性。其实,按照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观点,研究和研究对象本身是难以截然二分的。因为文本的意义并非完成于作者的写作,而是完成于读者(包括研究者)的阅读和阐释。就此而言,文本的意义乃是“活”在对于它的解释中的,解释的过程也正是意义的不断地生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总是被我们解释出来的。因此,对于它的开放性的理解,应该在文本与对文本的研究之间持一种辩证的态度。 一、马克思哲学开放性的内在逻辑依据 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开放性在于,这种开放性已经被先行地植根于哲学的本原处,从而成为整个哲学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从而也是一旦接受这种哲学就不能不肯认的要求。如此一来,开放性便不再是某种个人的偏好,不再是人们的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变成了哲学的内在本性的体现和表征。 同以往的一切旧哲学相比,马克思哲学不是把实践视作外在于理论的规定,而是把它作为理论的一个内在的规定,从而使自身获得了开放性的最为可靠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乃是青年马克思同旧哲学割席断交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那篇里程碑式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曾对费尔巴哈瞧不起实践、鄙视实践的态度给予强烈批评,指出:“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从哲学始源性基础的意义上正视并确认实践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无疑是实践的开放性在“反思”层面上的必然要求和表达。这一点,使马克思的哲学在学理上具有内在的开放性获得了可靠的保障,它归根到底植根于实践自身所固有的创造本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重视实践乃是一种哲学式的重视。他把实践作为其哲学的首要原则加以肯定,把实践范畴作为其哲学的终极原初性范畴加以肯定。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作“新唯物主义”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致力于建立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就意味着实践构成其整个哲学的最为原初的基础,从而真正给出了哲学向实践开放、进而融入实践的逻辑理由。 人的存在之所以异于一切非人的存在,其本质的差别就在于只有人的存在才是超越性和创造性的,而不是宿命的。这归根到底是由实践塑造的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决定的。实践本身是生成性的,而非预成性的,它能动地建构着人的独特存在方式。作为能动的建构活动,实践使人成为一种积极地实现其本质的存在。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他的生物学限制的物种,而这只有借助于实践这一创造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它意味着人的存在是发明性的而非发现性的。因此,实践意味着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正因为马克思哲学地把握了实践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基础,所以他才能够对哲学之为哲学所必须追求的超验性给予根本的改造,从而使其由宗教神学和旧式本体论的含义,彻底转变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亦即“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种“批判”或“改变”,无疑是对经验世界的超越,但它不再像旧哲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彼岸世界的真理”给予思辨的肯定和追求,而是通过实际的感性活动来“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但这并不是对超验性的拒斥,而是超验性本身的实现和表达。应该说,这才是一种最为本真的开放性,它植根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本身。马克思以其哲学的把握,将这种存在方式的特质以自觉的形式凸显了出来。 实践的生成性意味着前提与结果之间的非对称性和不可逆性,这正是历史性(而非历时性)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只有实践所塑造的人的存在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而不是历时性的。实践使人成为“此在”(Dasein)性的,而实践的生成性塑造并决定了人的此在的历史性。奠基于实践之上的马克思哲学,必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当然,有无“历史感”并不是马克思哲学同非马克思哲学划界的一个标准,黑格尔哲学同样有“巨大的历史感”(恩格斯语)。问题仅仅在于,这种历史感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由于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自身的原初基础,就本能地具有了契入现实、契入历史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实践的本体论地位的确立,使得整个马克思哲学获得了真实的历史感,从而克服并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那种以逻辑为根基的虚假的“历史感”。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这意味着离开了历史,哲学就将丧失自身的合法性,从而不能成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为自己确立了建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的使命。这意味着离开了历史,哲学就将丧失服务对象,从而变得没有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不能不承认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才真正地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之中了。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即使是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同马克思对话的资格。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写道:“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里是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维度同其异化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异化与历史性的内在关联究竟何在?诚如日本学者城塚登所指出的,“可以说,异化的逻辑只能建立在极为强烈的历史意识上。异化的逻辑与其说是在历史意识淡薄的启蒙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倒不如说是在力求克服启蒙(思想上)的黑格尔那里形成的。”[日]城塚登:《异化的逻辑和历史意识》,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合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无论是海德格尔暗示马克思是由异化出发而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还是城塚登所谓的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由历史意识而揭示了异化,都显示出异化同历史性之间不可剥离的紧密联系。但仅仅局限于承认这一点,更进一步的问题尚未触及,那就是异化同历史性其实仍然属于同一层面的规定,决定它们的共同基础实际上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所确立的那个原初范畴,亦即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这才是真实的根基。一般地说,异化是历史展开并完成自身的一个内在环节,而历史构成异化得以生成和消解的条件,两者都不过是实践的产物。人的实存同本质的分裂与统一,都只是实践的内在矛盾及其扬弃的历史表现而已。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而“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马克思还说过:“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而私有财产与异化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见,正是实践才赋予了人的存在以历史性的形式。 承认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必须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角色现身。这是向实践开放的最为纯朴的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家和革命家这两个角色是高度地集于一身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原本就是同义词。总之,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原初范畴予以奠基,使他的哲学获得了不断地与实践对话、与时代对话、与历史对话的内在诉求。这样的哲学必然要求人们不断地回到由实践决定并塑造的“此在”性的历史场景,从而做到与时俱进,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由“思想”向“学术”的转向。建立纯学术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和传统,其动机也许是试图恢复研究的科学性,但若把这种科学性理解为纯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立场和真谛。今天的学者似乎更在乎人们尤其是主流学术圈是否把他看成是一个地道的“学者”,而不太注重他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与现实的联系。法国学者阿隆曾批评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重建”方式,讽刺地指出:“这种重建是哲学家或神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工作。虽然这种重建需要‘经验的’调查(我对年轻一代的轻视不屑一顾),也就是认识在工业化社会中各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本质,然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却是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结果”[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阿隆的批评在有限的意义上是对的,即马克思终结了思辨哲学传统之后,其后继者们又复活了经学传统。这是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一个客观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是作为一个实际的运思者而存在的,但在他身后却留下了一个把他的思想加以对象化和主题化的任务。可是,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却忽视了一个危险,即在这样做的同时遗忘了其合理性限度。我们需要时刻反省: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才是恰当的?像马克思那样去做,还是把马克思当作文本去予以挑拣或阐释?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研究的经院化倾向,完全遗忘了马克思当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发出的深刻批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局限于“书斋里爆发革命”是无从真正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也谈不上真正领会并把握其实质和精髓。以遮蔽马克思哲学的特质为代价的研究,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葬送性的。毛泽东当年就曾提出“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的任务,并认为唯有这样,方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 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究竟应该如何建构才恰当?回顾一下思想史也许不无裨益。费尔巴哈当年之所以未能完成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任务,不能不归咎于他半是主动半是被动地“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从而远离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马克思则不然,他不仅直接介入实践,而且如梅林所言,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懂得德国哲学,而且也懂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嬗变有一个逆马克思心路历程之逻辑的“倒转”,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这一逆向发展,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抑或堕落呢?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东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却以其“实践能力的明证”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并因此显示出“理论的彻底性”。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因为“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銛、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这一逆向路径,面临着马克思曾经彻底摆脱了的那种思辨化的危险。这无疑是一种倒退。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的处理方式。总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唯有向实践开放,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哲学,并使之真正地“活”起来。 马克思哲学不是“过去完成时”的,而是“现在进行时”的;它不是一堆“死”的知识,而是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其采取恰当的看待方式。需要加以追问的是,究竟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参与者”来同马克思哲学照面才恰当?海德格尔曾经区分了“当下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状态”。这一区分意义重大,它对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进入“当下上手状态”,事物的本质才能向我们敞开;而在“现成在手状态”下,这种本质是向我们幽闭的。他以“锤子”为例,只有进入实际的敲打这一上手状态,锤子才成其为锤子,它的本质才得以开显。若将其放在手中把玩,它无非就是一个与锤子无关的普通之物。如此一来,锤子也就不成其为锤子,我们因而不能同锤子的本质照面。所以,海德格尔说:“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6页。对于马克思哲学,我们也应采取这种“上手状态”,如此这般才能使哲学的本质以其本真的方式向我们敞开。这种“上手状态”,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可供定义、分类、挑选、组合的“死”的知识,而是体现在我们的实际思考中的运思方式。 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史事实是,马克思从来都不把自己的哲学本身加以主题化,从而避免使自身沦为一种被定义的对象。我们很难从其哲学中发现定义性的表述。正如贝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指出的,“马克思从不提供任何定义”。这意味着马克思是在“做哲学”,而不是在“说哲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未真正读出这一特点。因此,“在马克思的文献中,‘展示’(revelation)被人们大大忽视了,其实它同‘解释’(explanation)一起,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后者不可能与前者分开”朱培:《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曼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第31页。。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所采取的姿态,与其说是语义学的倒不如说是语用学的更恰当。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通过下定义的方法去“谈论”哲学,而是通过实际的运思去“显现”哲学。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动词性的而不是名词性的。倘若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采取一种旁观者的立场,就不可能真正捕捉到这种哲学。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必须采取“此在”的方式,亦即要“哲学”起来。这样一来,哲学就不再是“死”的已成之物,而是作为一种向任何可能的方成之物开放的运思方式。人们总是说,哲学不在于研究什么,而仅仅在于如何研究。这就关乎运思方式本身,它真正涉及的不是研究的内容,而是研究的方式。 马克思以其全部著作,向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得出了那些个别结论,而且是他的一条运思道路。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也更能够代表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用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对自己的心路历程予以回顾和叙述,其用意显然不是要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演进的时间表,而是旨在表明他是如何展开其运思过程的。马克思所给出的是一种“指示”,而不是一种“刻画”。指示,就是揭示一条路径,从而指明或显现一种可能性。“刻画”的对象乃一“已成之物”,而“指示”则仅仅是昭示一种朝向未来的可能性。换言之,它开启一种恰当的运思方式及其蕴含的向未来敞开着的全部可能性。海德格尔的弟子比梅尔曾说:海德格尔不喜欢叙述他已发现的东西,而是要展示发现过程本身,愿意把他的著作作为道路来理解,并指出这是海德格尔毕生的决定性风格参见熊伟:《自由的真谛》,载熊伟:《在的澄明——熊伟文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6页。。其实,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应该说,马克思早已先于海德格尔这么做了。在已成与方成的关系中,马克思更注重从后者的视角去把握事物的自我绽现,且在自我参与中去把握;而不是作为旁观者、作为一个他者,去外在地把握作为已成之物的对象。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前言”中说过:读他的这本著作,“读者会感到自己被带到一条道路上了,这条道路是一位作者先已行走过的,而该作者碰巧作为auctor(作者、创始者)引发一种augere,即一种让生长”[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这里充满现象学意味:它不是描述一条道路让读者作为旁观者去“观看”,而是引领其思想“上路”。我们应该设想,假如马克思活在当下,他会从理论上对我们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及其蕴含的真问题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作出像马克思那样的学理反思和理论贡献呢?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是否在原本的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个真正的考验。 马克思当年所建构的哲学试图向人们提供的只是一种运思方式,而非现成的答案。对于教条主义,没有谁能够比马克思更深恶痛绝和排斥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南。青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通信中,就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他强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他还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马克思当年之所以一再坚决拒绝“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谓,其中的一个重要用心就在于他担忧自己的学说被当作一种供外在地旁观并已经终结了的封闭规定,被误解为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的永恒不变的信条,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它面前,人们“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值得深思的是,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作为一个极为严格的批判者,从不满足于自己的结论,反而却被变为最顽固的教条主义的肇端”[芬兰]维萨?奥特宁:《MEGA2与另一个马克思——马塞罗?默斯托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8期,第2页。。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当成了一种仅仅供旁观的研究对象。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教条主义的真正有效的“解毒剂”?传统上一般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乃是剪除教条主义的“不二法门”。诚然如此。但更深刻的路径则在于,调整看待哲学的方式本身。海德格尔在《什么是思想?》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经年累月地钻研伟大思想家们的论文和著作,这一事实仍不能担保我们自身正在思想,或者哪怕只是准备去学习思想。这种哲学研究活动甚至可能最顽固地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我们在思想,因为我们确实在‘做哲学’嘛。”[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8页。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一误区,就是因为对待哲学的态度一开始就是错的。而只有“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召唤思想的东西”[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5页。。海德格尔在这里所确立的乃是“此在”的态度和内在性的姿态。这同那种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哲学的态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