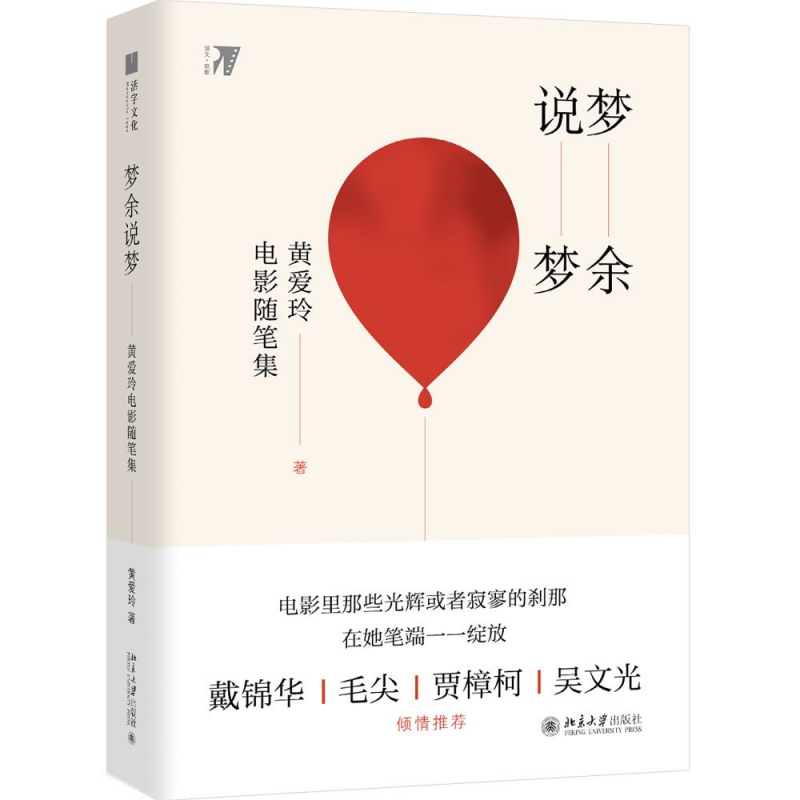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76.00
折扣价: 49.40
折扣购买: 梦余说梦(黄爱玲电影随笔集)(精)
ISBN: 9787301295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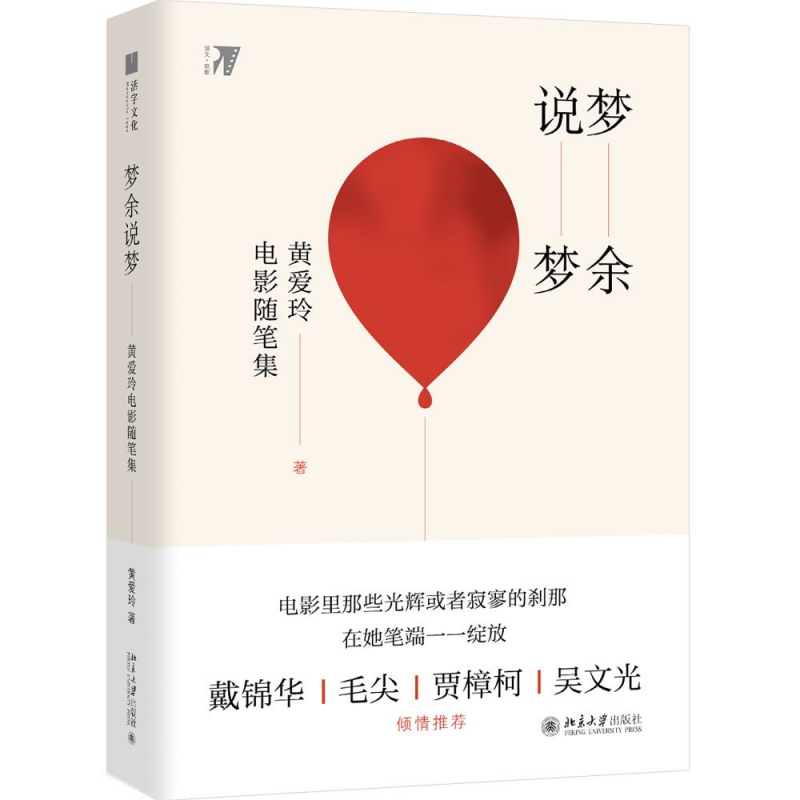
黄爱玲,资深影评人。1976—1985年游学法国,攻读电影,曾担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部负责人、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在电影资料馆工作期间,黄爱玲结合大量丰富的资料,历年编著了香港电影研究专著十多部,并参与影片修复计划。其编著的《诗人导演——费穆》一书被公认为最具分量的费穆研究专书。
废墟里的春天 我不能撒谎,说田壮壮的《小城之春》(2002)比费穆的原作好看,费穆当年拍摄这部小品,很有举重若轻的气度,在优雅中见随意,在矜哀中有坚持;单就新版本的女主角胡靖钒来说,她的气质虽然好,可就是没法跟韦伟比,后者手拿丝巾半遮着面的风情,怎么也“克隆”不了,那是一种魅力,跟演技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今天看田壮壮的这部经典重拍,倒别有一番感动,它肯定是跨进二十一世纪以来,用情最深的一部中国电影。 相信每一个看过费穆作品的人,都会注意到田壮壮在处理上有几项明显的改动—第一,取消了独白;第二,几乎没有特写;第三,镜头移动变得更含蓄内敛。在费穆的原作里,我们一开始就被韦伟梦呓似的独白,牵引着走进了女主角周玉纹的心理后花园,很有点杜丽娘游园惊梦的味道。往后发生的事,可能只是春梦一场,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真幻交错。田壮壮在他的版本里取消了独白,很多人不满,甚至嘲讽他没有看懂费穆的原作,我倒猜想他是要跟玉纹保持距离,也因而相对地走近了丈夫戴礼言和旧情人章志忱,做成了一种比较客观平等的整体感觉。 影片以玉纹在城头上漫步的远镜开始,很快就接上在小庭深院的破烂堆里磨蹭着的礼言,画外隐约传来火车声,志忱从火车上下来,最后老黄出场,他在破落的老宅里走动,从阳光耀目的回廊走进了礼言那阴沉晦暗的房间。第三天下午,一对旧情人相约在城垛上见面,镜头一直带着矜持的距离,玉纹指着挂在秃树上的手绢说:“你来的那天,就是这样,我睡着了,手帕就飞走了。”是的,这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玉纹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的。春风把女儿家的思绪吹远了,是志忱把它们重新找回来,交回到主人的手里。小妹妹十六岁生日之夜,玉纹穿起她跟礼言结婚时的旗袍,娇娆妩媚,几杯下肚,更把平素隐藏的风情都释放了出来,跟志忱划拳调笑。小妹妹仍不大懂事,礼言却全都看在眼里,他从后景缓缓走到右前景,看着灯光下的妻子及挚友,再绕到他们的背后,隐没在黑暗中,走出画面。镜头的移动很细微,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人物在有限空间里的走动,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情欲在掩映的灯光里蹦跳着,房间里的人都兴致勃勃,只有礼言是局外人。夜阑而人不静,他独自走到花园里,倚树痛哭,镜头体恤地遥伴着他,不忍干扰;而在房间里,已有几分醉意的志忱对妹妹说:“你记着,你以后再也没有十六岁。”他狂歌当哭,拉着玉纹的手不肯放,并把她的手绢铺在自己的脸上,他又何尝不是失意人?妹妹突然明白过来,她把手绢抢回来,拉着嫂嫂走。回到房间,玉纹伏在床上饮泣,然后走到梳妆镜前,眼泪擦洗掉了早前的风情,她把心一横,走出房门。 在费穆原来的作品里,结尾是丈夫和妻子同在城垛上遥送志忱,说不上是乐观,却也自有一份比较开阔的气味。大半个世纪后,还是由妹妹和老黄送志忱出城,礼言和玉纹却连家门也没有踏出半步,一个在楼下花园里修剪树枝,一个则仍跑到楼上妹妹的房间里绣花去。画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楼上楼下都若有所思,然后又重新投入手上的活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影片以一个城垛上的空镜作结,很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惘然。相比起来,田壮壮的江南小城比费穆的淞江更加荒芜寂寥,客去客来,老宅的主人仍是自我封闭在破落的庭院废墟里的春天 我不能撒谎,说田壮壮的《小城之春》(2002)比费穆的原作好看,费穆当年拍摄这部小品,很有举重若轻的气度,在优雅中见随意,在矜哀中有坚持;单就新版本的女主角胡靖钒来说,她的气质虽然好,可就是没法跟韦伟比,后者手拿丝巾半遮着面的风情,怎么也“克隆”不了,那是一种魅力,跟演技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今天看田壮壮的这部经典重拍,倒别有一番感动,它肯定是跨进二十一世纪以来,用情最深的一部中国电影。 相信每一个看过费穆作品的人,都会注意到田壮壮在处理上有几项明显的改动—第一,取消了独白;第二,几乎没有特写;第三,镜头移动变得更含蓄内敛。在费穆的原作里,我们一开始就被韦伟梦呓似的独白,牵引着走进了女主角周玉纹的心理后花园,很有点杜丽娘游园惊梦的味道。往后发生的事,可能只是春梦一场,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真幻交错。田壮壮在他的版本里取消了独白,很多人不满,甚至嘲讽他没有看懂费穆的原作,我倒猜想他是要跟玉纹保持距离,也因而相对地走近了丈夫戴礼言和旧情人章志忱,做成了一种比较客观平等的整体感觉。 影片以玉纹在城头上漫步的远镜开始,很快就接上在小庭深院的破烂堆里磨蹭着的礼言,画外隐约传来火车声,志忱从火车上下来,最后老黄出场,他在破落的老宅里走动,从阳光耀目的回廊走进了礼言那阴沉晦暗的房间。第三天下午,一对旧情人相约在城垛上见面,镜头一直带着矜持的距离,玉纹指着挂在秃树上的手绢说:“你来的那天,就是这样,我睡着了,手帕就飞走了。”是的,这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玉纹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的。春风把女儿家的思绪吹远了,是志忱把它们重新找回来,交回到主人的手里。小妹妹十六岁生日之夜,玉纹穿起她跟礼言结婚时的旗袍,娇娆妩媚,几杯下肚,更把平素隐藏的风情都释放了出来,跟志忱划拳调笑。小妹妹仍不大懂事,礼言却全都看在眼里,他从后景缓缓走到右前景,看着灯光下的妻子及挚友,再绕到他们的背后,隐没在黑暗中,走出画面。镜头的移动很细微,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人物在有限空间里的走动,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情欲在掩映的灯光里蹦跳着,房间里的人都兴致勃勃,只有礼言是局外人。夜阑而人不静,他独自走到花园里,倚树痛哭,镜头体恤地遥伴着他,不忍干扰;而在房间里,已有几分醉意的志忱对妹妹说:“你记着,你以后再也没有十六岁。”他狂歌当哭,拉着玉纹的手不肯放,并把她的手绢铺在自己的脸上,他又何尝不是失意人?妹妹突然明白过来,她把手绢抢回来,拉着嫂嫂走。回到房间,玉纹伏在床上饮泣,然后走到梳妆镜前,眼泪擦洗掉了早前的风情,她把心一横,走出房门。 在费穆原来的作品里,结尾是丈夫和妻子同在城垛上遥送志忱,说不上是乐观,却也自有一份比较开阔的气味。大半个世纪后,还是由妹妹和老黄送志忱出城,礼言和玉纹却连家门也没有踏出半步,一个在楼下花园里修剪树枝,一个则仍跑到楼上妹妹的房间里绣花去。画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楼上楼下都若有所思,然后又重新投入手上的活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影片以一个城垛上的空镜作结,很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惘然。相比起来,田壮壮的江南小城比费穆的淞江更加荒芜寂寥,客去客来,老宅的主人仍是自我封闭在破落的庭院里,什么时候还会重拾《花间词》的乐趣?而女主人呢,依然故我,每天挽着藤篮去买买小菜,然后穿过颓垣败瓦的市镇,到药材铺捎一包药,然后又到城垛待上一会儿吗?假如拍于一九四八年的《小城之春》是费穆对时代的一种回应,那么田壮壮的重拍也可说是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新纪元的一种态度。当多数人都手舞足蹈亢奋莫名地参与人类文明的毁劫的时候,他选择了默默地聆听,保持距离地观望,远离浮躁烦嚣的物质现实而回归到幽渺深沉的感情世界里去。 2004年11月里,什么时候还会重拾《花间词》的乐趣?而女主人呢,依然故我,每天挽着藤篮去买买小菜,然后穿过颓垣败瓦的市镇,到药材铺捎一包药,然后又到城垛待上一会儿吗?假如拍于一九四八年的《小城之春》是费穆对时代的一种回应,那么田壮壮的重拍也可说是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新纪元的一种态度。当多数人都手舞足蹈亢奋莫名地参与人类文明的毁劫的时候,他选择了默默地聆听,保持距离地观望,远离浮躁烦嚣的物质现实而回归到幽渺深沉的感情世界里去。 2004年11月 本书是当代著名电影评论家、影评人黄爱玲的经典代表作,内容包含了作者2002年以来创作的近百篇重要的电影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