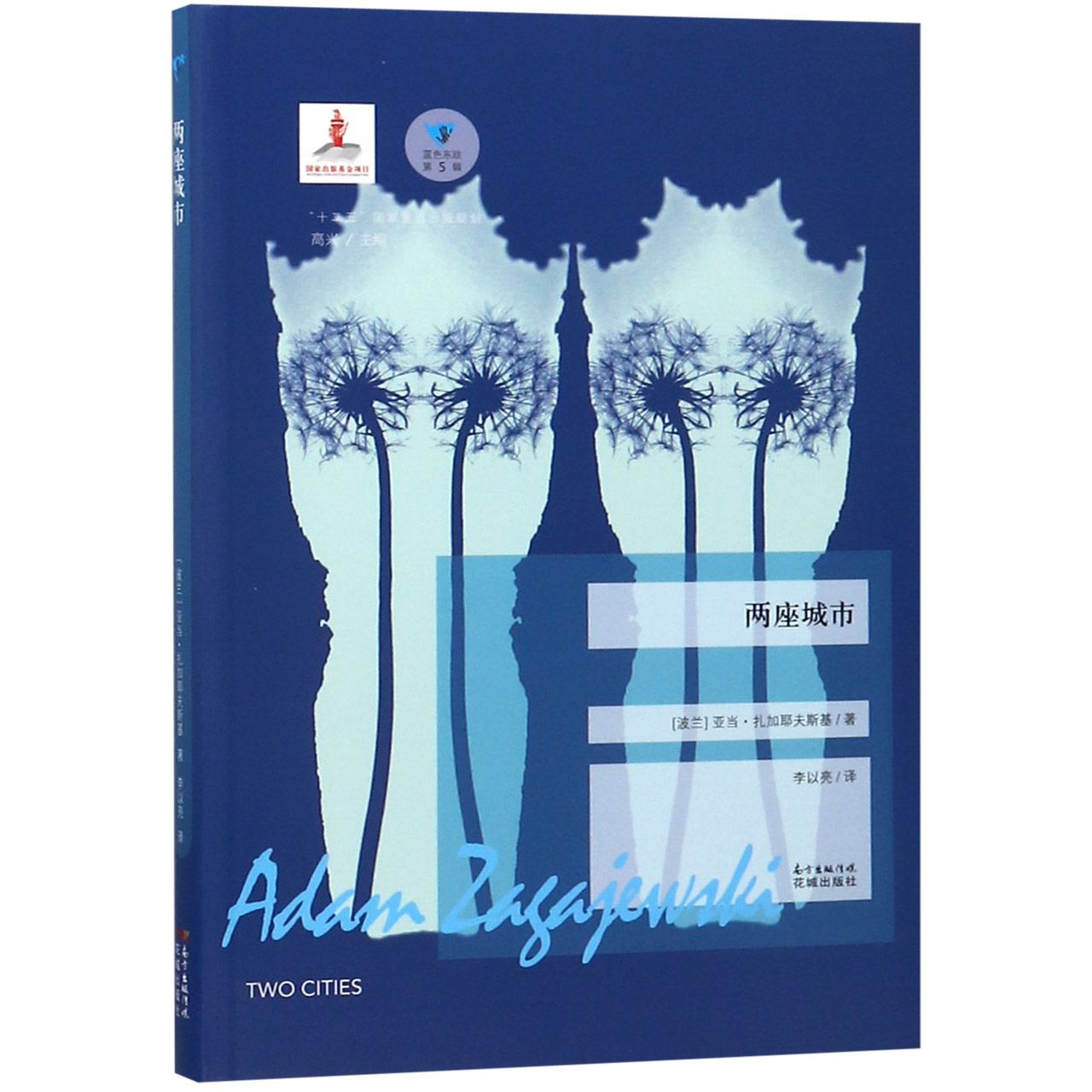
出版社: 花城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0.20
折扣购买: 两座城市/蓝色东欧
ISBN: 9787536087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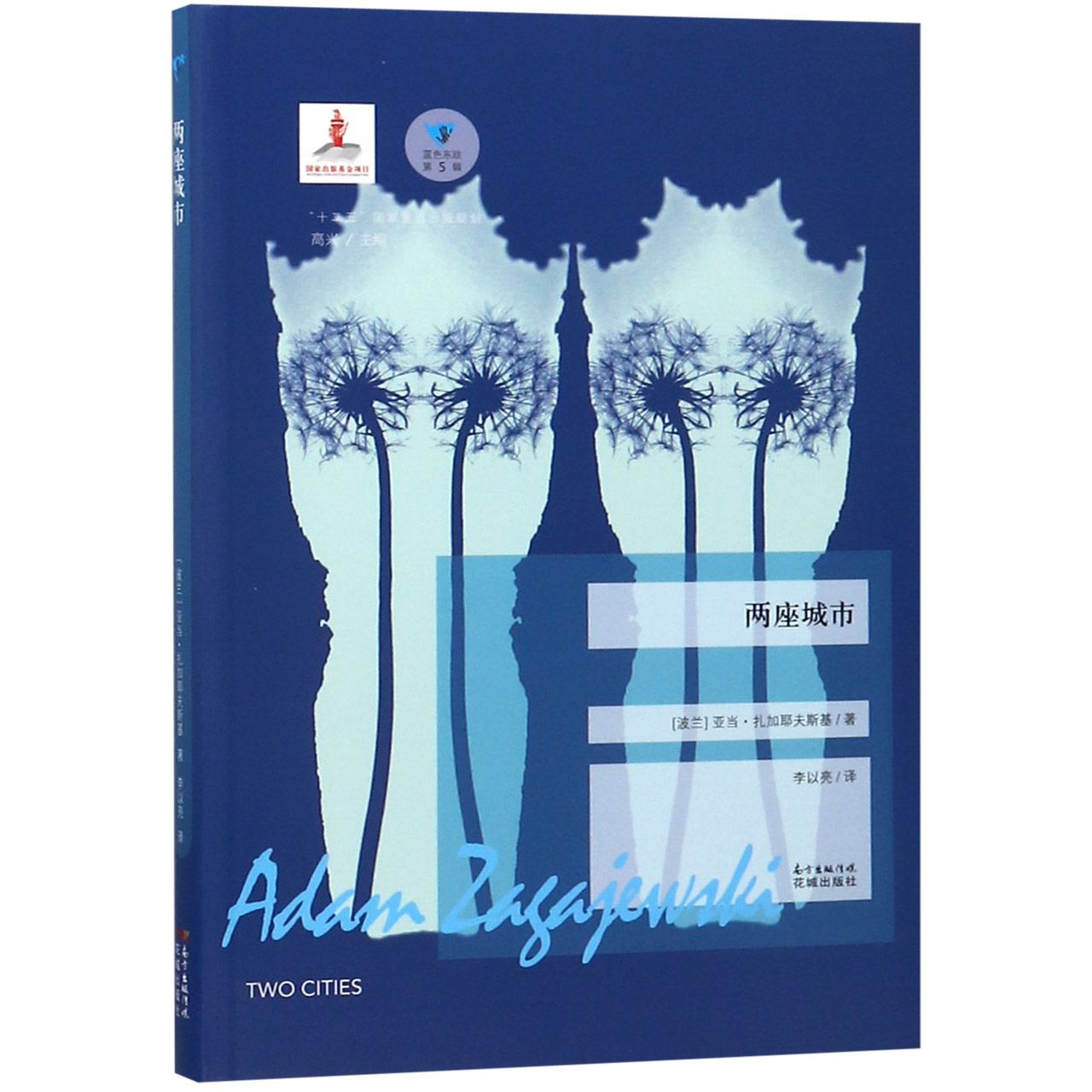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波兰著名诗人、随笔散文家和小说家。一九四五年出生在利沃夫(今属乌克兰),毕业于雅盖沃大学哲学系。波兰“新浪潮”诗歌代表诗人、主要理论阐述者。在一九七〇年代是波兰持不同政见的异议诗人。一九八二年移居巴黎。后往来于巴黎和美国之间,先后执教于休斯敦和芝加哥大学。二〇〇二年返回波兰,定居克拉科夫。主要著作有诗集《公报》《肉铺》《信》《多重性颂》《画布》《炽烈的土地》《震惊》《神秘学入门》《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永恒的敌人》和《无形之手》、随笔散文集《团结,孤独》《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另一种美》和《捍卫热情》等。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获得过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奖、米沃什奖、欧洲诗人奖等多项权威大奖,以及中国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和“中坤国际诗歌奖”,并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两座城市 雨连续下了四天。飘浮在城市上空的云,阴沉 、污浊,匆忙而急切地移动,仿佛连绵的货物列车 ,要把海洋输送到东方。 最后,太阳终于冲破云层,潮湿、热气腾腾的 屋顶瞬间成为一面面镜子,闪耀着,自在而得意。 如果将人分为定居者、移民和无家可归者,我无疑 属于第三类。这算是非常清醒的看法,并无任何多 愁善感或自我怜悯的矫情。 定居者通常生于斯、死于斯;有时,一个人眼 里的故乡,正是其家族世代共同生活过的地方。移 民往往在海外建立起他们的家,这样至少保证他们 的孩子们可以再次属于定居者那一类(不过,他们 说另外一种语言)。因此,移民便是一个临时的纽 带、一个向导,掌握着后代的未来。他将他们带到 另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在他看来,一个安全的地 方。另一方面,一个无家可归者,出于偶然、命运 的无常、本身的错误或气质上的缺点,从童年或从 锻造他的年少岁月起,他就不能或不想与他成长、 成熟的环境建立起紧密和深厚的联系。因此,无家 可归,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住在桥底,或是少有人出 入的地铁站(比如勒瓦卢瓦桥车站);而只是说, 那人有这个缺陷,不能将他的家可能所在的街道、 社区或城市,如通常那样称为自己的小家乡。 具体到我,一个确凿的说明(也许过于简单明 了),就可解释清楚,因为我的童年是在一个丑陋 的工业城市中度过。我被家人带到那里时,还不满 四个月。在那之后很多年里,我都会听到他们说起 那座被迫离开的、无比美丽的城市(利沃夫)。所 以,毫不奇怪,出于优越感,我在打量那些房子和 街道时,总是带有一丝轻蔑的味道,而从现实里, 我只不过获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我是如 此众所周知地无家可归(我这样说,尽量不想引起 任何的怜悯,同时,我也不想使人认为,对此奇特 之处我颇感自豪)。 我父母的生活被割裂为两截:迁徙前和迁徙后 。我的生活也是一样,除了在那个动人的城市里度 过的四个月,无论如何不能和后来成长的经历相比 。然而,无论一个人的生活从哪里开始分割和划分 ,它总是被割裂和划分成两半。如果我是生活了八 个月,善于数字计算的人也许会满意。然而,事情 的转折是以那样一种不同的方式发生的,神秘主义 者也许会感到高兴,因为那最初无意识的四个月, 闪耀着启示的光。 无家可归,但也并不总是不快乐。无论怎样, 这个更糟糕的城市也给我提供了各种卑微的财富, 首先便是头顶的一个屋顶。 而且,有时甚至也有一些更为慷慨的礼物。比 如,有一次——那时我很可能已经十六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