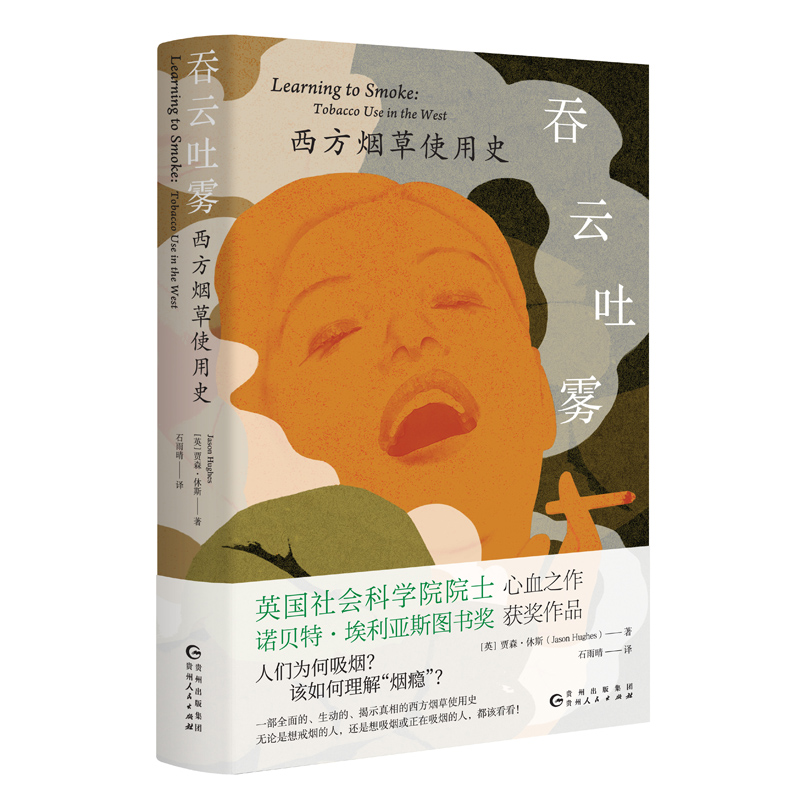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人民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0.80
折扣购买: 吞云吐雾:西方烟草使用史
ISBN: 9787221178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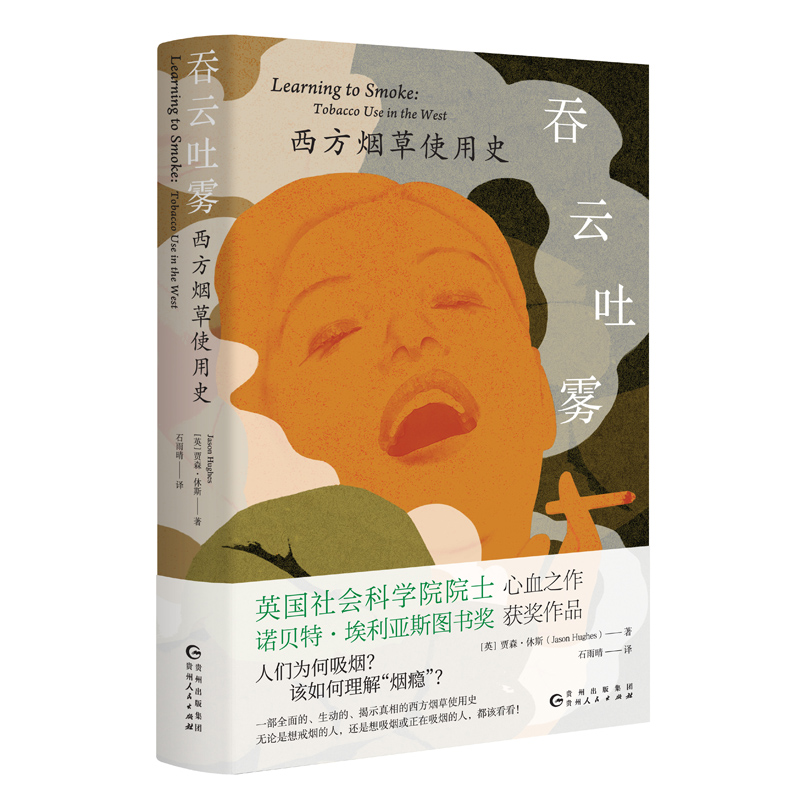
贾森·休斯(Jason Hughes),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药物与健康,以及情感、工作与身份等。英国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士,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成员。著有《吞云吐雾:西方烟草使用史》(Learning to Smoke: Tobacco Use in the West),该书获得2005年度诺贝特·埃利亚斯图书奖(Norbert Elias Book Prize);《性别、阶级与职业:工人阶级男性做脏活》(Gender, Class and Occupation: Working Class Men Doing Dirty Work,与他人合著);《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学:知识、相互依赖、权力及过程》(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ology: Knowledge, Interdependence, Power, Process,与他人合著)。
法理式吸烟社会 近年来,被动吸烟也成为了烟草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争论的主题之一,该主题的出现业已产生诸多影响。如今,不吸烟者合法阻止烟草使用者在自己面前吸烟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加大。此外,公众要求政府在公共场所禁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93年,英国环境部(U.K.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命人完成了一份名为《公共场所吸烟》(Smoking in Public Places)的调查报告,该调查针对的是公共场所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旨在确定有多大比例的公共场所听从了政府建议,落实了限制公共区域吸烟的政策。在调查开始之前的1991年12月,英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行为准则》(Code of Practice),为“所有者和管理者提供”有关限烟政策的“实用指导方针”(NOP 1993:1)。政府已经在一系列白皮书中制定了目标,“要在1994年之前将”80%的公共场所“纳入有效吸烟政策的覆盖范围”(同上)。最有趣的是,1993年的研究发现,这一目标已经在某些类型的公共场所实现(同上)。总的来说,在被抽样的所有公共场所中,有66%制定了吸烟相关的政策(同上)。因此,即便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许多公共场所自己也在日益加大对吸烟行为的限制。 与18世纪类似的是,烟草的使用再次被一步步地推到了“公共”生活的幕后。随之而来的是烟草使用观念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吸烟是一种公共的、集体的、社交的活动,这种礼俗式吸烟社会的观念在17世纪尤为盛行,在20世纪中期也较为流行。不过,人们现在已逐渐认可法理式吸烟社会(再次借用滕尼斯的术语)的观念:将吸烟视为私下的、个人的、单独的活动。 近年来,烟草使用的发展开始概念化,这种概念化或许有助于解释格里夫斯提到的一些过程: 从1950到1970年,女性以工人、家庭主妇或母亲身份出现在[香烟]广告中的情况逐渐减少。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鼓励中产阶级经营家庭生活。或许是新出现的证据让大家看到了吸烟的健康成本,广告商不得不做出改变,不再以积极劳动的女性形象来做宣传。……市场营销人员逐渐将女性吸烟定义为一种休闲、放松的活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过去20年中大幅增加,广告从业者已经开始将女性视为备受压力、需要放松的群体,香烟则被宣传为一种帮助放松的工具。烟草行业杂志专门瞄准了劳动力中那些倍感压力的女性,将她们视为西方“未开发的市场”。(Greaves 1996:24—25) 香烟广告商逐渐放弃用积极“劳动”的女性形象来营销,格里夫斯认为,这一转变与出现了可证明吸烟存在健康风险的新证据有关。格里夫斯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我认为,这一转变也有可能与迈向法理式吸烟社会的种种转变过程有关。格里夫斯为阐述自己对香烟广告变化的观察结果,举了很多广告案例。其中有一幅以女性为目标群体的广告图:一名女性正躺在浴缸之中,有一小部分手肘几乎看不见;浴缸上方写着“这里只有你”。这幅图暗示的是,女性可以一手放在脑后,一手夹着烟,放松地浸泡在浴缸中。这则广告的总标题是,“这不仅仅是一支香烟。这是独属于你的几分钟”(Greaves 1996:25;本书作者增加了强调)。顺便一提,这是女性专属香烟品牌伊芙淡味细长100毫米版香烟(Eve Lights Slim 100s)的广告。 这则广告想要营造的想象空间似乎聚焦于“暂时休息一下”“允许自己享受放松的奢侈”和“暂时忘掉外界的一切”。浴室象征着极其私密的空间,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吸烟者的身份也是隐形的。这则广告搭建了一个独处的、个人的、私密的场景。有趣的是,吸烟者身份的隐形反映了香烟广告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趋势。以吸烟这个动作为主角的香烟广告已经日渐减少,推动这一转变的不仅有政府对烟草广告的限制,我认为也有观念的更广泛改变。仿佛就连吸烟的画面也被推到了幕后。要了解这些变化过程,不妨看一下1996年2月2日《伦敦电讯报》(The London Telegraph)的报道: 美国中产阶级认为吸烟动作特别上不了台面,吸香烟已经成为最新的一种恋物癖,被称为“烟色剥削”(smoxploitation)。一个由小广告和内部通讯刊物组成的网络,正以24英镑的单价,成百上千地销售着年轻女性的吸烟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女主角们虽然穿戴整齐,但会摆出性感撩人的吸烟姿势。在各种视频名称中,《烟熏之吻》《女大学生吸烟联谊会》和《保拉》被公认是迄今为止最撩人的……恋物癖杂志《腿秀》(Leg Show)的主编戴安·汉森(Dian Hanson)说:“吸烟是90年代的恋物癖。任何遭到广泛谴责、被广泛视为禁忌的事物,都会被色情化,这是任何时代都难以幸免的。”……热门视频《保拉》的主角是一名年轻的金发女郎,魅力四射,她身着黑色的紧身长礼服,将曼妙的身材曲线展露无疑。她还精通吞吐烟雾的全套技巧。这段视频有30分钟,在播到一半左右时,她会拿出一根长长的香烟烟嘴,将观众的兴奋推上新的高度。(Laurence 1996:1) 这段报道确实是用了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但作者的观点十分有趣,他认为这些视频的出现与社会压抑程度的不断增加和吸烟在公众中的“隐形”密切相关。更笼统地来说,这篇报道证明了,尽管吸烟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特别流行,但这个行为还是遭到了广泛的谴责。 再说回格里夫斯的研究。吸烟开始被视为一种独自放松的手段,而这种观念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与此相关的一个主题(将香烟视为一种表现个人控制力与权力的方式)也已经在好莱坞电影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以1991年的好莱坞电影《本能》(Basic Instinct)为例,女主角将吸烟作为个人权力的关键表现形式。……在《本能》中,莎朗·斯通(Sharon Stone)饰演的女主角身负谋杀嫌疑,但面对警方,仍在继续吸烟,摆出了一种反抗权威的姿态。当时,西方的吸烟法规和吸烟健康知识都在不断增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做出这样的表演,恰恰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会用吸烟来反抗令人压抑的法规。通过女性来传达这一信息,为当代女性吸烟者的角色增加了力量与复杂性。(Greaves 1996:28—29) 这段引文的核心主题似乎是权力、控制和反抗。随着反烟的声音日益高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吸烟视为一种表达反抗的行为或姿态。事实上,在这些变化的推动下,一些吸烟者(尤其是女性)已经开始以反抗者自居,且形成了一个群体。对这些吸烟者来说,吸烟意味着拒绝一套强调健康伦理、要求顺从主流的价值观,接纳另一套鼓励冒险、反抗和个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上的转变可能是身份建构过程的核心。 控制的概念,特别是压力控制,成为了当代烟草使用观念中的主导性主题。电影、电视一直在强化吸香烟与压力控制之间的关系。吸烟行为常常出现在压力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之中或发生之后,吸烟者往往都是“倍感压力”的个体。事实上,电影制作人也意识到了香烟的强大象征意义,经常用吸烟动作来传达电影的言外之意(Klein 1993)。正如克莱因(Klein)所说: 吸香烟不仅是一种身体行为,也是一种话语行为——一种无言但强大的表达形式。这是一种完全隐晦、修辞复杂但叙述清晰的话语,充斥着众人皆可心领神会的惯例。从互文的角度来看,这些惯例与整个的吸烟文学史、哲学史和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淫秽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卫生问题,而吸烟也成为了一种淫秽的话语表现形式。(18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莱因想要论证,吸烟作为一种“话语行为”,与整个烟草使用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段叙述还是让人想到了在20世纪西方烟草使用观念中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主题:烟草的使用可被视为一种个人表达的方式(按我的话来说)。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距今较近的一个烟草使用发展“阶段”中定位到克莱因所提出的烟草使用概念。 烟草使用与压力控制(放松)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使用烟草可以让人放下工作、休息片刻,以及可以给人独处的空间。与之相关地,吸烟行为也被视为一种短暂逃离单调生活的方式。这些关联都清晰地体现在了洛霍夫(Lohof)对万宝路香烟广告含义的认真思考之中: 万宝路的形象代表着逃离,但并非逃避文明的责任,而是逃离文明所带来的重重挫折。现代生活宛如野草蔓生的泥潭,官僚体制及其他制度也盘根错节地与其缠绕在一起,“现代男人”[原文如此]只得在其中摸爬滚打,但往往只能收获无能的绝望,最终仍旧籍籍无名、一事无成。与此同时,他将嫉妒的目光投向了“万宝路男人”。“万宝路男人”威风凛凛地俯视着具有挑战性但容易理解的任务。……清白无辜和个人能力是你判断某个隐喻是不是代表万宝路香烟的标准。(Lohof 1969:448) 这里提到的“万宝路男人”由演员韦恩·麦克拉伦(Wayne McLaren)饰演。他以牛仔的形象出现在了万宝路的许多香烟广告中。正如洛霍夫所言,这些形象推广了吸万宝路香烟与个人自主、“真实可靠”和“逃离挫折”之间的关联。探讨到此,这些吸烟观念有多现代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万宝路在距今较近的一次广告宣传中,将“欢迎来到万宝路之乡”的广告语放在了美国崎岖不平的广袤大地之上。这一广告主题似乎再次强化了“逃离”的概念,呼吁人们逃往更简单、更平和的地方。不过,这里对“空间”的隐喻可能本就有着重要的含义。这或许是为了赋予自由一种“空间化的”广度,又或者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对抗公共吸烟“空间”不断减少的主流趋势?事实上,万宝路香烟广告的例子还凸显了当代烟草广告变化趋势中的一个更普遍特征。在这些广告中,不仅吸烟者“消失”了,取代吸烟者的形象也在变得日益复杂和隐晦。它们仿佛是在邀请人们自行解码其中高深难懂的含义。对广告商来说,被解码出的信息本身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光是“信息高深、需要解码”这一点就足以塑造出一个精巧高端的形象。 当代的烟草使用观念有很多有趣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的出现。我所说的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化吸烟的理由和反对吸烟的论点开始越来越趋同,都集中在了风险和风险承担的概念上。下面是来自美国喜剧演员丹尼斯·利瑞(Dennis Leary)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他将于几周后参加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想在会上做的是:让烟盒上的警示语更大!是的!他想让整个烟盒的正面都写满警示语。仿佛吸烟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未留意到那些警示语一样。这对吗?仿佛他能得偿所愿,突然就让全世界的吸烟者都醒悟过来,“是的,比尔,我有几支烟。……见鬼!这些东西对你有害!妈的,我原以为它们对你有益呢!我以为它们富含维生素C之类的营养呢!”愚蠢至极!这一切根本无关警示语的大小。就算直接以警示语为名,你也可能会买。装在黑色烟盒中,烟盒正面印有“肿瘤”二字和骷髅头加交叉骨形标志的香烟,你也可能会买。吸烟者可能会在街区各处排队买烟,“我可等不及要拿到那些该死的东西了!我打赌你一吸就会得肿瘤!”……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警示语有多大,也无关乎它们售价多少。如果继续涨价,我们会闯进你家,去抢那些该死的香烟,明白了吗!?它们是毒品,我们已经上瘾了,明白了吗!?(Leary 1997) 利瑞语言诙谐,这一主题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吸烟者群体中很受欢迎。他的口吻也确实像是在表达群体的观点——“我们会闯进你家”“我们已经上瘾了”。利瑞代表的是更广泛群体对政治正确的强烈抵制,他们反对越来越多人所秉持的吸烟者“软弱、不理性”的观念(Brandt 1990:169),利瑞完全接受医学活动家们的观点——吸烟会杀死你、吸烟会上瘾、吸烟“对你有害”——但那又怎样?他说:“我期待得癌症。”在利瑞看来,吸烟几乎就是力量的象征。他似乎想要主动拥抱吸烟所带来的风险。他开玩笑道:“我还记得,曾几何时,这个国家的男人以患癌为荣。该死的!在那时,患癌还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呢!约翰·韦恩(John Wayne)就曾两患癌症。第二次患癌时,他们摘掉了他的一个肺。他说:‘都取走吧!我他妈根本不需要肺!我会长出鳃来,像鱼一样呼吸!’”(Leary 1997)利瑞继续愤怒地声讨反吸烟者的观念: 你们从报纸、小册子里挖出来的所有微不足道的事实,都被你们装进了自己那该死的小脑袋瓜。我们一吸烟,你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连珠炮似的攻击我们,不是吗?我喜欢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比如,吸烟会让你折寿10年。”但那不是人生中最糟糕的10年吗?人生最后的10年!坐在轮椅上做肾透析的该死的10年。你们可以自己去过那样的日子!我们可不要,明白吗!?你们总在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每吸一支烟,你们的寿命就会缩短6分钟。若能现在就戒烟,就能多活10年,或是20年。”嘿,我有个名字要送给你们——吉姆·菲克斯(Jim Fix)。你们记得吉姆·菲克斯吗?那个非常著名的慢跑健将?他每天都要慢跑15英里。他出过一本关于慢跑的书,还拍过一个慢跑视频。后来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在他慢跑的时候!你敢不敢打赌,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尸体的就是两个吸烟者,“嘿!那不是吉姆·菲克斯吗?”“哇,太他妈悲剧了。走吧,我们去买点香烟。”(1997) 援引利瑞之言是为了凸显当代吸烟观念中的一个核心悖论。人们逐渐认同烟草会给健康造成长期、不可见、内在的伤害,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引发了一种对立。由于烟草引起的疾病,特别是癌症,有很长的发展期,而且主要发生在“老”人身上,因此,年轻人将吸烟视为一种蔑视死亡的表现。对年轻的吸烟者来说,死亡距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些长期、不可见、内在的伤害是什么样的。但吸烟在情绪控制、体重控制、自我表达等方面的影响是立竿见影且外在可见的,这些影响就对他们至关重要了。利瑞还强调,就算是过着健康生活的人,也同样有提前被死神带走的可能。他在第一段引文中提出,就算香烟顶着肿瘤之名,被装在正面印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形标志的黑色烟盒中,吸烟者仍然会买。其实,现在市面上真的有这种“死亡”牌香烟,它们正好装在黑色烟盒中,以骷髅头和交叉骨形图案为标志。这种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恰恰证明了,支持与反对烟草使用的理由交汇在了“风险”这一主题之上。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是万宝路的香烟包装,它一面印着诱人的标志,另一面印着政府的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正如克罗(Krogh 1991:37)所言:“美国人经常能看到所谓的人皮下的头骨:广告的最上方是面带笑容、身材苗条、美丽迷人的弗吉尼亚女人,沿着她优美的身体曲线往下,会看到美国卫生部长对她未来的预测。青春、美貌与死亡、疾病并存,前者是鲜活的色彩,后者只剩黑白。” 我想说的并不是,如今的吸烟者都是为了患癌而吸烟,而是想说对某些吸烟群体来说,风险恰恰是吸烟的一大魅力。关键是,这是未来的风险,无关当下。你可以认为吸烟表达了一种态度:“我并不投资未来,我只活在当下。”这种态度与许多变化过程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人们对年轻人身体价值的日益看重(Shilling 1993)。这些过程或许有助于解释近年来年轻吸烟者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以1982年的英国为例,在15岁的男孩和女孩中,经常吸烟者的比例分别为24%和25%。到198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28%和33%(Mihill 1997)。相比之下,英国成年人的吸烟比例下降得非常快。 克罗“人皮下的头骨”这一比喻清晰体现了人体内外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对当代的烟草使用观念至关重要。克罗提到的这些过程似乎聚焦于这样一种概念:年轻的身体其实就如同一件“外衣”,外衣之下掩盖着潜在的疾病,以及死亡这一必然结果。最终的悖论或许在于,如果烟草相关疾病不存在潜伏期,如果各年龄段吸烟者因使用烟草而患病的比例相同,且最关键的是,都随时有可能因该病丧命,简言之,如果烟草被视为一种更直接、更可见的危险,那么当代西方的烟草使用观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心血之作,诺贝特·埃利亚斯图书奖获奖作品。 一部全面的、生动的、揭示真相的西方烟草使用史。无论是想戒烟的人,还是想吸烟或正在吸烟的人,都该看看! ◎从烟斗,到鼻烟,到雪茄,再到香烟,烟草使用形式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从16世纪的“万灵药”美誉,到今天被贴上大流行病的标签,烟草的医学地位如何改变? ◎烟草使用是如何从美洲原住民文化转移到西方文化中的? ◎从烟草被比作女性,到女性烟民大幅增长,这中间有着怎样的观念转变? ◎文明化进程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烟草观和吸烟体验? ◎今天的烟民有着怎样的吸烟动机?戒烟的困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