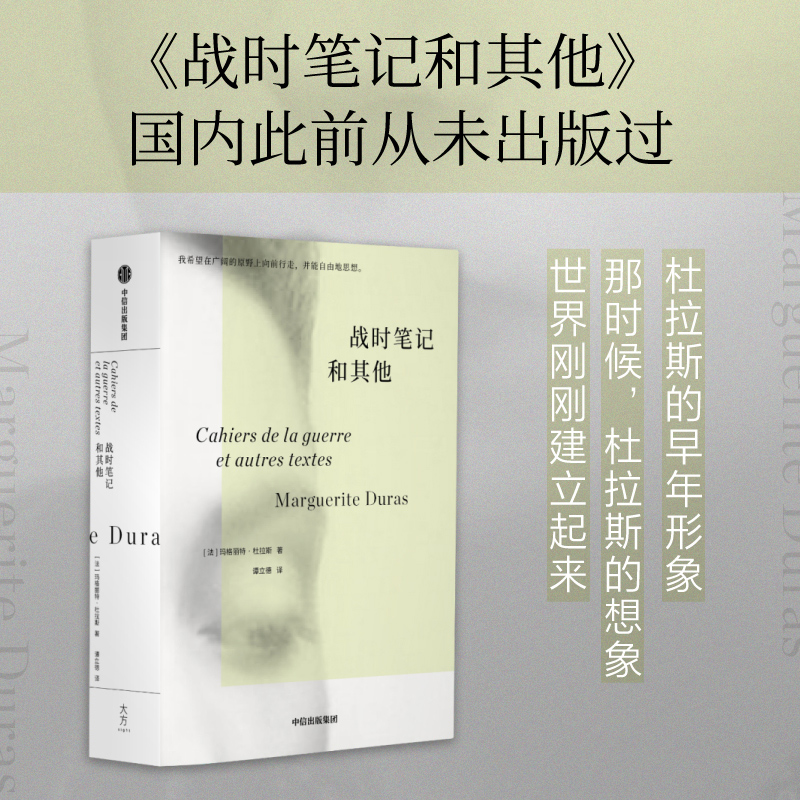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战时笔记和其他
ISBN: 9787521748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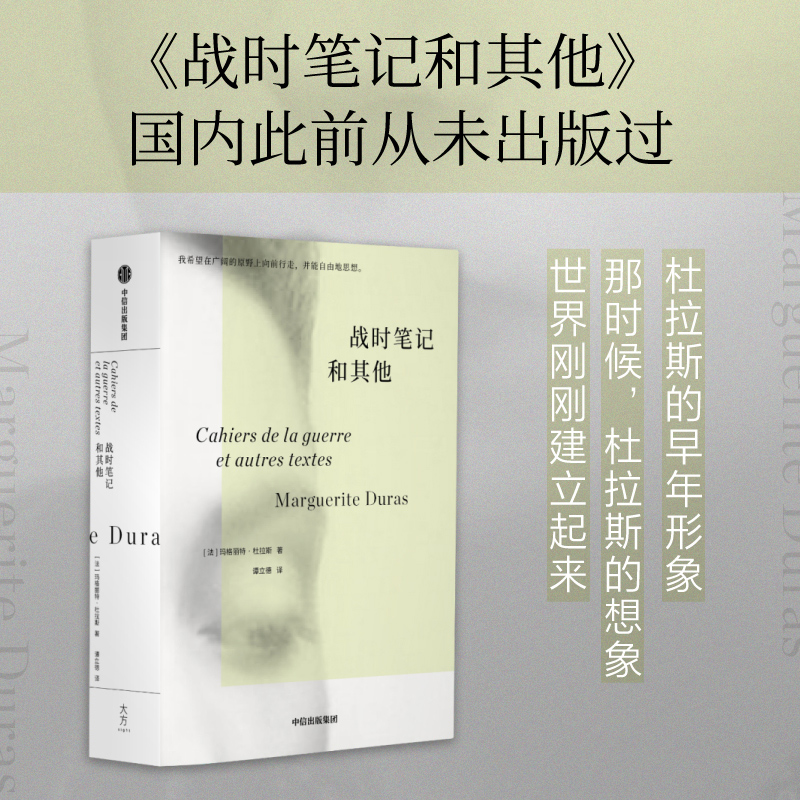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 充满野性、出乎意料的作家、剧作家、导演,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作品、十九部电影等。《情人》获1984年龚古尔奖,畅销全球。她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成就卓著,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杜拉斯生于印度支那,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九岁,这段生活影响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写作的源泉:作为她生命底色的童年的匮乏,永远与命运抗争却永远失败的母亲,偏爱大哥的母亲,总是和他要钱的大哥,亲近却早逝的小哥哥,死去的孩子……“活着让我不堪重负,这让我有写作的欲望。”她无时无刻不在写作,用写作解剖自己的一生,在写作中趋近自身的真相。
我是在沙沥和西贡之间的渡轮上第一次遇见雷奥的。当时,我回到西贡的寄宿学校,某个人,我再也不记得是谁,让我和雷奥同时搭乘了他的车。雷奥是当地人,但是,他穿着法国式服装,讲一口无懈可击的法语,他从巴黎回来。我,我还没满十五岁,我只是很小的时候在法国待过,我觉得雷奥挺优雅的。他手指上戴着一枚大钻戒,身穿米灰色柞丝绸衣服。在那些至今没有注意过我的人身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钻戒,而我的兄弟们,他们穿白布衫裤。鉴于我们的资产状况,我几乎难以想象他们有朝一日能够穿上丝绸西服。 雷奥告诉我,我是个漂亮的女孩。 “您熟悉巴黎吗?” 我满脸通红地说不。他熟悉巴黎。他住在沙沥。某个在沙沥的人竟熟知巴黎,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呢。雷奥向我献殷勤,我惊喜不已。医生把我载到了西贡的寄宿学校,雷奥设法告诉我,我们“将再见面”。我很清楚他极其富有,我着迷了。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雷奥,我是那么激动,那么没有把握。我回到C 小姐家里,我和另外三人,两位教师和一位比我小两岁,名叫科莱特的女孩一起寄住在那里。C 小姐从我母亲那里拿走了她几乎四分之一的小学教员的薪金,以此为条件,她向母亲保证给予我完善的教育。只有C 小姐知道我母亲是小学教员,她和我都小心翼翼地对其他寄宿生隐瞒了这一点,她们也许会对此感到气恼。当地小学教员的薪酬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大家都对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非常瞧不起。我自己尽我所能地、谨小慎微地对此守口如瓶。那天晚上,回到C小姐家时,我陷入绝望之中,我心想,住在沙沥的雷奥,不会不得知我母亲的情况,他只可能疏远我。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尤其不能跟一位主管的女儿科莱特说—也不能告诉C 小姐,她也许会把我从她的学校开除出去,我毫不怀疑,这一招很快就会置我母亲于死地。然而,我安慰自己。虽然雷奥熟悉巴黎,而且家资巨万,但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我却是白种人;也许他会将就一个小学教员的女儿。 小学教员的女儿这一身份使我在学校里感到沮丧,在那里,我只跟那些邮局职工和海关职员的女儿们来往,只有他们与当地小学教员身份、地位相同。C 小姐愿意接受我,因为她为人豁达,宽宏大量,因为,我母亲还是出了名的正派、诚实。然而,她对我比对科莱特更加严厉,同时又更加亲密。因此,C 小姐左乳下长了癌瘤,在整个院里,她只让我一个人看。通常,每星期天下午,我们吃了点心以后,所有人都外出时,她让我看。她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C 小姐身上会散发出这样的臭味,但是,在整所房子里,只给我一个人看她的癌瘤,使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我认为是由于我的小学教员女儿的身份。这并不令我不快,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她因这一信赖的表现而感到某种骄傲。这一幕发生在C 小姐的房间里。她露出乳房,走近窗户,让我看。我小心翼翼,屏息敛声地仔细看了足足两三分钟之久。“你瞧见了?”C 小姐问我道。“啊,是的,我看见了,就是这儿。”然后,C 小姐藏起她的乳房,我重新开始呼吸,她再穿上带黑色花边的连衣裙,叹了口气,于是,我对她说,她已经迈入老年,这种病不要紧的,她同意我所说的,不再难受,然后,我们到种植园去散步。 我母亲作为公务员的遗孀,并以公务员的身份(自1903 年起,她就在印度支那半岛任教),从总督府那儿获得一块位于上柬埔寨的种植水稻的租借地。当时,这些租借地每年缴付极少的年金,这些土地只有在若干年后开始耕作了,才属于它的受益人。我母亲不停地奔走,四处活动,得到一片八百五十公顷的宽阔的租借地和森林,位于大象山脉和大海之间,柬埔寨的某个偏远的地方。这片种植园位于离法属第一个关卡六十公里远的小路上,不过,必要时,这一弊病也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母亲雇用了五十来名用人,必须把他们从交趾支那迁移过来,并不得不在离大海两公里远的沼泽地中间建造起一个“村子”,然后把这些人安置在那里。对我们全家人来说,这段时期极其快乐。我母亲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时刻。除了建起一座村子,我们还在沿着种植园的小路边建造了一栋吊脚楼房。在1925 年,这栋房子花了我们五千皮阿斯特,当时可是很大的一笔钱。考虑到闹水灾的缘故,房子建在桩基上,完全是木制的,木头需要切割、锯开,并就地锯成木板。这些事情可能出现的诸多极其的不便,都没有阻止我母亲。我们在邦代—普热(种植园的名称)连续住了六个月,因为我母亲已经从西贡教育局获得离职批准。在建造我们的房子期间,母亲、我的哥哥和我,我们就在一所茅舍栖身,靠近“上面”来的仆人们住的草屋(村子坐落在离那条小路,即我们的房子四个小时船程的地方)。我母亲和我,夜里睡在一张床垫上,除此之外,我们完全同仆人们共同生活。当时,我十一岁,我的哥哥十三岁。如果我们母亲的健康没有垮掉的话,我们肯定会非常幸福。眼见我们即将摆脱困境而产生的兴奋和快乐,与她格外难受的更年期同时来临。当时,我母亲曾有过两三次癫痫发作,一发作,她便处于一种嗜睡性昏迷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延长至一整天。那个时候,在柬埔寨这个地区,不仅不可能找到一位医生,而且连电话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的发作使那些土著仆人又惊又怕,每次,他们都威胁着要离开。他们害怕得不到报酬。他们围住茅舍,在茅舍周边的斜坡上,静静地坐上这发作持续的一整天。茅舍里,我母亲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轻轻地呻吟着。我哥哥和我时不时地走出茅舍告诉这些仆人,我母亲并没有死去,让他们放心。他们只是很难相信这一说法。我哥哥对他们说,即使我们的母亲死了,他发誓,无论如何,他也会把他们带回交趾支那,而且,他会付钱给他们。我哥哥,我说过,那时,他才十三岁;他已经是我从来未遇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同时有能力让我安心,让我相信,不应该在仆人面前哭泣,因为这无济于事,让我相信,我们的母亲会活下去。确实,当太阳从大象山脉后山谷那儿消失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恢复知觉了。这种发作有这样特别的地方,它一点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痕迹,第二天,我母亲又重新从事她的日常活动。从第一年起,这片种植园二百公顷土地的耕作便与我们房子的建造、村子的建立、搬运以及仆人们的安排诸项工作齐头并进,耗尽了我母亲二十四年公务员生涯里攒下的积蓄。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算定第一次收获就几乎可以完全补偿因安顿而花去的费用。我母亲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不断琢磨的这一计算看来是确凿可靠的。我母亲“知道”,四年后,我们将会成为百万富翁,因此,我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那时候,她还与我去世多年的父亲保持联系。如果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她什么也不会干的,所有这些有关未来的规划都是他授意的。据她说,这些“措辞”只是在将近凌晨一点才形成,这说明我母亲的确度过了辗转不眠的夜晚,而且,这使她在我们眼里拥有一种奇特的威望。第一次收获的结果是几袋稻谷。由总督府拨的八百五十公顷地是盐碱地,而且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被海水淹没。除了房子周围离大海比较远的那几公顷地,全部收成还没到收获时就在涨潮的一夜间“烧”了。海水一退,沿着我们种植园的河流重新可以通行时,我们就去看我们那二百公顷被盐烧毁的稻田,我们乘坐八个小时的小船,来回走了一趟,察看我们全部被毁坏的东西。但是,当天晚上,我母亲便决定借三十万法郎,修筑堤坝,这些堤坝也许能使我们的稻田永久免遭海啸侵袭。鉴于我们的种植园还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将种植园作抵押,而且,即使有这种可能性,由于这种植园在一片盐碱冲积地内,经常被海水淹没,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我母亲去找的所有信贷银行都断然拒绝借给她这笔巨款,我们无法用什么东西来为这笔钱作抵押。总之,我母亲去找了一个“chetty”(泰米尔放债人),也就是说一名放高利贷的印度人,他同意借给她这笔钱,条件是以她小学教员的薪金为抵押。这事情不可能瞒过教育总局,对我们三个人都是非常不光彩的事。于是,我母亲不得不重新工作。她每周五晚上从她任教的沙沥动身,驱车八百公里,然后在周日至周一的夜间再返回。Chetty 收取的利息,就是他一个人耗费掉我母亲薪酬的几乎三分之一那么多。在这些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我母亲从不气馁。建筑这座可能庞大宏伟的堤坝,使她陷入极度的兴奋中。我们与她关系密切,相依为命,和她一样狂热。我母亲并没有请教任何技术人员,以便获知这堤坝是否有效。她认为就是有效的,她总是按照某种高级的、无法控制的逻辑行事。我们雇来了几百名工人,在我母亲和我们的监督下,堤坝在旱季建成。从chetty 那儿借来的大部分钱都用在它上面。不幸的是,堤坝被潮汐期间陷入的大量螃蟹啮咬,于是,下一年,当大海涨潮时,用松散的土壤所建成的,已被螃蟹侵蚀的堤坝几乎全部崩塌。 所有的收成又一次丧失殆尽。显然,没有石块来加固是无法修筑堤坝的。我母亲明白这一点,她无法找到石头块,便说起要在地上坡面部位放置方块状的红树树干。她又一次找到了办法。她有了这类发现并把这些发现告知我们的那些夜晚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她特有的创造性使她陷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以致那几个还留在家里的“上面”的仆人也同她一样狂热。下面的那些与我们分开居住的仆人,他们留下来仅仅是因为我母亲对他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厚、慷慨。他们作为佃农来到这里安家,然而,稻田却几乎没有任何收成,我母亲认为自己必须把他们当作工人来对待—这并不适合我们的经济状况。用红树树干的办法耗尽了那个chetty 出借的钱。情况并不那么糟,一部分坡面挺住了,其他的则将坍塌。妈妈取名为“决定性试验”的四十公顷稻田是她的慰藉和骄傲。庄稼长出来了,我们每星期六都去看。唉,到了收成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希望落空。住在村里的仆人不约而同地背着她,出海重返交趾支那—带着我们在三年内能收获到的仅有的稻谷。我母亲又一次打定主意。三年里,堤坝的建筑使她神经紧绷。一部分堤坝没有被冲垮这一事实让她感到很欣慰。我母亲的天真无邪与她的无私是谁也比不上的。她对堤坝感到厌烦,不想知道下一年就是那些得以挺住的堤坝也会坍塌。尽管如此,后来,她继续每年都让人播种几公顷的地作为试验。她认为海水不会迟迟不退出她的稻田,她的努力将会得到回报的。我们获取万贯家财的期限更远了,但按她说,并不是遥遥无期。有时,我们怀疑一块冲积土层的地是否就能在这么短短几年有所改善,但我们的母亲让我们放心。她就这样在感情上确信这一点,我们还是和她一样。 我们彻底破产了。母亲或多或少忽略了种植,绞尽脑汁支付chetty 的借款。当时她注意到我,决定让我去学习,她发奋实现这个计划,相当于对修筑堤坝和房子所倾注的热情。她不管我的哥哥,说他不聪明,并试图说服我。她认为我比我哥哥更适合学习,不过,这不无某种蔑视。我的哥哥也一样。我哥哥对我说:“我不聪明,我留下种地。”不然就说:“我没有你那份聪明,我不配母亲为你所做出的牺牲。”他是真诚的。他还对我说:“我应该留在沙沥使你有可能上学。”他就待在沙沥。我哥哥的谦卑是我忧郁的真实原因。我母亲确定他缺乏才智,而他就单纯地顺应这一“降低身份”的境遇。同样,我母亲认定我天生是读书的料。我在中学获得的成绩糟透了,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我在每门学科上都是最后一名,不过,我时不时地在法语方面获得的成绩还可以—这时,我母亲就高地流下眼泪,感到自己的牺牲得到了回报。最初,她经常开着我们的老雪铁龙和我哥哥一起到C 小姐这里来看我。然而,由于他们当时靠着我母亲那难以置信的劳作在维持生活,他们的造访很快就变得稀少了。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要自己设法去沙沥,星期六乘卡车启程,法国人从来也不坐这种卡车,因为,正常情况下走四个小时的路程,它要花八个小时。我有时就利用这便宜的机会回家,后来,在其中某一次返回途中,我遇见了雷奥。 ? 本书为国内首次引进出版。 ? 内容充满正义感和悲悯之心。 ? 文字真诚、动人。 ? 情人故事的最初版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最初版本,漫长的等待和集中营里归来的丈夫,死去的孩子,门房太太的不顺从……还有童年和母亲,永远的童年和母亲。 ? 杜拉斯不仅是一位女性,她更是一个真实地活着的人。她比任何人都敢于面对自己的欲望和恐惧——自己的真相。在小说里,她像个外科医生一次次剖开自己,反复拆解那些影响她一生的苦难;而在这本书里,不再有修饰,极致的脆弱、巨大的恐惧、强烈的爱欲,都赤裸裸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 译者谭立德曾翻译过《广岛之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