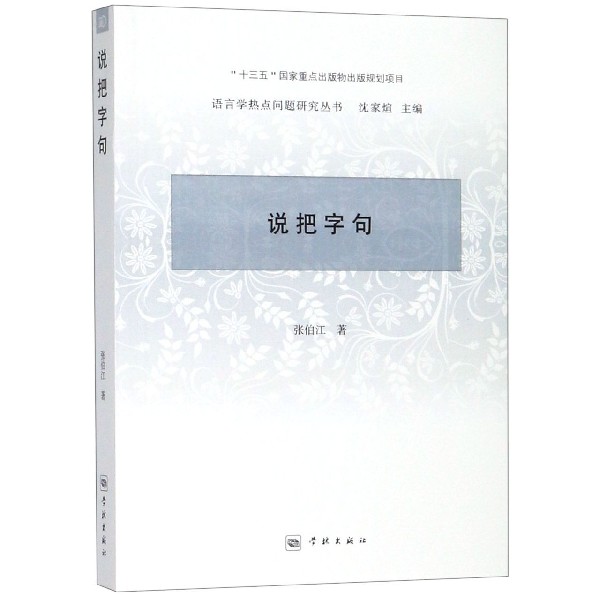
出版社: 学林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3.10
折扣购买: 说把字句/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15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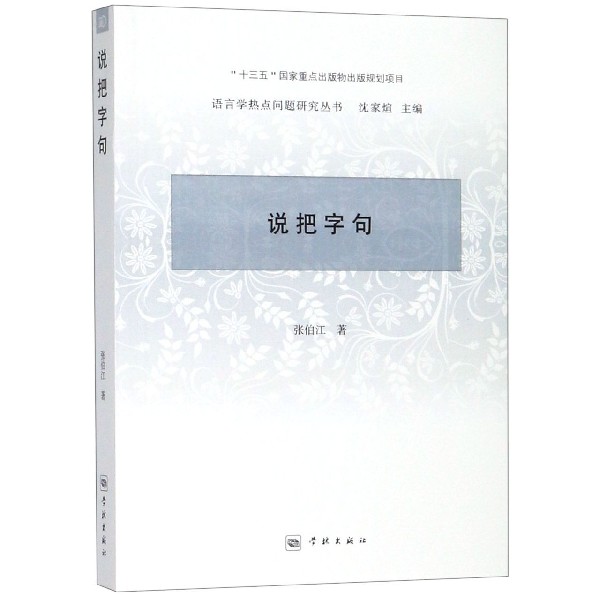
张伯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多年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代表作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与本书相关论文有《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汉语句式的跨语言观——“把”字句与逆被动态关系商榷》等。
把字句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有多长,把字句的研究史就有多长。这样一本小书的概述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相关研究,但研究把字句所关注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些方面:它的构成,它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它的句式语义,它的语用特点。我们围绕这几个问题的讨论,也可以说已经把这一句式的主要矛盾揭示出来了。所有这些问题,给人以最强烈的启示,是什么呢? 可以看出,研究史上一条清晰的脉络是,不断试图比附印欧语研究中的观念,不断因这种努力而苦恼。最初,是比附句法宾语的移位说,断言把字句的实质是宾语的提前,但事实说明“把”字后面的宾语很多无法放回到后面谓语的宾语位置上去。这个矛盾从吕叔湘(1948)开始就已充分展现了。其次是比附句法概念“有定(definite)”和“无定(indefinite)”,后来逐渐发现不完全对得上号:不仅是因为汉语没有类似于英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那样的标记,而且汉语相同的词汇形式(无论是光杆名词还是前加数量词的名词)竟可以表示完全相反的指称范畴。这里的麻烦,在王还(1985)里显露无遗。格语法和语义角色配价理论影响汉语后,人们试图用语义角色和动名语义关系来描写把字句的配价特征,以期揭示其中的语义结构,到了叶向阳(2004)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一个个的标明把字句主语和宾语的语义身份,对把握把字句的句式语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叶向阳用致使意义统摄把字句的语义关系,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汉语的基本语法关系是“话题-说明”;陶红印、张伯江(2000)用基于语用意义的可辨性(identifiability)理清有定和无定的纠葛,原因也在于,汉语名词的指称属性,根本还是语用属性。 §4.3.2介绍了生成语法关于“‘把’并不给其后的NP或者把字句的主语指派论旨角色,它唯一的作用是给其后的NP赋格”的说法,李艳惠(1990)认为汉语从本质上说是核心词居尾(head-final)的语言,句子基本成分的顺序应该是“主-宾-动”(SOV),也就是说,宾语在初始的D-结构里处于动词之前。这跟一般人对汉语基本语序的看法大相径庭,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汉语把动词的支配对象放在动词前边的情况是相当多的,比如做次话题的需要,作处置对象的需要等等。而放在动词后面的情况也不少,往往是作为目标成分,用以表明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总的来看,都是语用动因的驱动,不同的语用动因造成不同的语序。由此可见,包括把字句在内的汉语语序问题,仅从句法着眼,是难免捉襟见肘的。 再看第5章讨论的用汉语把字句比附句法过程的做法。种种比附,都是基于一个思路:外国语言里普遍存在的句法范畴,代表着“语言共性”,于是汉语的某种语法现象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总要去靠上一种。事实上,人类语言之所以有共性,在于共同的交际需求,语言的使用才是根本的共性。(Thompson,2003)其他语言里那些充分语法化了的句法过程,是语用规律的固化;汉语里像把字句这样的句式,也基本定型为自己的形式,也是语用表达的固化。各自的语用动因和语用目的未必相同。前面我们讨论过,汉语把字句弱化主语、突出宾语的倾向,跟逆被动式并不相同,把字句比附为逆被动式并不合适。再说“被动主动句”,即比附为“have+V被动”句的看法,一旦遇到我们§6.2讨论的“追究责任”类的句子(如“大虾把我的肚子吃坏了”),也要面对“have+V被动”句无法读出“追究责任”语义的困难。可见,比附的思路总是看汉语的把字句像哪种外语句式,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只是,外语里的有些句式,有点像汉语的一部分把字句。 近三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语言共性”意识越来越强,很多过去看来很有个性的汉语事实,得到了共性的解释,认识于是得以深化。如果用简单类比的办法看汉语把字句跟语言“共性”之间的关系,越看越不像,越看越显得把字句特殊。近几年有的学者在比附的路数上进一步努力,终于为把字句攀上了亲:“从跨语言的视角,发现把字句平行于作格语言的逆动句,是语态现象。这样,不但统一解释了把字句的句法规律,同时覆盖了尽可能多的语料。更有意义的是,把字句因此也纳入了语言共性行列。这一研究模式,既是对把字句语法性质的全新认识,也是对把字句语言地位的重新定位”(叶狂、潘海华,2012);“从被动主动句这一跨语言的现象入手反观汉语中的特殊结构把字句。……不仅找到了语言普遍的一种用复合谓词表达的致使结构,还将把字句纳入被动主动句的类型分布中,使其不再成为汉语中的一种孤立的句式。”(朱佳蕾、花东帆,2018)问题是,汉语把字句究竟是不是“孤立的”、“特殊的”东西?符不符合语言共性?这取决于对“语言共性”的看法。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绝大多数从事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研究的学者都认同一个观念:语言的交际功能,即语言的现实运用,是决定人类语言各种相同选择和差异选择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语言共性是语用性质的。实体信息的已知和未知,陈述里的预设和焦点,说话视角的主观和客观……都是人们组织句子时关注的重要语用因素。如本书第4章我们介绍过,有的语言重视“话题-说明”这种语用关系,就选择了受格句法系统;有的语言重视“新信息”的引入,就选择了作格句法系统。各种语言有各自重视的语用区别,形成了各自着重的句法区分。汉语注重“话题-说明”表达与一般陈述表达的区分,同时也非常注重主观性表达与客观性表达的区分,这两条语用区分,决定了汉语里绝大多数句子形式的选择,也铸造了把字句这样的句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把字句不仅不该说成孤立与特殊,反而是对语言共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 汉语语言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突出的热点问题。有些问题经过多轮讨论,依然热度不减。而近些年,汉语语法学界在进一步认识到汉语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重要的新问题。面对海量的论争资料和纷繁的观点,很多学者,特别是初学者,有无所适从甚至盲从的倾向。《说“王冕死了父亲”句》为本丛书之一种。 有鉴于此, 本着摆脱印欧语眼光,摆脱传统(主流)观点束缚,带有导向性,在综述中铺垫出解决问题的新方向的宗旨,沈家煊先生主编了“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系列”丛书,筛选出十几个理论相关的语言学的热点专题,就每个专题,以8万-10万字的篇幅,全面整理海内外相关资料,对文献做出深入透彻的分类梳理,力求客观呈现各家的主要观点,对其优缺点作适当分析点评,指出学术发展的前景。该丛书以吕叔湘《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和朱德熙《语法答问》为楷模,追求站在汉语的立场上看汉语,用汉语的方式说汉语的“自我表述”。有助于推动汉语句法语义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大专院校中语法专题讨论课的教学开展。